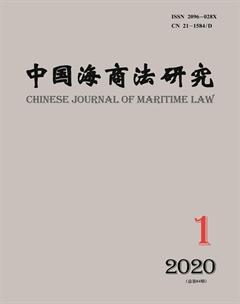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中的核心问题
李歆蔚 初北平
摘要:针对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中的核心问题,提出公约应适用于根据出售国法律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赋予司法出售证书决定性证据的效力;在公约中以“具有国际效力”取代“国际承认”的表述,并明确规定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条件;对司法出售通知的内容设定最低标准;原司法出售法院对认定司法出售证书是否有效、司法出售是否无效或应予中止具有专属管辖权。同时,深化研究违反重要通知事项的法律后果;优化并协调司法出售国际效力条件;评估船舶不予扣押的“公共政策”例外的后果;设计更为便捷的机制使买受人摆脱注销登记和再登记困境。
关键词:船舶司法出售;《北京草案》;清洁物权;国际效力
中图分类号:D996.1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0)01-0094-09
The key issues on the draft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judicial sale of ships
LI Xin-wei,CHU Bei-ping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Focused on some key issues on the draft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judicial sale of ship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vention shall only apply to judicial sales of ships which, under the law of the state where they are conducted, confer clean title to the ship on the purchaser; to give the certificate of judicial sale the effect of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the convention shall be cast in terms of “having international effects”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expressly set forth conditions for giving international effect to the judicial sale; to establish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content of the notice of judicial sale; and to confer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n the original court of judicial sal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avoid a certificate of judicial sale or to avoid or suspend the effects of a judicial sale.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legal consequences of a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important notice requirements; optimizing and harmonizing the conditions for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judicial sale; ass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ublic policy” exception for the obligation not to arrest; and designing a more convenient mechanism to get purchasers out of the registration and deregistration dilemmas.
Key words:judicial sale of ships;Beijing Draft;clean title;international effects
從产生于世界不同法域的案例来看,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问题由来已久,目前,各国基于“礼让原则”对外国船舶司法出售予以承认,存在诸多法律不确定性。现行国际公约涉及到船舶司法出售的问题,都没有对有关船舶司法出售及其国际承认进行整体的调整,因此,需要制定一部新的国际公约专门对此空白地带予以规制。《关于外国司法出售船舶及其承认的国际公约草案》(简称《北京草案》)是国际海事委员会历经数载的成果,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六工作组于2019年正式承担起《北京草案》的讨论会议相关事宜。制定单独、完整的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有利于提升船舶司法出售的信用,增强买受人的购买信心,提高船舶的出售价格,保证船舶融资的安全性,从而使利益相关各方①受益。笔者将针对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一、文书的形式、目的及定位
(一)文书的形式
2019年5月13日至17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UNCITRAL)第六工作组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第35届会议,会议首先取得的进展是,一致同意以《北京草案》为案文展开讨论。与会代表对《北京草案》进行了逐条的详细探讨,并最终审议通过了会议报告。[1]以《北京草案》为基础,秘书处采纳了工作组第35届会议的讨论与决定,编写了《船舶司法出售文书草案:附加说明的
〈北京草案〉第一次修订本》[简称《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2]并于同年11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工作组第36届维也纳会议上对其进行了讨论,最终审议通过了会议报告。[3]基于第36届维也纳会议的讨论与决定,秘书处又编写了《船舶司法出售文书草案:附加说明的〈北京草案〉第二次修订本》[简称《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4]拟将其作为第37届纽约会议讨论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北京草案》采取了公约的形式,但在第35届纽约会议上尚未确定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文书将成为公约还是示范法。在第36届维也纳会议上,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与会代表在讨论中为寻找妥协方案所做的努力,在大会最后关于文书形式的表态发言中,压倒性的意见是希望所谈判的法律文书将来能够成为公约②。示范法相较于公约明显缺乏约束力,各国可以随意选择是否予以采用,唯有通过一部能够对各缔约国产生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才能提高该领域的法律确定性,达到保护买受人利益和促进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的目的。
(二)文书的目的与定位
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根本目的,之前体现在《北京草案》及其第一修订本的序言中,即“向船舶司法出售中的买受人提供必要和充分的保护”,而《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特别增加一条“目的”条文,突出公约的目的是为司法出售在其他缔约国发生效力而设定条件,包括为了船舶的注销登记与再登记。但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内容却不这样简单明确。目前草案文本既涵盖了诸如船舶优先权、抵押权、船舶司法出售效力等实体性问题,又包含了诸如司法出售的通知、船舶的注销登记和再登记、国际效力、认定无效以及中止等制度问题。另外,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通过牵涉到多方、多层利益的平衡,例如:船舶司法出售不同利害关系人之间、不同机关之间、不同国家(地区或经济体)之间、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等;不同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内河航运发展的模式存在差异,其对内河船舶的适用观点不尽相同;此外,在各国代表的讨论当中,不同法系之间的法学原理的冲突所带来的协调困境也非常明显。举例来说,英美法系下,船舶司法出售可能发生在对物诉讼(action in rem)和对人诉讼中(action in personam),在对物诉讼中索赔人对船舶有船舶优先权,在对人诉讼中索赔人对船舶所有人有海事请求权;相较而言,在大陆法系下并无“对物诉讼”这一概念,这就导致了就某些条款需要对两大法系进行协调,比如有关个人索赔的内容。类似的,在公约试图对“担保权”(charge)、“司法出售”(judicial sale)、“船舶优先权”(maritime lien)、“人”(person)、“买受人”(purchaser)和“船舶”(ship)下定义时,不同法系之间的冲突均彰显出来。上述任何一个问题足以在各国之间造成众多冲突,而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试图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可以说,尽管它的条文不多,但将是一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国际公约。使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更具复杂性的是,当前国际上已经存在一系列的公約涉及到相关问题,船舶司法出售公约必须妥善解决与相关公约的衔接,也就是该公约草案的定位问题。
首先,涉及与《1967年关于统一船舶优先权与抵押权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和《1993年船舶优先权与抵押权国际公约》关系的处理。上述两个公约包含有关“强制出售”(forced sale)的通知和效力的规定,当船舶司法出售公约涉及诸如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的定义、司法出售的通知和效力之类的问题时,必须妥善处理与这两个公约的衔接,既要
借鉴适用
上述两公约中既定的概念以避免分歧与冲突,也要充分认识到它们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与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目标的差异性。
其次,为了明确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定位,还应区分并协调船舶司法出售公约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缔结的三个公约之间的关系。
1.《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简称《选择法院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起草的一部基于各方协议的管辖权公约。[5]《选择法院公约》项下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签订“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exclusiv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为解决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有关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指定一个或多个法院享有对该纠纷的专属管辖权(第3条)。《北京草案》及其修订本的内容并未涉及裁判导致司法出售纠纷的法院管辖权,而仅规定了司法出售发生后司法出售国法院对司法出售质疑诉讼(challenge to judicial sale)的专属管辖权。鉴于《选择法院公约》调整的对象是纠纷(disputes)①,[6]司法出售质疑诉讼显然不属于《选择法院公约》调整的范围。因此,目前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文本与《选择法院公约》并无冲突。
2.《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
《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简称《判决公约》)第3条第1款(b)项明确将公约项下的“判决”(judgment)定义为“any decision on the merits given by a court”。[7]尽管在某些国家船舶司法出售的决定可能包含在法院实体性判决之中,[8]但船舶司法出售本身是一种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相关国家的法院判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不约而同地将船舶司法出售定性为基于所适用的法律而生效的外国事实②。鉴于《判决公约》第2条第1款(o)项在规定适用范围的例外时,明确将执行措施(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排除③
,[9]同时,其第3条第1款(b)项又将临时保全措施(interim measure of protection)排除,船舶司法出售并不受《判决公约》的调整。[HT5K]
3.《1965年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1965年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简称《送达公约》)旨在调整民商事司法和司法外文书的国际送达。[10]《北京草案》及其修订本有关“司法出售通知”(notice of judicial sale)的条款是公约重要的条款之一,条文内容同时涉及司法出售通知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则。尽管在草案文本中使用的措辞是“发送”(given)而不是“送达”(service),但《送达公约》并没有对“送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事实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曾指出,“送达”一般是指向收件人递送(delivery)司法和(或)司法外文书④。由此可见,《送达公约》可以适用于船舶司法出售公约项下的通知,因此,必须谨慎考虑船舶司法出售公约项下的通知方式与《送达公约》规定的送达方式之间的协调。
二、“完全的”还是“限定的”清洁物权
《北京草案》第4条规定司法出售的效力时明确指出:“司法出售前在船舶上存在的任何所有权及全部权利和利益都将予以消灭,……买受人应获得对船舶的清洁物权”;而《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第6条规定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时也明确指出:“本公约所适用的在一缔约国进行的司法出售,在其他缔约国均具有将对船舶的清洁物权授予买受人的效力。”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首要目的是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其核心在于清洁物权(clean title),但由此产生了一个争议,即如何在最大限度保护买受人利益的同时又不侵害其他船舶司法出售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日本等国家就此指出:在其法域中,司法出售不一定具有消灭出售财产上所有权利和利益的效力,例如,船舶租赁权⑤。
(一)“买卖不破租赁”的排除适用
该争议背后隐藏的理论问题是关于租赁法律关系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目前被大多数国家法律承认的原则,但在船舶司法出售上是否仍可以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或是应有其他的考量?
首先,从国际立法层面,《1967年统一船舶优先权与抵押权某些规定的公约》第11条第1款在规定清洁物权获得的条件时,特别在条文最后指出,“任何租船合同和使用船舶的合同,都不得被视为本条所述的优先权或财产担保”。据此规定,船舶司法出售后船舶租赁权似乎应继续存在。然而,《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在规定清洁物权获得的条件时却将前述内容删除,租赁权不再成为清洁物权的例外。另外,从比较法的层面来看,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可以适用于已登记的船舶,比如《德国民法典》
第578a条和《意大利民法典》第1599条与之相反,有的国家则将“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适用限制在不动产领域,比如西班牙第4/2013号法律
第14条;[11]又如芬兰,其最高法院在诸多案件中认定动产的租赁合同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对出租人的债权人没有约束力。[12]
其次,从公共政策层面,国内学者认为,基于比较法的视角,“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立法目的主要出于保护承租人利益的公共政策考虑。[13]而保护承租人利益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弱势地位,因为不动产尤其是住房关乎承租人阶层的生存利益。相比之下,动产不关乎承租人的生存利益,其多具可替代性,故动产承租人无法判断是否为经济上的弱者。[14]此外,对于船舶这种特殊动产而言,通常情况下,船舶上存在船舶优先权,船舶优先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公共政策性质的私法权利,如果船舶司法出售能够消灭船舶优先权却不能消灭由租赁合同所产生的普通债权,一是存在逻辑困境,二是由于租赁合同的续存影响了船舶成功出售或出售价格,进而很大程度上有害于保护船舶优先权人的利益,明显与公共政策不符。
再次,从法律关系层面,区别于船舶私人出售(private sale)中存在买方、卖方和承租人三方的法律关系,在船舶司法出售中出现了第四方债权人。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向法院申请扣船并导致船舶被司法出售,此时,问题的焦点不再是第三方承租人与买方、卖方之间的关系,而是变成了第三方承租人与第四方债权人的权益哪个应该得到优先保护的问题。就此,有的国家比如奥地利,其法律明确规定已登记的租赁权被视为物权,[15]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原则,承租人的權益应该受到优先保护。然而,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登记的租赁权虽然具有了物权的某些特征,其本质上仍不等同于物权,因此承租人的权益相比于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护的优先性似乎缺乏理论依据。
最后,从实践层面,基于法院船舶司法出售的相关经验,不消灭租赁权会对船舶的成功出售造成困难,即使船舶能够被出售也会较大影响卖船价格和时间,这种结果对所有债权人都是不利的。另外,基于登记机关船舶司法出售后注销登记与再登记的相关经验,若船舶司法出售后允许租赁权继续存在,将在船舶登记层面造成一系列新的障碍,例如,原有光租登记是否需要注销后办理新的光租登记?原光船承租合同是否需要变更出租人?若不注销原光租登记,新的船舶登记如何完成?等等。
综上所述,“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在船舶司法出售领域的适用需要平衡买受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除租赁权之外,根据希腊、德国、西班牙等国各自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船舶司法出售后某些权利也会继续存在,买受人并不能获得清洁物权①。[16]322-325船舶司法出售公约如果从买受人的利益出发,应该统一性地规定船舶司法出售的法律效力,即授予买受人对船舶的清洁物权,司法出售前在船舶上存在的所有权及全部权利和利益均已消灭。
(二)非清洁物权排除适用公约
会议讨论中,仍有代表从关切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出发建议公约提出解决方案,有观点认为:可以在统一性地规定关于船舶司法出售的法律效力的同时,通过在司法出售证书中注明船舶租赁权等继续存在的方式,适用于根据司法出售国法律未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qualified” judicial sales)②。这实际上涉及到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实质适用范围(substantive scope),《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对此给出了两种方案:一是规定公约仅适用于根据司法出售国法律买受人(已经)获得清洁物权的司法出售(“方案A”);二是规定所有的司法出售均产生清洁物权,同时考虑如何在公约中纳入那些根据司法出售国法律未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司法出售(“方案B”)③。
笔者认为,就“清洁物权”的问题很难在所有法域内达成统一观点,公约只能争取在可能的限度内达成共识,这也符合公约的精神①。目前各国法律中大多没有对船舶司法出售(judicial sale of ships)及其效力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几乎都规定了某种特定的程序能够导致船舶司法出售后买受人获得对船舶的清洁物权。[16]247-382有鉴于此,公约可以参考《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架构,不对司法出售国的司法出售及其在司法出售国的效力作出规定,仅限于规定公约适用于依照司法出售国法律可以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以避开不同法域中船舶司法出售获得清洁物权的例外情况,促进公约的顺利通过。如果公约也调整那些根据司法出售国法律未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司法出售会导致一系列的困境,比如登记层面:在这种情况下,登记官应酌情决定是否注销该船舶登记或者应取得保留的抵押权和担保权持有人的同意,而这会对公约通过司法出售证书便利船舶注销登记的基本目标造成不利影响②。有关该议题目前各国代表达成了较为广泛一致的意见,因此《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第3条第1款(b)项明确规定公约将适用于根据司法出售国的法律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
三、证书具有“国际效力”还是得到“国际承认”
《北京草案》关于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的条文中涵盖了两个层次的承认:一是登记机关的承认(第6条);二是司法机关的承认(第7条)。承认的内容包括:(一)买受人已获得清洁物权;(二)出售后船舶不附带任何抵押权或担保权,由买受人承担的抵押权和担保权除外。其结果是,如果因在司法出售之前产生的求偿权而向缔约国法院提出扣押船舶申请或船舶被缔约国法院下令扣押,在买受人或后续买受人出示船舶司法出售证书后,法院应驳回、撤销或拒不接受扣押申请或解除对船舶的扣押③。《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依然保留了《北京草案》的理念,但不再使用“承認”的措辞,而是在第6条规定了司法出售具有“国际效力”。尽管前面已论述船舶司法出售并不受《判决公约》的调整,但《北京草案》第7条所规定的司法机关的承认是否需要在公约讨论中完善仍然值得研究。
(一)司法承认的必要性
从法院的层面考虑,在没有国际公约规制的情况下,各国法院对船舶司法出售的承认与执行基于“礼让原则”。因此,任何主权国家不能强迫另一国家接受其船舶司法出售,实际上将承认外国船舶司法出售法律后果的权力保留给每个国家。[17]147基于“礼让原则”进行的承认与执行完全取决于一国国内法,有的国家对于该问题有完整的国内法规定,但大多数国家没有相关立法,而是完全凭借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导致了有关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方面的法律的不确定性。
从不同国家法院的判词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倾向于对外国的船舶司法出售效力给予承认。举例来说,英国Hewson大法官即在The Acrux案中指出承认外国船舶司法出售效力的重要性:如果本法院授予的清洁物权受到质疑或干扰,善意的买受人将遭受严重损害。不仅如此,世界的整体海事利益也将受到损害④。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些对外国船舶司法出售承认持较开放态度的法院,也不可能对外国船舶司法出售无条件地承认,实际上不同国家法院对该问题都有一些保留。比如前文提到的Hewson大法官同时在The Acrux案中指出,法院认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competent court)作出的正当的船舶司法出售(proper sale),即管辖权和正当程序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另外,仍有国家的法院对外国船舶司法出售的承认持相对保守态度。以土耳其为例,根据其最高法院对1956年颁布的《土耳其商法典》第1245条的解释,船舶仅在国内强制出售的情况下才能终止产权负担。经过2004年和2012年两次修订后,新《土耳其商法典》第1350条明确规定,在满足某些最低标准的条件下,土耳其船舶的外国司法出售将具有消灭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的效力。然而,这些“最低标准”包括,在土耳其各地发行量超过50 000份的报纸上发布出售公告或者强制性通知土耳其船舶登记处、在登记处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以及其他权利和应收款持有人。如果未能满足这些强制要求,土耳其法院和行政机关将不承认该外国船舶司法出售,因而拒绝从其登记处注销船舶登记或根据新船东重新登记船舶。[17]149-150土耳其法律的严格规定导致了不止一次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认争端的发生①。由此可见,从法院的层面出发,船舶司法出售公约中作有关“国际承认”的统一性规定有其必要性。
(二)证书的域外效力
在第35届和第36届会议讨论中,与会代表们似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域外效力完全不同于司法判决或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在域外被承认的效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善意买方的介入,这使得即使在法院的强制干预下船舶出售存在瑕疵,但在买方按照法院程序要求支付购船价款的情况下,其应当被归类于善意买方而得到保护。假设某国法院作出一个扣押船舶的命令或者是一个强制执行船舶的裁定,原告或申请人试图向外国法院寻求其承认与执行,此种情形才构成判决或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域外承认与执行。
在回答应赋予船舶司法出售证书何种法律效力之前,须回答另外一个疑问:基于买受人的视角,船舶司法出售与私人出售哪一个更值得信赖?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在英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18]司法出售相比于私人出售通常更受欢迎,因为通过法院进行估价和公开拍卖是一种更可靠的方法,可以为所有利害关系人获取尽可能高的船舶价格。海事法院的作用是确保船舶的出售最大程度地保护所有海事索赔人,而最佳办法通常是坚持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估价方法和公开招标方法②。同时,法院完全控制出售程序,从而保障出售程序的正当性和完整性,并最终逐步培养司法出售的可信度和地位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私人出售的物权凭证——卖契尚可得到域外登记机关的承认,法院基于司法出售签发的物权凭证——船舶司法出售证书更无不被承认的理由。卖契通过公证、认证程序来保证其卖方意图以及交易内容的形式上的真实性,其并不能保证卖方对于船舶权属的绝对真实性,而《北京草案》修订本中设计了司法出售证书的储存公示机制④,法院签发的司法出售证书的真实性也有望得到妥善解决。从国际商务角度来看,即使国际上没有关于司法出售证书的国际公约存在,其域外效力也应得到国际普遍承认。
但一个国际公约的重要价值在于,如何让原船舶登记机关愿意在没有原船舶所有人提出注销登记申请的情况下将船舶登记进行注销。从国际船舶登记机关的调研结果看,几乎所有的船舶登记机关并不抗拒接受船舶司法出售证书,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船舶登记机关具有扩大本登记机关船舶登记规模的动力;二是船舶登记机关并不愿意介入是否符合登记条件的争端。相反,船舶登记机关并没有去注销本登记机关船舶登记的主动性,而且不依据原登记所有人的申请去注销船舶登记的情形与常规的商务行为相背离。目前,鲜有国家在其船舶登记法律中明确规定应依据他国法院的司法出售证书注销船舶登记,故船舶登记机关需要国际公约规定证书的域外效力,以赋予其注销登记的法律依据。换言之,公约如果要对登记机关的行为作出规范的话,其本质上就是针对注销担保物权登记和原船舶登记两种情形,当某国登记机关不履行公约义务,船舶买受人请求原登记所在地法院签发命令注销船舶登记时,该国法院应当支持此种诉求。因此,《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将《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第7条的标题由“船舶的注销”修改为“登记官的行为”,使公约条文的目标进一步彰显,值得支持。同时,无论司法出售后的船舶是否已经被原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在司法出售证书被出示后,基于司法出售前发生的赔偿请求而向缔约国法院提出扣押船舶申请或船舶被缔约国法院下令扣押,法院应驳回、撤销或拒不接受扣押申请或解除对船舶的扣押。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第8条第4款增加了“法院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例外,这在司法出售后船舶的不得扣押方面增加了不确定性,理由在于适用公共政策的弹性较大,容易刺激司法出售前的债权人产生申请扣押船舶的动机,而支付了购船款的无辜买方通常迫于船舶被扣押之后的经济压力而选择妥协,客观上不利于平衡买受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当然,如果申请人在司法出售法院取得认定该司法出售证书无效、或者该司法出售无效或中止其效力的生效判决书,则应该准许扣押船舶。上述法律关系中,四类法院可能介入船舶司法出售相关的法律行为:原船舶司法出售的法院,扣押或扣留司法出售后船舶并提起诉讼的法院,原登记地或者拟注销登记地的法院以及新登记地的法院。这使得不同法域间的冲突增加,为减少此种冲突,未来公约的替代解决方案是:强调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决定性证据效力,出具该证书即可在域外登记机关获得船舶的永久登记,而不必等待原船舶登记的注销证明①。但该方案的弊端在于,如果原船舶登记机关不主动注销登记,则一艘船舶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登记,这会给船舶运输管控造成困扰。
(三)从“国际承认”向“具有国际效力”转变
《北京草案》第7条的标题使用了“对司法出售的承认”(Recognition of Judicial Sale)的措辞,尽管中文本将其译为“司法出售的确认”,但仍然引起一定的误解:公约似乎旨在解决某国司法裁判文书在域外的承认问题。《1993年船舶优先权与抵押权国际公约》中并没有类似《北京草案》第7条的规定,并且《北京草案》第4条已经涉及了司法出售的效力,由此极易引发是否需要单独规定司法机关承认的争议②。如果能够达成广义的“判决公约”,可以解决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问题,但就此达成国际共识显然具有挑战性——虽然在地区范围内存在成功的多边条约③,但是,这些地区性公约大多是在一个地区性组织主持之下缔结的,这些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法律制度较为相近。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曾特别强调,此类公约必须以缔约国对彼此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关的信任为基础④。此外,《北京草案》的最初构想其实是,在一国进行的船舶司法出售作为决定性证据(conclusive evidence)可以直接被另一国的船舶登记机关承认,或者是就登记与否产生争议时被外国法院所支持。也就是说,凭船舶司法出售证书买受人可以在相关登记机关办理船舶的注销登记和再登记,这并不以重新登记机关或者原登记机关所在地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为前提条件。
因此,船舶司法出售公约首先应该规避的敏感领域是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其次也应该谨慎考虑其他法律文件的承认,以确保公约的谈判过程中因为涉及司法协助的话题而对参会代表的发言带来限制,尤其是对于统一行动地区性组织成员国代表而言,其习惯于确保发表的观点不超越自己的权限。为促进公约顺利通过,更智慧地处理公约中有关国际承认的内容,自《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开始,秘书处采用的处理方法是选择在文本中避免使用“承认”(recognition)的措辞,代之以“效力延伸”(effect extention)和具有“国际效力”(international effects)的策略⑤。此种处理方式对于解决法院送达困难可以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一般而言,“送达”涉及到正当法律程序的根本问题,若未能送达导致被告未能准备正当的答辩,那么判决很有可能失去其效力,有关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基本都会将其列入拒绝承认的理由⑥。规避了“承认”的措辞之后,法院的司法出售程序中的相关“送达”用“通知”来替代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在法律后果上有利于解决通知瑕疵所带来的救济难题。《北京草案》两个修订本的方案皆值得支持。
四、司法出售的瑕疵与救济
《北京草案》及其修订本为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设定了条件:一是管辖权条件;二是符合出售国国内法的规定以及通知应满足的条件⑦。这实际上与前述Hewson大法官在The Acrux案中提出的管辖权和符合法院程序条件基本一致。上述草案还通过专门的条文规定了司法出售不具备(国际)效力的情形:(1)船舶在被司法出售时不处在出售国的实际管辖之下⑧;(2)司法出售明显与公共政策相抵触;(3)买受人通过欺诈获得司法出售①。这几个条文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是否應该予以整合也取决于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这在大会讨论中虽有触及但并不详细,有待后续案文修改时完善。此外,将具有(国际)效力的情形和不具有(国际)效力的情形放在连续的两个条文中是否更具合理性,虽然有不少公约采取连续条文的形式,但目前尚不是讨论的重点。
(一)通知瑕疵的救济
在船舶司法出售实践中,通知到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并非易事,且因通知难而导致的延误对船舶价值及船员均有不利影响。在公约采用“效力延伸”策略或“具有国际效力”策略的情况下,即使通知没有送达个别利害关系人②,其并不影响该司法出售的效力,这样至少能够保证善意的买受人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从草案目前的规定来看,有五类人员应被通知:(1)办理该船舶登记和光租登记的船舶登记处的登记官;(2)可公开查询到的抵押权人;(3)提出索偿的船舶优先权人;(4)船舶所有人;(5)在船舶登记处登记的光船承租人③。在这五类人员之中,第一类涉及船舶能否順利登记,其他四类则涉及利害关系人自身利益。对于第四类和第五类人员而言,他们通常是诉讼的被告或者是有关船舶物权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其未能获得通知,应构成严重违反程序规定的情形,该司法出售的效力应当受到质疑;而第二类和第三类人员如因未能获得通知导致此次司法出售未获得有效清偿,其可以向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人提出索赔,但不应影响该次司法出售的效力。因此,笔者建议在公约中应进一步明确对于第四类和第五类人员通知要求的违反将导致司法出售无效,从而平衡好原船舶所有人及其他债权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利益,且不应简化通知要求和将有关问题留给国内法规定,更不应将通知相关条款全部删除。公约可以对司法出售通知的内容或者信息设定最低标准,《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中新增加了“与船舶司法出售国国内法一致”以及将附件中信息作为最低要求的规定,借此避免了有关法院程序的冗赘规定,值得支持。
(二)成功质疑的后果
船舶司法出售证书具有决定性证据的效力在会议中基本达成共识。缔约国的船舶登记机关从履行公约义务的角度出发,接受基于出具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登记申请并予以登记,只有在质疑船舶司法出售获得成功的情形下,登记机关才有可能拒绝接受登记申请,这一精神已经被《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明确规定。
公约草案的基本设计思路是:以便利船舶买受人为核心,以承认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效力为常态,以支持符合条件的质疑为例外。当质疑的程序被提起并获得成功时,其根本的目标是撤销原来的司法出售,这在任何一个法域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以中国为例,如果法院作出撤销裁定,则拍卖自始无效,在因执行机关的原因给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甚至可以触发国家赔偿。[19]因此,公约如果能够生效,其最大的功绩之一将是统一了质疑之诉的管辖法院为原司法出售法院,同时将“不予登记”或“不予注销”的行政行为是否得当与船舶司法出售程序是否错误相区分。但公约没有必要设定质疑船舶司法出售的条件,而应将其留给司法出售国国内法规定。这与《纽约公约》不干涉仲裁地国家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但是设定了不予承认和执行裁决的基本情形类似。因此,如果公约保留质疑的规定,其内容将仅限于质疑的专属管辖权以及质疑后的法律后果。
五、结语
在未来的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过程中,一方面,笔者支持公约现有要点:(1)关于“完全的”还是“限定的”清洁物权,公约应该适用于根据司法出售国法律授予买受人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2)公约应赋予司法出售证书决定性证据的效力;(3)在公约中以“具有国际效力”取代“国际承认”的表述有利于在不同法域内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条件应有明确的条文规定;(4)对司法出售的通知内容设定最低标准,使其与船舶司法出售国国内法规定以及公约附件中的示范信息保持一致;(5)原司法出售法院对于认定司法出售证书是否有效、司法出售是否无效或应予中止具有专属管辖权。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的案文包括:(1)应明确通知船舶所有人和光租人是重要的通知事项,因为二者通常是诉讼中的被告,违反该通知事项可认定该司法出售无效,且不应简化或者删除通知要求并将其留给国内法规定;(2)有关司法出售具有国际效力和被认定无效的条件应优化并协调,明确管辖权和正当程序是司法出售具有国际效力的两个要件,并考虑增加一项司法出售不具国际效力的情形,即
在司法出售程序中通常作为被告的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未获及时通知从而未能准备正当的答辩;(3)船舶不予扣押的“公共政策”例外应慎重采纳;(4)应设计更为有效和便捷的机制使买受人摆脱注销登记和再登记困境。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Report of Working Group VI (Judicial Sale of Ships)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fifth session[EB/OL].(2019-05-24)[2020-02-27].https://undocs.org/en/A/CN.9/973.
[2]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Draft instrument on the judicial sale of ships:annotated first revision of the Beijing Draft[EB/OL].(2019-09-10)[2020-02-27].https://undocs.org/en/A/CN.9/WG.VI/WP.84.
[3]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Report of Working Group VI (Judicial Sale of Ships)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ixth session[EB/OL].(2019-12-02)[2020-02-27].https://undocs.org/en/A/CN.9/1007.
[4]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Draft instrument on the judicial sale of ships:annotated second revision of the Beijing Draft[EB/OL].(2020-02-11)[2020-02-27].http://undocs.org/en/A/CN.9/WG.VI/WP.87.
[5]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EB/OL].(2005-06-30)[2020-02-27].https://assets.hcch.net/docs/510bc238-7318-47ed-9ed5-e0972510d98b.pdf.
[6]HARTLEY T,DOGAUCHI M.Convention of [STBX]30 June 2005[STBZ]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EB/OL].[2020-02-24].https://assets.hcch.net/upload/expl37final.pdf.
[7]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EB/OL].(2019-07-02)[2020-02-27].https://assets.hcch.net/docs/806e290e-bbd8-413d-b15e-8e3e1 bf1496d.pdf.
[8]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Norddeutsche Landesbank Girozentrale v. The Ship “Beluga Notification” (No.[STBX]2[STBZ])[EB/OL].(2011-06-10)[2019-12-28].https://www.comcourts.gov.au/file/Federal/P/NSD432/2011/actions.
[9]GARCIMARTI F,SAUMIER G.Judgments convention:revised draft explanatory report[EB/OL].[2020-02-27].https://assets.hcch.net/docs/7d2ae3f7-e8c6-4ef3-807c-15f112aa483d.pdf.
[10]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STBX]Convention of 15 November 1965 [STBZ]on the Service Abroad of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EB/OL].(1965-11-15)[2020-02-27].https://assets.hcch.net/docs/f4520725-8cbd-4c71-b402-5aae1994d14c.pdf.
[11]GONZALEZ PACANOWSKA I V,DIEZ SOTO C M.National report on the transfer of movables in Spain[M]//FABER W,LURGER B.National Reports on the Transfer of Movables in Europe Volume 5.Munich: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11:406.
[12]KUUSINEN M.National report on the transfer of movables in Finland[M]//FABER W,LURGER B.National Reports on the Transfer of Movables in Europe Volume 5.Munich: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11:336.
[13]王利明.論“买卖不破租赁”[J].中州学刊,2013(9):49.
[14]张双根.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M]//王洪亮,张双根,田士永.中德私法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16.
[15]戴永盛.奥地利普通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210.
[16]BERLINGIERI F.Synopsis of the replies from the Maritime Law Associations[C]//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CMI Yearbook 2010.Antwerp:CMI,2011.
[17]BLEYEN L.Judicial sales of ships:a comparative study[M].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
[18]CHENG J K.Judicial sale of arrested vessels[J].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2019,31(1):72.
[19]毋爱斌.司法拍卖无效认定程序体系论——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5号谈起[J].法学,2017(1):127.
收稿日期:2020-02-28
作者简介:李歆蔚(1989-),女,山东济南人,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海事政策法规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成员,E-mail:lxw@dlmu.edu.cn;初北平(1972-),男,山东莱阳人,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海事大学海法研究院院长,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成员,E-mail:chubeiping@dlmu.edu.cn。
① 包括出售前船舶所有权人,船舶抵押权、质押权、其他担保物权或船舶优先权等权利人,船舶的买受人和后续买受人,银行,等等。
② 工作组商定在今后的届会上作出最后决定,不排除最后法律文书成为示范法的可能性,参见A/CN.9/1007,第99段。但为了行文一致,笔者统一采用“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的表述。
① 《选择法院公约》的解释性报告明确指出:该公约不适用于各缔约国的程序法,包括上诉和其他类似救济。参见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Explanatory Report,第88段和第92段“Procedural law”。
② 比如,北欧商业银行—欧洲银行(Bcen-Euro Bank)诉佛他贸易有限公司(Ferta Trade Ltd. S.A.)船舶抵押权纠纷
案[(2005)津海法商初字第401号]中,天津海事法院明确指出,船舶被外国法院出售是一件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只有发生和未发生的区别,而不管他人是否承认,它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天津海事法院确认船舶被外国法院出售属于对法律事实的认定,而不是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
③ 参见Francisco Garcimartín & Geneviève Saumier:Judgments Convention:Revised Draft Explanatory Report,第82段:“enforcement orders, such as garnishee orders or orders for seizure of property, do not qualify as judgments.”
④ 参见Practical Handbook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ervice Convention,4th ed.,2016,第23段。
⑤ 参见A/CN.9/973,第35段。
① 比如,根据希腊法律,船舶司法出售不能消灭船员养老金请求权。
② 参见A/CN.9/973,第37段和第92段。
③ 《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第4条第2款采取了声明机制(declaration mechanism),即只有司法出售国声明的担保权才能保留在船舶上。
① 《北京草案》及其修订本的序言中指出:“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就司法出售通知、出售法律效力及船舶的注销或登记颁布统一的规则。”
② 参见A/CN.9/973 ,第93段。
③ 除非扣押当事人是利害关系人,并提供显示第8条“可暂停或拒绝承认的情况”所述任何情况存在的证据。
④ 参见The Acrux, [1962] 1 Lloyds Rep. 405。
① 參见以下案例:Goldfish Shipping, S.A. v. HSH Nordbank AG, Nos. 09-2314 and 09-2399, 21 April 2012, United States Court Opinions, JU 4.15;Bridge Oil Limited v. Fund Constituting the Proceeds of the Sale of the MV “Mega S” (formerly the MV “Aksu”) and Others (AC 58/2002) [2003] ZAWCHC 24 (12 June 2003)。
② 参见Den Norske Bank ASA v. Owners of the Ship “Margo L”[1997] HKEC [STBX]767[STBZ] (The “Margo L”)。
③ 参见The “Turtle Bay”[2013] SGHC 165,第17段。
④ 《北京草案》两个修订本的第12条拟建立一个在线集中存储库(repository),用于储存和公布司法出售的通知和证书。参见A/CN.9/WG.VI/WP.84,第8(k)段。
① 当前多数船舶登记机关的登记规则要求永久登记的条件包括船舶原登记机关的注销登记证明,否则船舶只能凭临时登记证书在证书有效期内航行。
② 参见A/CN.9/973,第49段。
③ 比如:欧盟2001年颁布的《布鲁塞尔条例I》和2012年颁布的《布鲁塞尔条例I(重订本)》。
④ 参见Gasser (Case-[STBX]116/02[STBZ]), ECR [2003] I-14693,第72段。
⑤ 《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第6条规定了司法出售具有国际效力的情形,对《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中“效力应延伸至所有缔约国”的表述作出了改变。
⑥ 参见《判决公约》第7条第1款(a)项。
⑦ 参见《北京草案》第4条、《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第4条和《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第6条。
⑧ 自《北京草案》开始,有效的司法出售对于管辖权的要求是:出售当时船舶处于出售国的实际管辖之内。该管辖权也应依据司法出售国的法律判定。
① 不同于《北京草案》两个修订本的第10条的规定,《北京草案》第8条还设定了司法出售国主管法院已经中止司法出售的效力或认定其无效的情形。
②除非是没有通知被告或被司法出售船舶的所有人,但这种情形在实践中极为少见。
③ 就此《北京草案》(第一修订本)与《北京草案》(第二修订本)有明显的差别,后者增加“光船承租人”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