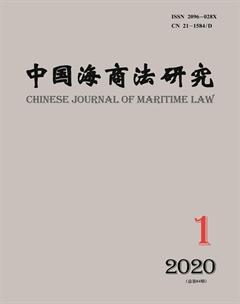论海上运输习惯在海商法中的法律渊源定位
袁发强 南迪
摘要:海上运输习惯在海上运输活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不仅对航运实务操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司法实践中解决海事海商纠纷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仅仅在涉外法律关系的适用中规定了国际惯例的补缺适用。这样的立法思路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运输市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相吻合,但在新近的《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继续维持这一规定的做法,既不符合海商法特殊的立法精神,也未能在民商合一的背景之下紧跟《民法总则》的步伐赋予习惯以法源地位,使海上运输习惯无法适用于国内运输。因此,应当在《海商法》的修订中打破国内国际海上运输法律适用壁垒,明确赋予海上运输习惯一般法律渊源的地位,使其优先于一般法适用。这样才能体现海商法的国际性和中国海商立法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为中国建设海事司法中心服务。
关键词:海上运输习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
中图分类号:D922.29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0)01-0083-11
On the legal source of maritime transport customs under maritime law
—also on the revision of Article 268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YUAN Fa-qiang,NAN D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Abstract:Maritime transportation custom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not only playing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shipping,but also being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solving maritime disputes in judicial practice. Regrettably,Article 268,paragraph 2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only provid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foreign-related legal relationship. Such legislative idea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trong planned economy of the domestic transportation market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but the practice of maintaining this regulation in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Revised Draft)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pecial legislative spiri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nor is it 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commercial combination. Rather, i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maritime transport customs to be applied to domestic transport. Therefore,in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the applicable barrier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laws should be broken,and the status of the general legal source of maritime transport custom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giving priority to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law. In this way,we can embody the internationality of maritime law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ime-oriented nature of Chinas maritime legislation,and serve our country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deeply participate in the legal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maritime transport customs;source of law;international practice
《中華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正处于修订过程中,已公开的《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维持了将国际惯例作为涉外法律关系适用的补充性法律渊源的做法①。[1]这使得法院在审理国内案件时一旦遇到《海商法》没有规定的情况,就跳过海上运输习惯直接适用民法的相关规则和原则。这既忽视了国内水上运输习惯的存在,更忽略了其在判断当事人权利义务中的作用。维持此种做法无法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事实上,海上运输习惯本身无所谓国内和国际的划分,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社会中各国海商法的传统法律渊源,但在中国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位。虽然《海商法》中规定了国际惯例补缺适用的原则
②,但“国际惯例”只能在含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运输关系中适用,不能适用于国内水上运输关系。这实际上否定了国内水上運输存在运输习惯的客观事实,不利于国内水上运输争议的公正合理解决。因此建议摒弃“国际惯例”的提法,将“海上运输习惯”作为正式法律渊源写进新修订的《海商法》总则部分,使之既能适用于处理国际海上运输法律争议,也能适用于处理国内水上运输争议。
一、国际惯例在现行《海商法》中的适用局限
从中国现行《海商法》的立法背景看,国际惯例的适用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内外有别”的立法政策所致,也是适应计划经济的国内航运市场模式的结果。国际惯例本身就存在着内涵模糊、适用范围受限的缺陷。这不利于国内运输争议的解决。
(一)国际惯例在立法中存在历史局限性
回顾《海商法》的立法过程,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采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经济③。[2]此时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背景下,沿海内河实行国家宏观干预的航运政策。国家对沿海内河运输市场根据市场运力需求情况实行宏观调控;远洋运输则由交通主管部门实施市场准入管理④
。这样的政策措施虽然已经适应当时改革开放的总体步伐,但还是人为地将航运市场割裂为国内和国际两个部分,分别采用不同的规则调整。对于国内市场主要采用政策和指令性计划,
对于国际市场则采用市场加法律。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政企分开,航运市场逐渐开放。但直至《海商法》问世,国内水上运输市场仍旧存在着计划经济管理的特征,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造。在当时立法环境的限制之下,《海商法》对海上运输关系的调整实行“双轨制”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海上运输立法安排的一个“权宜之计”。[3]这个“权宜之计”在立法中表现为只承认在国际海上运输中运输习惯的法律适用,否定国内水上运输存在习惯,否定运输习惯在国内水上运输中发挥着调整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作用。
在海上运输的国内市场完成了市场化改造并且飞速发展的今天,继续维持双轨制下的不同法律适用,只承认“国际惯例”在含有涉外因素的国际航运中可以适用,排除国内航运纠纷可以适用海上运输习惯的做法对于中国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海事司法中心,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利的。
(二)国际惯例的范围模糊不清
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适用原则最早出现在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简称《涉外经济合同法》)当中⑤。此后,“国际惯例”的措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简称《票据法》)以及《海商法》等法律中一直沿用下来⑥,但有关国际惯例的内涵和范围至今都没有一个被学界公认的说法。
在法律词典当中,international custom和international usage的释义是互通的,都可以翻译为国际习惯或国际惯例的意思。“国际惯例”这个提法首先
并不是作为一个法律用语,而是作为改革的口号和原则出现在政治性场合,之后才被接纳为法律用语。
此后的中国法学界很少再使用“国际习惯”一词①,这为以后有关国际惯例的内涵之争埋下了伏笔。仿佛“国际惯例”不同于“习惯”,范围更为狭窄、具有更强烈的法律色彩。
商业习惯或商业惯例起源于中世纪商人法,经过商人们在贸易中反复实践被确定为可以分配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则而广泛适用于国际社会。在学界有关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中,由于不同学者秉持的法理念不同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4-6]立法和司法解释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和指引。司法实践中往往采取限缩范围适用国际惯例的保守做法,以避免陷入争议。
海商法学界有很多学者都尝试过对海事国际惯例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航海贸易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也有人认为:“国际航运惯例通常是指在国际航运中,对同一性质的问题所采取的类似行动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逐渐形成的,为大多数航运国家所接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7]除需要具有广泛知悉、普遍遵守以及正当合理等作为国际惯例普遍拥有的特点外,可以看出,在《海商法》语境下,学界对于海上运输中国际惯例的界定基本上都在强调“国际性”。这是将“航运惯例”的适用放在涉外法律适用一章中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海上运输习惯进行了狭义的理解,没有将思维跳出现行法的框架来考虑。
(三)忽略了国内运输争议的法律适用
国际惯例在《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规定下有两个适用条件:一是只能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中适用;二是只有在法律和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补充适用。这使得海上运输习惯在司法审判中仍然只能适用于涉外海事海商案件,而无法解决国内海上运输争议中的问题。即使是在涉外案件中适用,也仅仅将海上运输习惯定位为任意性的补充,使得本身就是海商法源头的海上运输习惯尴尬地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当中。由此也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非涉外案件当中,如果遇到《海商法》没有规定的情形该怎么办?难道直接回归到民法基本原则中去吗?民法的基本原则能够直接解决纷繁复杂的海事海商纠纷吗?国内海上运输没有形成一些习惯性做法吗?国内海上运输争议没有相应的运输习惯可以参照适用吗?或者说,可以忽视海上运输习惯对国内运输关系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调整作用吗?
事实上,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业,国内水上运输当然形成了一些传统的运输作业习惯或惯例。例如,在散货运输的积载作业中,黄砂、煤炭采圆锥形堆集状态运输,而不允许平仓;在交货重量的计算方式上,以水尺线为计重标,而不是采用地磅秤称重量;还有甲板货与深舱货的装载习惯等等。另外,由于国内水上运输长期以“运单”方式体现运输合同关系,在运单上通用的记载用语和注意事项都体现了国内水上运输习惯的存在。交通运输部虽然在2016年废止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简称《货规》)和《港口货物作业规则》②,但这两个规则中的许多内容都是运输船舶和港口长期作业习惯的体现。国内水上运输企业和港口作业单位并没有因为规则的废止而停止这些作业习惯。
由于国内海上运输习惯没有被法律确立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司法机关对于国内海上运输争议在适用海上运输习惯裁判案件的时候做法不一,态度不明。部分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审理和仲裁国内海事纠纷案件时虽然在最终的审判效果和结论上与运输习惯相一致,但却不能明确对运输习惯的态度。法官和仲裁员为了保护海商法赋予海事纠纷当事人各方的特殊利益而不愿直接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则。在运用海上运输习惯作为裁判依据之后,却在裁判书中对适用了海上运输习惯含糊其辞,或者转而寻找其他有类似内容的可直接适用的规章办法。
例如,大宗散货短少千分之五免赔这一航运惯例的适用问题,因案件是否涉外就存在差异。武汉海事法院在2005年“中国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诉星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③中,主要裁判理由为:由于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存在特殊风险,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合理误差等因素,承运人对大宗散货短少5‰免赔,这已经在国际航运界形成习惯做法,其承认了免赔5‰是航运惯例;而在2005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诉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保险代位求偿纠纷案”④中,天津海事法院的裁判理由为:“被告不能证明油类运输5‰的允许误差属于国际惯例;承运人应按提单表面记载的货物数量交付货物……原被告对交付涉案货物时是否允许5‰的误差没有明确约定,而中国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被告应按照提单的记载交付货物。”广州海事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有类似的判决,虽然有些案件会以《进出口商品重量检验鉴定管理办法》关于水尺计重的准确度为5‰作为裁判的依据仍然支持了承运人的主张,但均不承认其主张为海事惯例①。
事实上,国内水上运输采用水尺计量重量早已形成惯例。在已被废止的《货规》中明文规定,国內水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散货交接的重量计算办法;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船舶水尺数计量②。在按照水尺计量散货重量的情形下,误差是难免的。如果只认可在国际海上运输中5‰误差免赔的习惯,而否定这个习惯在国内水上运输争议中的适用,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综上,国际惯例在海上运输涉外法律关系当中的适用
受立法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其本身的含义和范围模糊不清,同时其适用还阻碍了海上运输习惯对非涉外海事海商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有效调整,因此已经不能够满足海上运输实践的需求。
二、海上运输习惯应当作为《海商法》的法律渊源
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谈到:“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领先于法律……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发展进步的。”[8]法律落后于实践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而习惯的存在恰恰可以弥补这种落差。海上运输习惯本应是海事海商司法审判中不可或缺的裁判依据,而且在国际社会中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传统的法律渊源,但在中国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位。明晰海上运输习惯能否作为《海商法》的法律渊源还要从航运市场的特性、海上运输习惯与《海商法》的内在联系以及其他国家对运输习惯的态度来分析。
(一)海上运输市场天然的统一性
运输业具有生产场所的广阔性和过程的流动性,尤其是海运业具有更强的自由性和全球性。海上运输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行业。船舶运输服务对市场统一度的要求比一般的服务产业高,国际环境也使得航运市场比一般的产业服务市场更具对外开放性。[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来就具有无国境化特征的国际航运企业更趋国际化,其市场空间也更加广阔,国内经济活动与涉外经济活动的规则亦日益趋同,相关规则的参照体系也会更具国际性。
海上运输法律关系的调整具有涉外与非涉外之分,但海上运输的操作规范却实难切分,这与海上运输市场的全球性和统一性是紧密联系的。运输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在海上航行的规则可能因国内和国际水域的不同存在差异,但货物的装卸以及港口的操作规则往往是一整套下来,不可能因为装运的进出口货物或非进出口货物而产生运输行为规范上的差异。货物在港口的装卸作业也不会因货物或船舶的国别而有明显的不同。航运业有其特定的在长期运输实践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套规则,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用来调整海上运输关系的国内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内法的内容大都来源于海上运输习惯。
(二)“民事习惯”并不当然涵盖“海上运输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简称《民法总则》)虽然确立了习惯作为法律渊源,但未在条文中对习惯做出任何解释说明,目前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从学界来看,民法学和商法学对此的看法不一。
民法学界对于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的态度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习惯等同于习惯法:“习惯指非立法机关制定,而由社会各组成分子反复实施,且具有法的确信的规范。”[10]“《民法总则》中作为法源的习惯应指习惯法,而非事实上的习惯。”[11]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所称习惯,指具有法的效力与价值的习惯,也即‘习惯法或‘习惯法则,而非‘事实上习惯或‘单纯的习惯。”[12]另一类则认为,习惯不等同于习惯法。“习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过反复实践的交往规则,这些习惯能否被承认为习惯法,还需要区别对待”。[13]“这一法源条款意义上的‘习惯不能像通说那样被等同于‘习惯法”,“习惯本身并不是(有效的)法,所以它不是行为规范;但它可以作为法官裁判依据的认知来源,成为裁判规范。”[14]“习惯始终是个习惯而不是习惯法,它不能独立于制定法与判例法共同构成一个‘法律类型。”[15]此时的习惯要想成为具有法律渊源效力的习惯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事实上习惯规则的存在、内心确信以及法官认可。
商法学者对于能够作为法律渊源的商事习惯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商事惯例(也有学者称为商业习惯)在法源上既是民间法又是国家法,从其自发产生的起源上看为民间法,从其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它又是国家法。”[16]有学者认为认定商事习惯的实质标准是“合理性和可预见性”,形式标准是“合法性和合公序良俗”。[17]182也有学者认为商事习惯的认定应当类比民事习惯法,即能够作为法律渊源的商事习惯应当满足“事实之习惯+当事商主体的‘法的确信+法官认可,但相较于民事裁判而言,应降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标准”。[18]可以看到,商事习惯究竟应该以何种标准来界定也是没有定论的。此外,学者对于检验商事习惯的公序良俗标准态度几乎一致,认为“商事习惯要想成为商事法律渊源也必须经过公序良俗的检验”,但“公序良俗隐含非理性因素”
,“并非客观标准”,
“将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19]“民法总则第十条将公序良俗作为习惯适法性判定的标准”,
“没有充分关注商事习惯所具有的特殊技术性品行”,“商事习惯相较于民事习惯而言具有较弱的公序良俗色彩”,[20]因而主张审慎动态地理解公序良俗与商事习惯的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对于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其法源性质和认定标准在目前来看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公序良俗的检验标准对于商事习惯来讲似乎也并不合适,从这一点来看,《民法总则》第10条仍旧以狭义民法立场作出规定。海上运输习惯作为商事习惯,其认定标准应当符合商事习惯的认定标准。然而,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究竟是事实之习惯还是习惯法我们无从得知。该习惯如果能够包括海上运输习惯的话,作为法律渊源的究竟是海上运输过程当中的那些事实之习惯,还是仅仅包括已经确定下来的成文规则,如《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涉外性,能否以认定习惯的标准去限制那些已历经了几个世纪在无数航运贸易中千锤百炼并不断发展的海上运输习惯,以期达到《民法总则》规定的有资格作为法律渊源的习惯的要求?现行立法和理论界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因此,在《海商法》中单独确立海上运输习惯的法源地位十分必要。一旦海上运输习惯的法源地位被确立下来,其司法适用就不必被限制在一般法的“习惯”的框架之内,硬着头皮去证明“习惯之所以为习惯法”,作为商事特别法渊源的海上运输习惯在法律适用时就可以只需证明所要适用的习惯属于航运领域的习惯性做法,从而依其特殊性而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三)《民法总则》中习惯的适用顺序影响海上运输习惯的司法适用
《民法总则》确立了习惯与法律规则的适用顺序为“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这其中的“法律”范围究竟指什么?除了学界观点和少量的司法案例之外,没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进一步阐述①
。因此,在现行立法下,海上运输习惯能否优先于任意性规范不得而知。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海商法》没有规定,是否要先适用《民法总则》的条文规定,然后才能适用“习惯”?
如果海上运输习惯的法源地位没有被确立在《海商法》当中,那么在海事海商司法审判时,是否要依次检视法律以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确定这些“法律”都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在海事海商领域中的“习惯”?这样做显然在“以民法立场来确定习惯的民事法律适用程序,忽视了商事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以及在商事交易中的特有作用”。
[21]68
另外,《海商法》调整的众多领域与其他民商事一般法多有重合,例如海上运输合同,其一般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的运输合同一章;船舶碰撞侵权,其一般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海上保险合同,其一般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显然,这些都属于上文提到的“法律”。
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如果发现某一海上侵权纠纷的解决无法从《海商法》的条文中找到依据,某一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也不能在“海上保险合同”一章中得到解决,那么依照目前的立法机制,即便存在着“没有法律的,可以适用习惯”这样的条文,法官恐怕也不会适用习惯的。因为此时并不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在《海商法》之外还有《侵权法》《保险法》等一般法严阵以待。此时,习惯的适用与法律原则的适用顺序相似,变成最后适用的规则了。
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综上,海上运输习惯应当被确立为法律渊源,其适用顺位应当是在《海商法》的强制性规则没有规定时,适用海上运输习惯。只有如此,才能“用盡海商法”。
在习惯的法律适用顺序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态度不同。这也造成两大法系商法发展程度不同,在世界范围的商业界受欢迎程度和影响程度不同。
习惯自始至终都是英美国家三大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英国法院将各种法律资料整合加工成一套可适用于整个英国的普通法。[22]普通法的历史就是习惯法的历史,在英美法系判例制度下,一项习惯一旦被法院所采纳,就转化成了具有法律形式能力的规则。[23]英国学界普遍认为商事习惯不是源自英国本土的法律,而是学习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商人习惯法,经过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努力,通过判例将欧陆的商事习惯法并入了英国普通法。[24]英国学者罗伊·古德(Roy Goode)认为,[25](英国)海事法院处理涉外纠纷的法律依据不是英国的国内法,而是与国际海事商事相关的贸易规则和习惯①。可以看出,英国直接将海上贸易习惯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适用于海事海商案件当中。美国对商事习惯的运用以成文规则的方式集中体现在《统一商法典》中,第1-205条规定:“交易惯例指在一地区、一职业或行业中常为人们所遵守,以至于有理由预期在有关争议之交易中也会得到遵守的任何交易的惯常做法或交易方法”;“当事方之间的商业往来和当事方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为中为当事方所知悉或理应知悉的交易惯例”。该条款能够指引法院在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借助交易习惯和其他商业标准和实践来解释合同和填补合同。法典的主要起草人卡尔·卢埃林(Karl N. Llewellyn)将其称之为整合思路(incorporation approach),
[17]180为法院适用商事习惯提供了一个通道。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直接将海上贸易习惯作为审理海事案件的法律依据,而是通过给予交易惯例以正式法源地位的方式充分肯定了商事习惯在商法中的地位,进而适用于海上运输纠纷当中。
在成文法传统深厚的大陆法系下,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习惯可以作为有效的法律形式,否则法院不得援引习惯来裁判案件。德国将关于商事惯例的规定置于《1900年德国商法典》第四编“商行为”的第一章“一般规定”的第346条:“在商人之间,在行为和不行为的效力和意义方面,应当顾及在商事往来中适用的习惯和惯例”。这一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在交易习惯中,行为人所做的法律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除了适用法律的基本规定,同时也可以适用商事习惯。[26]实际上,这是对《1896年德国民法典》第157条“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习惯”这一规定的适用和补充,因此商事惯例具有解释性和补充性。在德国法中,商事惯例基于事实运行的基础之上,因此,它的确定也属于事实确定的范围,在实际运行中是“事实的法律产生渊源”,而非“规范性的法律适用渊源”。它自身并不能因属于《1900年德国商法典》第346条的适用范围而获得法律约束性,而必须通过借助于它的帮助而解释或者补充的法律行为。[27]也就是说,商事惯例的效力仅仅通过法律行为的解释和补充的间接途径来实现。
与《1900年德国商法典》相似,《1899年日本商法典》全文共689条,有关商事习惯法的内容规定在第一编总则第一章“法例”第1条中:“在关于商事而于商法无规定者,适用商惯习法,无商惯习法者,则适用民法。”日本学者松波仁一郎在《日本商法论》中写道:“虽然该条之所主者,实在于欲定商惯习法与民法之适用之前后,于商事应重惯习。殊于有法之效力的惯习为然,因而特置于民法之上。”[28]也就是说,对于商事习惯,《日本商法典》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明确表示有商事习惯法的首先适用商事习惯法,使商事习惯法优先于民法。然而这一规定也是经历了一些变化得来的。在旧商法典中,第1条的规定为:“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民法之有关规定及商习惯”,将商习惯与民法置于并列的位置。经修改后的新商法典确立了商习惯法优先适用的地位,确立了商法、商习惯、民法的适用顺序关系,有效解决了商事习惯在司法审判中的法律地位。[29]
总体看来,对待商事習惯适用顺序的态度不同,商法的发达程度也不一样。那些赋予商事习惯优先于民事一般法律适用顺序的国家,其商法对世界的影响力更广一些。这应当成为中国在《海商法》修改时确立海上运输习惯法律渊源地位的重要参考。
三、海上运输习惯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法律意义
如前所述,海上运输习惯作为商事习惯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将其作为正式法律渊源不仅可以解决一直以来海商法与一般法在适用上的冲突,在尊重《民法总则》的指导精神的同时,还能凸显出海商法独特的价值追求。
(一)解决海商法与一般法的适用冲突
在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若无法明确商事习惯的通行做法,那么就难以很好地保护商事利益。民法在海商法没有规定之时可以进行补充,但何为海商法没有规定的情形,需要对上下文以及立法意图进行分析,否则就会出现
对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违背。而在实践中,法官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往往难以探求海商法的立法意图。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简称《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一般性法律在有关于迟延交付、船舶抵押权、托运人的诉讼时效以及过错责任等规定和制度上都与《海商法》的规定有所出入,能否将这些一般法的规定直接补充适用于海事海商案件中应结合立法背景和立法意图来解释。例如,《海商法》第四章对迟延交货的情形只规定了一种①,即“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交货的”,而《合同法》却约定了两种情形,一是“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交货”,二是“未能在合理期限内交货”②。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用《合同法》规定的“合理期限”来弥补《海商法》的所谓“没有规定的情形”,但实则在《海商法》第50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一个“六十日”作为可视为货物灭失而提起索赔的具体时间③,并没有给出适用“合理期限”的余地。其背后的立法意图是刻意排除没有明确约定交货时间的情形,这是当初《海商法》在制定过程中对《汉堡规则》条文进行取舍的结果。[30]在海事海商司法审判中注重对立法意愿的探究也符合“用尽海商法”的理念要求,即在海事司法中不能一遇到海商法没有规定的情形就立即适用一般法的规定,而应尽量发掘海商法的渊源体系和立法本意④
,而海上运输习惯作为海商法的法律渊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1]
然而,在现行《海商法》语境之下,海上运输习惯的地位还仅仅是作为涉外的补充性法律渊源。当实务中出现了裁判某一国内案件时既没有法律的规定,也没有国际公约的支持的情况,按照目前中国法律的规定,无法适用海上运输习惯,只能按照“没有特别规定的,应遵守一般法”的原则,去适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但海上运输有其独特的行业管理和规则进行指导和规范,海上运输习惯当中也蕴含着航运业从中世纪起就遵循的行业价值和理念,民商法的一般规定和原则在面对这种种特殊性时,其指导意义仅仅只存在于一个宏观的理论层面上,无法深入具体问题的解决。因此,确立海上运输习惯正式的法律渊源地位不仅可以解决法院在审理国际海上运输合同纠纷时产生的《海商法》与一般法之间的法律适用冲突,还可以解决调整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关系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
(二)体现海商法特有的内在价值追求
虽然中国是民商合一的立法国家,但是民法和商法在法律关系上存在着天然的区别,这种区别尤其体现在风险分配的考量上。如果说民法的价值理念更注重公平,那么作为商法的特别法——海商法的价值理念更加注重效率。海上运输法律对于效率的追求有时甚至会以牺牲个案公平为代价。
在追求自由平等的民法中,公平原则甚至可以挑战成文规定,但是在商事立法和商事审判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助性的特点,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32]在商法领域应追求更高层次的公平和自由,因为商事关系建立在主体当然具有理性的假设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其对于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行为的后果,应当被看作是公平的。而在自由与公平之间,法律又选择了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前提下去追求自由的最大化。[33]商事关系的内在驱动力是对“效益”和“效率”的追求,“海商法可视为一套成本分摊体系,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对所有参与航运业者都最有利的解决方案”。[34]海上行业由于风险的特殊性,商人习惯形成有限责任。
这体现在海上运输合同中船方众多的免责条款和海商案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当中。但这也导致了人们对海商法律公平公正的质疑。实际上这是为应对海上风险而设立的独特的风险分配机制,是商事规则的本质使然,而非对正义的放弃。
由此可见,民法与海上运输法律的立法价值追求不同,一味追求海商法与民法原则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海商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动辄适用民法的规则和原则,容易使得海事海商案件无法得到正确、科学的审判。只有将海上运输习惯普遍应用于海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当中,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公正审判的发生。
(三)贯彻《民法总则》对海商立法的指导精神
《民法总则》第10条首次将“习惯”作为正式法源的做法对海上运输习惯的法源地位具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其本身并不排斥《海商法》单独规定海上运输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
合理分摊海上运输风险是海商法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商法创设了许多特殊法律制度,与一般的民商法相比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正是因为海商法体现出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学界某些学者认为,海商法并非民商法的特别法,而是自主独立的法律部门。[35]实际上,海商法在性质上即具有民商法的平等性、普遍性、权利互惠性,也追求商事领域的交易便捷、安全和公平。[36]中世纪重要的海商法都是由私人编纂的惯例或裁判汇编,是以习惯法的形式服务于海上的商事活动,主要是商人自治的产物,偏重于航运实践方面的指导性规则,缺乏法学理论基础。为了保证海商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必要用民商法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体系来为海商法做支撑,正视二者之间在相关理论、原则和制度上相融合的趋势去揭示海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以民法补充海商法”的原则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和实务界解决海商法与民法之间的法律冲突、补充《海商法》立法漏洞的惯性思维。在中国,海商法没有自己的基本制度,
需要借助民法的基本制度,例如它需要使用民商法的基本概念,如物权、债权、合同、侵权等;它需要借助民商法的基本制度,如合同订立的要约承诺制度、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等;它需要借助于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公平、等价有偿等。[37]如果失去了民商法的滋养,海商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然而,在确定海上运输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时,也将海商法回归到民商法理论当中去就不一定恰当。从国内民法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合法的、符合公序良俗的习惯才能成为民法的渊源。强调公序良俗是从一般法源角度的考量,笼统地说,似乎是恰当的。不过,当涉及到具体的商业习惯和行业习惯时,一概以之衡量可能过于苛刻。因此,在《民法总则》肯定习惯作为补充法源的背景下,商事特别法中肯定商业习惯的法源地位是对《民法总则》精神的贯彻,本身并不违反一般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海上运输习惯应当作为一般法律渊源,而不是补充性、解释性的法律渊源,这是中国民商合一体制下民法对海商法立法层面的指导决定的。《民法总则》已然规定习惯可以成为一般法律渊源,那么作为特别法的《海商法》在修订时理应紧紧跟随一般法的调整步伐,抓住一般法原则性指导的理念,及时调整其不合理的地方。
四、《海商法》第268条的可行性及其修改建议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种包容开放的姿态不仅是面向国际社会,也应当面向国内。武断地否定国内水上运输存在运输习惯,或者排除国内水上运输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不利于中国航运经济的发展,也不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夺取话语权。
(一)《海商法》单列海上运输习惯法律渊源地位的可行性
《民法总则》已经确立了习惯作为法律渊源,旨在处理民事纠纷时能充分吸纳民情民意,以符合现实需要,展现时代特色。在“民商合一”的体制之下,习惯能否精准适用于商事关系,解决商事纠纷,
学界说法不一。《海商法》作为商事特别法,海上运输习惯不能被“习惯”所替代,其适用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适用顺序、内涵以及弥补国内水路运输纠纷中习惯的适用缺失上。
首先是海上运输习惯在适用顺序上的可行性。有学者认为,得到民法确认其重要作用的习惯,尤其体现在商事领域。在适用顺序上,商事交易习惯应当优先于法律的任意性规定。这一适用顺序规则显然与“法律优先于习惯”的规定有所出入,因此该学者同时建议“此项规则,如民法总则不便做出规定,可以考虑将来在民法分则中予以规定。”[38]可以看到,在内涵上,该学者肯定了《民法总则》中习惯的内涵包括商事习惯;但在适用效力上,认为应当在民法分则中单独确立商事习惯的效力。这意味着,《民法总则》中规定的“习惯”在适用效力上无法满足当事人在商事交易过程中对适用商事习惯解决纠纷的需求。如果想要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对于商事习惯的适用意愿,就有必要在商事特别法当中确立商事习惯的地位。
有学者更加充分肯定了商事习惯的独立性,认为商事习惯与民事习惯不同,其根源于商事主体的自治性。“民商合一体制,既不是要抹杀商事纠纷的个性,也不是要在法律适用方面,将商事纠纷削足适履地向民事纠纷看齐”,认为“将普遍性的民法规范‘僭越地适用于商事纠纷”的做法并不妥当。[39]在习惯与商事习惯的内涵方面没有过多阐述,但也赞同“只有当商事习惯不能解决相应规范的时候,才能适用其他任意性规范,从而保障商事交易的自治性”。更有学者直指商事习惯与民事一般法的适用顺序,认为“商事习惯的适用不能简单地适用法律规范优先于习惯的规则,相反,法律应该确定商事习惯优先于法律的效力”。[21]67可见,用《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的“习惯”来代替商事习惯的做法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其中反对观点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商事交易的特殊性不能以简单地归入民事规则的方式被抹杀。在商事领域占据特殊地位的海上运输活动中的习惯,就更加不能被“普遍空洞化”了。
其次是海上运输习惯在内涵上的可行性。在习惯的内涵方面,《民法总则》规定的习惯能否完全涵盖海上运输习惯呢?据统计,在中国现行法范围内,除了《民法总则》第10条之外,共有25个条文规定了习惯,其中有20个条文涉及交易习惯①。在这些条文中,只有《合同法》分则规定了具体情况下的商事交易习惯,即买卖合同、客运合同、保管合同②。可以看到,交易习惯在商事特别规则中出现的场合局限于合同领域。同时这些交易习惯只涵盖了部分商事习惯,在《合同法》中没有一般性适用的规定。这意味着,民事一般法中的“习惯”只是小范围地适用于某些商事领域,还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繁荣纷杂的商业社会,不能满足商事纠纷解决的需要。海上运输业作为一个极具专业性的行业得以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该行业内的各个领域内都存在着具有高度适用效力的习惯或惯例。[40]这些习惯或惯例是自中世纪以来航海贸易的习惯性做法。这些习惯性做法不只约束买卖、运输、保管合同这类的内容,更多的是对海上运输中特有风险的利益平衡,例如船舶碰撞、共同海損等。在此背景下,《民法总则》规定的习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海上运输的作用,但远远无法涵盖海上运输的方方面面,难以达到海上运输习惯的精准覆盖。
最后,海上运输习惯弥补了国内水路运输纠纷适用上的缺失。中国水上货物运输法律适用实行双轨制。现行《海商法》第四章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排除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的适用,海事法院审理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时只能适用《合同法》第十七章的规定。在此之前,《货规》曾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关于部门规章权限范围的规定而被废止。《货规》被废止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其虽然不能作为判决书引用的法律依据,但可以作为确定当
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这表明,《货规》中的很多内容已经成为能够反映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海上运输习惯。虽然不是国际惯例,但已经成为国内水上运输习惯③
。《货规》被废止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更加欠缺充分的法律依据,航运实践中因《货规》形成的一些运输习惯也缺乏充分的正当性。[41]因此,就目前有关于规制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市场的立法而言,不仅《海商法》第四章无法适用,之前能够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依据的《货规》也被废止,国际惯例更是没有适用的空间。
《货规》是以《合同法》为依据,参照《海商法》第四章的相关内容制定而成的部门规章。[42]3其立足于国内水路运输发展情况,对国内水路货物运输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相比于《合同法》第十七章而言,内容更为全面具体,更加符合行业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43]例如,《合同法》第311条规定了承运人的免责事项有三项①,但《货规》第48条将其扩充为十项,其中(四)至(九)项是对托运人过错的具体细化。[42]70除此之外,《货规》中关于运输单证、航次租船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等的规定更是填补了《合同法》的空白。被废止后,《货规》不能再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但其原有内容在长期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实践中形成的成熟做法,仍然可以在日后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当中作为运输习惯而得以使用,从而解决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此外,《民法总则》确立了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之后,《海商法》再单独列出海上运输习惯来作为特别法的法律渊源,这一做法并不构成立法上的重复,而是一种强调,强调的是海上运输习惯在内涵和适用顺序上的特殊性。故此,认为《海商法》因此而没有必要确立海上运输习惯法源地位的立法逻辑是不正确的。类似的立法逻辑在《民法通則》确立国际惯例补缺原则之后,《海商法》等法律将其表述照抄进来时也有体现。因此,无论是在习惯的内涵方面,还是在适用效力方面,《民法总则》中的习惯都无法完整涵盖海上运输习惯,在海上运输领域,海上运输习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修改建议
为了顺应《海商法》的历史演进过程,遵循《民法总则》对于习惯作为民法正式法源的立法目的,使得《海商法》在结构上更具合理性,在法理上具有[LL]一致性;同时鼓励法官利用海商法特有的立法价值和理念去准确、科学地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提高办案质量,更好地维护海上运输秩序,对于《海商法》第268条给出如下修改建议:删除《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的规定,在第一章总则中单列一条:“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海上运输习惯。”
首先,删除原文中的规定,将海上运输习惯在海事司法审判中的适用不仅仅局限在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使所有的海事海商案件的审判都能够适用海上运输习惯而不区分国内案件还是涉外案件。将原本含义和范围模糊的“国际惯例”改为“海上运输习惯”,突破“国际惯例”在《海商法》立法之初的历史局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减少对航运业发展的不恰当干预;同时体现出《海商法》在调整商事关系的过程中特有的内在价值追求。
其次,将海上运输习惯的适用放在总则部分,确立了海上运输习惯正式的法律渊源地位,使习惯在海商法中不再仅仅作为补充性的法律渊源,同时解决了海商法与一般法的适用冲突,这也更加符合《民法总则》对海商立法的指导精神。
最后,修改过后的法律条文可以确定海事海商司法审判中法律适用的顺序,即《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海上运输习惯;海上运输习惯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等一般法。
五、结语
《海商法》的修订应当紧跟《民法总则》第10条赋予习惯正式的法源地位的做法,同时根据海上运输活动的商事性质,明晰海上运输习惯在航运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将海上运输习惯作为《海商法》的正式法源,要求法官在司法审判中贯彻“用尽海商法”的理念,
尽量发掘海商法的渊源体系和立法本意。在审理案件时多以《海商法》独特的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作为考量,使得非涉外案件也能受到海上运输习惯的调整,保证海事海商案件的审判质量。这有利于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提高中国海事审判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交通运输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EB/OL].(2018-11-05)[2019-03-24].http://xxgk.mot.gov.cn/jigou/fgs/201811/t20181105_3109896.html.
[2]198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EB/OL].(2006-02-16)[2019-03-24].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84 1.htm.
[3]张永坚.对完善中国海上运输法律制度的思考[J].国际法研究,2015(4):23.
[4]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31.
[5]韩德培.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1.
[6]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
[7]吴焕宁.海商法学[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3.
[8]亨利·萨姆奈·梅因.古代法[M].高敏,瞿慧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
[9]李光春.航运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9.
[10]楊立新.中国民法总则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1.
[11]彭诚信.论《民法总则》中习惯的司法适用[J].法学论坛,2017(4):27.
[12]施启扬.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55.
[13]王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2017:56.
[14]雷磊.习惯作为法源?——以民法总则第10条为出发点[J].环球法律评论,2019(4):65-66.
[15]陈景辉.习惯法是法律吗?[J].法学,2018(1):3.
[16]周林彬,王佩佩.商事惯例初论——以立法构建为视角[M]//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中国商法年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17]陈彦晶.商事习惯之司法功能[J].清华法学,2018(1).
[18]许中缘,高振凯.司法裁判文书中商事习惯的实证研究——以《民法总则》第10条中“商事习惯”的适用为视角[J].民间法,2018(20):369.
[19]艾围利.商事习惯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2:36-37.
[20]曹兴权,卢迎.商事习惯司法适用特殊性问题的体系阐释与因应[N].人民法院报,2018-11-14(7).
[21]许中缘.论商事习惯与我国民法典[J].交大法学,2017(3).
[22]高鸿钧,等.英美法原论(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7.
[23]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三卷)[M].廖德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99.
[24]姜世波.英美法中的习惯法渊源[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2):33.
[25]GOODE R.Goode on commercial law[M].5th ed.London:Penguin Books,2017:3.
[26]范健.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1.
[27]卡纳里斯.德国商法[M].杨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50.
[28]松波仁一郎.日本商法论[M].郑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8.
[29]王琰.日本商法典制定过程和启示[J].新西部,2007(10):118.
[30]刘子平.论以民法补充海商法的单位[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4):112-116.
[31]司玉琢.海商法专论[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30.
[32]赵万一.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化[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1):56.
[33]袁发强.论商事冲突法的价值选择与规范表现[J].法学评论,2016(5):64.
[34]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0.
[35]王世涛,汤喆峰.论海商法之于民法的独立性[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23(3):114-120.
[36]何丽新.论新民商立法视野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订[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1,22(2):51-57.
[37]李莹莹.海上侵权责任分担法律规则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7:67.
[38]王利明.论习惯作为民法渊源[J].法学杂志,2016(11):11.
[39]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J].中外法学,2018(1):146.
[40]司玉琢,李天生.论海法[J].法学研究,2017(6):78.
[41]孙思琪,陈博雅.《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废止的影响与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2):7-11.
[42]叶红军,翁笑冰.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港口货物作业规则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43]黄毅.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适用[J].世界海运,2013,36(1):52-54.
收稿日期:2019-09-30
作者简介:袁发强(1966-),男,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york000618@163.com;南迪(1996-),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E-mail:1072454483@qq.com。
① 参见《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16.1条对《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修改意见为:“保留原条文”。
② 参见《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③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