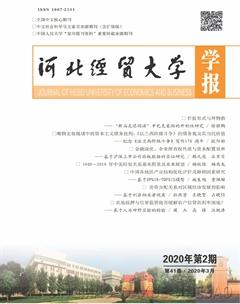基于新经济生产方式考量下的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升级研究
董翔宇 赵守国
摘要:新经济发展模式下,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探索新经济产业生产方式下,人口红利的新内涵及其市场“瓶颈”问题,从劳动要素属性出发思考要素市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边际效率低于潜在效率,使得要素市场仅有劳动力定价,缺少人力资本定价机制,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扭曲。此外,基于劳动要素属性、价值创造与消耗均衡及较低折旧率的延迟退休政策提高了劳动要素有效时间供给,缓解要素市场扭曲。科学认识“人力资本红利”,破解经济转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约束,更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基于要素属性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人力资本红利;劳动要素供求市场扭曲;人力资本定价机制;人力资本价值创造与消耗均衡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2-0037-08
一、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1]认为,如果300年后的人们书写我们的历史,最主要的事件应该就是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提高100倍,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当然,萨默斯的言论前提假设是指中国人均GDP可以连续70年保持7%水平以上。然而,如此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仅维持了30年,紧接着“民工荒”、涨薪潮、老龄化等成为了新闻报道的常见词汇。此时,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剩余劳动从此消失,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也趋于消失[2],中国因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陷入经济增长陷阱。面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劳动市场阶段性转折,因此有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补救政策,如调整人口政策,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3]、抓住因寿命预期延长而增加储蓄的“第二次人口红利”[4]、延迟退休、提高劳动者素质等。
上述观点和结论应该是当前主流思想,然而不管刘易斯理论还是人口红利理论都是利用人口学观点,基于传统生产方式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关系提出的新学说,并没有从劳动要素属性、生命周期及其价值创造和消耗均衡的纵向历史视角出发,研究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结构跃迁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和延迟退休的必然性。如果从劳动要素属性视角出发,“民工荒”及无法普遍观察到的实际工资增长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储蓄动机降低和劳动力供给短缺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内涵是什么?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金缺口是延迟退休的理由吗?
笔者认为简单地运用传统理论经验式分析的刘易斯拐点及人口红利理论,只研究短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从偶联有限的人口与经济宏观数据计量结果,为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而感到恐慌欠妥。尤其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要内容,以基于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对劳动生产率提高日益有决定性作用。劳动要素质量的整体跃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相比于之前的单纯的人机替代的数量论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力资本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要素,“人力资本红利”必将取代“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劳动要素新内涵的属性研究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从人力资本的生产供给、新经济产业升级需求及报酬的定价扭曲视角研究为什么当前人力资本红利不能充分发挥,进一步从人力资本的生产供给周期、价值创造和消耗均衡视角研究延迟退休的必要性。有助于破解当下西方传统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效力乏微的困境,完善并拓展传统理论,为相关政策、人力资本定价、延迟退休等方面提供指导。
二、文献综述
伴随着新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学者们对劳动要素需求的认识也逐渐由因“人口红利”消失而担忧,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的深入探究,基于这两个阶段的转变,文献的研究脉络也主要分为两大主线:一是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辩证认识;二是人力资本的探究性思考。
第一类研究脉络可追溯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爆发的民工荒现象。国内著名学者蔡昉教授认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點”,并等同于人口红利的消失[5]。刘易斯认为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农业部门由于生产效率较低,劳动力相对过剩导致其流向较高生产效率的工业部门,此时,工资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物资生活资料[6]。随着工业部门的进一步扩展,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工资不再主要取决于物质生活资料而是其边际生产力,出现刘易斯拐点。而“人口红利”概念是Bloom和Jeffrey在研究战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所提出的新观点[7]。他们认为战后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存在大量剩余劳动,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由高到低,进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逐渐形成富有生产性劳动力的人口结构。短期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形成了“人口机会窗口”,促进了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将这种“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8],当人口生育率进一步降低,老龄化程度升高,经济回落到较低的稳态增长水平上。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也恰逢事宜的印证了上述观点。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经济增长不能按照不变的工资雇佣劳动力,劳动力由剩余到短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不难发现,刘易斯拐点与Bloom的人口红利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从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视角研究,是资源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流动的正常配置过程。后者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源的有限性假设下,劳动年龄结构增加会引致资本配置的增加,避免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所以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张同斌认为人口由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推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9]。从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说认为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储蓄率上升和劳动力供给增加两个源泉。然而,保罗·舒尔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当期储蓄与年龄结构之间并没有显著的依赖关系[10],贺菊煌[11]和Johnson[12]通过实证研究也没有得出生育率的降低对提高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并无证据证明中国储蓄增加是收入增加所致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致。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13]:一方面,人口总数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比,不难发现这只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概念,并不符合经济学意义。现实经济活动中,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和隐形失业,而这些失业者并没有剥夺其社会资源的分享。另一方面,整体的抚养比统计数据,忽视了中国区域间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生育率要低于西部地区[14],因此,我国人口红利的释放期也应该是梯续变化。李建等认为当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总抚养比下降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当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即使总抚养比上升,也不会抑制经济增长[15]。
从技术创新发展视角来讲,当前技术创新大众化、创新周期缩短及人力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自我实现,使得要素之间从传统的替代关系升级为互补,通过要素之间的协同升级提高参与要素的潜在生产效率。华小全通过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认为劳动生产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16]。当出现近似设备水平的系统竞争时,劳动者技能作为区分效率的关键程度凸显[17],知识型、能动型劳动要素(人力资本)升级为劳动市场主要需求对象,部分低技能、低知识型劳动要素不适应当前经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相对过剩劳动要素。人口红利理论和刘易斯拐点理论主要基于理论经验式分析方法,缺乏时代现实特点。
第二类研究脉络实际上是基于劳动要素质量提升的背景而来的。人力资本的概念被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在1935年首次提出,后经西奥多·W·舒尔茨[18]等人发展完善形成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形态即凝结在人体中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价值的总和。OECD对人力资本的最新定义是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19]。Emran和Stiglitz指出人力资本是“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用以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20]。可想而知,21世纪劳动要素质量取代数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难发现,人力资本理论已经推翻了人口红利数量论的观点,因此,人口红利消失也必然成为一个伪命题。高建昆[21]认为随着我国教育强国计划的实施,人力资本大幅度提升,人口红利正由劳动力型向人力资本型转变,人口红利因结构升级,而不会消失。张同斌[9]认为2002—2013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劳动供求关系导致“人力资本红利”取代“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海峥等结合我国经验性数据,对Jorgenson-Fraumeni终身收入法修正,构建了人力资本指数,并进行测度[22]。
基于上述分析,人口机会窗口实质上存在人口红利与人口负担的替代效应,而非等于人口红利期。充分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而西方人口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符合人口红利发挥的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理论建立在传统劳动要素数量论和要素替代的理论基础上,忽略现代劳动要素的新内涵和经济增长机制的转变。基于该假设及其分析方法,强调劳动年龄结构数量,弱化劳动异质性的积极作用。同时,国内学者提出依靠寿命延长及社会保障完善提高储蓄动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但是储蓄转化为投资仍建立在传统产业生产要素替代式升级的分析环境下,任何单方面的要素改变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都是短期效应,而长期都具有边际递减效应,这种理论的基础是要素条件处于相对静态假设。同时,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大多集中于劳动要素质量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层面,没有从劳动要素理论出发解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报酬定价及市场瓶颈问题。然而,新经济生产方式是基于人机互补而非替代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4.0主导下的新经济产业升级,将致力于打破年龄、性别的束缚,对劳动要素的需求全面升级为人力资本型,要素之间不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替代的关系,更是一种互补。人力资本与生产工具协同升级,充分发挥参与要素的潜在生产效率,并且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再生产提高潜在生产效率。因此,新经济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和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内涵更丰富的劳动要素和与之相适应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红利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
熊彼特认为经济社会的变化包含两个过程:循序渐进和非循序渐进[23]。前者是在一个经济结构中连续不断的适应数据的变化,因此,这种增长是自然數据变化的静态过程,该增长方式中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后者是经济社会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是经济由数量上的增长到质的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是产生的新生产方式和新组合并不能由旧组合要素来执行,也不是对闲置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是基于传统资源质的变化的基础上,利用现有资源做新的事情,而不管这些资源数量上的增减。新的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要素具有更丰富的技能、知识等能力满足新价值创造过程的改变。人力资本以承载更多知识、技术、技能等能力的劳动要素新形式成为生产要素主体需求,使得产业链分工重组。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对产业系统的重构,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比于前两次而言,实现了由人机替代到人机互补的生产方式转变,即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潜在效率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人机结合。因此,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分为三种:一是与其他物质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投入;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核心投入品;三是知识、技术、技能等能力的代际传承。
第一,人力资本是直接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内化于人力资本自身更高的技能和知识提高了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有助于改善要素配置状态。但是,配置比例的优化并不是效率提高的充分条件,而更高技能和知识的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决策效率,这种因人力资本自身升级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被舒尔茨称为“内生效应”[18],进一步而言,相对静态经济发展条件下,随着大部分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时,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推动需求由规模化向小众化、个性化发展,生产系统由“产品设计—产品开发—产品制造”向设计、开发、制造一体化发展,人力资本不再是机械操作,更兼具能够准确理解市场需求和产品架构并能直接参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及执行能力。网络信息技术充分发展,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动态互动及数据存蓄与运用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种生产关系使得劳动者更愿意参与长期的技术学习,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实现其他要素边际报酬递增,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效应被阿罗称为“外部效应”[24]。人力资本与传统劳动力及其他物质资本的投资属于完全不同的逻辑范畴,物质资本的积累源自于经济活动内部,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经济活动内部的“干中学”和经济活动外部的自我学习和培训获得。
第二,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核心投入品。人力资本既是知识和技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主要传播载体。具有非竞争性特征的知识通过“溢出效应”提高经济系统的生产效率,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作为技术研发、吸收与扩散的必要条件,其质量和数量状况决定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加速器效应的大小,人力资本需要物质资本投资尤其是技术投资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网络信息技术为这种结合的跨区域合作创造了条件,拓展了合作空间[25]。当下由精英创新到大众创新的转变,人力资本对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分布式创新和发展激发知识化的劳动要素的潜在创新能力,并通过共享经济系统实现价值转化,激发新经济动力引擎,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人力资本作为知识、技术、技能等能力的代际传承载体,通过“物化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源泉是创新发明和人力资本提高。物质化技术创新是指新产品、新生产工具等资本设备的不断发明更新,是人力资本承载的创造能力内部化于物质化创新发明中,主要依靠“物”进行传承[26]。人力资本增进型技术创新是指通过公共教育、知识积累及“干中学”等形式提升劳动要素的技能和生产效率,主要依靠“人”作为传承载体。人力资本通过将自己的智慧及技能物化于资本设备,在一定人力资本规模及质量水平下,进一步进行创新的成本较大,人力资本将更多的时间投入个人生产能力的提高,减少物化创新。随着人力资本规模与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一期的物质创新将不适应当前的人力资本要求,此时人力资本将更多的时间进行物化创新。人力资本作为传承的关键要素,使两种传承方式相辅相成,实现技术、知识代际之间的物化及人力的传承,同时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自我升级和再生产,使其灵活适应当期的生产方式和对抑制效率发挥要素的升级改造,共同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四、我国人力资本供求扭曲的现实影响分析
目前国内具有基础性或通用性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供大于求,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出现了就业困难的局面,但很多企业也存在招聘困难,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招聘,人才市场呈现“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二元化特征。而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不够与人力资本的素质较低,忽视了人力资本与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之间的扭曲关系。研究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韩国持续增加的教育开支与高失业率和劳动报酬下降持续并存的现象[27],表明人力资本数量增加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与技术结构及技术结构升级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早期欧美发达国家作为技术和工业的开创性国家,以更少的引进和更多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量与质的自然升级。克拉克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包括物质资源、劳动要素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的一个动态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这些要素的升级密切相关。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更多的以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其引进的技术并不一定适合自身的发展阶段要求,一味地追求现代化而忽视劳动要素的属性,两者间的矛盾也是制约转型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长期以来,具有明显“赶超”性质的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是发挥资源优势,而是更多地受制于经济发展目标,致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不匹配,尽管通过投资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物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最优效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一)人力资本供求扭曲:生产、再生产供给与新经济产业升级需求视角
1. 人力资本的生产、再生产供给。人力资本的投资目的是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价值,追求更高报酬。因此,对于劳动要素个体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层次,即人力资本的生产供给,与人力资本的预期工资、投资成本和机会成本有关。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通过增加或提高劳动要素的智能和体能而最终反映在劳动生产率增加上的所有投资支出。间接成本指人力资本投资期间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和形成伴随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劳动要素也面临着是否选择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形式、投资层次等一系列选择的机会成本。劳动要素之所以选择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投资形式和层次是因为在当前人力资本生产和需求多元化的情况下,该种选择相对于个体当前及将来情况来说是一种最优选择,同时满足预期工资将会弥补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但是劳动要素选择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层次建立在当期生产条件下的未来相对静态预期,由于存在很长的投资周期,人力资本形成时,人力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人力资本的价格也会与预期有所不同,导致有些人力资本供不应求,有些人力资本则供给过剩,这样的人力资本市场及其形成的价格体系又会引导人力资本投资调整。但是当现在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效果时,人力资本市场的供给结构又会发生变化,还是会出现供不应求和供给过剩现象。因此,生产的时滞性导致人力资本商品供给结构具有滞后性,使得人力资本市场难以出清。
人力资本市场无法出清的原因除了投资的时间成本以外,还包括教育系统由精英式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化不完全,造成人力资本生产内容上单一(均为通用型人才),在技能上无法直接实现使用价值,即人力资本多层次差异化需求与通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矛盾。在不改变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根本方向的情况下,大力扩大教育规模,又极力维护传统教育的价值观,缺乏实用性和差异化需求的服务理念。工业4.0条件下,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产业升级的突变性越来越明显,学生主要偏向于获取有用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成为以承载高深知识和培养思维、情感的教养为主要目标的文化精英。新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异于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产品周期缩短与个性化需求凸显并存的生产环境下,终身学习或再生产对人力资本供给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显得尤为重要,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应向更广的社区提供服务[28],教育系统把提供教育、培訓的功能扩展到范围更广的新领域及专业技能化领域,真正实现人力资本从初级供给到再生产供给的异质化和实用性。
2. 人力资本需求多层次差异化趋势。循序渐进的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较多的承接性,其引起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的变动较小。我国前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于劳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循序渐进式的产业升级,通用型人力资本的规模较大,具有较高的供给弹性,专用性人力资本供给弹性较小[29],“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是典型的表现。而非循序渐进的产业结构升级则呈现出较多的突变性,其引起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的变动较大。归根结底是我国当下以数字制造、AI等基础制造技术的创新和突破的非循序渐进式产业升级与只能呈渐进式路径变化的人力资本结构不相适应的结果。
3. 产业发展社会分工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反应。基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对劳动者去技能化的管理思路,以机器“替代”劳动者技能。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良好人机互补的数字化、智能化设备潜在生产效率充分发挥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30]。前者延续了“科学管理”传统,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产业升级。而互补逻辑则认为智能化与人工之间是互补的合作关系,机器复杂化的目的在于延伸劳动者的技能应用空间,良好的人机结合反过来又促进了自动化、智能化装备的发展。因此,相比之前,人力资本也是更高级化的人力资本,是知识化与“干中学”集一体的劳动要素,是一种非循序渐进式的产业升级。
(二)人力资本报酬定价机制缺失的现实影响
传统经济分析理论认为劳动要素的工资取决于其边际产出,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要素的高级形式应该也由其边际产出决定。但是传统理论边际产出分析法关注点在于劳动要素所处的行业性质,并没有考虑劳动要素的属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工资不仅取决于个人、家庭维持费用,还包含培训和教育的费用,实质上是考虑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问题,但是没有提出人力资本工资定价机制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回报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补偿问题。
我国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扭曲必然导致人力资本报酬过低。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需,由于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导致国内产品缺少价格主导控制权,唯一可控的是劳动力成本。同时,近年来,国际贸易战争、货币战争日益加剧,国内企业只能通过内部成本控制抵抗外部风险。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国内GDP增加,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很大,而工资弹性相对较低,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相应的提高。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其收入预期并不是与城市平均收入和生活成本比较,而是与农村及劳动力之前的收入比较,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单纯为了生活保障务工,幸福感作为背井离乡务工的缺失因素,已经纳入劳动力预期成本当中。中国经济发展在没有带来收入分配效应提高的现状下,过低的工资已经无法补偿带有幸福感的务工成本,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宁愿选择在家或家乡附近务工,虽然工资相对减少了,但是整体效用提升了。
对于人力资本而言,由于供求市场的扭曲造成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定价机制缺失,不能弥补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成本和间接成本,劳动要素失去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导致社会出现人力资本返贫现象,“读书无用论”是典型代表。“现代机械和知识型员工”对“传统机械和简单劳动”逐步进行替代的过程,不仅在于现代制造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更在于现代制造体系生产出的产品具有更好的性能、更强的功能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人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不是用单调重复的手工劳动“替代”机械生产,也不是用经验式的技能“补充”机械生产,而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创造性地“主导”生产过程。现代制造降低了工业对简单劳动的依赖,同时赋予产品更加丰富的竞争要素。因此,制造的价值创造能力、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甚至超越其他的价值创造环节。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等在生产系统中的重要性和在契约网络中的投资专用性都大幅提高,产品承载要素的丰富及信息、能力的重新配置要求人力资本报酬定价机制体现异质性,人力资本通过知识、技能提高生产效率而凝结在商品价值中的差异化,即人力资本报酬定价机制应该内化技术和知识等要素。
(三)人力资本要素的有效时间供给扭曲:延迟退休机制的要素属性依据
主流学术观点主要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劳动者收入与闲暇的替代关系考察劳动者的退休决策,王作宝[31]分别利用外部冲击与跨期替代弹性考察实际工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调整最优路径的影响;Lumsdaine和Mitchell[32]将退休选择视为包括养老金与工资预期在内的期权价值,并利用期权价值估计劳动要素某一年龄选择退休的概率。以上学术观点的重心在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比较,收入增加更倾向于提前退休,但是未考虑到劳动要素属性变化、有效工作时间缩短、生命周期延长及劳动者价值创造与价值消耗的均衡关系。目前学术界、政界的主要共识是延迟退休,这是迫于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金压力。然而,基于本文对劳动要素生产供给周期、价值创造与消耗均衡等属性的研究分析认为,当前观点并未对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延迟退休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辨析,也未考虑当前产业升级的新内涵所引致的劳动要素需求的新变化。因此,基于老龄化、财政负担、养老金等数据上的偶联性研究延迟退休,忽略劳动要素及其需求变化,结论除了政策性支持以外,在理论却显得十分牵强。
由上文分析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来看,养老金压力是有效工作时间缩短与生命周期延长之间的矛盾,因此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养老金压力的因,表面上看,养老金压力与延迟退休的关系有莫大联系,但养老金增加是延迟退休的果。延迟退休是劳动要素有效工作时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依据也必须基于劳动要素、产业环境的变化及符合生命周期的创造价值与消耗价值的均衡。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下的产业升级通过自动化、智能化手段降低劳动复杂性,劳动要素的工作效率并不单纯取决于劳动者年龄,而与劳动要素从事特定工作的时限、工作组织和环境设计相关。高度自动化、智能化將有利于降低劳动强度和劳动复杂性,大大缩减人力资本的折旧率,改善劳动要素的工作环境,增加高龄人口和女性对劳动的适应性,提高人口的劳动参与,尤其是高龄人口和女性的参与。新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和环境增加提高了劳动要素的参与率和适应性,降低了劳动要素的折旧率,为劳动要素延迟退休提供了充分条件。另一方面,当前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对未来较高收入的预期,使得更多的劳动要素选择通过教育方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人力资本生产供给具有很长的时间周期,短期内劳动供给减少。从世代交替的视角来看,当期在教育的年轻劳动人口分享上一代劳动要素的成果,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劳动要素个人具有直接和间接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间接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的收入提高,传统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假设各期消费支出不变,忽略人力资本的正负外部性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和寿命的延长,消费周期延长及消费需求内容和质量增加,尤其是退休以后的医疗、健康等消费需求增加较快,但是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时间却没有延长,延长的退休生活和较高的生活、健康等需求同样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最终导致劳动要素价值创造与价值消耗不均衡,只能由政府负责个人的负外部经济成本。因此,人力资本为了满足延长的生命消费周期和递增的消费需求,以及为减少自身的社会经济成本的负外部性,延长有效工作时间具有必然性,最终实现价值创造与消耗的均衡。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由于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的存在导致人力资本生产供给与产业结构升级需求不对称,造成劳动要素供求市场扭曲,同时,缺少内化人力资本知识、技能等能力要素的工资决定机制,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扭曲及返贫现象,从而使人力资本不能进一步扩大规模和提升质量,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本支持,技术创新受到抑制,产业结构升级遇到瓶颈,中国经济将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停滞或衰退阶段。由于人力资本供求市场扭曲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工资弹性较低的共同作用,导致工资趋同,而不是劳动力短缺(刘易斯拐点)造成的。这种劳动力市场扭曲,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人力资本市场的数量问题,更是一种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与内容的优化提出的差异化要求。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传统观点更多基于数据上的偶联性,包括对数据的解释更符合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缺乏严格的机制逻辑分析,忽略了新经济生產方式条件下对劳动要素新的内涵要求。本文主要结论:(1)中国“人口红利”并不存在“消失论”,城乡仍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剩余劳动力;(2)人力资本主要通过要素投入功能、效率功能和传承升级功能,以新的要素配置方式和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3)人力资本边际效率低于潜在效率,使得要素市场仅有劳动力定价,缺少人力资本定价机制,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扭曲;(4)基于劳动要素属性、价值创造与消耗均衡及较低折旧率的延迟退休政策提高了劳动要素有效时间供给,缓解要素市场扭曲。
(二)展望与研究局限性
1. 展望。首先,工业4.0是对传统产业的重构,生产方式多样化及消费需求个性化、小众化提高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要素的多元化,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必须满足实用性要求,而传统教育的价值观缺乏实用性和差异化需求的服务理念,政府必须积极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引导教育系统的服务价值理念,构建劳动要素信息服务平台,积极促进人力资本由生产到供给符合产业发展需求,减少市场配置调整时滞性造成的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次,人力资本作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动力,我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发展的导向更应该考虑人力资本要素禀赋水平,而不是“赶超”,只有充分保证产业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本报酬定价机制,激励劳动要素选择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和投资层次,实现潜在人力资本效率。最后,延迟退休渐进式方案不仅仅考虑年龄问题,应该从劳动要素属性出发,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率速度。同时,利用公共和私人养老金制度及税收制度等激励因素鼓励劳动要素主动延迟退休。一方面,每一个劳动者有权根据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做出退休决策(提前退休或延迟退休);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或其他健康福利激励劳动者延迟退休。
2. 研究局限性。尽管本研究丰富、拓展了新经济下劳动要素理论,并基于现实经济,在理论上详细分析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对理论和现实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理论上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但并未实证检验三种机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大小,将来作者希望能对此通过结构性分解剖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2)本文对人力资本报酬定价机制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分析了人力资本生产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价值创造与消耗均衡,但未对其进行数理上的量化,希望下一步能构造具体的定价模型,更有利于实践应用。(3)提出延迟退休的要素属性依据,但是没有确定延迟退休的具体边界。未来研究希望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属性的价值创造与消耗模型,确定不同质量、领域劳动要素的具体延迟退休方案,为政策提供更好支撑。
参考文献:
[1]萨默斯.日本失落的十年值得中国反思[N].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1-23(30).
[2]蔡昉.中国劳动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4-14.
[3]易富贤.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J].社会科学论坛,2008(6):75-96.
[4]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
[5]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索中国未来的这种源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Arthur Lewis. Reflection on Unlimited Labour,in Di Marco,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M].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2.
[7]Bloom David E,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R].Cambridge: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1997.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9]张同斌.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到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兼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J].经济科学,2016(5):5-17.
[10]保罗·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经济学(季刊),2005(4):991-1018.
[11]贺菊煌.人口红利有多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24-35.
[12]Johnson,D.G. Population Development[J]. China Economic Review,1999,10(1):1-16.
[13]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齡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5):29-39.
[14]刘怀宇,马中.“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J].人口研究,2011(7):65-74.
[15]李健,卫平.产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7):5-12.
[16]华小全.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因素分解[J].财经理论研究,2015(3):9-15.
[17]封凯栋,赵婷婷,等.生产设备与劳动者技能关系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从工业4.0模式谈起[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4):42-52.
[18]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15.
[19]OECD.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The Rol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R].Paris:OECD,2001.
[20]Emran S, J E Stiglitz.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Financial Restraint,and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EB/OL].www.gsb.columbia.edu/faculty/jstiglitz/download/papers/2009_Financial_Liberalization.pdf,2009.
[21]高建昆.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2(4):58-64.
[22]李海峥,梁玲,Barbara Fraumeni,等.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8):42-54.
[2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24]Barro R e Lee,J w. 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R]. Washington: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2000.
[25]刘智勇,胡永远,易宪中.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86-95.
[26]代谦,李唐.技术传承方式与长期增长:对传统中国增长停滞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10(6):143-156.
[27]Temple Jonathan R W. The New Growth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37(1):112-56.
[28]马丁·特罗.从大众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4):6-14.
[29]刘方龙,吴能全.“就业难”背景下的企业人力资本影响机制——基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3(12):145-158.
[30]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6.
[31]王作宝,吴振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负担——四种测量模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3):85-89.
[32]RL Lumsdaine,OS Mitchell.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retirement[R]. Washington:Pension Research Council Working Papers,1999.
责任编辑:母爱英
Research on Upgrad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Human Capital Dividend based on New Economic Mode of Production
Dong Xiangyu, Zhao Shougu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hanxi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the key facto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w connotat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bottleneck" problem and its market under the new economic industry production mode, thinking the factor market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starting from the labor factor attribut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uman capital marginal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e potential efficiency, make the factor market only has labor force pricing, lack of human capital pricing mechanism, eventually led to the distortion factor market.In addition, th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labor factors, the balance of value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he low depreciation rate increased the effective time supply of labor factors and alleviated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market.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uman capital dividend", breaking the human capital constraint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break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based on factor attributes for the postponing retirement policy.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gift,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market distortion, human capital pricing mechanism, human capital value creation and consumption equilibr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