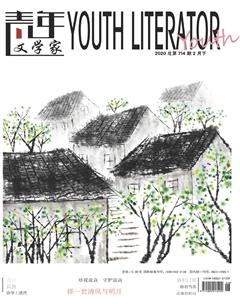《幻世浮生》母女共生幻想关系分析
邹心怡
摘 要:詹姆斯·凯恩的《幻世浮生》刻画了一位美国单身母亲米德尔德·皮尔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奋斗挣扎和梦想幻灭过程。其中她与女儿薇妲之间的爱恨纠葛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矛盾之一。二者物质—精神的相互寄生符合伊基·弗洛伊德“共生幻想”母女关系理论。以此视角出发,剖析人物内在冲突,为解析小说的人伦悲剧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幻世浮生;共生幻想;母女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6-0-02
荷兰心理分析学者伊基·弗洛伊德在其著作《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中着重探讨了母亲对女儿人格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共生错觉”这一术语,指代“母亲一直依赖于孩子的认可。需要孩子表现出粘着自己”的倾向。[1]《幻世浮生》表面上讲述了一出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中产家庭的伦理悲剧,实则皮尔斯和女儿薇妲之间畸形的“寄生”关系是小说幻灭走向的重要内在因素。她们“共生幻觉”的强烈性压倒了个体生存的独立性,成为皮尔斯清醒认知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使女儿从天使堕入魔女。母女俩胶着对峙的过程构成凯恩黑色风格的高潮,同时也引发我们对皮尔斯太太幻世浮生一场的深思。
一、母親的精神共生
凯恩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由此突出社会动荡带来的家庭动荡。皮尔斯太太因丈夫破产出轨与他离异,选择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凭借自制馅儿饼的好口碑,她孤注一掷,借助各种机缘,通过自我奋斗开启了餐饮事业,成为小有成就的女企业家。然而真正支撑她披荆斩棘的动力应属大女儿薇妲的“鞭策”。皮尔斯认为薇妲生而不凡,注定不会在平庸的生活中灰头土脸。因此她倾其所有为薇妲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面对女儿的矫揉造作她不仅不加教育反而纵容。病态的母爱贯穿薇妲的整个成长过程:让她接受最好的钢琴教育、满足其虚荣的上流社会梦、眼见女儿与自己的情人放肆调侃却不加管束……皮尔斯一再退让的前提建立在薇妲是她生育的女儿,每当听到别人对薇妲的赞美,她愉快地长出一口气,仿佛自己才是对方极力赞美的对象。
皮尔斯的行径符合共生幻觉的表现——一种精神上的共生投射:她混淆了自我和女儿作为不同个体的差别,硬生生地将女儿幻化成另一个自我。薇妲的虚荣实则就是她的虚荣,薇妲的成功,万人迷形象就是她内在的欲望。伊基提出“女儿必须实现母亲的愿望而不是自己的渴望”[2],剧情则是对此论断的化用。皮尔斯将虚荣的精神诉求寄生在薇妲身上,由此衍生出与传统母爱不同的畸形母爱。拉康认为“女人渴望成为欲望的对象”[3],皮尔斯作为一位单身母亲,虽也有男性的青睐和追求,但她的情欲更多还是倾注在薇妲身上。即是与纨绔子弟蒙蒂的幽会,都是建立在他能在自己和薇妲之间构建一个温馨和谐的相处之桥。此种畸形母爱即是欲望对象错位的表现。
二、女儿的厄勒克特拉式叛离
如果说母亲自始至终怀抱着共生幻想的话,那么女儿则经历了从共生幻想到完全分离的转变。薇妲类似原型分析中“塞妊”形象,并且其幼年时期也符合“恶童”的设定。她能够洞悉细节却装作天真不经意地提起以戳人痛处,嘲讽皮尔斯服务员身份被扇巴掌后,“她却短促地笑了一声,满不在乎地大声说:‘真是天下之大滑稽。”[4]成年后薇妲的言行举止更加放肆,她嘲讽母亲低下的身份,勒索敲诈富人,最后甚至抢夺了母亲的未婚夫。文中对薇妲最精辟的洞见要属音乐家特拉维索对其的形容:“她就是一条蛇,一个居心不良的女人,一个花腔女高音。”[5]正是这样蛇蝎般的女儿,早期一直潜伏着,为了金钱和有朝一日的出离和母亲共生在一起。
薇妲的共生不是精神上的而是物质上的,因而她能够保持主体的独立性和疏离性。对母亲的讨好和娇俏的卖弄都是为了使其为自己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和与上流社会接触的平台。当皮尔斯将自己幻想成她的一部分并丧失自我主体性时,薇妲却始终能保持自我。一旦有了丰满的羽翼,她就会想方设法地离开母亲,离开家庭,跃入更高一层的平台,将皮尔斯狠狠地抛诸脑后。
伊基提到共生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她们会产生对母亲的愤怒,并用疏离来伤害母亲。”[6]这种女儿的叛离和对母亲的仇视也通常被归在“厄勒克特拉”主题中。在整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薇妲对皮尔斯一丝的真情实意,她表露出的“温情”是虚假的,有目的性的。这源自她对母亲和父亲的未婚先孕的鄙视,也厌恶母亲在父亲破产后的抛弃行为。在她看来,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足够的钱,我就能离开你这个笨头笨脑、闷闷不乐的可怜虫。”[7]薇妲冷酷、虚荣的天性固然导致其人物性格走向,然而皮尔斯的一味纵容和教育缺失对其“恶女”形象的造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早期父亲角色的缺失也使得薇妲更加仇视皮尔斯。
三、自卑式的自我价值确立
《幻世浮生》讲诉新时代女性面对“女人”和“母亲”双重身份的两难,特别是她如何获取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又如何处理与女儿的关系。马科斯·扎菲罗普洛斯在《女人与母亲》一书中探讨了女性在文明社会、社会团体中的位置,他反对弗洛伊德 “在所有人为构造的团体机构中,比如教堂和军队,其中女性作为性对象完全没有任何位置”[8]的表述,反而认为“女性有时候是坚定团体的建造者。”[9]皮尔斯虽然自始至终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但她建立起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劳动小团体,只是她的劳动团体与薇妲追求的闲适上流阶层格格不入,这才导致她们的无法相容。皮尔斯的悲剧之一就在于她妄图将劳动所得的金钱作为共生幻想的工具,获取薇妲的认可,然而这其实也是幻想的一部分,也是她对自我价值质疑的表现。作为无一技之长的家庭主妇,她要靠劳动获取社会地位,这与当时游手好闲的上流社会形成强烈对比,连她的情人蒙蒂也说只有下层人才工作,由此加深了皮尔斯内在的自卑感。由此可以说明皮尔斯行为背后的内在驱动力:“共生幻想是一种极强的自恋性联结,它保护着母亲脆弱的自我价值感。”[10]薇妲一切出格的举动正好可以使皮尔斯的自卑有所遁形,因此无论薇妲的举动多么过分,皮尔斯都要疯狂地将她圈置在身边。就像普鲁斯特在其早期作品中描写的一位母亲,“只要你需要我,我会倾尽所有对你好;一旦你要离开我,那我就会恨你。”[11]这也是为什么当皮尔斯得知薇妲离开自己后居然混得风生水起,她的心仿佛沉入了冰窖的原因。
通过对《幻世浮生》母女关系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小说悲剧的内在因素。亲密的亲子关系固然是联结家庭的重要纽带,然而过于窒息、丧失自我主体性的亲密“寄生”却有可能引发伦理悲剧。由此出发分析文本,对于指导现实生活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注释:
[1](荷)伊基·弗洛伊德. 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4.P3.
[2](荷)伊基·弗洛伊德. 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4.P3.
[3](法)马科斯·扎菲罗普洛斯.女人与母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1.P1.
[4](美)詹姆斯·M·凯恩.幻世浮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P40.
[5](美)詹姆斯·M·凯恩.幻世浮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P278.
[6](荷)伊基·弗洛伊德. 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4. P4.
[7](美)詹姆斯·M·凯恩.幻世浮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 P352.
[8]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巴黎:PUF.1991.P80.
[9](法)马科斯·扎菲罗普洛斯.女人与母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1. P74.
[10](荷) 伊基·弗洛伊德. 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4. P16.
[11]Proust, M. Jean Santeuil.‘goodnight kiss episode P13.
参考文献:
[1]廉菲. 追寻彩虹的漫长之旅--以拉康心理分析理论解读《幻世浮生》女主人公的自我建构失败.北京交通大学. I712.074.2014.
[2](法)马科斯·扎菲罗普洛斯.女人与母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1.
[3]蘇往.影像难以讲述的“幻世浮生”.文艺报. 2013.09.18(008).
[4](荷)伊基·弗洛伊德.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4.
[5](美)詹姆斯·M·凯恩.幻世浮生.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