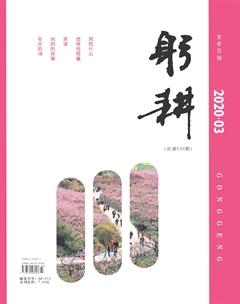乡村匠人(外一篇)
翟传海

从前,乡村流动着的锻磨匠、剃头匠是乡村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他们就如同大姑娘小媳妇们花裙子的走水,有它不见得多些啥,没了它,那裙子就显得特别的平淡和空洞;他们又如同日常饭菜中的佐料,有它不见得多些啥,没有它,那饭菜就显得特别的寡淡和无味。
锻磨匠
先前,人们吃的五谷杂粮都要靠石磨来研磨。石磨是石匠用坚硬的石料凿成的,圆形,上下两片。上下片各凿有凸出和凹陷的齿槽。下片固定在磨盘上中心有轴,上片中心有轴套合在下片上,旁边有两个圆形的磨眼。粮食倒在磨顶,驴拉或人推转动上片,粮食就从磨眼里流进两片之间,被一圈圈旋转的凸凹齿槽磨碎。长期使用,石磨的齿槽就会秃损变饨,磨钝了磨粮的效率也就变低了。所以,经常需要请专业的锻磨匠来打凿磨齿,清洗龙口(从中间的磨眼向四周旋送麦粒的沟槽)——这就叫锻磨。
锻磨匠是石匠的一支,技术要比一般的石匠更专业一些。他们的行头很简单:一条不甚讲究但很结实的布褡裢,一端装一把短把铁锤,一端装几根半尺靠下长短不一的小铁凿。出门做活,把布褡裢往肩上一搭,还能前抄手呢。
过去,用来磨粮食的大石磨只有生产队里才有(少数户家也有磨芝麻、磨豆腐的“小花磨”),而且多是置放在村里的队长家。所以,锻磨匠做活一般是“走村”不“串户”。他们走进村子径直走到队长家,进院却不“登堂入室”直接拐进磨坊。没有招待也无须交代,取下肩上的布褡裢掏出铁锤、铁凿,在磨坊里随便找个空地一放,卸下磨杠和磨扇,或蹲或立,一手执錾一手拿锤“叮当叮当”就开工了。虽然“铣牙”(把凹槽打深,把凸齿隆起)和“颠牙”(把铣锋利的磨牙打磨光滑)都是在原有的齿槽间“走老路”,那也得平心静气,全神贯注。一不留神就要打出豁牙来的,打出豁牙粮食就难磨碎,甚至磨出的粮食还会有囫囵个。所以,他们做活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耐着性子,一下一个白印子,而后再把许许多多的白印子串在一起。
我记事时,到我们庄上锻磨的是一个姓余的锻磨匠,他可能排行十八,大家都叫他余十八儿,而我们一群孩童们就直叫他“驴屎巴儿”。他有多大年纪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听说他的父母过世很早,就留他一个人一直娶不下媳妇。直到后来才领回一个傻女人,傻女人给他添了一个男孩也不怎么聪明。他出门做活就把那男孩带在身边,我见他的时候也有七八岁了,人们说“你唱个歌吧”,他就灰脸突噜,涎水一把鼻涕一把地仰起脸来两句。大家说“你翻个跟头”,他便就地打起滚来。孩子他爹也跟着没脾气,人家问他“吃干饭(蒸米饭)不吃?”,他说“干饭太烤脸”!人家问他“想吃炒鸡蛋不?”,他又说“炒鸡蛋一股鸡屎气儿!”直到我长大了,才感觉他说的是一种无奈。
后来,那个叫“余十八儿”的锻磨匠就死了。听说,他死后他所在的生产队,要给他的傻女人找个家儿,条件是:倒贴一头驴!
剃头匠
人们说到一厢情愿的时候,总是打比方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也确实,过去理发的大多要走村串户,所以他们经常肩着一副小挑子。挑子的一头是一副很是夯实(结实耐用)的大马扎,凳腿间却打造成了带抽屉的小柜子。柜子上边的抽屉可以放置刀、剪、推子(专用的理发剪)和木梳之类的理发工具。下边小柜子里除了放置理发用的围布之外,还可以藏放理发师傅的一些个人物什。挑子的另一头就是个简单的小炉灶,灶膛的木柴总是半着不灭地燃着,烧燎得黑黢黢的铁桶里断断续续地飘着热气,上面反扣着一个大沿黄铜盆,单等顾客随到随理。说一个人讲的故事或写的文章太短,就会说:剃头扁担——不长。那是因为剃头的挑子总是落着地,所以用短一点的扁担两手便于把持,以免走起路来磕碰。
以往乡村理发多是“葫芦瓢(光头)”,小孩们顶多留个木梳背(前顶留一木梳宽的头发),所以管理发叫剃头,从事剃头的人就叫剃头匠。那时剃头的都是剃“包头”,所谓“包头”,就是村里人的头发由一个剃头匠包下来,专门由他到村上来剃。“包头”一则是省钱,二是不必急着付钱(其实是按男人的人头收点粮食),快到年底时一起给,一时没给上的也可以来年一起算。
他们进得村来并不吆喝,总是在村头树荫下、牛棚边甚或是老粪场上等,固定的地方摆好架势。等来人坐定了,剃头匠人便磕去烟袋的烟灰,习惯性地甩开围布不紧不慢给来者围上。而后翻开扣在炉灶上的铜盆,舀几瓢半温不热的热水,伸手试试便按下剃头人倔强的脑袋撩洗起来。头还没擦干,他便手执剃刀,在炉灶边上挂着的、黑明黑明的辟刀布上“噌噌”地来几下。而后再次按着剃头人倔强的脑袋,只听得头顶“嚓嚓”几声响过,一簇簇湿漉漉的头发便应声撒落一地。头顶剃光了,刀子开始在脸上游刃有余地、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地扫荡起来。脸庞和嘴唇周边的胡子消灭了,躲在耳朵周围的一些散兵游勇也不放过。这就是天下头等大事,世间顶上功夫啊!
他们虽然很是古板,总是用着那套老掉牙的工具,理出的总是那种永远过了时的发型,有时还会给人们光秃秃的脑袋上弄出几道血印子,但憨厚的乡民们对他们总是念念不忘的!
长在心头的两棵树
数十年来,我的心头一直长着两棵树,一棵是黄楝树,另一棵是皂角树。我的家乡在八百里伏牛山南麓,东有“杏花山猿人”遗址,西有楚长城残垣断壁。村庄的身后,是一座渐次升高的大山——“神仙路”,左右各有一条长长的小山岭,总的感觉好似一张大圈椅,又如母亲的怀抱。
我的家紧挨着“圈椅”的右臂,一出门就到了村口黄楝树下。那棵黄楝树,因生长在麻骨石山岭的末端,常年如贫苦的母亲般贫病交加,瘦骨嶙峋。我记事时那棵黄楝树已有碗口粗,直到我十六七岁离家外出,它依然那般粗细。通身约一人多高,整个主干虬曲古怪,树皮暗而粗糙。其上枝丫不过三叉,幼枝灰而细短,叶似椿小而稀疏。花小无瓣,几乎不见,果似花椒,夏青冬红,可以入药,可以炼油,通体干不直、枝不繁、叶不茂,叫人入眼一看,就有一种身材弱小、病态连连、可怜兮兮的感觉。
它之所以身材弱小、病态连连、可怜兮兮,不仅因为它孤孤单单,重要的是它生长在麻骨石山岭的末端、全村人进出村子的路边上。不仅石地坚硬贫瘠、雨水难存,而且還要饱受村里人畜的踩踏和摇、拱、啃、砍、咬。村里人收工后多是把种地用的镢、锄、犁、耙等农具,一股脑地挂在它的枝杈上,把卸了套的牛、马、驴等大牲畜拴在它的身子上,常常遭受着撞、扯、拽、咬、摇之苦。我还亲眼看着年年春节,整个村子的猪羊都要用大大的铁钩,挂在它的枝杈上开膛破腹,猛砍细割。
因那棵黄楝树紧邻我的家,整个童年及至少年间,我曾无数次在它的身上爬上爬下。寂寞时骑着它瞧看外面的景致儿,躲避父母打骂时偎依着它哭泣,饥肠辘辘时靠着它盼望着母亲的归来,可以说是我儿时最亲密的伙伴。
虽然它没有父母及其同伴的呵护与呼应,虽然它常年得不到近在咫尺的井水、潭水及其老粪场粪土的滋养,但数十年中它始终艰苦卓绝地生长着,并守护着我们的村庄,为进出村庄的人们指路、为收工的父老高挂农具提供支架,为等待家人归来的爷奶、子孙提供依靠,也为牛、马、驴提供小憩之地,为村民杀猪宰羊提供方便!
然而,那棵黄楝树究竟生于何时,甚至殁于哪年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提笔前才电话询问老家年近七十的家兄,家兄说:“我们记事时它已有胳膊粗了。家后坡半坡处曾有两棵一搂粗的大黄楝树。它们的种子飘落到了坡头石头旮旯里,才长出那棵小树苗。那两棵大黄楝树,后来被砍走了。”哦,原来亲亲的伙伴还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
“你说的那棵黄楝树,早在十几年前年就被庄上人借故拔掉了。庄里有几户人早就嫌它长在路边既无用又碍事了,苦于害怕几十年的老树有灵气不敢砍放。2000年207国道改道,那几户人方才借助推土机将其推倒。”唉,让我魂牵梦绕的黄楝树啊,只有永久地长在我的心头了!
那棵皂角树是生长在我们村庄,左边山岭将尽处猛然隆起的土包上的。它很粗壮,也很漂亮。树高擎天,整体虬枝铮铮,叶色苍翠,混如华盖。树的底部有一排排隆起的疙瘩,像极了虬龙潜行;身子圆圆鼓鼓,一如弥勒佛的大肚子;树身向上,干分股,股分杈,枝长杈,杈生叶。叶上闪着油光,细枝绿叶,浓而不密,翠而不暗,秀而不苍,娇而不媚。
每到立夏时分,它盛开出极小的五瓣黄花,密密匝匝,香气四溢。到了盛夏,锯齿形的绿叶下面就会缀满一挂挂筷子长、麦镰宽的皂荚儿。微风吹过,形如刀鞘的皂角板儿哗哗作响,一如一挂巨大的风铃。
皂角树枝杈间长有许多钉子一样的大硬刺,人们说它是在自我保护。这是树木中为数不多的,是其他枝叶任人玩赏攀折的花草、树木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村庄里树木虽然繁多,但皂角树却是唯一的一棵,是村上树木界的鲁殿灵光。它在那里生长了多少年,村里人谁也说不清。奶奶在世时说:“我奶奶说‘我嫁过来时它就长在那了!”
皂角是洗涤剂的天然原料,是肥皂的祖先。皂角树,因其果实而取名,又名“皂荚”。 属于落叶乔木,豆科植物,雌雄异株,雌树结荚。皂荚还是上等中药,能消积、化食、开胃,治疗便秘效果更佳;皂角刺、树皮可祛痰;皂荚里的豆豆更好,鼻孔不通时,弄颗豆子放在鼻孔里,很快就喷嚏连连了。
贫困的岁月中,皂角不仅是人们洗涤衣物、冲洗头发的尤物,也是村人祈福驱灾的寄托。一挂挂皂荚象征着多子多孙,是男婚女嫁的吉祥物。谁家姑娘出嫁,都少不了在箱子或被褥中放上一些皂角。谁家小孩有了病灾,就会在皂荚树枝头绑上一根红布条儿。红布条儿在风中一飘动,全村便充满了吉祥。
洗衣时将皂角放在衣服内,再用棒槌敲打。不一会儿衣服上就会泛起许多白色的泡沫。在水里一冲洗,把衣服晾晒在河边干干净净的石头、野草上。晾晒后的衣物,就藏满了太阳的清香。母亲在清澈的河水中涮洗时,捣碎皂荚弄出里面的皂角籽,剥下皂角籽上的白皮在河水中一涮,直接塞进我们的嘴里。那感觉美极了:有点像牛筋,有点像脆肠。筋筋的久嚼不烂,即充饥又解馋。
村头的皂角树和黄楝树,一如握在“母亲”两手中的两束花草,既呵护着怀抱里的亲人、召唤着离家的游子,也欢迎着远到的客人。它们是村庄的坐標,是老家的灯塔。从小到大,从大到老,每次回家,远远地望到它,心中总是油然升起一种久违的亲切和美妙激动。
村头的皂角树和黄楝树哟,你将永远长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