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与莫言小说的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建
王西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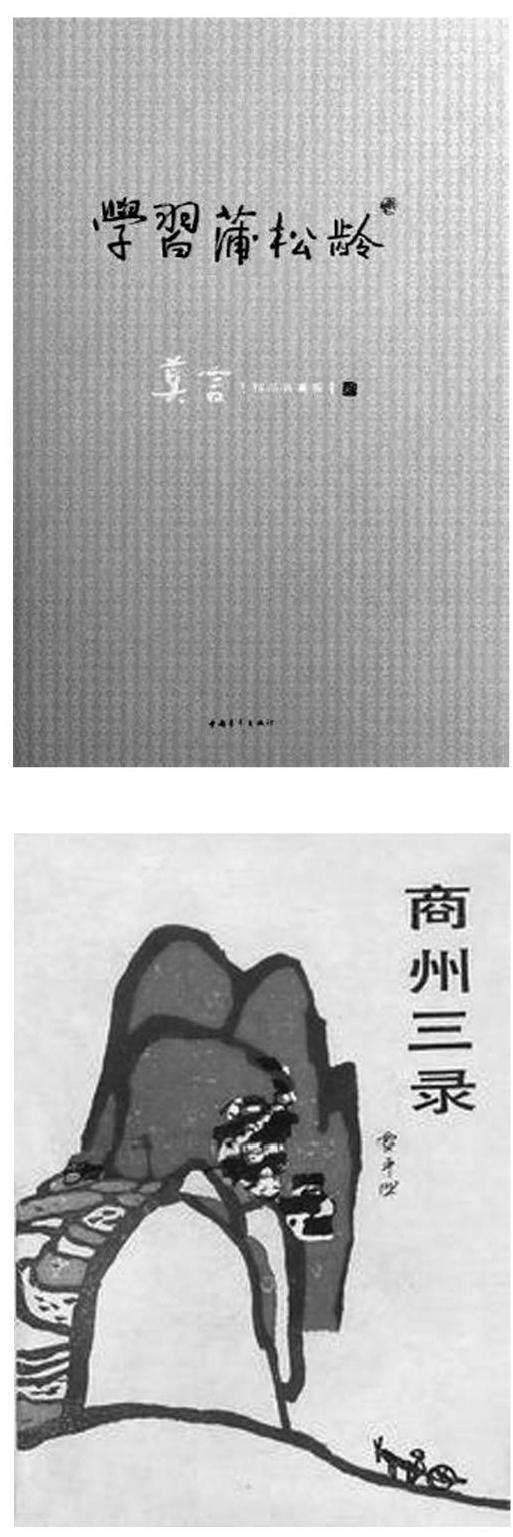
同是出身乡村、客居城市的作家,莫言和贾平凹的文学活动轨迹和文学思想的变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們是同代人,经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政治变革和历史变迁,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户籍身份和文化身份迁移;他们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并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并批判了当代中国社会及人文的“病”与“变”;他们不断努力探索、参与开创并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代表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两个地域文化作家群——“鲁军”和“陕军”;他们笔耕不辍、高产多产,不断自我超越、不断自我更新作品的叙事艺术和审美风格,多次引起批评热潮,均多次获得国内外诸多文学大奖,作品均被译成多国文字,获得了世界级的文学声誉;在过去近40年间,他们通过众多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有深度的反思与批判,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个性化思考,记录了大变革时代的民生、民风、民情、民瘼,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变革的审美记录者。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和贾平凹都有很强的叙事创新自觉,均不断通过叙事探索与创新为读者奉献了深具地域文化色彩和中国气派却又个性鲜明的文学作品。我们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向西方文学阅读期待展现了中国作家在叙事艺术和现实关怀层面上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与高度,通过独特的“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与历史”,“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①;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也具有相似的艺术特质:在叙事上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立足自己熟悉的“商州山地”和“西京城”,不遗余力地表现着山民与市民的喜怒哀乐和时代变迁,“从20世纪80年代始,就执着地进行着中国式文学艺术叙事的探寻”②,“以自己独具的文学艺术天赋,创造出融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普遍性人文精神为一体的、独树一帜的文学世界”③。
作为从乡村到城市的“文化迁移者”,莫言和贾平凹都以生养自己的故乡及其文化深蕴作为其文学叙事的空间蓝本和文化底本,不断结撰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和鲜明个人风格的“乡村/城市故事”,分别营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享誉世界文坛的“高密东北乡”和“商州山地”。
一、莫言与贾平凹小说叙事的
文化母本与审美“血地”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阐述了影响艺术家产生及其艺术风格和美学气质形成的三种决定性因素:种族、环境和时代。在比较分析莫言与贾平凹小说艺术风格(本文的讨论集中在叙事美学风格上)的过程中,因其所属种族与所处时代一致,我们重点关注“环境”——物质生存环境和故乡文化母本对作家创作风格形成的影响。
从作家出生地的地理区位和所属的文化样态来看,莫言出生长大的山东高密县境属古齐国故地,是兵家文化的发祥地,兵家文化崇尚大开大合、雄奇壮丽,尚谋略、不拘细节、神秘“诡诈”;齐地近海,在文化上具有海洋文明开放、大气、奇伟、神秘的鲜明特征。齐地的民俗和民间文艺因此充满“奇思怪想,天马行空,取材随意,情趣盎然”④,齐人民风“刚健不屈,侠肝义胆,豪放旷达”⑤,齐地民间文学资源丰富,民间故事多涉神鬼狐怪,想象丰富大胆,寓民间正义于奇谭怪事之中,产生了像《聊斋志异》这样志异志怪、神秘奇幻、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巨著。莫言有一本题为《学习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学习蒲松龄》《奇遇》《夜渔》《良医》《翱翔》《嗅味族》和《草鞋窨子》等篇什颇具志异色彩,无疑是其追忆童年“耳朵阅读”经历和向故乡文学大师蒲松龄学习、致敬的作品。此外,莫言小说还有多个故事和人物都是以董均伦和江源收集整理的山东民间故事集《聊斋汊子》和《聊斋汊子续集》中的故事和人物为故事母本和人物原型的,这些故事多流传于齐地,是齐地志异文化的历史遗存。因此,在谈及幼年在故乡听到的民间故事对其创作的影响时,莫言说:“这些故事一类是妖魔鬼怪,一类是奇人奇事。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故乡最丰厚的馈赠。故乡的传说和故事,应该属于文化的范畴,这种非典籍文化,正是民族的独特气质和禀赋的摇篮,也是作家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⑥可以说,莫言小说艺术风格中个性鲜明的灵气、鬼气和“匪气”正是他深受故乡齐地文化和民间文艺影响的结果。
从1955年出生到1976年参军离开高密东北乡,莫言长达有21年的农村生活经验,这段时间是莫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成型期,也是其文艺观初步形成的阶段,莫言最早的、最重要的文学教育也主要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关于故乡风物和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莫言曾说过:“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⑦。莫言在其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总结了“小说家与故乡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小说家创造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故乡的关系”,⑧指出“故乡是‘血地”⑨。齐地旷达的民风、奇彩的民俗、志异志怪的民间文艺风气都是莫言生长、浸淫其间的文化和文学教育环境,是莫言文学成长的“文化血地”。
莫言小说中的种种创新与陌生化追求,贯穿其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故事叙述方式、叙述者的身份、语言风格和意象营造等各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多变性和复合性,不管评论界将其界定为作家有意识的锐意创新、努力求变,还是将其评价为借鉴模仿、先锋作怪,甚至是将其贬斥为乱耍花枪、故弄玄虚,但谁也无法否认莫言作品本身充盈丰沛的生气、灵气、大气和鬼气,而这“四气”恰就是齐文化的精气所在。就莫言小说已经表现出的审美气质和文化样态来看,开放大气的海洋文明影响之下的齐地齐风齐文化孕育了莫言小说的以下几种颇具齐地文艺风采的文学气质和美学特征:众声喧哗的杂语交响、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煞有介事的叙事腔调、天马行空的意象交织、泥沙俱下的语言浊流、深沉刻薄的思想能力、亲切真诚的民间立场和模糊朦胧的文本表意。
贾平凹出生在秦巴山腹地的古商州——商洛市丹凤县棣花古镇,商州地处秦岭南坡,是秦时卫鞅的封地、商山四皓⑩的隐居地。北有百里秦岭苍茫大山使之与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西安)相阻隔,四围皆山,在地理上处于南北交界处,却是偏南方的气候,山水灵秀。
与莫言的父辈世代务农不同,贾平凹出生在农村读书人家庭,自述其父是中学教师,“对我是寄了很大的希望的,只说我会上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去省城上大学,成为贾家荣宗耀祖的人物”11。贾平凹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推荐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接受了相对系统的文学教育,毕业后进入文学杂志社任编辑。贾平凹上大学之前即开始文学创作,1974年就有作品发表,其早年作品基本都是以商州山地的风土人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1978年,贾平凹凭借表现农村新人新气象的《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年不及三十,名满天下。
贾平凹是一个讷言敏行的作家,他勤于思也勤于作,始终关注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之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始终坚持通过体察并描写百姓生活的细微处和普通人内心深处的灵魂震颤来展现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对于如何表现时代,又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民生样态来表现社会变迁,贾平凹在其早期的创作中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在是表现“城”还是反映“乡”、是反思“传统”还是批评“现代”之间表现出了游移不决。“1983年初,贾平凹在遇到创作的大苦闷时,产生了一个大行动,一过春节,他就重返商洛。……思想上经过苦闷之后的深刻反省,行动上领略商州的大山大河,感受时代迁转流动的风云,使贾平凹创作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越。……他不但更深入地认识了商州,也吃惊地发现了自己;不但找寻到自己最适宜的描写地域,也从商州民俗向中国文化系连,摸出了同商州世界相应合的美学精神”12。此时贾平凹在创作上已经初有成就,八十年代初的这次“回归商州”其实是他在文学审美精神上的向“故乡文化”的一次回望与回归,是他在有了城市生活经验之后反观“故乡”、重新发现“故乡”,是一种“还乡书写”,他从此即在很长的一个时段内坚持写“商州故事”,以“商州人事”作为其文学创作的文化資源和主要表现对象。这与莫言自从在《白狗秋千架》中首次使用“高密东北乡”作为其叙事空间来铺陈“故乡”故事后就将其绝大多数小说的叙事空间设置为“高密东北乡”的做法是相似的13,与当时“寻根文学”的主潮是合拍的,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还乡书写”也是一脉相承的。贾平凹在这次回归之后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商州三录》《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商州》等,都明显着力于展现商州山地文化的魅力,在文风和格调上也明显倾向于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散文和笔记小说的笔法,追求简洁、雅致,尚白描,这种文风是与贾平凹“回归商州”期间的阅读经验紧密相关的,“在此之前他阅读过各方面的杂书,熟悉了中国古籍中洒脱简括富于神韵的叙写文字,这次他每到一县,先阅读县志,县志是一种地域史,对该县辖区的地理、历史、民俗、人物都进行纵的和横的大扫描。这种方志文体的全局眼光,质实而又通脱自由的描述,给贾平凹创造新文体以极大的启发,正应合了他俯瞰地、历史化地表现商州的形式需要”14。我们不难推断,阅读这些由商州历代士人编撰的地方史志,无疑会让贾平凹在文化精神、审美气质和语言风格上更深刻地体认“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隐逸文化”的精髓,自觉地承继这种“故乡文化”并以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母本”,同时以这种自己天然携带的地域文化基因去对接、“系连”中国文化,从而可以“较多地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到《浮生六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承的古典艺术美学精神”15。因此可以说,费秉勋先生所谓的贾平凹“摸出了同商州世界相应合的美学精神”,无疑是指贾平凹对于“商州山地文化”与“商山隐逸文化”的发现与体认,而贾平凹对“商州”的发现,其实就是对其个人审美气质的发现与自我强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化文学创作风格。
早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对莫言和贾平凹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莫、贾两位都曾多次自报,在《变》和《我是农民》中也各有详述,无需赘引。在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文学成长过程中,都有多次“还乡”经历,他们出身乡村,客居城市,每次回乡都是一次“精神还乡”。正是在一次次的“还乡”之旅中,他们不断对比着“城”与“乡”的差别,尤其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大潮中,他们都在认真思考、寻找着文学创作的突破口和叙事展开的“文化场”,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生长其间的“故乡”“故土”。在试笔成功之后,他们都不断加大对“故乡”的书写力度和挖掘深度,不断开疆拓土,但是两位作家努力的方向和效果却又大不相同。
二、作为叙事场的“高密东北乡”
和“商州山地”
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关于“故乡”,莫言更多地强调其在早年农村生活中所经受的苦难、孤独与饥饿,在对待“故乡”的态度上,他是爱恨交织的。因此,在其“故乡书写”中,莫言并没有对“高密东北乡”表现出太多的温情和回望时的怀念与向往,他没有固守“高密东北乡”的实在地域,而是不断对其时空外延进行拓展,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涵盖一切事件、包罗所有人物、容纳各种情绪的叙事场。贾平凹对待“故乡”的态度则是前后变化的,其早期作品多以温婉唯美的笔调摹写故乡人事、民风民俗和自然山水,是学习孙犁《白洋淀纪事》风格而对故乡山水田园牧歌般赞美式的回望,在赞美的弦歌之外别有空灵高蹈的庄禅味;后期则反思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书写被现代文明熏染了的乡村与自然的种种不美好与无奈。作为叙事场的故乡“商州”的时空外延基本上没有得到拓展,故乡故土故人故事都是作家“还乡”时的观察所得,“商州”一直都是贾平凹的实在“故乡”商州,其间的人事,在文化外形和精神内质上都具有典型的商州特色,全不似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的山水、风情、人物和故事,多是作家从外在于“故乡”的“别处”挪移而来,如江海纳百川而包罗万象。“莫言地理建构的历史跨度很大,自清末以来至今天一百多年历史的重大事件、细枝末节、野史狐禅尽收笔底,这与鲁迅、沈从文他们从一己经验出发的、对于故乡的现时进行描写是不一样的,也因此他的作品多长江大河式的长篇巨卷,这反映出作家想以自己建构的一小块地理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缩影、历史寓言的野心”16。实际上,莫言与鲁迅、沈从文在“发现故乡”之后“重塑故乡”上的差异,也正是他与贾平凹之间“故乡书写”的差异。
关于“高密东北乡”这一叙事空间,莫言自己曾做过这样的表述:“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17这段话语大致可作如下解读:其一,莫言清醒地认识到了“地理故乡”与“文学故乡”的差异,“地理故乡”是父母之邦,是作家个体生命的“血地”,而“文学故乡”则是对“地理故乡”的诗意想象与审美擴张,是无限开放的,可以不断生成新的时空意义,是作家“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历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18以展开审美想象的“文化酵母”,是作家文学生命的“文化血地”;其二,莫言借助“高密东北乡”所进行的诸种审美想象的深层目的是表现中国生活,讲述中国故事,并使小说成为“人类情绪的容器”,以满足作家代表“人类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古老的雄心”19;其三,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经验的基础上,莫言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设定了高层次的、与世界文学对话接轨的目标,期待其创作可以获得国内外读者的普遍认同和精神共鸣。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对他这种叙事空间营建努力的最高奖励和认可。
贾平凹书写“商州山地”的目的,不像莫言那样试图将其营造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叙事场,而是出于对故乡故土人文的亲近和讲述故事的情感便利,尽管“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的笔下也有同样的叙事情感功能。贾平凹书写“商州山地”,有着文学和审美之外的现实目的:“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20对比而言,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是作为文学想象的“故事”的发生地、叙事展开的背景和空间场域被书写的,并非是莫言小说创作的最高目的和最终指向;在贾平凹笔下,尤其在其数量众多的“商州小说”和散文里,“商州”就是作者书写的对象和目的,是其文学世界的中心意象。因此可以说,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在“实在”地理区域基础上的想象性审美生成,是一个被作家想象出来的、美学意义上的“故乡”——“文学故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更多的是作者对“商州”现实世界审美过滤后的艺术再现,是一个经过作家艺术加工的现实“故乡”的审美翻版,是一个“文学化的故乡”。
在莫言的“想象故乡”或“故乡想象”叙事中,总有一个显在的、作为故事人物或叙事者的“我”或“莫言”存在着。莫言在其小说文本世界里结撰了很多“虚构家族传奇”故事,大量使用第一人称“我”和“类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复合人称视角,如“我爷爷”“我奶奶”等)来讲述故事。作者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无疑是放置这一类故事和叙事人称的最佳场域。这类叙事人称视角的大量使用,是莫言为了增强其“故乡叙事”的“我在感”和现场感,为了获得叙事语境和情感上的参与感和亲近感,是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事空间的完美结合。在莫言小说积极而有效的叙事探索中,叙事视角的变化所带来的叙事美学上的创新是极具有文本试验意义的,莫言在叙事上耍的这些“花枪”无疑是他对自己生长其间的齐地文学“志异志怪”的陌生化审美传统和兵家文化“诡/诈”的言行方式的继承与发扬。在贾平凹的“故乡书写”或“书写故乡”叙事中总有一个隐在的“我”,这个“我”藏而不露、秘不示人,这与其小说叙事多采用全能叙事视角有关。因其是全能叙事视角,作者不以第一人称“我”去参与故事或叙述故事,而是以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来讲述“故乡”“故事”,但因其所叙述的“故乡”“故事”只能是作者的“故乡”“故事”,那么这个隐在的叙事者便与作者高度重合了。作者“隐在”却又无处不在,故乡、故人、故事、故情都在其笔下自然地、原生态地呈现,贾平凹对故事叙述节奏的把控力很强,开合有度、收放自如,这是全能叙事的优点,也无疑是与贾平凹深受“商州山地文化”自闭内敛和“商山隐逸文化”中“隐”与“藏”的精神追求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是贾氏对明清小说叙事传统——全能叙事、全面掌控、舒缓自如——的继承与发扬。
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情感态度基本上保持着“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那种爱恨交织、二元对立的情绪,叙事的情感维度基本上是连贯的、完整的;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赋形完全因时因地制宜,“高密东北乡”时而是水草丰美人迹罕至的蛮荒水洼子,时而是土匪横行好汉啸聚的青纱帐,是晚清的辖地、民国的小村、新中国的县城,时而是外族入侵时的“难所”,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屠宰村”,始终变幻不居,边界模糊却又不断扩张而致包罗万象。贾平凹对城市与乡土的情感是自我矛盾、前后冲突的,在贾平凹的文学世界里并存着“商州山地”与“废都西京”两个分立的叙事空间。贾平凹早期的文学书写歌咏乡野之美,却也真心礼赞乡村与农民的现代化进步,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而在其中后期的乡村/城市叙事中,却又表现出对城市文明与市民文化的厌弃,以及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给植根于农耕文明的道德传统带来的冲击和乡民精神世界失序的焦虑与担忧。在贾平凹“城”与“乡”二元分立的叙事空间里,他的叙事情感是自我矛盾、自相对立的。相比而言,对于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传统)文明间的关系,贾平凹基本上将其处理为对立、对峙的关系,而莫言则基本上将其处理为对话、过渡或融合的关系。
我们再把两位作家对于“故乡”的书写放置到整个“乡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作一对照。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乡土”,莫不是士人诗人们笔下的“田园”“山林”和“怀乡”,我们可以称之为“田园叙事/怀乡抒情”。在这样的中国“乡土文学”背景下,我们可以见出莫言和贾平凹在“故乡叙事”空间营建上的异同: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莫言和贾平凹都在“故乡”找到了叙事场域和叙事激情,其叙事精神都深深植根于、汲力于故乡的文学精神和地域文化传统,并以天纵之才将其发扬,自成其惊泣鬼神的巨匠神气,在文学创新的同时,不断感受着时代的脉动,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情怀”;不同之处在于,莫言和贾平凹小说“故乡叙事”场域的时空外延不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想象的故乡”——一个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故乡”,贾平凹的“商州”是一个“实在的故乡”——一个“文学化的故乡”,尽管二者都是作家文学世界中的“故乡”,但它们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所占的权重不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作家精心营建的一个叙事场域,但却不是作家书写的中心和重点。贾平凹的“商州”先是作家倾力表现的对象,后来才又变成其“商州故事”的叙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