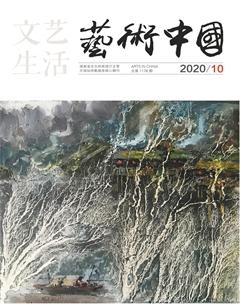华鬘的妙品
周游

谈及“扬州美女”,华鬘是不可忽略的。明末大画家陈洪绶《隐居十六观·缥香》是为华鬘画像。华鬘削肩,身材修长,柔若无骨,衣纹屈曲萦回,含蓄从容,透露着一种娇媚的气息,表现出超凡脱俗的风韵。
华鬘,姓胡(一说姓吴),本名净鬘,小名小宝,又名鬘华、净德,是陈洪绶侍妾。陈洪绶擅长人物、仕女、花鸟、草虫和山水画,被誉为“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张庚《国朝画徵录》)。华鬘长期跟随陈洪绶,自然获益匪浅,善画花草、虫鸟,而且还懂得佛学,能作佛像。因而,时人把陈洪绶和华鬘比作“东坡朝云”。朝云是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的侍妾王朝云,书画学苏氏,颇为雅致。
陈洪绶多才多艺,但是时乖命蹇,屡试不第,因而索性抛下书本到红楼去买欢逐笑,经常“酒劝扬州女,歌听吴市童”(陈洪绶《失题》),甚至“红楼宵宵复相寻”(陈洪绶《癸亥长安》),“非妇女在从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毛奇龄《陈老莲别传》)。“客有求画者,虽罄折至恭,勿与。至酒间召妓,辄自索笔墨,小夫稚子,无勿应也。”(朱彝尊《陈洪绶传》)
崇祯癸未(1643)秋日,陈洪绶路过扬州,邂逅华鬘,爱不释手,纳之为妾,留下了九首《桥头曲》,其中写道:“闻欢下扬州,扬州女儿好,如侬者几人,一一向侬道。”一天,陈洪绶携华鬘去扬州铁佛寺礼佛观光。铁佛寺规模宏大,前前后后掩映着一片高大、苍劲的枫林,其时正呈现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绚丽景色。陈洪绶触景生情,很想把它描绘下来。但那时他的右臂正患风湿痛而麻木,难以挥毫,遂让华鬘代为写生。华鬘凝视片刻,当即调朱研墨,胸有成竹地挥洒起来。不一会儿,一幅《丹枫图》便展现笔底。陈洪绶见着华鬘的生花妙笔,欣然悬之室内,并叹息道:“此扬州精华也。”当时,钱塘有个叫冯砚祥的名士,是陈洪绶的挚友,见到这幅《丹枫图》,还以为是陈洪绶的经意之作,因此特赠诗一首以赞,其中云:“三百年陈待诏来,调铅杀粉继前人。”陈洪绶见诗,也作了一首《自笑》诗,诗中的“文词妾想追前辈,画苑高徒望小妻”两句,即向冯砚祥道明了华鬘绘画的真相。由此可见,华鬘的画艺与陈洪绶的指授是分不开的。
陈洪绶娶华鬘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尽管父母已经谢世,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但他毕竟已有妻子儿女,华鬘如何面对他们?陈洪绶又如何协调他们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陈洪绶抱得美人归诸暨,立刻就像衣锦还乡的高官大款一样重修家祠。可惜,家祠修好不久就被人破坏了,不但没有光宗耀祖,就连祖传家业也被毁于一旦。陈洪绶携带华鬘离开家乡,前往绍兴,寄居青藤书屋。不久,陈洪绶听说崇祯皇帝自缢,“辄痛哭,逢人不作一语。姬人前问好,绶径执姬人手,跽地,复大哭。”(戴茂齐《茂齐日记》)面对国破家毁,陈洪绶像徐渭一样疯了,时而出家为僧,时而回家作客。华鬘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悉心相夫教子,持家有方,以至于陈洪绶“老去争书媚,情深怯妇娇”(陈洪绶《种蕉》)。由此可见,华鬘绝非凡人!
除了做好家务,华鬘还常与家人展阅古今名画,从中汲取艺术涵养,并把自己的画艺悉心传授给儿女陈道蕴(一说是陈洪绶与来氏所生)。陈道蕴自幼即喜绘画,华鬘便鼓励她刻苦努力,继承家法。陈道蕴起初临摹父母的作品,数年下来,几乎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于是,她自命得意,挑选了几幅满意之作请母亲教正。华鬘浏览过后,并没有夸赞,而是语重心长地说:“你父亲小时候上杭州府临仿宋代画家李公麟的七十二贤画像石刻,闭门画了十天,临出一个副本,别人都认为他临得很像。可他听了却一言不发,又照样临了一体,别人说‘这回临得不像了。他这才真正高兴起来。因为他在學习李公麟画法的基础上,又摆脱了李公麟的窠臼,形成了自己的面目,而你现在怎么能停留、满足于这个‘像字呢?”听了母亲的教训,陈道蕴深以为然。于是她便开始融冶古今,锐意创新,后来也终于以诗、画驰名江浙。她精于翎毛、花卉、人物画,尤喜写竹,“晴箨新篁,洒脱出神”(《宣统诸暨县志》)。
华鬘的花鸟、草虫画在明末清初画苑中有着较高的声誉,清代文学家王士祯称其绘画“皆入妙品”(《池北偶谈》)。遗憾的是,华鬘传世作品仅有与陈洪绶合作的《山水梅花合册》(该画册曾由清代书画篆刻家文鼎收藏,后来辗转到近代名医张骧云手中,现藏苏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