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尾巴
沈书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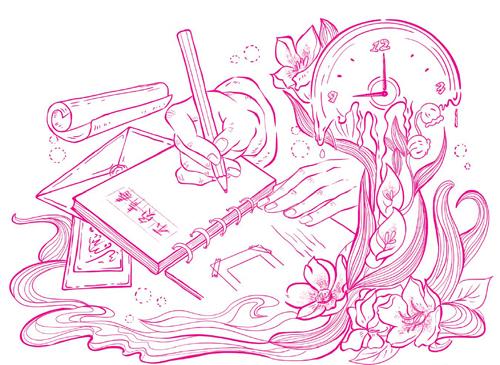


高考前一个多月,班上的气氛明显放松了。班主任不再管我们是否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才下自习,老师们也不再逮着每一个突然空下来的晚自习,拿着卷子跑过来说“这节课没有老师上,我们来讲讲我们的卷子”。所有课都早已上完,我们每天上课的内容只是做卷子、讲卷子。一切皆按部就班,但在那有条不紊又暗暗压抑的紧张中,一根弦竟自己奏起轻轻的歌来了。
同学们开始互相写留言本,赠送照片——在2002年这样如今想起来已十分久远的年份,手机还远未流行到县城的高中,我们的告别仪式仍十分古老,保持联系基本靠留下家里的地址,而想让同学能在想你时有所寄托,自然就是送他一张照片。学校门口文具店卖起花花绿绿的留言本,同学几乎人手一份。这本子印得朦朦胧胧,里面每一页都有些固定的栏目,后面画好了横线,姓名、地址、电话,这些都还好——虽然很多人家里并没有安装电话——此外却还有些身高、血型、星座甚至偶像要人填写。大概是从香港那边传来的风气,本意是彰显时髦,流传到僻地,却兀地有了些浮浅意味。好像一个过于活泼快乐的城里人,在愁苦的乡下人面前,总显得不合时宜。同学因此都不填这些,把横线空在那里,只去写下面几道长横线。
留言本的缺点在此显现无疑,因为知道这本本子是要给全班人写的,大家且都热衷于翻看别人写了什么,因此除非是最后写的那个,自己写的都会被后面的人看到。隐秘的话是无法说了——本来就未必有勇气开口——关系近的同性之间,想多写几句,几行就用完了,翻到下一页,已是新的姓名、地址、电话,不好意思再费一张纸,也就匆匆打住。同学平常都忙着做题、听课,课间就趴在桌上补觉,除了座位离得近或是一个宿舍的,实在很少有十分好的交情。留言本的可看之处也就寥寥,大多是回首这三年或两年(文理分科之后同班)的同学之情,感到不舍,接着便是祝福,因为连着后面便是那影响我们一生的大考,以及各自的奔赴前程,说的都是些大而土俗的话:
“祝你前程似锦,一帆风顺!”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有的同学会把“万事如意”或“一帆风顺”的第一横或者第一竖用连笔串到一块来写,也是很土俗的写法,但那时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来写,觉得是好看的装饰。虽然那时我们不知道,等待我们中大多数的,都不是这样如花似锦的前程。教室里洋溢着过年般的气氛,下课时常能在教室外看到匆匆交换纪念册的人,同学间互相打招呼,开口就问:“你同学录可叫人写了?”
或是:“我那个同学录赶紧给我写哎!多写些话哦!”
或是:“过两天给我把同学录写一下,记得给我一张照片哦!”
但我们打开同学录,兴致勃勃看看前面人写了什么的时候,还是难免失望。有意思的留言太少了。妹妹和我是双胞胎,在隔了三间教室的理科班,她首先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去文具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蓝色软壳笔记本,只给班上十来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写,后一个人写时,就把前面的封起来,余下平常只是打打招呼的同学,则买几沓那时在县城流行的A4大小彩色信纸,一人一张信纸请他们写。又问别人借了傻瓜相机,拍了些学校教室、花草的照片,洗出来贴在留言本前面。同学送的照片,也贴在那人写的留言后面。这样留言本就很丰富,同学的留言大大变长。我见这主意很妙,于是依样画葫芦,买了一模一样的本子和信纸,请班上同学写起来。
这样不怕麻烦,除了想要拥有一本漂亮的留言本之外,还有自己秘密的心思,不能为外人道。想等所有人都写完后,把本子拿去给自己有好感的那个人去写,这样别人就不会看到了。看见前面人都写了那么多,他也会受其影响,不知不觉写下一些真实的话吧。每个人的留言后都贴好了他们的照片,那样就算无法说出“请你给我一张照片”这样的话,对方也会知道附赠一张照片过来的吧。
然而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勇气开口。没有办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大方方地把本子递过去,对他说“请你帮我写一下留言吧”,更没有勇气趁教室里只有两个人的时候走过去——虽然这样的时候很多。
高考前三天,第二天学校就要放假了,给学生自己在家或学校休息,调整状态。放假前一天晚上,我们又留下来一起说话。到了深夜,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沉默地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并排来回走着。远处路灯光色黯淡。
第一场是语文,这是那时我最擅长的科目,虽从高二时起,就因为总也写不好考卷后的议论文,也十分烦恼了起来。有时发了气,磨着不愿动笔,最后就把只写了一半的作文交上去。高考这一天的作文题我照例觉得没有话说,只想写一点故事,而没有什么可发表的议论,想了想,索性心一横,照着自己想写的漫然写去。下午数学,这一年的数学卷子较为简单,我竟然感觉还不错。第二天上午文综,这也是我比较擅长的科目,因此都平淡无波地过去了。最后一场英语,把答题卡填完,又重新把试卷检查一遍过后,还剩最后二十分钟。我终于松了口气,抬起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只见水杉碧塔般树尖上,已有些黄的太阳光照耀着,在此刻人的心上留下些关于美与哀愁的印痕。头顶上吊扇开到最大,呼呼吹着,不时有人翻动试卷的声音。就这样结束了啊,我的高中时代。这样暗暗想着,忽然有一个流泪之意,把英语试卷翻过来,在最后空出的白页上写了一首诗——这卷子等我们散场后就会像废纸一样被收走,因此我知道在这里写字无碍。
再见已是学校填报志愿的那一天。考试结束以后,学校很快发下估分手册,我们凭着记忆,把除了作文之外的试卷又重做一遍,对照正确答案,估出自己大概的分数,然后根据往年录取分数线,琢磨着报哪个学校。妹妹填报了湖南一所大学的建筑系,而我则模糊鎖定了北京一所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十分热闹地挤在一起,看学校名录,相互询问着各自想报的学校和专业,直到人散得差不多以后,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于是鼓起勇气走过去问:“你准备报哪个学校呢?”
“我想报北京大学,但是班主任不让我填,他怕我分数不够,到时候跌下来。”
那一年他考了学校文科的第一名,分数上北大是很足够的,只是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办呢?”
“我看看要不要填个北京的别的学校吧。”
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的估分比他的要低五十分,他想报的那些学校,我一个都考不上。于是我走掉,去到妹妹班上看他们填志愿。大姐在这一天也陪我们到学校来,她对于我们以后要学什么专业虽全无概念,但凭直觉也知道历史系听起来不如其他同学纷纷填报的法学、英语、电子商务有前途。这时候见到我们高一的语文老师(后来一直在理科班教妹妹),知道我很听他的话,便请他劝一劝我。
于是语文老师看见我,就问我准备报什么学校。我们一起翻了一下学校名录,末了他对我说:“你那么喜欢语文,报苏州大学的中文系不好吗?苏州大学的中文系很不错,我看苏州这个地方也很适合你。”
我想了想,好像无法反驳,而内心更深处涌上的,则是一种无处着落的虚无感。这样想着,我便改了主意,把第一志愿改成了“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系”。
交了志愿表之后,我们随即跟着大姐去了那时她工作的南京,直到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才回来。回来那天到了县城,走到学校大门口,看见通告板上录取的红榜已热热烈烈地张贴满了。除了第一批提前录取的军校外,文科班的榜上第一个便是他的名字——填的是北京一所有名的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正是那时我们觉得“有前途”的去处。
在多年以后,我才终于明白,那确乎是一场影响我们一生的大考,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却又是完全无法被一场考试简单注定的。在命运的森林里,我们穿过的,始终是那样幽暗多歧的小路。而那些年我们曾津津乐道、以为重要无比的高考作文题,我早已是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