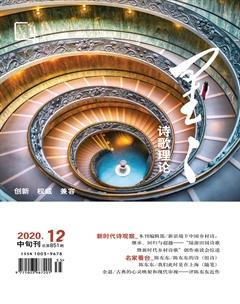诗歌中的分裂
杨紫晗,1998年出生,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
出梅入夏
陆忆敏
在你的膝上旷日漂泊
迟睡的儿子弹拨着无词的歌
阳台上闲置了几颗灰尘
我闭上眼睛
抚摸怀里的孩子
这几天 正是这几天
有人密谋我们的儿子
夜深人静
谁知道某一张叶下
我储放了一颗果实
谁知道某一条裙衣里
我暗藏了几公顷食物
谁知道我走出这条街
走出乘凉的人们
走到一个地方
蹲在欢快的水边
裹着黑暗絮语、笑、哭泣
直到你找来
抱着我的肩一起听听儿子
咿叽嘎啦的歌
并抱着我的肩回家
这一如常人梦境
这一如阳台上静态的灰尘
我推醒你
趁天色未明
把儿子藏进这张纸里
把薄纸做成魔匣
独具特色的女性意识构成了陆忆敏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使她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不同于“第三代”其他女诗人们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陆忆敏诗歌中更多运用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相结合的方式,在文本中形成对话,显现出某种“自我分裂”的倾向。这种独特的方式也帮助诗人避免因过度关注自我而陷入“情感的泥潭”(陆忆敏《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并在诗人与自我的对话中创建了一个开放且具有收敛能力的诗歌创造空间。
《出梅入夏》是诗人的早期作品,在整首诗中,作者以一个母亲的视角表达了对诗意人生的渴求。“我”和“你”在每一节中交替出现,使抒情主体分裂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并且在诗中交流和互动。开首第一行“在你的膝上旷日漂泊”使用的是第二人称,似乎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儿子弹拨着歌曲,灰尘在阳台静默着。随后视角开始转换,“抚摸怀里的孩子”的是“我”而不再是“你”,叙述者开始介入到故事之中。叙述者作为“你”的他者,在诗歌中已然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并且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在表达着自我。紧接着“有人密谋我们的儿子”给诗歌营造出一丝诡异惊恐的氛围,并且以“我们”“你”“我”这类人称代词来丰富诗中叙述者的形象,构成了一种戏剧化的效果。作为抒情主体的第二节主要讲述了诗人的梦境,梦境描绘了母亲对于“失去孩子”的痛苦与挣扎。在“夜深人静”“谁知道某一张叶下/我储放了一颗果实/谁知道某一条裙衣里/我暗藏了几公顷食物”,这里“叶下的果实”和“裙下的食物”都具有一种孕育的属性,从“一颗”到“几公顷”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深切的爱。之后诗人继续以第一人称视角往前推进,“我”带着一股极端的焦虑情绪脱离周圍的世界。叙述者离开“乘凉的人们”,走出“欢快的水边”,由此进入到“裹着黑暗絮语、笑、哭泣”的恐惧之中。在这一节中,多个“我”在同一场景中的重复出现,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观察的体现。以“我”对“我”的观察切入,两个“我”构成诗人的一体两面,统一在梦境中的主体之内。紧接着视角再一次转换,“你”和“儿子”的再次出现暂时缓解了“我”恐惧的情绪,梦境到此结束。
诗人通过对无意识“梦境”的有意识分析,意在对自我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此实现对自我的找寻。“这一如常人梦境”是不断重复且常见的,就如同阳台上“静态的灰尘”。日常经验的书写在陆忆敏诗歌中是普遍的,正如崔卫平所说:“陆忆敏诗歌中没有那种恶狠狠的、险象丛生的意象和言词,她更宁愿采撷日常生活的屋内屋外随处可见的事物:阳台、灰尘、餐桌、花园、墙壁、屋顶等等,她有着一份在女诗人那里并不多见的与周围世界的均衡感和比例感,因而她能够举重若轻。”(崔卫平《文明的女儿》)诗人对日常生活中细微事物的体认非常敏感,这些极易被我们所忽略的琐细之物,是陆忆敏诗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使诗人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互动。一如胡桑所言:“她眺望外部,总携带着一种被自我体验浸润过的目光,这种目光保证了外部世界的柔韧度甚至神秘性。”(胡桑《隔渊望着人们——论陆忆敏》)此外,诗人也借助神话中的意象来增添诗歌的神秘色彩。在自我中分裂出的两个独立个体,趁着暗淡的天色,“把儿子藏进这张纸里/把薄纸做成魔匣”。这里的“魔匣”是借用了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这个神秘的魔盒可以象征女性的子宫,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理解诗人为何要将儿子藏进用纸做的魔匣里。在潘多拉的神话中,所有罪恶被释放,只有“希望女神”被关在盒子中。从这个视角来说,“儿子”藏进魔匣之中,似乎是希望正在被孕育。然而,潘多拉的魔盒仍然是一个装满过疾病、害虫、恐惧等一切负面因素的盒子,它的开启给人们带来过灾难。因此,这里的“魔匣”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儿子”的保护,另一方面似乎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一种可能被释放的危险。
陆忆敏的诗歌中存在着不少“自我分裂”的叙述,在这种分裂之中诗人重新认识自我,从而完成对自我的找寻。在《出梅入夏》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由诗歌进入到庸常生活而产生的不适感与分裂感。诗歌创作是一项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活动,正如西尔维娅·普拉斯无法兼顾好生活与创作,而选择在煤气中自杀一样,陆忆敏在后期也渐渐停止了创作。她所关注的是置身现代生活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女性被生活所围困的冲突与挣扎是诗人创作的题材之一。诗人在诗歌中关注自我,解剖自我,这样的一个“我”是深邃繁杂的,同时也是分裂和残缺的。特别是陆忆敏并未局限于自我,而是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普遍的焦虑之上。正如她所说:“一个女诗人最突出的优点,其实并不在于情感的泥潭特殊的缠绵。”(《谁能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诗人努力地挣脱了同时期女性诗歌的桎梏,她可以从一种母性视角来建立更加广博的女性主体意识。这种意识的建立,“也在一定意义上缓和了与男性话语的尖锐对立,化解了男性‘话语场(程光炜语)的绝对权威”。(陈利《女性诗歌的另一种风景——陆忆敏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