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东西长着长着就像凹村的人了
文/雍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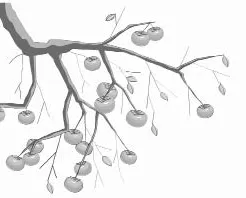
昨天,凹村有两家人在院墙上斗嘴。风把两家斗嘴的话刮得到处都是,仿佛满凹村都在斗嘴。
一家说:“那棵树是我家的种,只是不知道哪场风或哪次水把它移到你家田坎上了。”
一家说:“你让树喊你一声,我就相信那棵树是你家的种。”
两家人从早上闹到晚上,风故意从早上往晚上刮。它想使坏,整个凹村都闹腾起来,它才不寂寞。两家人都不服气,他们各自从自己家的树上摘来一个果子,拿在手里做对比。他们相信能从果子上各自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两个果子在围观的凹村人手上过了一遍。有的说像,有的说不像。轮到达噶手里,他看都不看就说:“既像又不像,是两家人的果子。”
两家围着达噶闹开了,让他说出原因。达噶坐在石头上,慢吞吞地说:“很简单,我看树就知道结果了。这棵树比平时的树要矮些,树皮皱得跟他家人脸上的老皱纹一样,我就知道树是他家的种。”达噶看着其中一家人说。那家人得意起来:“你看,我说是我家的你不信。”
另外一家人不服气,正要质问。达噶又说:“这棵树叶子圆中带长,长中带扁,扁中带尖,像你家人的脸型。我就知道说是你家的也并不错。”这家人也高兴起来:“瞧,我说是我家的嘛。”
这场斗嘴没有结果,但是两家人都高兴地回家了。他们没有往深处去想达噶模棱两可的话。达噶解决了两家人一天的斗嘴。风在这里凑不上热闹,丧气地刮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走在散开的人群里,垂着头想事情。达噶从我身边走过,我拽了一下他的袖子。他停下来看着我。我问他:你是怎么从一棵树上看出这棵树是谁家的种?达噶说:其实这再简单不过了,很多东西长着长着就像凹村的人了。说完,他呵呵笑着,满嘴的烂牙争先恐后地露出来。
达噶掉了两颗门牙。他的缺门牙让我想到他家圈里的老牦牛。老牦牛老得不行了,掉了好几颗门牙,却怎么也死不了。达噶每天弓着腰割草喂它。有次,我站在圈门口偷偷看达噶喂老牦牛。他和老牦牛面对面地坐着,牦牛吃一口,达噶喂一口。老牦牛吃饱了,达噶就坐在那里边摸老牦牛的头,边说掏心窝子的话。我从背后吓他,老牦牛和达噶一起瞪着惊恐的眼睛看我,他们的眼神出奇相似。那次我还开玩笑说:吓住你们两兄弟了。达噶从地上捡起小石子打我,我嬉笑着躲开。他怒着气说:差点把我和老牦牛的魂儿都吓掉了。如果魂真正掉了,我们两兄弟的魂儿看你怎么赔得起。
现在想想,达噶早就明白了,有些东西长着长着就像凹村的人了。他只是没有告诉任何人。或是他根本不想告诉任何人,他想保守一个人的秘密。
达噶的话扯着我。我觉得凹村的很多东西之间都存在某种联系。
我家门口种着一棵柿子树。树小的时候,我和它是朋友。我经常对着柿子树说话,说不能给大人讲的话。我说完每句话都会对它说:懂没?柿子树有时摇头,有时点头。不动的时候,我用手轻轻碰碰它,我怕它错过一些我说的重要的话。
后来柿子树越长越高。它长的时候,我也长。可我怎么也长不过一棵树。我每次坐在它的根上摆龙门阵,感觉是对着一个人的屁股在说话,这让我很不舒服。我在问它懂没懂的时候,得仰着头。仰着头问话,我觉得我在对着天说。天不理我,我没有权利问天懂没懂,天懂得比我多,它会嘲笑我。
我不理一棵柿子树,好几年都不理它,像跟它生了很大的仇气。直到有一天,阿拉拿着一个红红的大柿子逗我。她把柿子放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最后说:奇怪,凹村大柿子要不是扁的,要不是椭圆的,你家的柿子怎么就长成了方柿子。她疑惑的时候,我也疑惑。我已经很久没有关心过一棵柿子树的果实了。阿拉看看柿子,再看看我,突然哈哈笑起来。她说这个柿子真像你的脸,整棵树上的柿子都像你们家人的脸。
当时,我不信。后来我仔细观察过这棵树,它和凹村的很多柿子树都不太一样。它的果实、叶子、长势都和我们家人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家人的脸是凹村出了名的方脸,很多人背地里议论,说我们家上辈子富得流油,个个肥头大耳。大柿子树不但果实长得方,叶子也圆中带方,和我们家的脸一样。它粗粗的树干不是笔直地冲上天,而是长得不紧不慢。它长一节,打一个结,长一节再打一个结,像累了有人放根小凳子在那里一样。这个结像极了我爷爷的驼背。只是爷爷长不了那么高,只能在自己的背上打一个小结。爷爷也想在长累的时候,歇一歇。
当我发现这个秘密时,我摘了很多凹村人种的核桃树、梨树、桃树、花椒树的叶子、果实和我家的一一做了比较。这些叶子、果实和我们家的都不一样。我家果树的果实和叶子的长相都像我家人的脸,方方的。后来,我把我摘的凹村每家的叶子和果实再还回每家时,我再次发现,凹村每家人的果实和叶子都不相同,它们都像每家人的脸,长的、圆的、椭圆的、尖的、扁的。树干的长势也各异,笔直的、弯弯的、高高的、矮矮的、粗的、细的。我不禁感叹,树在模仿凹村人的一辈子。
夜里,我听风刮树的沙沙声。那是树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柿子树说话的声音像我阿爸的声音,粗粗的;核桃树的声音像我阿妈,柔中带尖;苹果树的说话声像我那死了的阿哥,硬硬的;葡萄树说话的声音像我和阿姐,叽叽喳喳的。
我越来越注意凹村的很多东西,包括土地、畜生、每场落在凹村门口的雪、每条经过凹村的路、每天挂在凹村天上的星星、白云甚至是生长在谁家门口的一棵野草、一朵野花,我都认真观察过。观察得越多,我越肯定,每样东西都在模仿凹村人的一辈子。那些模仿凹村一辈子的东西,汇集在一起,又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凹村。某个凹村在一个我们看得见但却不太在意的地方生长起来。
从我发现这个秘密之后,我对待每样凹村的事物都客气起来。我犯不着去得罪它们,得罪它们就是得罪另外一个凹村。路上,我遇见谁家去放羊,我先给羊的主人家招呼,再去给一群准备上山的羊招呼;遇见谁家在打核桃,我先问候核桃树上的人,再去摸摸那棵树,嘴里说着:你辛苦了。树上的人从密叶子里回话:不辛苦。我想和凹村的所有搞好关系。说不定下辈子我也会投生成凹村里的一棵树、一头牛、一条路,长着长着就像凹村谁家的人了。
关键是我还明白一个道理:凹村的很多人是活不过凹村的一块地、一棵树、一条路的,如果我这辈子和它们搞好关系,下辈子再投生到凹村,我就不会那么孤单,至少我有那么一些我熟悉的东西在那里,它们不会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对待我。
我在路上遇见达噶。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他嘴里的门牙又掉了两颗。他老得不能再老下去了。像他家院子里干裂的杏树,活着也没多大意义,随时等待一阵风把它带进土里。
达噶背着手,又是冲我呵呵地笑,他的笑声仿佛来自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
“知道那个秘密了?”我点点头。
“知道怎样做了?”我摇摇头,顿了顿,又点点头。
“那就对了。”达噶笑着从我身边走过。我看不见他缺牙的嘴。
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我想,达噶肯定生长在另一个凹村了。
我得走遍整个凹村,去找一条像达噶的路或是一棵树。
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