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将一面与梅花
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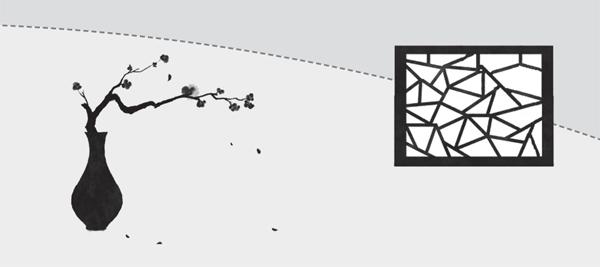
清代诗人何钱,所留诗作不多,但有一首《普和看梅云》值得点赞:酒沽林外野人家,霁日当檐独树斜。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
年轻时读到它时,心有感动,感动在于一个“留”字。但还是未能记住,很快便忘掉了。后来,偶然读到漫画大家丰子恺先生的两幅同题漫画,印象便深刻起来。一幅叫“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另一幅叫“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桃花”。就改了一个字,梅花改作桃花。而画面景致却有所不同。
首幅:修竹茅舍在后,平阔野地屋前。东篱之下,摆一小几,好友三个环几而坐,留得一面,邀来一树梅花;另一幅:松柳茅舍后,峦岩小屋前,还有兰花几株在石上,优雅得令人惊叹。空留那一面,是一树桃花。人仨花一,围坐举杯,相聚甚欢。
与梅桃同醉,是古人常有的生活趣味,现代人恐怕学不来,因为生活得太过现实。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既如斯,就该与万物心灵融合,相敬如初。所谓天人合一是也。何谓天?即大自然,当然包括自然万物。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留将一面与梅花”与梅同吟同醉,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乃人心丰富美好的一面。包容万物,才是人类该有的伟大情怀。我们人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自然万物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的。万物皆有灵之说,非空穴来风,是自然科学不断地在证明着的。当白发覆额,所求无多之时,我倒有些依恋起农耕文明来了,原因在于,它与自然界靠得最近,可以说相依为命,不分彼此。山顶洞人的存在,就是一例。
我们的古人,尤其古代文人墨客,对花木的眷恋之情是有史可查的。他们亲近花木,呵护花木,将它们看作亲朋好友,是一种心灵寄托。因为它们,给予人的精神慰藉,有时是优于我们同类的。有一例很典型,那就是唐人白居易所说:“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结庐西湖孤山的宋代处士林逋,终身不娶,以种植梅花,饲养野鹤为人生乐趣,人称“梅妻鹤子”。他有一首《山园小梅》的七律,赞赏梅花别出心裁:“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有人会说,他活得太傻,太不现实。也许是。但人各有志,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人的私事,我们用不着去武断评判。“梅妻鹤子”又有什么不好呢?大自然历来是人类最可信赖的情人,如斯,留将一面与梅花,是情理之中的事。人与人之间,流露真情,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往往带有风险。而与花木,说真话、动真情,只有回报,而无风险。人,有时心生苦闷,就想走进大山大野,让山水草木来慰藉心灵,而且往往收获颇盛。如斯,可以说,与大自然对话,是心灵得以畅明的有效途径。诗人何钱懂得此理、此益。当梅花盛开之时,他邀得两三好友,与梅花环坐小几边,谈天说地,吟诗抚箫,何等潇洒,何等优雅。这才是心灵之需求吧?比起灯红酒绿来,不知高超了多少倍?此时,梅花无语胜有言,意,尽在不言之中。
往往,心灵交流是需要宁静与悟性的。你瞧:茅舍、松柳、青竹、幽兰、正在吐蕊的梅花,高蓝的天空、墨绿的大野、原木的陋几、新茗与家酿的老酒,菜蔬是屋外所植的新品,还有雅士,以及他们珠璣般的谈吐,这便是一切,人生还需要什么呢?这比起娱乐至死的生存状态来得健朗,来得高雅,来得痛快淋漓。这使我想起高松下对弈的和合二仙来。也许有人说,这也太脱离现实的生存状态了。乍看,的确如此,然而细细琢磨,也不是。因为这是繁杂人生的另一面,是忙里偷闲,抚慰疲惫心灵的有效方式。如今世界,旅游业盛兴,人们扶老携幼走出家门,亲临大山大水,究是为何?只是为了观光与开阔眼界吗?不是,是为了寻求心灵慰藉,为生存储备养料。也许,有些旅游者没有细想这些,然而,潜在的收获都是相同的。山水花木慰人心,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只是人们常常忽略了。
我在蒙古高原的杜尔伯特草原生活了近二十载,草原留给我的人生感悟与教诲,是多方面的。她的辽阔与宁静,她的温馨与情愫,使我的心灵由幽暗变得敞亮。
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年的七月,正是草木葳蕤之时,我领命到巴颜红格尔草地去采风。蒙古包的主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额吉。她在冬营地留守,伴随她的是一顶蒙古包,一辆勒勒车,两头乳牛与牛犊,一条牧羊犬,还有蒙古包旁盛开的三株莎日娜花(即山丹花)。额吉把三株莎日娜用羊砖围了起来,唯恐牧羊犬与牛犊将它无意中踩踏了,而且时常去抚摸、浇水。有一天清早,我在晨梦中听到额吉与谁在说话:“呼恒,翁达斯布?嚯若嘿!”她是说:“闺女,渴了吧?可怜的。”我以为额吉的女儿回来了,赶紧披衣出门。不料,额吉正弯下腰,在与那几株莎日娜花说话,并用铜壶为她们浇水,那一条牧羊犬也蹲在一旁,静静地听,似有感悟。这使我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我默默地站在那里,听见自己血液的流动声。抬手抚摸自己的胸脯之时,两眼不由得潮湿起来。于是,这一蒙太奇般的镜头,永远地留在了心灵深处。
这一场景,与“留将一面与梅花”,何其相似。
摘自《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