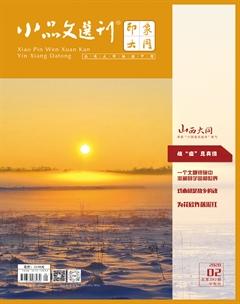远古的呼唤
蒋丛发

当面对电脑显示屏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感到深深的茫然。这种茫然来源于一种对遥不可及时光的隔阂。我用电脑替代纸笔写作已二十年,二十年前的旧事有很多在记忆中已然模糊不清。而追溯到祖辈生活过的时代,已是遥远的清代,而清代已被学术界列为古代。在这里,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金宋、元、明这一长段漫长历史都要被一笔带过,直接进入到已毫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这真是让人觉得像是在时光隧道中穿行一样,耳边生风,眼前电光火石般闪着或明或暗的朝代的影迹。又像被轰隆轰隆的列车载着,一站一站地走过,期间不停车,直接走到目的地。带着长途旅行的疲倦和终于到站的些许的兴奋,我的内心迸发出一声想要刺穿云层的呼喊:远古,我来了!这是我一脚踏进位于大同市云州区的吉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真实心境。
而远古留给我们的,又有什么呢?除了眼前这座展览馆式的建筑内珍存的从遗址出土展出的这些石器、骨器和黑陶。
我长时间驻足在展柜前,看着石镞、石纺轮、石環、石刀、石斧这些石器和骨匕、骨钩这些骨器。它们经过漫长岁月的剥蚀已然残缺不全,或许它们在远古人使用时就已被磨损成这样。这些石器和骨器真实地记录着远古人的生活,他们用石镞射猎,用石纺轮纺线织布,用骨匕切割,用骨钩缝制衣裳,用石刀、石斧砍开荆棘。他们的工具简陋之极。他们就用这样的工具做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活计。佩戴着叮当作响石环的女人,出出进进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硬骨做成骨钩,围在火坑边,借着微弱的一闪一闪的火光一边御寒一边缝制衣裳,她们的周围是一群欢蹦乱跳着玩耍的孩子。这真是一副很温馨动人的生活场景。尽管男人们为获取食物而与野兽搏命甚至血肉横飞,尽管日子过得或许缺吃少穿无暇去做长远的打算。
而生活总会向前发展,因为黑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生活因黑陶而变得前所未有得美好。我有时想,为什么这个时代不被叫做陶器时代,而仍然被叫做石器时代,或许是因为他们使用的工具还是石器。那条被生活在这一流域的人叫做桑干河的母亲河,滔滔不息地奔流过这里,使逐水而居的远古人在这里定居下来,一代代繁衍生息。时光在这里的流动是缓慢的,缓慢得让人觉得是静止的。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开启了对吉家庄遗址的考察与发掘,出土的石器和骨器证明这里曾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文明发祥地,出土的陶器和陶片证明这里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这真是一个笼统的年代概念!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到4000年间。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以动辄千年的模糊性一带而过,让人觉得那时真是一个现实中的神话时代,天上一日人间已是千年。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左右”也要以动辄百年的大气魄述说。这就让人觉得时光既在极其缓慢地流淌又在以光速般的快速飞逝。这真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哲学问题,讲述着时间与空间的奥妙。它们离我们是如此遥不可及、如隔星河,而它们与我们又是如此贴近、就在眼前。
石器和骨器不会让见多识广的今人看到美感,而黑陶却以震憾心灵的触动力拨动起我们审美的心弦。这是一种很耐看的世间罕有的美。耐看这词我不曾在任何文本中见过,我觉得这词更能准确地表达出我的所想。对于耐看的解读,我想就是第一眼被吸引,之后越看越爱、越品越有心得、越想越有内涵的意思吧。那些出土展出的罐、瓮、盆,口沿有侈口、敞口、直口,纹饰有粗绳纹、磨断绳纹、兰纹、弦纹、素面纹。这些器皿及其口沿和纹饰让我看到了远古人对生活之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既包含对便利的需求,也包含对审美的释放。每一种新器皿的发明,每一种口沿的发明,我想一定源于某种漫长的厚积后的薄发。它渗透并体现着远古人开创性的智慧。开创的产品以今人的眼光看或许并不高明,但如果没有开创的创举,又怎会有之后绵绵不绝的再创造与再发明呢?形体与纹饰呈现出的那种粗犷之美、大器之美、自然之美、简朴之美、静谧之美、任性之美,让我看到了远古人对于艺术和审美的本源性、发祥性认识和理解。它古朴、大器、自然、任性等气质直接影响了上古、三代、秦、汉的整体艺术风格。它继续一路前行开枝散叶,影响出了唐代九大名窑之一浑源窑的“茶叶末釉”和“酱釉”,影响出了辽金时期的“黑釉剔花”。从一种地域文明很气派地走向了一种行业文明。
它是技术与艺术骨血交融后的结晶。我无法想象那个发明黑陶技术的人在远古人部落中会受到何等样的尊敬,也无法想象那些把泥土神奇地变成黑陶的远古匠人和艺人会不会被他们部落里的人叫做神。同时,它又是最原始的化学反应——火与土的优秀儿女,它来源于火与土刻骨铭心般的爱情,它是土在火的疯狂亲吻后的爱情结晶。
今人能复原出这种美吗?在这种美的感召下,这里成立了陶瓷文化产业园区,有多家创作基地和研学基地入驻,有上百人在那里创作与研学,一台台电动拉坯机在大如展厅般的工作室呈两长排从这头一直延伸向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那头。一位做了近三十年陶艺的技师在我们面前揉好泥,揉到什么程度才恰到好处呢?要揉到泥里没有气泡,这全要从感觉中得出。艺术本就是一种自我性的感觉。揉好的泥坯放在拉坯机上,一个陶坯在旋转中由粗糙到精巧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陶坯干透后,要用细纱纸继而用手掌磨掉坯痕,之后蘸釉。釉比漆略稠,调制好后倒入盆内。用手指捏牢盏等陶坯的底沿置入釉中。蘸釉要做到均匀,没有釉痕。这就是吉釉的做法了。如要做茶叶末釉和同玉,则要更换釉料。如要做黑釉剃花,则要在陶坯上先行手工雕花。忍冬纹饰是一种吉祥而又美观的常见性纹饰艺术表现形式,是云冈纹饰的一大代表,所以成为黑釉剔花的首选。
黑陶顾名思义通体黑色,是一种沁于骨里、浸入心底的黑色,哑暗的光亮,黑到深邃与神秘。舜、禹和夏是崇尚黑色的,《史记·夏本纪》里说,“帝(舜)锡禹玄(黑色的)圭,以告功于天下。”《韩非子》里说,“禹做祭器,黑染其外,朱画其内。”《礼记 ·檀弓上》说,“夏后氏尚黑,大事(丧事)敛用昏(黑夜),戎事乘骊(黑马),牲用玄(黑毛牲畜)。”黑色在那个时代承载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敬畏意味,这种意味传导给了黑陶的黑。黑陶的形体往往或有足或有耳或有环或有鼻或兼二、兼三有之,雕刻手法有线雕、浅雕、深雕、镂空,工艺复杂到难以尽窥全貌的程度。它们承载着其实让现代人都惊叹的光辉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承载着一种唯美主义的生活观照,在数千年极尽辉煌后,埋没在不见阳光的历史的尘埃中。
是谁听到了你的呼唤?是我们这些一脚踏进这个恬静山村小镇的旅人吗?是那些拿着手铲、刷子小心翼翼地找见灰坑这种远古人生活痕迹的考古者吗?是那些有着文化情怀一心想要点燃文化兴区富民之火的当地官员吗?是我眼前的这些对黑陶艺术充满着信仰般热情的研学者吗?我站在烧制黑陶的低矮窄小的土炉边,听一位研学者讲解烧制黑陶的传统技术,其要领是用柴烧后从窑顶加水产生浓烟的渗炭工艺,这技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消逝无踪,却又在上世纪神奇地复原。
近在眼前的马头山看上去并不高大,嵌进洁净的蓝天白云中,显得线条格外明朗。这山恰是大同睡佛的局部。遥想当年,远古人真是会择地而居。这里南临马头山,北临桑干河,山明水秀风光迤逦,可猎可渔物产丰富,真是一块吉得不能再吉的吉地,这村名或许就源于此吗?桑干河在这个乡流经近20公里,河道里细腻的粘土富含矿物质,为制作黑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件件黑陶被神奇之手形神俱备地从远古甚至上古、三代、汉、唐、辽金等朝代复制粘贴出来,走进大众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触摸到远古及各代的温度,感触到远古及各代的气息。远古,印象中像神话一样遥远的远古,你原来可以与我们如此贴近!
大巴在落日余晖中驶离吉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驶离这块远古人曾生生不息的吉祥之地。马头山在我的视野中渐渐远去,连绵的山峰形成的大同睡佛也渐渐清晰地展露出无比庄严而慈祥的全部真容。睡佛是见过这里世事变迁的唯一的法相。睡佛会一点点告知我们这里在远古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神奇,让我们更加接近远古、理解远古、亲近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