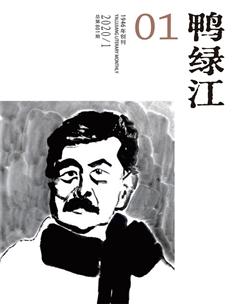拾烧草的时光
这世上所拾之物,最不值钱的,恐怕就是这拾烧草了。
在我的家乡——苏北的大潮河畔,以前谈到拾烧草,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寻常得有如见到花要赏、钱要挣一样。若有人和你闲聊,对你说“你是个跌倒拾把草的人”,那么请你不要误解,不要见怪,那是在夸你呢。至于为什么是夸你呢?当然得走进那个年代,体味一下那个特定条件下农村人对烧草的感情,你才能真真切切地明白“你是个跌倒拾把草的人”的内涵,以及它的寓意。
回溯流年,我的记忆定格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彼时,我还是个天真的孩童,却在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人生历炼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拾烧草这一桩往事。
那时,我家也和许许多多的普通农村家庭一样,在一间不大的土墙苫草的灶屋内,砌有一口灶台,上面放有一大一小、一左一右的两口铁锅。灶台是用黄泥巴砌土砖而成,模样拙朴。可别看它外表是粗糙的,却维系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左邻右舍谁家都离不开它。
由于粘结土砖的黄泥巴时常会裂开缝,而青烟却是见到裂缝就带着火苗开溜的主,往往因这裂缝而搞得满屋尽是青烟弥漫,呛得人打咳嗽,辣得人眼泪汪汪。遇到这种情形,母亲便急了。这呛人也好,辣得人眼泪汪汪也好,母亲一时半会都能接受,唯独这火苗往外跑她不能接受,因为这样浪费烧草,她特别心疼。她会立即挽起袖子,一边挽一边迅速地跑到门前不远处的池塘边,用手剜来新鲜的黄泥,把缝弥合上。她的嘴里常会念叨着:“不漏气的锅,煮饭快,又省草……”
铁锅接触灶台的一圈儿有时也会有火苗窜出,那也是因为铁锅边的黄泥巴开裂或脱落导致的。为了不让这火苗往外窜,母常不知是自创的还是跟别人学来的,她爱找来废报纸或废旧书本来,裁下二寸宽的纸条,沾上水,然后粘在铁锅和灶台的接合处,这样黄泥就不易开裂或脱落了,当然也就不会有火苗从铁锅四周外窜了。
多年来我一直想不通,这普通的纸条贴在铁锅和灶台间怎么就烧不掉呢?想来:是因为灶台边的黄泥和铁锅的共同保护,才得以勉强幸存吧!
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她得保证家里的烧草不断,保证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能够正常地维持下去,所以她才对这类浪费烧草的事情特别地留神、坚决地杜绝吧?而开始我却对她不怎么理解。
我的母亲是属于那种心直口快、肚子里有话留不住的人。从她平时的话语中,我慢慢理解了她,感受到她的想法正如我今天的想法一样;也可以说:我今天的想法,是把母亲的想法书写了出来而已。
记得生产队的那阵子,在生产队那十几亩地的土质场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草堆,队里的每家每户每年都要分得两次烧草回来。作为地地道道农民的我那父母亲都会齐心协力,而且相当仔细地把草垒成堆,或长、或圆,无不棱角分明、有模有样。他们往往一个站在地面上,一个站在草堆上,彼此递接着草,你来我往,配合得相当地默契。
夏天麦收时节,我的父母会把那些凌乱的麦秸堆成圆顶后,再用麦芒屑掺进淤泥,搅匀,然后用这淤泥把草堆顶涂抹起来。他们涂抹得相当仔细,均匀、光滑,在阳光下像和尚的头顶一样闪着光亮,以此来防雨防雪等自然天气,还怕你雨水落到上面不滚落掉?
秋天收稻谷时节,他们会将一把把黄橙橙的稻草码好,苫好,小草屋一般。
冬天棉花结束,他们不停地拨着秸秆,拔啊拔,即便手上磨出大血泡还是小血泡,也不丢手。然后,他们将拔好的棉花秸秆运回家,堆得像大乌龟似的,顶部则也用稻草苫好,用掺了麦芒屑的淤泥涂抹好。
而那些夏日或秋日收回来的玉米秸秆,则被他们一捆捆簇拥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个大型的圆锥。而圆锥里面却是空空的,别有洞天,是当年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时玩捉迷藏,最爱躲藏的就是这些“圆锥”的里面了,宛若钻进了尖顶的蒙古包,有一种別样的风情。
一直到后来的分田到户,我家屋舍的四周总是不间断地堆着这样那样的草堆,俨然成了住所周围特有的摆设与点缀,有如巨型的沙盘画。都是父母的大手笔,以草为笔,绘就了立体的一个个草垛,伴着我家土墙的瓦屋,以及土墙苫草的灶屋,在明艳的阳光下,奕奕著,自有它们的丰采。
我的父母亲看在眼里,高兴在心里。母亲有时会欣慰地说出大致这样的话:“我们家里养着一口老母猪,下的小猪崽子要烀熟食喂养,烧的草少不了要比一些人家多得多。看着这些草堆,我的心里多少有点踏实了……”
可是她的心里终究还是没有完全地踏实,还是怕断了烧草。
有了这一份小小的忧患意识,我的母亲在平时烧草锅的时候,格外地注意节省柴草。她一般不会轻易地去揭那正烧着的草锅盖子。若是烧水,她凭经验,听锅内的水声,就能知道水有没有烧开。母亲会对我们传授着她的经验:“水特别响时没开;响声由大变小时水才开。记住!”母亲还会说:“不要轻易去揭锅盖,揭一次,就得多烧三把草。记住!”
我们每次都含糊地应着,却真地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几十年过来了,一直记到今天。
为了能使家里的烧草多多益善,不至于上季不接下季、烧了上顿没了下顿烧,母亲常会鼓励我和妹妹在闲暇的时候去拾草。
当时家里有一个专门用来拾草用的铁耙子,是父亲用粗钢丝做成的。父亲做的这铁耙子比街上卖的竹耙子沉重得多了,我和妹妹常常扶着它的长长手柄、在自家附近的乡村土路上拖来拖去,搂那些零星散落的草秸。铁耙子在我们的身后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同时伴有扬起的一缕缕灰尘。
有时,也会有邻里的小伙伴和我们在一起搂着草。大家都嘻嘻哈哈着,像小马驹似地快活。我们这些孩童,哪是在劳动?哪是在拾草?分明是在做着欢快的游戏,在享受着童年的欢乐与人生的乐趣。
曾经有过一、两次,正当我们在土路上搂草时,不小心撞到了正在走路的某个大人的怀里,惹得被撞的大人忍不住地笑起来,笑我们麻痹大意,像小牛犊子顶撞母乳一般,笑我们小小年纪就知道干活、为父母亲分忧。当然这笑里更多的是鼓励与褒扬。被撞的大人往往还会一边笑着、一边一再叮嘱我们:“当心这路上的手扶拖拉机!牛车!还有自行车……”“噢!……”我们会仰着一张张童稚的笑脸、响亮地应着。
那时的家乡,马路上的车辆少。我们很少有过和车辆发生磕磕碰碰的情况出现,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些车辆格外地提防,更因为大人们对我们格外地呵护,有如呵护春风里的一棵棵小树苗。
和谐的社会,温暖的人与人之间,大概就是像这样构成的吧?
每当夏收、秋收的时节,乡村的土路上散落的草秸格外地多,我们这些孩童也会格外地起早贪黑地搂着草,因为更多的时候得去离家不远的小学校去读书。
深秋时节,当季节性的草木枯萎、凋零时,苜蓿也停止了生长。我们一群孩童,这时便会觊觎起生产队的苜蓿园来。我们会在某个晴好的日子里,挑个没霜没露水的时候到里面去疯狂,去搂苜蓿根下面陈年的枯草。
这苜蓿园生产队仅有一块,好几亩地大小。当春天的气温上升到一定的时候,整个园子便呈现出一片新绿,绿地毯似的,茵茵复茵茵。随着气温的再次上升,眨眼功夫,苜蓿园又变成了一片开满紫色花絮的海洋,这时会引来无数的小蜜蜂,整天“嗡嗡嗡”地叫着。也会引来无数的彩蝶,翩翩地起舞着。苜蓿园里,还会有老蚂蚱蹦哒着,带着一群刚出生不久的小蚂蚱在举家一起玩耍着。有时,我们还会见到苜蓿园里有野兔子的身影,一只或几只,会顺着田埂跑得异常地迅捷,不等我们去撵,已在一瞬间跑得不见了踪影……
这苜蓿园虽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诱惑,我们一群小朋友平时却并不敢随便跨入,只因怕那专门看管这苜蓿园的老头儿刘四爷,怕他那严厉的表情,更怕听到他那大声的吆喝,跟打雷似地吓人。
刘四爷是生产队的猪倌。生产队的猪场就设在苜蓿园的南边,像亲密时的恋人似地相互紧挨着。刘四爷他整天泡在猪场里,两对大眼珠子不时地紧盯着苜蓿园,一旦发现有小孩进去,立即就会把他的那副长脸拉得长长的,表情严厉地吼道:“苜蓿草都被糟蹋死了!生产队这么多的猪要不要吃啦?再不走,告诉队长,扣你们父母的工分……”
如此情形下,我们一群小朋友当然怕,当然没人敢轻易去涉足这苜蓿园。
可是,到了晚秋,这情形便有所改变了。为了使苜蓿能够安然过冬,刘四爷他们停止了对它的收割,生产队的那些猪改用了豆粕等成品饲料饲养着。这样,刘四爷就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转悠,常常是喂了猪食,便不见了他的人影。我们便如鱼得水,趁机溜进苜蓿园,逮那些长大了的、也是我们垂涎已久了的蚂蚱。我们会把逮到的蚂蚱穿在狗尾巴草上,准备带着回家,让母亲用火又挑着、用柴草在灶膛里烤熟给我们吃。
可是玩归玩,我们可并没有忘记进苜蓿园搂草这一正经事情。我们会使劲地用耙子搂那些苜蓿根部的枯草。这些陈年的枯草,厚厚的一层,搂几下就是一小堆,这让我们兴奋得忘乎所以。不一会儿,我们都搂得可观的一大堆枯草,这才各自捆好,踌躇满志地背着草,拿着耙子,提着蚂蚱,走出苜蓿园。
也有一、两次,我们正准备离开苜蓿园时,刚好被刘四爷回来发现,就见他又拉下脸,嚴厉地对我们吼道:“苜蓿草都被糟蹋死了!生产队这么多猪要不要吃啦?……”我们吓得慌慌张张,赶紧抓起各自的耙子,背着各自捆好的枯草,提着各自的一串蚂蚱,脚底抹了油似地离开了苜蓿园。
其实,刘四爷只是嘴上狠,却没有实际行动,属于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角。
今天想来,他是在为集体好,心里肯定也是怜爱着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淘气的吧?可是当年,我们却特别地恨他、诅咒他——真的是冤枉了好人啊!
可他早已不在了,再多的抱歉话也都成了无从对证的往事了。
拾草,在当年,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孩童热衷的事情,也是某些大人热衷的事情。
记得有个邻居夏大奶,经常在我家旁边的乡村土路上拖着个竹耙子,扶着木手柄,也像我们一样、走来走去地搂着草。她的身后也是留下一串串耙子的“沙沙”声,以及扬起的一缕缕灰尘。
夏大奶当年大约有七十多岁了,瘦小的个子,常年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褪了色的粗布裤褂,脖子上围着的是一条陈旧的三角巾。她有一只眼一直闭着。大人们说她闭着的这只眼什么也看不见,仅靠另外一只眼辨别着周围的一切。有一次,我见她险些儿被奔跑着的手扶拖拉机蹭到。这可能和她年迈、以及视力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为了搂点烧草,她闲不住啊!
想来,当年的夏大奶,在不辞辛劳地忙于搂草的同时,内心一定憧憬过未来,希望自己、以及家人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吧?
如今在家乡已很难看到有人在搂草、拾草了。
而夏大奶,以及我的父母,也都如刘四爷一样早已作古了。他们那为烧草而忙碌的身影,也一同成为无从对证的往事了。
我怀念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农民。虽然他们的文化低,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可他们却深谙人生之道,知道打开门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知道烧草是首要的一件事情,少不得,也缺不得。
我难忘他们淳朴而勤勤恳恳的一辈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栖”,默默无闻地走完自己平凡的一生。
我多么想请他们向你陈述一下,“你是个跌倒拾把草的人”的内涵与寓意,让他们现身说法、亲口告诉你:那是在夸你具有勤劳持家的风范,亦如他们一样,在跌倒时不顾疼痛,不忘拾起那微不足道的一把烧草来。
我多么想吃母亲用柴草煮的草锅饭,还有那小鱼豆子加锅贴……
我多么想让母亲用柴草在灶膛里再为我烧一次蚂蚱——那个馨香啊,无以言表,至今难忘。
我多么想再帮父母去拾一次草,拖着儿时那个铁耙子,搂啊搂啊,搂啊搂啊……
可往事如同东逝水,早已成了乌衣巷里的旧时光,或许只有那堂前的燕子,还记得,同我闲聊、呢喃这一切。
作者简介:
刘喜权,连云港市作协会员,有多篇作品发表于刊物及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