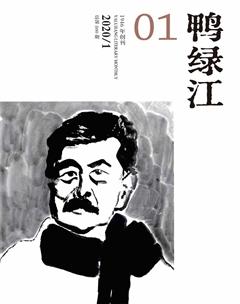池鱼屋
索耳
雨滴。雨滴像无数的眼睛落下。她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手里拿着伞,穿过城中村的巷子。脖子上的项链泛着白光。项链是某位男士送给她的,她从来不会买这种东西,即便在路上拣着了,或者是别人送到面前,她也未必会戴。只是因为是那个人送的。只要是他送的,她肯定就会用。自我提醒。今天第三次走过这条路,清晨时走过的路,是干燥匮乏的,中午走过的路,相当暴躁,下午,就是现在走过时,涌动着甜液的潮湿。大概是一点多的时候,她把屋里的长寿花拿到窗台上晒,突然就滴起了雨。雨簌簌地下,伴随着楼上的咳嗽声。咳嗽声总比吐痰的声音好听。楼上的姑娘一直在吐痰,每吐一口,产生一次被凿穿的感觉。每天晚上,她几乎睡不着觉,因为这种被凿穿的感觉,越闭上眼睛就越精神,于是她坐起来,打开手机查看那个男人的信息。有些字句她觉得有必要抄下来。不能淹没在数字信息的洪流里。她把它们都抄下来,都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等着有一天她把它们都寄出去。今儿她觉得是把它们寄出去的良机了。因为这场雨。这些雨滴。即便她今天已经出门过两次了。这次她换上了最好看的衣服,戴上最好看(唯一)的项链,把信笺藏在贴身的内衣里,像前面两次一样,穿过凉风吹拂的楼房之间的甬道。就像某种怀孕的昆虫。鞋底踩在地面凸起的白色管道上,发出咝咝的响声。
她拼命回忆着那个男人的名字,她将要寄信的对象,只有一个名字,但她怎么也想不起来。从去年开始,她的记忆衰退得非常厉害,吃多少药也不管用。医生的忠告是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医生居然奉劝不要吃药。一个不称职的中国醫生。她依旧按时吃药,药物使她的月经变得不太正常。这是她控制自己客流的一种方法。不然,她没法压抑住自己接客的欲望。只要一想起寄信这件事,她就想接客,她就会打扮好,站到那些湿漉漉的甬道上去。老幼高矮胖瘦的诸多客人从她面前走过。只要有人从面前走过,她都会身子向前一倾,脖子一伸,用尖锐的下巴震慑他人。往往有人被这个举动吸引住。这时她慢慢低下头来,眼睛绽出笑意,仿佛一蓬降落的雪莲,一枚闪耀的硬币。此方法屡试不爽。别的姑娘学也学不来。只有她才能这样吸引客人。实话说,这个方法不是她想出来的,是那个男人给她想的,在漫长、无数的信息流当中,他给她的其中一条语音信息描述了这样一个动作。他们初次见面的镜头。慢放、静止、倒带。重复。她当时大概是站累了,漫不经心地伸直躯体,在他眼里,变成了撇清世界万物的动作。无法消除的烙印,他对她说。没有什么是忘不了的,除非你根本不想忘记。就像他离开后,她想给他寄信,更想站在机械传送带般的甬道里面,用自己尖锐的下巴刺穿那些男人的心脏。
起风了。斜的雨滴,以轻盈的姿态钻进伞底。褐色的公路在爬升。另一个方向上,车辆驶过留下的残光散裂成千万缕,褶皱,然后笔直向前逃逸,生成一个多彩的线性世界。一切都在变慢、变快、再变慢、再变快。公交车驶过来,变慢,停止,启动,加速离开。她在等车,等了有十来分钟,跟其他人一块在等。其他人上车了,又有另外一批人走过来。除了她,还有一个女人,一直站在原地。女人穿着卡其色棉袄,灰色牛仔裤,黑色皮靴。本来她没注意这个女人的,但是后来她发现女人有点面熟,至少见过一两面。肯定不是自己那片单元的,不然她就能准确叫出女人的名字。她觉得有点奇怪。一种很朦胧的感觉,也许是无意识趋同感,每个陌生人都似曾相识。她猜想那女人对自己也是同样的感觉。两人尴尬地在雨里站着,隔着两米来远的距离。她能闻见女人身上的香水味,那是一种内敛、沉寂的香味,她鼻子一贯灵敏,但是她无法分辨那是哪个牌子的香水。因为她只认识自己身上的香水。很搭配,她暗想。女人一直朝前方看,安详的脸像一块未拓荒的大陆。对面公路只有罗汉松和隐藏在罗汉松中间的亭子。树上还挂着卡通气球。节日的馈赠和排泄物。有什么能令一个人变得安详?并不是眼前的事物,它们急切等待着被消解和寄存。她产生了冲动,她抬腿走向那个女人身边,两米远,她的腿足够长,只需要两步。不会有任何侵犯的感觉。这时她发现,那个女人也在移动,离开了之前的位置,跟她的速度保持一致地溜上了刚刚驶来的公交车。
车上空旷、宽敞,只有几个穿戴整齐的老年人,大概是一块约好去出行的。她直接走到女人旁边的位置坐下(女人已经先她一步坐在窗边),她们似乎彼此对视了一眼,但是没有后续交流。她像没事一样,望着窗外的景色。树迎着风,像扯满的帆,剌剌地鸣叫着。坐了两站,邮局到了,提示音开始播报,但她放弃了下车的念头。她不打算寄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定,也许是此时,也许是上车以后。也许见到女人的那一刻起。又过了几站,女人打算下车,她给女人让出位置。女人走到车门旁边,她还在座位上。但是屁股已经感受了一股炽热。发焦,滚烫,可食。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几乎是同时地,她跟着女人从车门冲了出去。这时候女人明显已经有些恼火了,但是没立即发作。她们一同沿着路边走过去。走着走着,女人开口问说:你老跟着我干吗?她回答:我觉得我认识你。女人说:我可不认识你。她说:你记得傅秋来吗?话一出口她就吃了惊,她本来忘记了这个名字的。女人说:没听过。她说:也许你忘了他的名字。但是你肯定记得他。长着一张瓜子脸,小眼睛,厚嘴唇,皮肤白白的,老爱唱歌来的,什么“遇上几多的他随着烟花绕,其实哪个对我最紧要”“迷失在这地球,为何不顺性放手,载沉又载浮,太率性不甘心颤抖”。女人沉默了一下,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她说:是吧,我猜你肯定知道。女人抬眼问她: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她说:哪有什么关系,就那种关系呗,跟你差不多吧。她们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女人用脚踢开路中间的易拉罐子。你别跟着我,女人说。她问:为啥?女人说:我不会跟你说任何事情的。她说:你怎么知道我问什么。女人说:反正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她露出微笑:随你好了。
她们一块走过了两条天桥和五条街道。其间她们保持着微妙又和谐的关系。雨渐渐停了,天空如同巨大的兽壳从水底露出。她跟在女人后面,拐进了一个小区里面,里头种满了大王椰和相思树。楼房紧挨着,但明显比她们住那地方要宽敞、整洁得多。女人走进了某个单元楼里,按下了电梯。十八层。她们随着某种东西,某种空白的欲望,仿佛一个装满了气体的格子,逐步爬升。叮的一声响,电梯到了,她们走出去,在楼道拐了一个弯,到了一扇门前,门牌后写着1802。真正吸引注意的是门旁边的墙上挂着的牌子,整体是一个卡通形象的屋子,上面用彩色字写着:池鱼屋。她想: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女人瞟了她一眼,按响了门铃。很快就有人来开门,里面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喧闹声。她的心怦然一动,好久没听过这么悦耳的声音了。她随女人走进去,眼前出现的是一间宽敞的公寓,客厅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羊毛毯,六七个小孩子正在上面玩玩具。孩子们的年纪从一岁到五岁不等,但彼此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社会。天真的热烈的直率的气泡从心底冒出。她忍不住露出微笑。童真会传染。她本来就觉得自己笑起来很可爱,准确地说,脸的下半部分,长得特别可爱。别人也一直这么说,包括那些男人。“最性感的部位就是牙齿,最动人的是你的微笑。”藏在内衣里的信就是证据。这时她听见了女人跟刚才开门的那个人在讲话。那个人估计是这里的主人,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性,身材高大,皮肤细腻,一直笑眯着眼睛。她们声音不大地交流,但她全部听得一清二楚。女人问:彬彬呢?房主回答:在房里刚睡着,哄了半天,不巧你就来了。女人接着问了孩子的饮食和作息情况,房主一一回答。问完这些后,女人要去看看孩子,于是房主带着女人进了卧室。她不好意思再跟上前去。过了一会儿,俩人走出来,女人的神情看上去像是通了宿便一样轻松愉快。仿佛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她冲女人笑了笑,女人回以致意。她们之间第一次有了善意的互动。这时女房主才留意到她,问女人:这位是?女人回答:一位朋友。
她们坐在沙发上等待。这是一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放大。女房主为她们端来了咖啡。女房主,一个经验丰富的操盘手,调控着空间内的情绪变化,一会儿坐到地毯上去陪孩子们玩耍,一会儿去厨房为大家切水果,一会儿独自倚靠在桌子旁边专心地喝着水。当她沉静的时候,她是活泼的;当她活泼的时候,她却又好像自个儿在思考着什么。沙发上的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以一种彼此都觉得舒适的频率。女人问她: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她告诉女人:杨惠纯。你呢?女人说:庞小蒙。她说:彬彬是你孩子吗?女人迟疑了一下,回答:没错。她问:多大了?女人说:四岁了。四年了。意味着比她多认识了三年,或许还要以上。酸溜溜的感觉悄悄在聚拢。女人的脸确实像是一张比她更深沉的脸,不像她那样,看起来苍白、猴急、忧虑、奔突、易碎,携带着语词的灼热和混乱。当然,也许,几年前,两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样的假设让她心里好受。女人告诉她,孩子在这里也待了有四年了。她说: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呢?女人叹了口气:我也想啊,可是我那里的环境不适合他,还是让他在这里成长,这里一切都好。她问:房主是你朋友吗?女人说:对,算是吧。她看了女人一眼,说:这儿确实不错啊。她本来还想接着说点什么的,可是说完這一句,气管里好像被什么扯了一下,顿时停住了。女人接着说:是啊,这里办了有五六年啦,是她老公临走前的心愿,哎,得了那种——只要得了就好不了的病,他们俩也没孩子,她老公走后,她一个人掏了所有积蓄买了这套房子,办起了这家托儿所,她把这里弄得简直跟福利机构一个样,进来的孩子,穷的,单亲的,长得不好的优先,收的费用又不高,所以她自己也只能勉强维持着。她们说这些话时,趁着女房主正在厨房里忙活。勉强维持?她反问了一遍。女人回答:没错。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孩子午休醒来。他踮着脚尖,扭动门把手,把门打开,从房间里走出来。当时坐在客厅的三个女人都愣了一下。庞小蒙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孩子招手:彬彬,过来跟妈妈玩。彬彬咧嘴笑了(一艘船游荡到海底岩洞深处所发出的探照光线),他轻快地跑过来,仿佛滚动的黏糊糊的糖球,跳进了母亲的怀里。从那一瞬间开始。西斯廷圣母。圣母的婚礼。坐着的圣母。卡尔代利诺的圣母。金丝雀圣母。带金莺的圣母。草地上的圣母。花园中的圣母。福利尼奥的圣母。椅中圣母。阿尔巴圣母。一群圣母和圣子的黏合体。从草坪滚到山上,从山上跳到云端,从云端坠入大海,从海面潜入海沟。杨惠纯坐在一旁,她感觉自己尴尬得像是手脚都脱离了位置,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女人只要是有了孩子,都会变成这样吗?她伸手摸着自己的肚子,摸到了一些褶皱的纸张。还好,只是纸张,不是孩子。纸张也不可能变成孩子。她还没有中过流弹,除了运气好,她自我保护的措施也很严格。即便是对于那个男人而言。她宁愿为此跟他翻脸。他很迷人,就是脾气暴躁。这个缺点是伴随一生的印记,谁都有这么一个印记,谁都无法抹去。杨惠纯记得,有一次,因为她拒绝了男人“不戴套做一次”的要求,男人把她家里几条冈本的库存全部扔在煤气炉上面烧掉了,离开前,还摔烂了她家的门框。整整半个月,他都没有过来找她。那时候,他们已经好上了,正是你侬我侬之时,她根本没跟他收过费。她为此伤心了很久,尽管如此,她也没有屈服。她的目光停留在庞小蒙的肚子上面,那里早已没有任何痕迹。那里平滑而塌陷。塌陷是应该的。她仿佛觉得,庞小蒙是一个温柔的人,杨惠纯这样想,考虑到这个,塌陷也不是不能承受的意外之事。一个执念和柔软的塌陷。能够且正在把一切吸入。
他们准备离开。庞小蒙、庞小蒙的孩子彬彬还有杨惠纯。女房主和他们告别,带着习惯的眯笑,把他们送到门口。在电梯里,两个女人分别站在一侧,小男孩处于她们之间。肯定不是故意这样站的,但多少显得有些好笑。彬彬左边看看自己的妈妈,右边看看杨惠纯,接着又转过头去,说:“妈。”庞小蒙说:“嗯?”彬彬说:“这个阿姨是谁?”庞小蒙说:“妈妈的同事,叫纯姨。”彬彬转过头来说:“纯姨好。”杨惠纯也笑着说:“彬彬好。”同事这个词语让她觉得挺幽默的。她以为庞小蒙会说是朋友。多年至交。好朋友。坏朋友。献血时偶遇的朋友。一起看过五十部电影的朋友。认识了一天的朋友。一个小时前刚刚搭讪的朋友。无限派生的词语。可她没想到,庞小蒙说了另一个词语。这个替换而来的词语把所有的关系链条尽数斩断。很粗暴。但她觉得好笑。他们一块走出电梯,沿着来时的路,母子俩走在前面,杨惠纯跟在后面。母子俩有很多话可以讲。但是杨惠纯已经不觉得尴尬了。她尽量把他们的讨论听得一清二楚。她觉得自己也是他们的一部分。两个半人。她了解自己的这种愿望,因为她喜欢他们俩母子。就是这么简单。
下午四点钟。有点早,有点晚。雨后的空气渗漏着一种古代绢帛的颜色。他们谈论着下一步该去哪里。杨惠纯以为他们早已经商量好的,加入他们的话题后,她有些惊讶,你们为什么不去游乐园呢。对哦,游乐园,是个好主意,离这里不远,又可以玩好一会儿。她觉得没有理由会不想到那里去。可是庞小蒙母子俩讨论的方案里,游乐场的选项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等到她提出来,他们又一致爽快地同意。彬彬说:好久没去过游乐园了啊。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们走到路边打车,一辆银灰色的丰田停在他们面前。杨惠纯并不太想坐上去,可是庞小蒙和彬彬先进去了,她不得不也跟着进去,她没有坐在副驾驶位上,而是跟他们母子挤在后座。司机回过头,跟她打了照面。他剪着一头板寸,下巴留着胡子。某些方面上看,他跟上次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是有点像的,包括开的车的模样,但是她知道不是同一个人。面前这位是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辈子都能遇到好人,好人只跟好人交往。这些话也只有乡下的父亲会信。每次回家她都会跟父亲冷战,隔着一张饭桌,两人甚至坚持一个月不说话。父亲每天在家里给祖宗上香磕头,逢节日又到庙里给佛祖烧香,他强逼她同自己一起去,“不然你会下地狱的”,父亲跟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是,下地狱。新港一街的人都会下地狱,新港二街的也会下地狱,新岸小区的都会下地狱。她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的都是一群烂人,烂人跟烂人交往。杨惠纯朝庞小蒙和彬彬看了一眼,彬彬也抬起眼睛看她。彬彬的眼睛大大的,带栗色,不像他爸,像他妈。庞小蒙也住在新岸小区里。但是他们俩母子都不是烂人。有这点就足够了。
车上度过了十分钟,司机把他们送到了游乐园的西门口。付完钱后他们从车里出来,依旧是庞小蒙母子走在前面,杨惠纯跟在距离他们身后一步的距离。彬彬一直跟母亲谈论大象和狮子的事情。他说,一头狮子肯定打不过大象,但是十头狮子就难说了;白天狮子打不过大象,到了晚上就难说了。很戳心的话。都不知道这孩子哪里看来的这些东西,杨惠纯想,是不是去动物园会让他更高兴一些呢。他们走到售票处,杨惠纯争着给他们三人买了票,然后从月牙形的门洞里进去。导览图就在门口附近,他们站在前面看了一下,彬彬说,我要去玩波浪飞椅。庞小蒙说,那个离这里太远了。飓风快车呢?不行,你年龄不适合。转转鸟好了。庞小蒙说行,那就去吧。杨惠纯走在前面带路。她看到迎面走来的成双成对的人们手上至少拿着一个纸风车,要么是一杯冰激凌,像是某种标记。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吗?他们有父子,有母女,有父女,有母子,有情侣,没人像他们这样三个人一块走。她回过头去,问彬彬:“彬彬你要冰激凌吗?”彬彬说:“要啊。”她说:“要什么味的?”彬彬说:“香草味的。”走了一会,果然看到了甜筒售卖点,在一个蘑菇建筑下面,挨着海洋3D世界的入口。两两一对的人群从前面经过,绕蘑菇建筑一周,接着又像花苞一样四散。杨惠纯从人缝中钻入,给三个人分别买了不同口味的冰激凌。庞小蒙嘴里说着不要,但还是接过去,用嘴巴跟最上面的奶油接了下吻。杨惠纯看到彬彬舔得特别快,就问:彬彬,好吃吗?庞小蒙接了一句:“快说谢谢纯姨。”彬彬扬起头,唇边还沾着冰激凌,眼里都是荡漾的笑意。彬彬笑起来很像自己,楊惠纯想,确实如此,她早就这么觉得了,虽然自己跟彬彬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这浪漫的笑容变奏曲。这甜品回收处。如果小时候有甜品吃的话,她也许会更快乐一些。但是父亲是绝对不允许的。庞小蒙说:“彬彬就喜欢吃甜的东西。”杨惠纯说:“是啊,小孩子都喜欢。谁不喜欢呢。”庞小蒙说:“怕他吃坏了牙齿。”
不多时,走到了转转鸟前面。那里已经排起了一条队伍。他们三人排在后面。借此空隙杨惠纯和庞小蒙聊了会儿天,这次她们不像之前感觉尴尬了。杨惠纯发现庞小蒙其实并不像外表所呈现的那样。庞小蒙某些方面和自己还挺相似。毕竟住在同一片小区,同一职业,跟同一个男人有过关系。她问庞小蒙:“你喜欢傅秋来哪点?”庞小蒙说:“性格吗?”杨惠纯说:“对,性格。”庞小蒙说:“我喜欢他多情,滥色,我喜欢他招人喜欢。”杨惠纯有些惊讶地看着她,说:“你是认真的吗?”庞小蒙说:“认真的,你觉得很奇怪?”杨惠纯说:“乍一听还挺奇怪的,不过仔细想想,他招人喜欢这点,不假。”庞小蒙说:“我爱他,连他一切弱点都喜欢。可那不是他弱点。他很自信,天生迷人,好色,多情,这些我都做不到。真的,我羡慕他,因为我做不到,也没有他的天赋。我一直都很自卑,死板,冷漠,跟块棺材木头没啥分别,别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杨惠纯睁大了眼睛,说:“你怎么会这样想自己?”庞小蒙说:“他也说。他跟我说,小蒙,你特别不招人喜欢,你跟我不太一样,你跟别人都不太一样,我不太喜欢你这样,我觉得跟你没法交流,你太孤僻了,跟你交流我觉得自己很疲惫。”杨惠纯说:“他真这样说的?”庞小蒙说:“嗯,说了这话,第二天他就走了。再没出现过。”杨惠纯说:“你们好了多久?”庞小蒙回答:“三个月吧。”说到这时,场内的提示音响起,轮到他们一拨人进场玩了。庞小蒙牵着彬彬的手,走到其中一个飞船座位旁边,她用手抱起彬彬,把他放在座位上,然后自己也坐了上去。杨惠纯坐在后面另一只鸟形飞船上。音乐响起,飞船开始启动,爬升,绕着中心旋转,逐渐加快,然后变慢,向下俯冲。杨惠纯觉得自己像一颗滚石滑落悬崖。被某人拾起,又掷向山顶。耳边回响着机器呜呜呜的声音。这声音和游戏音乐混杂在一起,挤压,对抗,形成复调。两个影子。两个影子在心里凸现。一对恋人在争吵,女人扇了男人一耳光,男人把女人打倒在地上。三个月!杨惠纯喊道。什么?庞小蒙没听清,回过了脸。我说——半年!杨惠纯说。什么半年?庞小蒙说。我跟他好了半年!杨惠纯大声地说。庞小蒙点了点头,把头转回去。彬彬正紧紧抓着母亲的手,紧张地大叫。过了一会儿,飞船渐渐停下来,三人从座位上下来,彬彬说:“妈妈,我还想再玩一次。”庞小蒙和杨惠纯相互对视一眼都笑了。杨惠纯说:“来,彬彬,过来,纯姨抱你上去。”于是彬彬走过去,让杨惠纯抱起来,他把两只手搭在了杨惠纯的脖子上,那一刻杨惠纯心里一动。他的两只小手充满了能量。直到坐到座位上,他才把双手撤走。杨惠纯跟庞小蒙说:“让彬彬一个人坐,没问题吗?”庞小蒙说:“没问题。”飞船再次启动后,她们两人走到塑料围栏旁边等。杨惠纯突然很想抽烟,但她控制住了。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庞小蒙说。杨惠纯尴尬地笑了笑。接着庞又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的事?”杨惠纯说:“我想想,几个月前,四个月吧,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去年的事了。”庞小蒙盯着她的脸,像是刚认识她一样,说:“你还喜欢他。”杨摇头说:“不不。”庞说:“你在说谎。”杨说:“我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庞说:“我不信。”杨惠纯不说话了,过了会儿,突然说:“我知道他在哪里。”“你说什么?”庞小蒙说,她明明已经听见那句话了,可是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她的眼睛瞟向前方,她的孩子,彬彬,正在朝她们走来。
他们离开转转鸟,沿路走到4D影院,刚好赶上放映场次。影院在三楼,他们跟着人群,沿着木制的楼梯上去,在门口的铁栏旁边排了一会儿队。过程里她们两人什么话也没讲。空气有点闷。一点点暮色从天窗斜着掉下来,映在人群旁边的墙上,成一个耀目的Z字。彬彬显得比之前都安静,他两只手抱着母亲的大腿,仿佛抱着一根巨大的桥柱。宁静会传染。庞小蒙一动不动,背对着杨惠纯,腰挺得直直的,从后面看上去,杨惠纯觉得庞小蒙有一米七。当然她没有那么高,一米六八大概是有的。算是比较高挑了。他们一块进场的时候,杨惠纯跟在庞小蒙后面,她踩着庞小蒙的影子,特别有安全感。此刻在她眼里,庞小蒙是一块上宽下窄的棱形,黑色,阴晦,因为背对着自己的关系,她想要上前一步,更进一步地,把对方转向自己。选座位的时候,她坐在庞小蒙的旁边,本来她可以坐在彬彬旁边的。戴上眼镜,动画开启,座位开始上下腾跃,扶手喷出的水雾盖在了脸上。她们同发出惊叹。杨惠纯趁机把手放在庞小蒙的手上,刚一接触,她们马上收回手去。杨惠纯觉得庞小蒙心里有一点微小的愤怒,因为自己也是。她有些失望。但还没有放弃。远没到那个时候。混乱。无法言说,并不是不可描述,而是没有到达语言产生作用的层面。仿佛楼上邻居的水管爆裂了,水流不断从你天花板钻入地面,你能冲上楼去,把邻居的门撬开,把他拖出来揍一顿吗?不会。不是一个层面。动画放映完后,他们沿着通道走出影院,彬彬的情绪已经被点燃,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稍微脱离了他母亲的范围。庞小蒙和杨惠纯走在后面。杨惠纯想,不管如何,自己一定会说出来,不管她同不同意。这是唯一的方法。他们走到外面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晚了,四周的事物显示着迟钝的色泽。庞小蒙叫着彬彬的名字,彬彬跑过来,跟母亲说:妈,我想去尿尿。庞小蒙说:“去吧,我们去找找厕所。”公共卫生间离得不远。性别明确。彬彬去蓝色标记的一边,杨惠纯和庞小蒙去红色标记的一边。她们各自走进一间厕所,两间紧挨着,隔着一道树脂高压板墙,能相互听见尿液冲击马桶壁的声音。她们认为对方都听见了。咳,杨惠纯说。那边没什么动静。她接着说下去:“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带你们去见他,怎么样?你和彬彬。”马桶冲水的声音。马桶盖被掀起的声音,嗒的一声响,像是老迈的牙齿攻破坚硬的核桃。杨惠纯接着说下去:“彬彬还没有见过他吧?你觉得这样没问题吗?我再说一遍……”她边说边从厕所里出来,刚好庞小蒙也转过身来,正对着她,她吃了一惊,顿了一下,话没再接下去。我答应你了,庞小蒙说,我们去见他。
她们从卫生间出来,彬彬已经站在花丛旁边等待了。再去玩一玩吧,他说。不了,庞小蒙说,有点晚了,下次再玩好不好?彬彬嘟起嘴说:“好吧。”他像一束光从花丛钻进了母亲的衣服里。他们沿着同来时相反的方向离开,在路上,彬彬一直紧紧贴在母亲的大腿外侧,也许是母亲在用手拼命地摁住他,仿佛只要一松懈,孩子就会瞬间飞走。杨惠纯几乎看不清楚彬彬跑到哪里去了。天色一暗,她就几乎看不清东西,她有夜盲症,每天都在补维生素A。现在她觉得只有两个人在走。自己还有庞小蒙。彬彬已经飞走了。彬彬还没有来到。彬彬像是一个不定量。也许在,也许不在。杨惠纯跟庞小蒙并肩走在一起,步伐一致,某种恐惧而乞怜的情绪不由自主地从她心中升起。她不停地跟庞小蒙聊天,她控制不住自己。傅秋来住的地方,在郊区,又穷又破,保证你去了一次就不想去第二次了。是吗,比我们住的那小区还破?破得多!你见了他,就跟他说,让他搬回来住,你们俩住一块,多好,一块儿养彬彬。真的吗,你说他会愿意吗?有什么愿不愿意的,自己的孩子,难道还不管了?他见了彬彬肯定会吓一跳。为什么?他肯定会以为是我随便找个孩子骗他来的。他要是敢这么想,这么说,咱俩就把他家房子给烧了。哈哈哈,咱俩一起烧吗。当然了,一起烧,他没了房子,还不得灰溜溜跑回来和你一块住。没错,那时候我就把彬彬从池鱼屋接回来。你不是说咱们那里环境不好吗?到那时候我们就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一个好的地方,我肯定不干那行了,找个正经的工作,他也是。“她们”说着说着,到了游乐园门口,开始叫车。叫来的是一辆雪铁龙,司机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像来时那样,“她们”朝后座挤进去,杨惠纯发现,这次后座的空间显得宽裕多了,不像来的时候那么挤。车的规格并没有大多少。她感到一点惊讶,但是这点惊讶很快就过去了。上车后,司机问“她们”去哪里。杨惠纯犹豫了一下,用一种不确定的声调说:“紫荆……”这时庞小蒙突然抢了一句:“淳安西路。”杨惠纯看向庞小蒙,她睁大了眼睛,对方也看过来,对方的眼里隐藏着栗色的深渊。杨惠纯非常难过,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把头转向车窗的一边,天好像又开始下雨,水珠之城结在玻璃上,仿佛某种飞虫的卵。
到了淳安西路,他们从车上下来,三个人都下来了。彬彬出现了。他刚刚从母亲的身体里分离出来。杨惠纯看到了彬彬。她快要不认识这个四岁的小男孩了。他安静地处于时空中,像他的母亲一样安静,他在母亲的体内待得太久了。杨惠纯朝彬彬喊他的名字。他抬起头,看向杨惠纯,眼睫毛似乎细微颤动了几下。他回答:“纯姨。”楊惠纯伸手去触碰他的肩膀,石一样坚硬,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纯姨带你去见一个重要的人,杨惠纯说,好不好?彬彬看着杨惠纯,摇摇头。我们走吧,庞小蒙说。母亲已经准备要过马路了,她的双手插进棉袄的兜里。杨惠纯牵着彬彬的手,跟在庞小蒙后面,他们走过马路,向右拐弯,直走,向左拐弯,从小铁门进去。他们能看见小区内的一切。他们经过人工池塘的时候停下脚步,不知道为什么要停下来,庞小蒙先停下来的。池塘里只有半池水,没有鱼,一条也没有。当然,客观来说,不一定没有鱼。可是有时候感觉比客观更重要。他们站在水边,风一阵阵吹来,凉意布满了全身。头发正悄悄地被露水打湿。黑暗里,彬彬又不见了。杨惠纯听到庞小蒙叫彬彬的名字。彬彬没有应答。庞小蒙又说:“我们上去了好不好?这儿风大。”过了一会儿,才传来彬彬的声音:“池塘里有一只气球。”母亲说:“哪儿呢?”彬彬说:“在那儿呢。”母亲说:“我没看到。”彬彬说:“是一只金鱼,它是碎的,没气了,看起来烂烂的,可是身上的鳞片真的很好看,前边是金色的,后面是红色的……”母亲说:“嗯,我看到了。只有夜盲症的杨惠纯没有看到。下次给你买一只,怎么样?”母亲说。彬彬“嗯”了一声,还是很小声,但是透着喜悦。我们走吧,庞小蒙说完转过身去,杨惠纯紧跟着她,走出树影的一瞬间,杨惠纯又看到彬彬像往常一样,紧贴在母亲的身侧。准确地说,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母子的情形。文艺复兴三杰也无法达到的程度。他们走进楼道里,乘电梯上楼,1802。杨惠纯还记得那个数字。叮的一声响,走出电梯,拐个弯,没错,门牌旁边的几个字。池鱼屋。杨惠纯对这个托儿所的名字印象深刻,虽然她一点也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是她知道这是一家很棒的托儿所,助人为乐、充满爱心,始于生命之终,终于生命之始。她回去会掏自己的积蓄资助一下这家托儿所的。她已经下定决心了。门打开后,是笑眯着眼睛的女房主走出来,说:“玩完回来啦?该吃晚饭了。”这时候他们才觉得肚子发饿。庞小蒙把彬彬往女房主怀里一送,说:“任务完成啦,该交接了。”女房主笑眯眯地回答:“没问题,交给我吧。你们也进来吃晚饭吧。”庞小蒙和杨惠纯同时摆摆手,说不了,回去再吃。客气了几番后,她们准备下楼。彬彬站在门口,跟母亲告别。“一只大金鱼,会飞的。”他提醒母亲。
杨惠纯和庞小蒙乘电梯下楼。在电梯里,庞小蒙一下子就哭了,稀里哗啦的,跟杨惠纯完全不同,杨惠纯要是哭的话只会一下一下地抽泣,她可从来没有试过像庞小蒙这样的哭法,她没有这样的天赋,她是这样跟庞小蒙说的,然后使得庞小蒙停止了哭泣。庞小蒙想笑来着,可是她一下子做不到。杨惠纯本来也想哭,可是她看到庞小蒙哭成这样,就打消了这个冲动,因为她觉得自己是没法在一个哭成这样的人面前哭的,也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她只知道,不应该两个人像这样同时哭。庞小蒙说:“对不起。”杨惠纯说:“什么?”因为庞小蒙带着哭腔所以没听清楚。庞小蒙又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杨惠纯说:“对不起什么?”庞小蒙说:“对不起,我食言了,我没法跟你去见他。”杨惠纯说:“没事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没法带你去见他。”庞小蒙说:“我知道。”杨惠纯说:“我们都知道。”庞小蒙说:“你可真明智。”杨惠纯说:“你也是。”庞小蒙说:“你真可爱。”杨惠纯说:“你比我更可爱。”庞小蒙说:“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的。”杨惠纯说:“当然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不是吗?”庞小蒙说:“是,我们是好朋友,不是什么鬼同事。”杨惠纯说:“我们是好朋友,也是好同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庞小蒙说:“你说得对,我喜欢你。”杨惠纯说:“我也喜欢你,我还喜欢彬彬。”庞小蒙说:“彬彬也喜欢你,彬彬悄悄跟我说了,他特别喜欢纯姨。”杨惠纯说:“彬彬真是个好孩子。”庞小蒙说:“你也是个好孩子。”杨惠纯说:“我26岁,你大我几岁来着?”庞小蒙说:“大你5岁。”她们从电梯走出来,沿路走出小区,在路口准备叫车。这时杨惠纯像是记起了什么东西似的,说:“我还有事,就不跟你一块回去了。”庞小蒙说:“怎么了?”杨惠纯说:“我得去寄封信。”庞小蒙说:“太晚了,明天再寄吧。”杨惠纯摇摇头:“不,今天一定要寄走。”内衣里的信纸又开始发烫。她们的情绪已经恢复冷静了,对于刚才说的话,感到有些难为情。她们开始说临别前的话。谢谢你。谢谢一天的陪伴。各自保重。然后她们相互道别,没有相互拥抱,各自慢慢离开。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