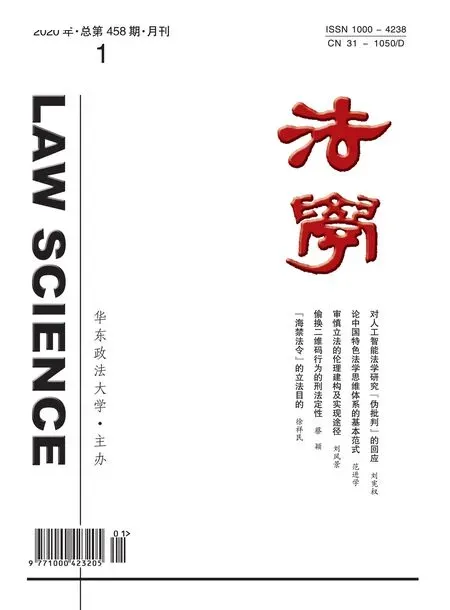自主占有与简易交付
●庄加园
我国《物权法》第23条前段“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之规定被称为交付原则。据此,动产所有权移转以交付为生效要件。但当受让人由于各种原因已对转让物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时,所有权移转所需的占有外观改变已经实现。立法者不必固守僵化的交付要求,强行要求受让人先将转让物返还给出让人,再由出让人送还受让人。此时,只要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移转所有权的合意就可引起所有权变动,〔1〕Vgl. Staudinger/Wiegand, 2011, § 929 Rn. 117.这就是《物权法》第25条有关简易交付规定的适用情形。
多数观点将简易交付归入观念交付,〔2〕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王泽鉴:《民法物权》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魏振瀛主编:《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页;陈华彬:《民法物权》,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刘家安:《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申卫星:《物权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少数观点则认为它与观念交付无涉,不过是受让人先行占有标的物。〔3〕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另有学者将简易交付直接称为“先行占有”,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41-442页。这种性质上的争论应该如何看待?简易交付多表现为租赁人等他主占有人已经取得占有,但若受让人以自主占有人的面目出现(如盗贼),我国《物权法》第25条是否也有适用余地?若受让人仅获转让物的实际控制力,并非民法上的占有,如作为占有辅助人为他人占有,能否根据简易交付获得所有权?如转让物处于对任意人开放的状态,简易交付可否适用?
立法者为实现便捷交易的目的,允许当事人仅通过法律行为移转所有权。但该法律行为究竟何指?学说因其是否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而持有不同立场。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于,常见的承租人等他主占有人作为受让人如何在简易交付中获得自主占有。如果出让人与受让人仅就法律行为层面达成移转所有权的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层面的自主占有移转究竟如何发生?
国内相关学说及司法解释几乎一致认为,简易交付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但德国民法典针对简易交付的善意取得设有不同的构成要件。〔4〕参见叶金强:《取得占有与动产善意取得》,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要求善意受让人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这一构成要件相较于现实交付显得更为严格。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有无必要对我国《物权法》第106条中的“交付”采取必要的限缩解释?
一、误解与澄清:事实支配力与自主占有
有学者认为,观念交付是间接占有的移转,非真正之交付,乃动产占有在观念上的移转。〔5〕同前注〔2〕,谢在全书,第99-100页。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并认为简易交付和占有改定、指示交付一样构成对现实交付的替代,属于观念上的交付。〔6〕同前注〔2〕,王泽鉴书,第 133页;同前注〔2〕,史尚宽书,第38页;同前注〔2〕,王利明书,第376页;同前注〔2〕,魏振瀛主编书,第230页;同前注〔2〕,崔建远书,第88页;同前注〔2〕,王轶书,第148页;同前注〔2〕,申卫星书,第173页。“观念交付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即使不实际移转占有,也可以完成交付行为。”〔7〕同前注〔2〕,王利明书,第376页。有学者以受让人的占有意思变动论证其合理性,简易交付之所以成为观念交付,是因为“转让人仅仅将自主占有的意思授予受让人,使受让人从他主占有变为自主占有,以代替现实的交付行为”。〔8〕同前注〔2〕,王轶书,第149页。只有梅仲协等少数学者认为替代交付的只是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让与返还请求权),简易交付不属于观念交付。〔9〕同前注〔3〕,梅仲协书,第520页。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2句的作用评价如下:“这一规定只是用于明确如果在物权合意达成之前,《德国民法典》第929条要求的占有取得前提已经完成,那么所有权移转的效力就已满足。《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2句并非独立的法定取得要件。”〔10〕Vgl. BGHZ 56, 123, 130.由此,简易交付并非“观念化”的交付,而是交付的修正形式。
这一争论更多地归因于对占有概念的分歧。深受德国民法影响的我国相关学说将占有界定为人对物的事实上支配力。占有移转也就自然伴随着事实支配力的变化,现实交付便是最典型的事实支配力更替,即由受让人替代出让人对转让物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在简易交付的典型情况下,受让人在动产物权移转前已经直接占有转让动产。因受让人提前实现对物的事实上支配,双方没有必要再行往复移转占有。正因为如此,当事人在达成移转动产物权的法律行为时,所有权基于合意直接移转。而在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的情形中,仅有双方当事人设立或移转动产物权的意思尚不足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必须发生双方当事人的占有意思变动,使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无论是在占有改定中获得创设的间接占有,还是通过让与原物返还请求权移转间接占有,都是受让人藉由他人(出让人或占有媒介人)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尽管间接占有已经远离占有概念的核心区域,学界借助于媒介人对物的事实支配力扩大占有的概念。由此,学说将占有改定和让与返还请求权都作为交付替代形式,占有移转的概念也通过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得以扩大化。
然而,罗马法虽将占有作为独立于权利的事实对待,但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支配秩序或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力。这就使得一个物上只能存在一个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力,而无法并存两个占有。只有当占有人以所有权人的意思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时,这种抽象的支配秩序才具有排他性效力。所以,罗马法只是将自主占有作为真正的占有,赋予其占有诉权、取得时效等法律救济。从这一视角出发,无论哪种占有移转形式都是为使受让人最终获得自主占有,即受让人以所有的意思对转让物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由此,出让人都会与受让人达成自主占有移转的合意,或将其更精确地表达为出让人为受让人的利益放弃自主占有,受让人接受自主占有。在现实交付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通过交付的方式表现出移转自主占有的意思。“短手交付”的常见情形多为承租人、借用人等已经对物行使事实上的控制力。由于他们并非以所有的意思占有,而是为他人而占有,所以仅处于持有(Inhabung)的地位,通常不能享有占有诉权、取得时效等保护。以上这些他主占有人借助于“短手交付”的方式,与出租人、出借人等达成合意,以便获得自主占有。在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的情形中,受让人虽仅获得间接占有,但伴随所有权移转的占有意思仍为自主占有。只要受让人以所有的意思占有即可,究竟是自己控制还是委任他人控制转让物并非决定性因素。
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源自不同的占有概念,由此也影响对占有移转的分类。简易交付要求受让人提前实现对转让物的事实支配力,其适用的多数情形也确实蕴含双方对自主占有移转所达成的合意。简易交付若侧重于受让人先行占有转让物,也难以回避受让人的占有意思变化,即自主占有如何从出让人处移转于受让人。因此,两种观点各自反映了简易交付的不同解释路径,它们的分歧对法律适用没有太大影响。
二、占有形态与适用范围
(一)受让人占有意思的类型
学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将我国《物权法》第25条中的“简易交付”等同于罗马法上的“短手交付”。〔11〕同前注〔2〕,马俊驹、余延满书,第308页;参见杨震:《观念交付制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75页;杨代雄:《拟制交付在物权变动中的效力——兼论我国〈物权法〉第26条的修订》,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88页,注2。当借用人已经在事实上支配借用物时,因其仅为他主占有,并未取得罗马法上的占有。借用人若想取得借用物的占有,只需借助于“短手交付”(brevi manu traditio)就可移转占有(以自主占有为前提)。〔12〕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3页。《学说汇纂》就此引用盖尤斯的观点:“有时,即使没有交付,纯粹的所有权人的意志即足以使物转让。例如,我向你出售已因使用借贷、租赁或寄存而在你之处的物;虽然事实上我并未出于买卖原因向你交付该物,然而,我现在出于买卖的原因允许这些物在你之处,(这种意志)使该物归你所有。”〔13〕D. 41, 1, 9, 5.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41卷,贾婉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简易交付的常见案型为借用人、承租人等基于占有媒介关系先行占有转让物,事后与出借人、出租人等达成合意移转所有权。受让人通常为他主占有人,其究竟为直接占有抑或为间接占有并无影响。例如,出租人甲将一台电脑出租给乙,而乙又将该电脑借给丙使用。此时形成多层的占有关系,即丙成为该电脑的直接占有人,乙是丙的间接占有人,甲则是最上层的间接占有人。若甲打算将该电脑所有权让与乙,并且双方已达成移转该电脑所有权的合意,乙作为间接占有人也可基于简易交付而获得该所有权。
即便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也不妨碍双方基于简易交付移转所有权。例如,甲拾得乙所遗失的小狗,由于其酷爱养狗,便收养该犬并悉心饲养。由此,甲便以所有权人的意思占有该犬。数周后,甲在街上遛狗,恰巧遇见所有权人乙。乙主张该犬为其所有,只是于数周前走失。甲表示其酷爱该犬,请求乙忍痛割爱。在双方达成移转该犬所有权的合意时,甲能否获得该犬的所有权?如果简易交付仅以受让人为他主占有人为前提,那么甲作为自主占有人,已无由他主占有变为自主占有的必要,占有意思如何发生变动?
即便受让人初始基于占有媒介关系占有他人之物,若其嗣后改变占有意思,由他主占有变为自主占有,侵占他人之物亦有可能。若出借人、出租人发现出借物、出租物遭到借用人、承租人侵占,而后表示愿意转让侵占物所有权,这时受让人同遗失物、盗赃物的占有人一样处于自主占有的地位,并无必要借助占有改定先从自主占有转为他主占有,再基于“短手交付”重新获得自主占有。
在以上例子中,受让人皆为恶意自主占有人,明知自己并无占有本权,但不能排除受让人为善意自主占有的情形。例如,虽然移转动产所有权的让与行为无效,但双方在移转动产所有权时不知无效情形。受让人误认为获得该动产所有权,一直以自己占有的意思对转让动产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若受让人嗣后发现出让人在转让所有权时无行为能力,出让人的法定代理人能否与受让人通过合意转让该占有物的所有权?
从比较法出发,与我国《物权法》第25条相关表述相似的是《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2句中的“简易交付”。该句最初并非针对受让人为借用人、承租人、保管人等他主占有人的情形,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仅将其适用于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的类型,如受让人拾得遗失物,或者受让人盗窃他人之物且以自主占有之面目出现于公众。因为在简易交付的通常情形下,作为他主占有人的受让人须与出让人达成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而在受让人作为自主占有人时,立法者打算避免一个移转自主占有的迂回方式,即受让人不必先成为他主占有人,再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2句与出让人约定变为自主占有人。《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2句的出现,正是为了避免毫无价值的来回移转自主占有。〔14〕Vgl. Ernst, Eigenbesitz und Mobiliarerwerb, Tübingen 1992, S. 82.在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起草时,占有的概念不再限于自主占有,而是扩大至他主占有(直接或间接占有皆可)。由此,原本作为持有人的承租人、保管人、借用人等摇身一变,成为直接占有人。藉由占有媒介人方能对占有物行使支配可能性的出租人、寄托人、委托人等,则被认为享有间接占有。占有人向占有媒介人转让所有权的情况成为适用简易交付最频繁的案型。〔15〕同上注,第83页。受让人作为自主占有人反而成为适用简易交付的非典型情形。
即使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并无占有媒介关系,受让人以自主占有人的面目出现,通常也不影响基于简易交付的所有权移转。若要严格贯彻受让人获得事实支配力的理念,简易交付获得认可亦无障碍,因为受让人已经占有转让物。换言之,交付原则所要求的占有状态变化已经提前实现。〔16〕Vgl. Westermann, Sachenrecht, 6. Auflage, Heidelberg 1990, S. 290.
(二)自主占有与“依法”占有
非基于出让人意思而占有的动产亦能适用简易交付,其通常发生于盗赃物、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情形。由于受让人已获自主占有,所有权变动之前的占有已实现转让物的将来归属状态,这也符合简易交付的规范目的。例如,甲盗窃某画家乙的作品,被警察抓获。乙发现甲酷爱其艺术作品,又具有鉴赏能力,就向甲表示赠与其画,甲在为承诺时便获得该画所有权。〔17〕同前注〔2〕,王泽鉴书,第136页。又如,V的一台打字机被盗后,打字机出租店K获得该打字机,并且K将其出租给M。在K支付补偿费后,V同意K保留这台打字机。〔18〕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当事人在订立旨在变动物权的法律行为时,由于占有状态已经实现,仅基于合意便可移转所有权。受让人是否基于出让人的意思获得占有在此并不重要。〔19〕Vgl. Staudinger/Wiegand, 2004, §929 Rn. 123.
但稍加检索我国《物权法》第25条的文义,便会发现该条所要求的占有前提必须为“依法”占有。如果受让人在所有权移转之前占有的动产属于盗赃物、遗失物,是否因不符合依法占有的要求而排除简易交付的适用可能性?〔20〕这一“依法”占有的困扰也出现于我国《物权法》第26条关于指示交付的规定。可供选择的解释方案是将依法占有等同于合法占有,但这将导致盗赃物之类无本权的占有脱离物无法适用简易交付。若贸然将依法占有解释为合法占有,将其等同于有权占有,势必限缩简易交付的适用范围,给交易当事人带来诸多不便。纵使受让人无本权占有盗赃物,之后出让人确实愿意转让该物于受让人,立法者并无理由禁止双方当事人在达成合意时移转所有权。将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相比较,当事人利益并无不同之处,歧视无权占有亦无充分理由。
早有学者指出,“依法”两字纯属画蛇添足,作茧自缚,且有害于交易便捷。在解释论上,应仿效对《物权法》第26条中指示交付内容的解释,最大限度地限缩该条中“法”的范围,将若干第三人无权占有的情形视为“依法”,而不应将其作为“违法”对待。〔21〕参见崔建远:《再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载《法学家》2010年第5期。也就是说,“依法占有”不等同于“有权占有”,与占有的本权没有关联。即使有人固守“依法占有”等同于“有权占有”,也可认为既然出让人事后同意转让占有脱离物的所有权,就表明其同意消灭原有的占有瑕疵,由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受让人的占有也就成为“依法”占有,简易交付的适用障碍得以清除。
(三)“长手交付”——“开放占有”的移转
若受让人已对转让动产获得事实上的控制力,或转让动产因其特性不易移动,使得包括受让人在内的任何人都能对该物行使事实管领力,双方当事人是否仍须按照交付原则移转直接占有?
早在罗马法时代,交易上就形成变通的交付方式。针对土地与其他较为笨重的动产,当事人可以在物的现场达成合意。如果买卖土地,出让人可以到临近的高塔向受让人展示土地的边界并表示由此完成交付,受让人也有必要到场参与,这就是所谓的“长手交付”(langa manu traditio):“如果我指示出卖人将我购买之物放到我家里,那么即使还没有人接触到该物,我也当然获得了对它的占有。又如,我购买了一块邻近的土地,出卖人在我的楼房里将它指示给我看,并且说已将空虚的占有转让给了我,那么我就像已踏入土地的边界一样开始占有。”〔22〕D. 41, 2, 18, 2. 同前注〔13〕,优士丁尼书,第 111 页。
“长手交付”在德意志共同法时期也获认可,《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2款便是明证。〔23〕同前注〔14〕,Ernst书,第 56 页。根据德国相关通说,基于合意而移转占有,要求出让人对物的占有处于开放状态,即任何人都能对该物行使事实管领力。也就是说,受让人能够不受障碍地实际控制仍处原地的物品。如放在森林某处的一堆木材,放置于自家院外的柴草,任何人行使支配力都没有障碍。倘若出让人将木材放置于自家围有栅栏的院内,则根据交易观念,并非任何人都能对此行使事实上的支配力。
尽管实务判决中尚未出现“长手交付”的表述,但已有判决将履行出租广告宣传牌的义务界定为“简易交付”。例如,在“昆明双梓广告有限公司与昆明爱邦广告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判决指出:“爱邦公司负有的主要义务是保证双梓公司对本案所涉广告宣传牌享有独家使用权,结合广告宣传牌是设置在规定地点的事实,即在本案中,爱邦公司无需将广告宣传牌实际交付给双梓公司。爱邦公司需要交付的标的物是在昆明市各小区电梯内外设置的12365质量监督宣传牌。……基于安装点位的广泛性以及安装场所和标的物本身的开放性,可以说宣传牌只要实际安装并获知具体点位信息,双梓公司即可以直接进行使用收益的。……本着简易交付属于观念性交付的特质,尽管爱邦公司未提交宣传牌的现实移交凭证,但当租赁物已安装完毕并设置在双梓公司知晓和掌控范围内时,租赁权即可由双梓公司行使,交付应视为完成。”〔24〕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四终字第32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一方面认为出租广告宣传牌的出租人无须实际交付租赁物,另一方面又主张简易交付完成了“观念性”交付。
该判决中广告宣传牌的占有移转只需当事人达成一个纯粹的合意。与现实交付的合意相同,出让人必须具有为受让人放弃自主占有的意思,即双方达成改变事实支配力的合意。〔25〕同前注〔14〕,Ernst书,第 58 页。此类“开放占有”的移转只须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简易交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受让人须于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先占有该动产。二是双方达成生效协议,并有转移占有的合意。”〔26〕同前注〔24〕。“长手交付”虽要求受让人和原占有人达成合意,但转让占有者必须是自主占有人,不能是占有辅助人、占有媒介人。倘若他主占有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开放占有的合意,并不发生移转自主占有的效力。〔27〕同前注〔14〕,Ernst书,第 60 页。
“长手交付”中的受让人虽未获得对转让物的现实控制力,只要其存在实施事实管领的可能,也应可适用我国《物权法》第25条。
(四)作为受让人的占有辅助人
简易交付的适用基础在于,在转让动产所有权移转前,受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交付的要求已获实现,所有权移转根据当事人意思而发生。若受让人虽已对转让动产行使事实上的控制力,但其并非法律上的占有人,如占有辅助人,此时,当事人能否同样基于合意移转所有权?例如,某职员正驾驶公司汽车出差,作为该车车主的雇主将该车所有权转让于他。为此,该职员废止与雇主的占有辅助关系,取得该车的所有权。同样,正在驾驶自己汽车出差的职员,也可与其雇主建立有关该车的占有辅助关系,向雇主转让该汽车所有权。〔28〕废止占有辅助关系容易使人误解为占有辅助人脱离既有的社会依赖关系。其实,转让双方所需要的仅是达成合意,使得受让人对占有物不再基于社会依赖关系而占有,而是作为自主占有人对物实施支配,实际上是“将某物从占有辅助关系中取出”。同前注〔14〕,Ernst书,第 85页。该类案型与出让人向占有媒介人让与所有权相似,都是作为所有权人的自主占有人不享有对转让物的事实支配力,而由他人对物进行实际控制。
占有辅助人虽在事实上对转让动产实施控制力,但其并非占有人,因此从逻辑出发,简易交付就无法适用于受让人未取得占有的情形。相关司法实践也有相同认识,“占有辅助人对物的支配和管领,实际上是贯彻占有人意图的表现,不是独立地支配标的物,占有辅助人不能依据占有的规定获得法律保护,故本案并不符合简易交付的情形”。〔29〕“孟富排、郭静追偿权纠纷案”,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11民终45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被查封财产的保管人究竟是占有辅助人还是占有媒介人值得深入讨论。笔者以为,被查封财产的保管人应为占有媒介人。如此一来,动产所有权如要发生移转,只能借助于对我国《物权法》第23条规定中“交付”的扩大解释。在占有人与占有辅助人作为物权变动双方的情况下,只要建立或废止其社会依赖关系,转让物虽未发生物理上的移动,德国通说也认为其满足了交付的要求。〔30〕同前注〔18〕,鲍尔、施蒂尔纳书,第359页。
针对通说的立场,批评意见指出,占有辅助人之所以被排除在占有人之外,在于否定占有辅助人对占有人行使占有保护请求权。这一基于占有保护的考虑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功能不同的占有移转。当占有辅助人已对转让物行使事实支配力时,无论这种支配力被称为“持有”或“占有”,交付原则旨在实现的占有与所有权合一的目的已经实现。这种情况与他主占有人先行占有转让物并无二致。而且就转让过程而言,占有辅助人与借用人、承租人一样,只需与出让人达成合意就获得转让物的自主占有。仅仅由于受让人并非法律上的占有人,转让双方就被强行要求移动有体物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解释者受困于概念法学,不得不拟制交付或者将有体物上的交付扩张到观念上的交付,这无疑是徒劳造法,忽视了便利交易的立法目的。〔31〕同前注〔14〕,Ernst书,第 84 页以下。也有德国学者认为,上述情形下的所有权移转究竟依据《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句,还是依据同法第929条第2句,在实质上都只需具备移转所有权的合意。〔32〕同前注〔16〕,Westermann书,第 286页。既然如此,当事人借助于简易交付实现所有权移转,在构成要件上就显得更为简洁明了。
在德意志共同法时代,“短手交付”也适用于占有辅助人受让对转让物的自主占有。这是因为占有辅助人只是为他人占有,仅处于持有的地位,并不享有法律上的占有。如果占有辅助人希望从占有人那里获得占有,只需双方达成合意便能取得自主占有。〔33〕Vgl. Wieling, Sachenrecht, 2. Auflage, Berlin und Herdelberg 2006, S. 302.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认为,出让人将物“短手交付”于非占有人的特殊之处仅在于受让人获得持有,即其已能对标的物行使事实上的管领力。该情形已被《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2款包括,因此没有必要另设条文。〔34〕同上注,第302-303页。
在此,旨在移转所有权的交付经由占有人与其辅助人废止双方的社会依赖关系得以实现,并伴随旨在变动物权而发生的占有意思变更,即受让人改为自主占有。由于占有辅助关系的废止,使得职员由占有辅助人转化为自主占有人,雇主则失去自主的直接占有。从物权变动当事人的视角出发,省却标的物的物理上移动更符合其利益。因为当事人所希望的占有状态已经实现,没有必要人为地制造麻烦,重新由受让人向出让人返还标的物,再交还于受让人。〔35〕这也正是我国立法者在规定简易交付(《物权法》第25条)时免去交付要件的理由。这一占有移转方式却不能扩展于占有人与占有媒介人之间建立与废止占有媒介关系的情形。因为在两者废止占有媒介关系时,作为受让人的占有媒介人之前已获得直接占有,通过废止占有媒介关系,其通过简易交付的方式(《物权法》第25条)取得了所有权,直接占有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由他主占有人成为了自主占有人。同理,在双方当事人建立占有媒介关系时,受让人通过占有改定(《物权法》第27条)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原来作为出让人的自主占有人由于失去所有权而变为他主占有人。出让人的占有意思虽然发生变动,但其原先便是直接占有所有物,在失去所有权后还是直接占有,只是占有的是他人之物,并未导致直接占有的移转。
由于日本法上的占有权仅限于自主占有,在受让人作为他主占有人的常见情形下,受让人并非占有人,只是对物享有实际控制力。因此,日本法上的简易交付不要求受让人为占有人,而只是要求其为现实控制(《日本民法典》第182条)。相关学说和实践没有将简易交付限制于受让人他主占有(持有)的情形,而是将其扩大为“现实支配占有物”。〔36〕参见[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94页。
由此可知,在动产所有权让与的过程中,占有辅助人与占有媒介人同样可基于简易交付受让所有权。但占有辅助人必须处于占有人支配领域之外,即出让人并未实际支配转让动产,两者同等适用才能获得承认。如果占有辅助人处于占有人的支配领域,例如工人仍在工厂使用锤子,那么占有人并没有放弃对转让物的事实支配力,其若要在原地将该物出让给占有辅助人只能借助于占有改定完成。据此,双方约定占有媒介关系,该物基于媒介关系仍停留在占有人的支配领域。〔37〕同前注〔14〕,Ernst书,第 86 页。
三、合意与“法律行为”
(一) 法律行为层面的合意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5条,“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简易交付的生效时间应为法律行为生效时。这一规定不同于《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2句“只需要关于所有权的合意”之规定,也不同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1条第1款第2句“于让与合意时,即生效力”的表述,富有特色。〔38〕我国《民法通则》并未使用“法律行为”的概念,只是以“民事法律行为”代称,并以合法性要件作为其特征。“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多在学理意义上使用,民事立法正式将其吸纳并写入《物权法》,值得关注。有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第25条所指的法律行为只包括买卖等合同。〔39〕同前注〔2〕,崔建远书,第89页。这类观点否认物权行为存在于我国民法,主张物权变动系基于合同与交付方可生效。其表现便是我国《合同法》第140条后半段“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的规定。既然买卖合同的生效与交付同步发生,所有权移转的两个构成要件自然得以满足,受让人理所当然地获得所有权。但这一解释却不符合占有与权利相区分的物权法体系。若仅从移转有体物占有的层面理解,交付只是发生了占有移转的法律效果。交付仅为行为人有意识地取得占有和丧失占有的事实行为,其意思并非针对物权变动的合意及其他法律行为世界中的意思。此外,《合同法》第140条后半段规定将合同生效的时间等同于交付时间,也混淆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不利于区分不同的法律效果。所幸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已经删除这一条文,将其归还物权法调整。
按照否定物权行为的观点,此处的“法律行为”只包括双方法律行为,即通常所说的合同。若其观点成立,则这类合同不应包括仅发生债法上权利义务的合同,如租赁、保管、委托、运输等,而是限于旨在设立、转让、移转物权的合同,诸如买卖、互易、赠与、出质等。相反观点则认为,法律行为生效时是指物权变动的合意成立时。〔40〕同前注〔2〕,魏振瀛主编书,第230页;同前注〔2〕,申卫星书,第173页。以上学者虽认为物权合意成立时发生基于简易交付的动产物权变动,但仍未摆脱我国《合同法》第140条的影响,将物权合意成立视为交付完成。这类观点多支持物权行为,认为当事人只要达成抽象的物权合意,便可引起动产物权变动。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变动的协议必须符合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否则,无效的法律行为不能产生先行占有的后果,即不能发生物权变动。〔41〕参见孙宪忠主编:《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在当事人达成物权合意时如存在意思表示瑕疵,表意人可撤销物权合意,由此使所有权移转失效。
相同的结论也出现于全国人大法工委对《物权法》第25条中“法律行为”的解读,即该条中的法律行为主要包括动产所有权人与受让人订立的动产转让的协议以及与质权人订立的动产出质协议。〔42〕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各级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物权法》第25条中的“法律行为”时,对其称谓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称其为“简易交付的合意”,〔43〕参见“南京德盛昌粮油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709号民事裁定书。有的法院将其解释为“物权让与的合意”。〔44〕参见“万小玉与王小兵买卖合同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771号民事判决书。“根据上述规定,成立简易交付的条件为:(1)被上诉人为涉案工程车的所有人;(2)上诉人于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占有该动产;(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仅有物权让与的合意,而且该合意已生效。”
在严格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法律体系中,此处的法律行为仅指物权合意,也被称为“裸露”的物权合意。在当事人基于简易交付移转动产所有权时,此时的法律行为内容应为移转所有权的合意。因为该合意作为处分行为需要出让人具有处分权、标的物特定等额外要件,若出让人对转让动产缺少处分权,则其所有权移转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依赖于其能否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若转让动产尚未特定化,移转所有权的行为也将由于客体原因而无法完成。〔45〕即便我国主流学说不承认物权行为,这一物权合意也能委身于买卖合同,无非是买卖合同既具有负担行为的内容,又具有处分行为的内容。
即便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未予区分,此处的法律行为仅指买卖、互易、赠与等旨在移转所有权的合同。处分行为的独特要件依然不可缺少,若非如此,出让人可能无权处分他人之物,严重侵害他人利益。可供选择的解释路径无非是承认买卖合同既有发生债法效力的效果意思,又具有发生物权效力的效果意思,两者需要满足不同的构成要件。其实质依然是要求让与所有权必须满足额外的处分行为要件。若回归于我国《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规定,则会过分优待违约的出卖人。这条退却之路已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3条的否定,难以重蹈覆辙。
(二) 事实行为层面的合意
简易交付所含的合意多聚焦于法律行为层面,对于事实行为层面的占有移转却关注甚少。就常见情形而言,作为他主占有人的受让人与出让人达成移转所有权的合意之后,即刻发生所有权移转,受让人也就成为转让物的自主占有人。不无疑问的是这一占有意思的转变究竟如何完成。
双方当事人就法律行为达成的合意仅在于移转所有权,此外还需就自主占有移转达成合意,使得受让人由他主占有变为自主占有。〔46〕同前注〔33〕,Wieling书,第 305页。这一合意仅针对占有事实,并不旨在发生特定的效果意思。从法律结构上观察,由于移转所有权的合意与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其构成要件自然相异。在占有改定、让与返还请求权(指示交付)之中,受让人取得自主占有同样独立于成立占有媒介关系与让与返还请求权的效果意思。〔47〕占有改定参见庄加园:《间接占有与占有改定下的所有权变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7条》,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让与返还请求权(指示交付)参见前注〔14〕,Ernst书,第281页。虽然两者多为同时发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区分,但在法律世界中却分属不同领域。自主占有取得属于事实行为领域,成立占有媒介关系与让与返还请求权则归属法律行为范畴。
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仅发生于事实行为层面,无须含有旨在发生特定效果的意思表示。简易交付所要求的所有权移转合意则需要满足法律行为和处分行为的构成要件。由于该合意属于处分行为,若出让人不享有处分权,则所有权移转行为效力待定,只能等待善意取得规则保护受让人。若所有权移转合意无效或可撤销,当事人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不受影响,则产生不同层面的法律效果。例如,所有权移转合意因错误、欺诈、胁迫而撤销;自主占有的合意仍是双方自愿为之,由此使受让人获得自主占有,即便因交易撤销导致所有权复归出让人,受让人之前的善意自主占有状态仍应受法律保护。
在适用“长手交付”时,德国主流学说认为,当事人通过合意就可实现占有取得。〔48〕Vgl. Staudinger/Gutzeit , 2012, § 854 Rn. 29. 反对学说主张该合意非法律行为,只是当事人达成的事实上的合意。参见前注〔33〕,Wieling书,第161页。这一合意并非事实上的合意,而是法律行为的合意,更确切地说是合同。因此,有关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的原理也适用。〔49〕倘若当事人由于错误、欺诈等原因达成合意,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撤销这一合意,由此导致占有物非基于出让人意思而由他人占有,即构成占有脱离物的情形。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移转占有的合意具有更高的、独立的意义。《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1款伴随的是人们在物理上对物的干预可能性,该条第2款规定仅需要双方合意就足以引起占有移转,当事人对将来的、潜在的干预可能性不如第1款表现得那样明显,为交易安全考虑,应由双方意思表示构成的合同移转占有。〔50〕同前注〔48〕,Staudinger、Gutzeit书,§ 854 Rn. 29.这一理由显得过于牵强。如果当事人通过“长手交付”移转所有权,那么双方不仅需要达成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而且需要对所有权移转达成合意。在动产所有权得以有效移转时,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因多为同时发生,解释上的独立意义较为有限。若是所有权移转因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存在瑕疵而无效,事实行为层面的自主占有移转也不能成功地发生,这将导致完全忽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尤其在当事人仅借助于“长手交付”移转自主占有而不移转所有权的情形下,如出借人向借用人交付在森林某处公开存放的木材,这一事实层面的合意达成尚需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对当事人未免有所苛求,也会给交易添加不必要的负担。
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与移转所有权的合意虽在概念上得以区分,但人们不禁将其视为法学家演练“概念体操”的副产品,其实益仍然有待澄清。笔者认为,这一区分不仅在概念上十分必要,而且在法律效果上也有重要作用。现行的民法学说之所以将其忽略,主要归因于实证法上缺乏自主占有的相关规范。先占、取得时效、孳息取得、占有推定等以自主占有为前提的重要制度在现行法上都缺少对应的条文。但在“所有人—占有人”的返还关系上,现行法仍设有对善意占有人的优待(我国《物权法》第242、243、244条)。假使受让人不知基于简易交付的所有权移转合意无效,或者出让人无权处分遗失物(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前提),而仍以所有的意思占有转让动产。若受让人面临返还所有物的请求,则其不但可以根据《物权法》第242条对于因使用而致的损害主张免责,还能向返还请求权人主张维护占有动产的必要费用。受让人若未曾从出让人手中获得自主占有,善意占有人享有的以上优待效果岂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
(一) 权利外观: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为无须登记的转让物交付给受让人。国内学界大多认为,该条中的“交付”毫无疑问地包含简易交付。〔51〕同前注〔2〕,王利明书,第 378 页;同前注〔2〕,崔建远书,第 100 页;同前注〔2〕,陈华彬书,第 259 页;同前注〔2〕,刘家安书,第106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持相同观点者参见前注〔2〕,谢在全书,第225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第18条“当事人以物权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方式交付动产的,转让动产法律行为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的规定与学界意见一致,〔52〕该司法解释释义书认为,按照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尚不能得出善意受让人须自出让人手中直接取得占有的结论,但对该问题的分歧尚待进一步研究讨论。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29页。该条的表述方式与《合同法》第140条后半段更为接近。如前所述,此处的“交付”并非有体物的占有移转,而是以当事人达成法律行为的生效时间作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时间。据此,只要转让物在双方达成合意之前已交付给受让人,即可满足客观要件。例如,无权处分人甲将他人之物租给乙,之后甲让与该物所有权给乙。若乙与甲达成合意时为善意,则可取得该物所有权。当然,占有取得不限于直接占有,也扩展于间接占有。如上例中的乙将该物又租给丙,即便乙为间接占有人,亦能善意取得所有权。〔53〕同前注〔18〕,鲍尔、施蒂尔纳书,第402页。基于本文所持的同等对待立场,在所有权取得中,无论出让人对转让物是否享有权限,善意的占有辅助人同样能基于简易交付的方式,从无权处分人手中取得所有权。〔54〕同前注〔33〕,Wieling书,第 384页。
针对简易交付的善意取得,《德国民法典》却设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要求善意受让人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从构成要件考察,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所有权要严于从有权利人处取得所有权。按照德国通说,受让人若未从无权处分的出让人或由其指示的直接占有人处获得占有,就会因缺少权利外观导致不能适用善意取得。〔55〕同前注〔16〕,Westermann书,第 352页。王泽鉴先生认为,基于缺少表征权利的信赖基础,尽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未设如同《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那样的规定,但学说对此持肯定立场,即受让人占有动产非来自让与人,不能仅因让与合意而取得所有权。〔56〕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同前注〔2〕,史尚宽书,第561页。
例如,甲将其爱犬交于乙美容,该犬从乙处逃走,为丙所得。丙甚爱此犬,得知它从乙处走失,遂向乙购买该犬。善意受让人丙在与乙达成物权合意时,已经占有转让之犬。而且该犬是所有权人托付他人照管,并非占有脱离物。若依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文义,无需登记的动产已经完成交付,若善意受让人已经占有转让物便可符合“交付”要求,善意取得自无障碍。但若贯彻“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的要求,即使乙以所有权人身份与丙达成转让该犬的合意,且丙先行占有该犬,由于丙取得该犬占有非来自出让人乙,因而不能善意取得该犬的所有权。
(二) 受让人自主占有的特殊限制
曾有观点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的要求应当被解释为如果出让人过去为占有人,之后所有权人不再占有转让物,也能满足善意取得。〔57〕同前注〔16〕,Westermann书,第 352-353页。史尚宽先生也追随此观点,即受让人无须直接由出让人处取得占有,只须出让人在受让人取得占有之前曾一度为占有人,而于该次让与占有后,其所有权人不复占有其物。〔58〕同前注〔2〕,史尚宽书,第561页。但异议观点认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第2款,从出让人过去的占有只能推定其为过去的所有权人,不能推定其为现在的所有权人,受让人难以得到适合的权利外观基础。因此合理的要求只能是,当受让人获得占有时,无权处分人必须占有转让物。若在双方达成物权合意之前,出让人的占有媒介人在未受上级占有人相应指示时将转让物交付给受让人,简易交付也可适用。〔59〕Vgl. Wieser, Zum gutgläubigen Erwerb beweglicher Sachen - BGHZ 56, 123, JuS 1972, 567, 569; 同前注〔16〕,Westermann书,第352页。所以,“出让人过去为占有人”在解释上的修正作用大大存疑。
《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与基于有权处分取得所有权的差别在于,前者即基于无权处分的所有权取得还需要满足“自出让人处获得占有”的要求。正如前文所述,该条与《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2句相比,构成简易交付的特殊情况,即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因为只有受让人在达成物权合意时已不再为自主占有人而占有,这样的所有权信赖才值得保护。〔60〕同前注〔16〕,Westermann 书,§ 929 Rn. 79, § 932 Rn. 27 f.如果受让人错误地发生自主占有,而且嗣后并非出让人移转占有,而是第三人移转占有,受让人就可能怀疑出让人的权利正当性(Legitimation)。添加“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的要件之后,就使受让人取得自主占有时不容反驳地被推定为恶意,〔61〕同上注,§ 932 Rn. 27.导致其不能援用善意取得。例如,甲以低价向乙购得一辆二手自行车,因乙告知甲其系代人保管车辆,甲不能满足主观要件而无法善意获得所有权。但甲仍以该自行车的自主占有人面目出现于外部。后有丙自称为该车所有权人,向甲要求返还该车。甲因用惯该车,遂同意以市场价受让该车。若事后发现丙并非所有权人,因为受让人甲系自第三人乙处而非自出让人丙处获得占有,所以甲不能善意取得该车所有权。
但若受让人自始获得他主占有,如基于租赁、保管等占有媒介关系为他人占有,则这一“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的善意取得要件是否仍有价值颇值怀疑。例如,甲出租带家具的房屋供乙居住。在租期未满时,甲移转该房所有权(包括室内家具)给丙,基于“买卖不破租赁”的原理,新所有权人丙继受甲的出租人地位。此时,乙打算向丙购买该房内的某套家具,双方达成合意便移转该套家具的所有权。事后发现,甲在移转该房所有权时患有精神病,房屋及家具的所有权移转因其缺乏行为能力而无效。当甲的监护人向乙主张返还该套家具时,后者认为基于简易交付已经善意取得所有权。但乙取得的家具占有并非来自于出让人(新出租人)丙,而是来自于原出租人甲。因此,“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的善意取得要求未能满足,乙只得返还自丙处受让的家具。又如,乙向甲借用某珍本古籍半年。3个月后,甲死亡。乙甚爱此书,便与继承人丙达成合意,依简易交付的方式受让古籍所有权。后在甲的家中发现其处分该古籍的遗嘱,甲将包括古籍在内的遗产都赠与老友丁。当乙面临丁的返还请求时,他能否主张善意受让古籍所有权?此处的障碍仍是受让人乙并非自出让人丙处获得占有,而是从被继承人甲手中取得古籍。
在租赁物所有权人变更而维持租赁关系的情况下,无处分权的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给承租人,承租人究竟是从当前的出租人手中获得租赁物,还是自以前的出租人处取得租赁物,都不影响其善意信赖。当所有权发生移转时,只要出租人对于受让所有权的承租人表现为真实的自主占有人即可。〔62〕同前注〔14〕,Ernst书,第 83-84 页。同理,在借用、保管等类似关系中,出借人、寄存人等只需对转让物的借用人、保管人表现为自主占有人。善意受让人在以上情形的信赖无可指摘,若不对其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可能为交易安全埋下重大隐患。
从立法史考察,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拒绝在简易交付中适用善意取得,因为那时的占有人只限于自主占有人,并不包括持有人(他主占有人)。〔63〕持有人(他主占有人)若要借助于“短手交付”获得所有权,可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2款。双方当事人只要基于合意便可移转占有。Vgl. MünchKommBGB/Oechsler, 2013, § 932 Rn. 27.由于在双方达成物权合意时缺少权利外观,自然缺乏善意信赖的基础。即便受让人为善意,亦不能取得所有权。至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起草时,占有概念不再区分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承租人、借用人等他主占有人一并被作为占有人对待。简易交付的善意取得类型不仅适用于自主占有的情形,而且扩张至他主占有的范围。因此,起草德国民法典的第二委员会认为,即便所有权移转与交付同时发生,受让人信赖所有权的基础也不会被削弱。立法者仅需防范原先所拒绝的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的善意取得情形。于是,自权利人处取得占有的要求才写入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846条第1款第2句),并保留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64〕Vgl. MünchKommBGB/Oechsler, 2013, § 932 Rn. 27.
所以,需要对《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限缩。基于简易交付的善意取得仅针对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的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受让人为他主占有人的情形,后者恰恰是适用简易交付最多的日常类型。〔65〕同上注,§ 932 Rn. 28, § 929 Rn. 79.即便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缺少“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之表述,亦可借助于权利外观理论作出解释,即当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时,善意取得因缺少权利外观而不能成立。
(三) 指令取得
在指令取得下,即使受让人自第三人处获得占有,也能发生善意取得。指令取得的权利外观早已不限于出让人向受让人交付的外观,而取决于出让人是否完全失去占有。即便比较受让人与所有权人的占有因素,只要前者的占有状况强于后者,善意取得的客观要件就能成立。至于受让人自何人处获得占有,并无决定作用。
当发生指令取得时,如果受让人首先从第三人处获得占有,然后与出让人达成物权合意,受让人很有可能阻止第三人作为所有权人追夺转让物。〔66〕Vgl. BGHZ 56, 123 = NJW 1971, 1453. 反对立场参见前注〔16〕,Westermann 书,第 352 页。例如,原告所有权人(被指令人)根据出卖人的指令,将对出卖人所有权保留的三台机器直接运给善意的被告,没有对被告保留所有权。被告认为出卖人是所有权人,通过结算清偿后者的价款。由于出卖人仍未清偿所有权人的价款,所有权人根据对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向被告请求返还三台机器。〔67〕Vgl. OLG München JZ 1957, 444.若被告基于简易交付善意取得所有权,需要满足“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的要件。而该案中的被告却是自既非出让人的占有媒介人亦非其占有辅助人的被指令人手中取得,而且原告基于所有权保留仍为自主占有人。但法院认为,即便受让人基于出让人的指示获得直接占有,简易交付的这一占有要求也获得满足,尤其是在保留所有权的供货人基于出卖人的指令将货物直接送交买受人时。善意受让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所有权,在于其占有源自出让人。受让人的信赖究竟是基于多数情况下未能察觉的出让人的事实支配力,还是服从出让人指令的第三人的占有获取力,其实并无差别。对于善意信赖支配力的保护而言,这样的占有取得要件应与构成直接占有的权利外观加以同等对待。通过外界运送获得货物的买受人并不关心出让人是否自己获得占有。具有关键性的事实仅为陌生的送货人是否服从出让人转让占有的指示。〔68〕同前注〔67〕。
在适用简易交付的情况下,受让人一方取得占有的每种形式几乎都能满足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但若出让人一方的人员仍为受让人充当占有媒介人,则不能成立善意取得。否认理由旨在防止规避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要求,因为受让人必须获得转让动产的排他性支配力,才能取得所有权。〔69〕同前注〔1〕,Staudinger、Wiegand 书,§ 932 Rn. 34.
在德国曾发生过一起颇具讨论价值的案件。所有权人E将一台挖掘机出售给买受人S,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即挖掘机所有权自S付清价款后发生移转。未经E同意,S不得处分(包括转让、让与担保等)该挖掘机。但S为担保国库的税款,将挖掘机的期待权转让给被告(国库)。E的挖掘机买卖价款逐步获得清偿,只剩下少部分余款。这时,S又找到原告,希望他帮忙还清价款。原告同意其请求,但要求S让与挖掘机所有权,以担保原告偿还挖掘机买卖的余款。在原告清偿E的余款之后,E确认所有权保留买卖履行完毕,其对挖掘机不享有所有权及相关权利。半年后被告成功地申请法院扣押挖掘机,将其变卖后得到21000德国马克。原告认为其已经(善意)取得所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因侵犯所有权导致的损害。〔70〕Vgl. BGHZ 56, 123, 124 f.
该案争议的挖掘机占有关系如下。受让人原告为间接占有人,出让人S为直接占有人,所有权人E为第三人。S在与原告达成物权合意时,基于让与担保所生的保管关系成为原告的占有媒介人。S若向受让人转让后者间接占有的标的物所有权,其为无权处分,受让人明知其无所有权而受让,不得援用善意取得规则。但若出让人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即E同意出让人S向受让人转让所有物,受让人在已获转让物间接占有时能否主张取得转让物的所有权?〔71〕Vgl. BGHZ 56, 123 = NJW 1971, 1453.
虽然挖掘机的出卖人E是所有权人,但其所有权保留只能延续至买卖价款付清之时。在原告为S付清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剩余价款之后,所有权保留便不再持续。由于被告受让挖掘机的期待权早于E同意S向原告转让所有权的时间,其在原告付清价款时就由期待权人直接变为所有权人。〔72〕Vgl. BGHZ 20, 88. 参见庄加园:《附条件让与所有权下的期待权转让——〈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20卷,第88页以下》,载田士永、王洪亮、张双根主编:《中德私法研究》2007年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以下。由此,E在余款获得清偿之后的同意转让挖掘机所有权就成为无权处分,因为此时的所有权人应为被告,而不是E。该案的讨论焦点便是受让人在已获间接占有时,能否善意取得系争挖掘机的所有权。
受让人善意取得的表面障碍在于,简易交付要求受让人必须从出让人处获得占有(《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而受让人却是自表见所有权人处取得间接占有,由此不符合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的要求。但上述案件的审理法院却认为,基于简易交付的善意取得所提出的占有取得针对的是通常案型,即出让人为表见所有权人,受让人信赖的权利外观需要表现为从出让人处取得占有。该案却涉及特殊的转让形式,占有物的表见所有权人并非出让人,而是第三人。由此,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需要根据交易的特殊形式加以调整,即受让人不再是经由出让人S,而是从同意出让人转让的第三人E(表见所有权人)处获得占有。这就使得该案受让人取得占有也符合《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的要求。〔73〕Vgl. BGHZ 56, 123 = NJW 1971, 1453, 1454.
简易交付的受让人无论获得直接占有还是间接占有,都能符合善意取得的占有要求。该案的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就此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但棘手之处恰恰在于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要求未获满足:出让人S在所有权转让之前就直接占有转让物,在所有权转让之后仍为直接占有人;受让人虽获得间接占有,却未获得对转让物的排他性支配力。具体言之,由于出让人S仍为直接占有人,出让人一方未完全失去对转让物的控制力,也未丧失为受让人利益所发生的权利外观。所以,受让人尚未达到善意取得中占有取得的排他性要求。同样的排他性占有要求也出现在基于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中。〔74〕同前注〔18〕,鲍尔、施蒂尔纳书,第404页。参见[德]托马斯·吕福纳:《间接占有与善意取得》,张双根译,王洪亮校,载张双根、田士永、王洪亮主编:《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以下。该案若适用占有改定方式,受让人也只有从表见所有权人手中取得直接占有,才能符合《德国民法典》第933条有关善意取得的占有要求。这样的排他性占有取得要求无论对占有改定还是对简易交付都应同等适用。〔75〕同前注〔73〕。
五、结语
我国《物权法》第25条规定的简易交付要求受让人提前获得对转让物的事实支配力,现实交付因此失去其价值。立法者为实现便捷交易的目的,允许当事人仅通过“裸露”的合意移转所有权。该合意区别于作为原因行为的合意,必须符合处分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果受让人为他主占有人,双方当事人除达成法律行为上的合意之外,还须完成移转自主占有的合意,该合意仅为事实行为层面的合意,无须满足法律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
简易交付的受让人既可能是常见的他主占有人,如占有媒介人,也可能是自主占有人。受让人若为自主占有人,其只需和出让人达成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可。此外,简易交付还能适用于“长手交付”和受让人与出让人存在占有辅助关系的情况,因为这两者都符合受让人已经对物行使事实控制力的情形。由于旨在实现占有保护的占有外延并不完全等同于移转所有权所需的占有,法律适用不应过分纠结于法律上的“占有”概念是否得以满足。
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并未对简易交付专设条文,《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却要求受让人自出让人处取得占有。其原因在于,受让人若未从无权处分的出让人或由其指示的直接占有人处获得占有,就会因缺少权利外观而不能发生善意取得。但对《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第2句的适用范围有必要进行目的性限缩,因为它针对的仅是受让人作为自主占有人的特殊情况,不适用于受让人为他主占有人的通常情形。即便我国现行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缺少这一条文,亦可借助于权利外观理论排除受让人为自主占有人的特殊情况。在基于简易交付的指令取得情况下,若出让人为无权处分人,受让人虽获间接占有,却未获得对转让物的排他性支配力,善意取得依然不能成立。
——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20号判决切入
——以受让人权益保护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