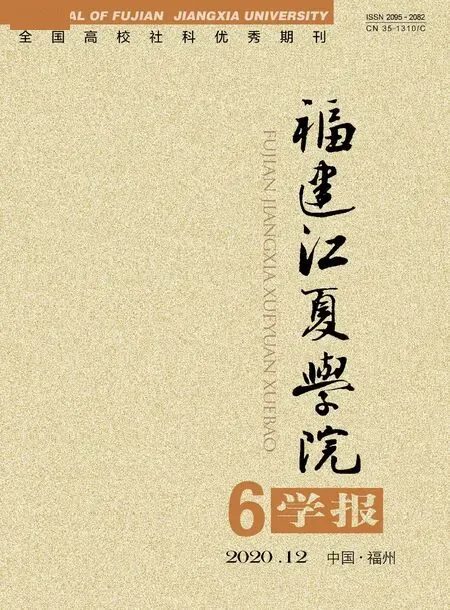“荒诞世界”与“反抗哲学”
——叙事视角下解析加缪的《鼠疫》
郑美香
(福建江夏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于1947年创作《鼠疫》,小说描写了北非阿赫兰市发生一场鼠疫被封隔后的情形,通过瘟疫持续9个月间里厄、塔鲁等居民的所作所为,表达了他关于人类在荒诞世界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真谛的思考和理解。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鼠疫》的论文不断出现,其中不乏从叙事学角度去分析读解的文章,如国外的埃德温·摩西的《结构的复杂性:〈鼠疫〉的叙事技巧》(Functional complexity: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the Plague,1974)以及波特·劳伦斯的《从编年体到小说:加缪〈鼠疫〉的艺术构造》(From the Chronicle to Novel:Artistic Elaboration in Camus'LaPeste,1982)等,主要从叙事形式和结构方面去研究《鼠疫》的文本内容①转引自谢魏学位论文《加缪〈鼠疫〉的瘟疫叙事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6年,第5页。;国内主要有:安霖从叙事技巧的运用和功能来分析小说的主题和风格[1];李炜从叙事者、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等方面研究小说文本的内容和艺术功用[2];杨晓敏通过零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三方面解读小说文本内容②杨晓敏《〈鼠疫〉中的多重叙事聚焦》,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08年年会论文集》,第467页。;谢魏从小说题材和叙事内容等方面分析小说中杂糅着侦探小说、多重叙事声音、互文本等后现代小说的特点[3]。
国内外这些研究论文多数从宏观视野对《鼠疫》的叙事策略和功能进行探讨。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拟深入解读文本,具体研究《鼠疫》独特的叙事视点、叙事风格及叙事功能,首次提出加缪在小说中设置三组独具特色的叙事视点——嵌套式+“镜中人”+双视点人物叙事,进而分析小说独特的主题内涵、艺术张力和叙事风格。加缪构建的三组叙事视点形象展现了“荒诞世界”与“反抗哲学”,对小说主题建构、人物关系、情节铺展、叙事风格等具有重大意义,也赋予小说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一、双视点人物互动叙事记录瘟疫事件
加缪在《鼠疫》中设置了里厄与塔鲁两个视点人物,讲述一个由鼠疫引发人类行动的故事,构建了“囚徒们”和“觉醒者”之间的张力,形成纪实小说的风格。
加缪一再强调《鼠疫》的纪实风格,指出这部小说类似新闻报道,具有客观叙述的性质,他甚至以“纪事”来称呼这部小说。小说选择里厄和塔鲁这两个视点人物第三人称内部聚焦来叙事。里厄作为医生坚守疫情一线治病救人,是这场持续九个月鼠疫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医生这一身份确保他对这场瘟疫见识客观、科学、精准。与此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叙述这场给阿赫兰市千千万万居民带来重大影响的鼠疫事件,加缪又设置社会活动家塔鲁记录的琐事细节予以补充印证。小说以一种不夹杂个人情感的视角,来讲述一个由鼠疫引发人类行动的故事,展现小说的荒诞世界与人类反抗,使《鼠疫》成为一部纪事体小说。通过双视点人物互动叙事,小说以见证人眼光切入这场疫情,全面客观地记录鼠疫肆虐下的荒诞世界。“作为忠实的证人,他必须首先记录的是人的行为,有关的资料和传闻。”[4]227-228小说的叙事客观而冷静,而选择第三人称内部聚焦写作,则有助于叙述人与其他人物保持某种距离,保持客观性和全景视角。在以里厄和塔鲁展开的叙事中,始终采用“客观”“冷静”“不带感情色彩”的零度叙事,形成了纪实小说的风格。
选择双视点人物第三人称内部聚焦来讲述瘟疫事件,与之对应的小说艺术张力也随之架构起来。加缪在1942年8月的《手记》中提到:“小说。不要把‘鼠疫’放进标题中。而是诸如‘囚徒们’之类的。”[5]这里“囚徒们”是指被隔离在阿赫兰市惶恐无助的众多居民。小说以里厄和塔鲁作为双视点人物,描写他们和格朗、朗贝尔、帕纳卢等“囚徒们”的所作所为,记录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走出荒诞的状态,从恐慌无助的“囚徒们”变成携手而战的“觉醒者”。这里“觉醒者”是具有群体性抵抗精神的人,小说讲述一场瘟疫引发人类反抗的故事,以“零度聚焦”来宏观展现由鼠疫引发的人类行动,展现不同身份、观点迥异的人们在荒诞世界中走向觉醒和集体抗争之路。通过双视点人物叙事,小说展现众多人物面对瘟疫的不同态度以及走向“反抗”的不同方式,小说一系列主题依托各具特色的人物一一展开。
在小说《局外人》中,加缪着力表现“荒诞世界”的真相,笔下的人物都是“囚徒们”,而在后来《鼠疫》《反抗者》等作品中,出现了“觉醒者”和“反抗者”形象。在《鼠疫》中,里厄只想做一个尽职的医生投身于与鼠疫的抗争中,不信上帝的塔鲁为了内心安宁组织志愿队抗“疫”,格朗作为政府人员每天统计疫情死亡人数,记者朗贝尔从局外人变成觉醒者留下来“和大家有难同当”[4]156,神父帕纳卢目睹奥通幼子被病痛折磨致死后,认为“上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4]168,里厄的母亲“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4]208,患哮喘病数鹰嘴豆的老人说“鼠疫就是生活”[4]232,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鼠疫患者”[4]189的塔鲁坚持抗疫,科塔尔在瘟疫消退后变成疯子……当鼠疫来临,人们挣扎着抵御瘟疫的奴役,小说通过众多人物表达出人类对瘟疫的反抗态度,而对瘟疫持欢迎态度代表荒诞的科塔尔的行动则是一个反例。小说众多人物体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正是荒诞引起的分离与反抗,形成了“囚徒们”和“觉醒者”之间的巨大张力。
加缪在《鼠疫》中多次交代小说类似新闻报道,这一构思是通过双视点人物叙事得以实现,小说的整个故事线没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更像是一部写实的报告文学,形成了纪实小说的特点。加缪强调,《鼠疫》描写的众多人物“直面同一荒诞时诸多个人观点的深度对等”,他讲述一座被隔绝城市里的故事,描写挣扎在疫情一线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各个人物观点呈现不同观念的冲突与交融。他通过双视点人物叙事,写出众多人物从“囚徒们”走向“觉醒者”的转变历程。其中,视点人物里厄和塔鲁代表着加缪的一部分观点。加缪曾说过:“最接近我的,不是圣人塔鲁,而是医生里厄。”[6]他在1957年的受奖演说中,指出“作家只有忠心耿耿竭尽所能地为真理和自由服务,他的职业才能因此变得伟大。”[7]163-164福克纳在给加缪的悼文中写道:“加缪说过,诞生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7]154-155在小说中,加缪通过双视点人物讲述一个由鼠疫引发人类行动的故事,写出众多人物从荒诞中觉醒,在反抗中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镜中人”互文叙事讲述寓言故事
加缪在小说中设置了“镜中人”互文叙事,讲述了一个充满感情与思考的寓言故事,构建了“冰山风格”和“生命激情”之间的张力,形成了寓言小说的风格。
加缪在小说中设置一面“镜子”,“双重叙事人”身份的里厄作为“镜中人”互文叙事,通过“自画像”来审视自我。开篇引出超叙事“笔者”,而主叙事则以里厄医生为视点人物,作品结尾透露“笔者”原来就是里厄,超叙事“笔者”时时对主叙事里厄“照镜子”,进行自我观照、反省和思考,作为叙事人里厄与人物形象里厄之间的界限消融了。加缪说过:“反抗,即时时刻刻都质疑世界……反抗,就是人时时刻刻面对自身。”[8]63他在小说中设置“镜中人”互文叙事,通过里厄“时时刻刻面对自身、时时刻刻质疑世界”来讲述一个令人深省的寓言故事,提醒读者小说的醒世意味。
警示作品堪称法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加缪创作《鼠疫》的初衷是取得某种历史性的警示效果。《鼠疫》的核心意义不是描述鼠疫事件本身,小说中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类故事,加缪通过“镜中人”互文叙事,构建一类关于人与灾难、荒诞抗争的寓言故事,从而丰富了小说的主题,《鼠疫》也成为一部警示小说。《鼠疫》卷首题词引用笛福的一句话寄寓小说意旨:“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加缪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介入小说叙事,“笔者”里厄充当忠实的记录者身份,视点人物里厄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通过“镜中人”互文叙事去思考“如何为自己画好像”。
《鼠疫》在表层上是记录一场关于鼠疫的故事,而更深的表意层次上,这一故事隐含着一个令人回味、发人深思的寓言。加缪通过双重叙事人里厄,不断回顾、反省“镜中人”,使小说成为反思人性意识的心灵独白。正是通过真诚的反省,里厄找到了人性的弱点与光辉,激发了生命的激情,实现了自我救赎。加缪通过讲述这个充满感情和思考的寓言故事,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曾经发生的灾难。
在小说中,加缪所讲述的寓言故事包含着丰富的象征含义与隐喻色彩,隐含着人类的处境、内在的冲突以及人性的问题,他使用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的叙述手法,即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写作,排斥主观情绪和感情的叙述调子,这一点与海明威“冰山风格”很相似。同时,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是生命的激情,这种激情是要热爱生命,在对荒诞的反抗中寻求生命的意义。通过里厄“镜中人”互文叙事,加缪将客观的描述、主观的情感贯穿在整篇小说中,讲述一个充满思考与感情的寓言故事。“冰山风格”和“生命激情”形成巨大张力,使读者内心深为震撼,进而去思考和领会小说的警示意味。鼠疫象征的是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它们潜伏在人类身边,随时有可能爆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面对生存困境,加缪寻求解答“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要用爱的力量去战胜苦难。
在小说中,加缪通过“镜中人”互文叙事写到三个人的死,就充分彰显了“冰山风格”和“生命激情”之间的张力。首先,客观地描述守门人的死,门房是阿赫兰市第一例鼠疫感染死亡病例,象征着鼠疫攻入“城门”,主叙事的里厄见证了门卫之死,而作为超叙事的里厄则思考瘟疫发生的危机。其次,客观详实地描写预审法官奥东的儿子之死,叙事人记述了孩子整个死亡过程的每个细节,描述了里厄、塔鲁、格朗、朗贝尔、帕纳鲁神父的神情与态度,尤其是为后来神父满怀悲悯之心改变态度投身于抵抗鼠疫的行动埋下伏笔。再次,“仪式般”描写塔鲁在鼠疫悄然退去之前死去,里厄聆听他临终前的自述式演讲,目睹这个自称小鼠疫患者的“圣人”死去,超叙事的里厄借数鹰嘴豆老头之口说“最优秀的总活不长”[4]231,彰显了寓言小说的意味。小说描写这三个人的死亡极具象征意味,面对死亡威胁,作者叙述三类人:死了的人、疯了的人(科塔尔在鼠疫末期发了疯)、活着的人。在瘟疫无情的荒诞世界中表达“死亡”意识时,加缪通过里厄这个“镜中人”互文叙事,引发人们思考一个人类永恒主题:面对生命的苦难特别是死亡时,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与状态去生存,警醒人们要从灾难中记住什么。对于过去了的这场灾难,加缪通过“镜中人”互文叙事,把瘟疫故事作为一个寓言小说写下来,他并不是为了记录人类战胜瘟疫,而是要人们在共同的困境下用爱去抗争,因为“知道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4]233。
三、嵌套式叙事展开深刻哲思
在小说中,加缪精心设置了嵌套式叙事,展开了一场面对人类灾难图景的存在主义哲思,构建了“历史叙述”和“文学虚构”之间的张力,形成哲理小说的风格。
嵌套式叙事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事视点层层相套的方式叙事,现代小说常常采用这种叙事方式。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对叙事层进行区分,指出叙事者有时会再造出观察者,将“说的人”和“看的人”分为几个叙事层。[9]加缪在《鼠疫》中将三个叙事层的叙事视点层层相套:一是“超叙事”,叙述故事前添加序言,引出“笔者”即“说的人”,说明故事的来源,使叙事人获得全知全能叙述的权利,这是小说最大层的叙事套;二是“主叙事”,里厄医生作为“看的人”,让这个瘟疫事件的亲历人讲述其所见、所闻、所感,呈现有限视角的叙事,这是小说第二层叙事套;三是“次叙事”,小说在里厄的叙事中又造出塔鲁这个“看的人”,主叙事不断引用塔鲁的记录本作为鼠疫事件的补充见证,塔鲁这一人物视点形成小说第三层叙事套。以上三个视点一层套一层,形成超叙事、主叙事、次叙事等三个叙事套,视点层层相套完成小说叙事。
加缪认为“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他继承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传统,通过《鼠疫》这篇虚构的小说来表现其哲学思想,创作一部哲理小说。他设置的嵌套式叙事视角除了承担讲述故事、表达情感、塑造人物形象之外,还展开一场面对人类灾难图景的存在主义哲思。加缪主张用形象而非用推理写作,认为“伟大的小说家是哲理小说家”[8]117,他在《鼠疫》通过嵌套式叙事层层相套展开小说文本,把相关的视点人物当作某种思想、某种品格的物质承担者,在小说中表达某种哲理,从而把小说打造成形象化的哲学。
小说的虚构性往往需要我们对虚构者的真实意图有所了解和理解,加缪深受存在主义影响,他称自己的思想为“荒诞哲学”,在《鼠疫》采用三个层级的叙事套子进行嵌套式叙事,一方面,小说突出编年体的史诗化写作方式,以历史学家“见证”叙述的视角,使得《鼠疫》成为一部历史叙事小说;另一方面,这场瘟疫明显是“不存在的事”,小说采取一种不夹杂个人情感的叙事视角来叙述,其真实感来源于文学虚构。加缪采用超叙事(笔者)、主叙事(里厄)、次叙事(塔鲁)等三个层次的叙事视角,整合了编年史的历史叙事和文学的艺术虚构叙事,表现为以故事来建构“历史”,通过小说书写“历史”,再经由文学艺术的加工,借助史诗般的情感叙述,赋予一场瘟疫超脱于生活真实的震撼力。
凭着对历史叙事和文学虚构的独特理解,加缪在小说中设置这一组嵌套式叙事,形象地展现他面对人类灾难图景的独特思考与理解,传达其存在主义哲学观和世界观。他并不要求读者相信鼠疫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营造一种历史真实感,在读者内心认同鼠疫事件真实可信。加缪从表现存在主义哲思出发,在小说中采用嵌套式叙事,通过虚构的“历史”艺术地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进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不要简单地把小说当成一部虚构故事或者记录历史的编年史来读,而要通过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思考,要穿过小说的虚构透视荒诞世界和现实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
总之,加缪在《鼠疫》中成功运用嵌套式+“镜中人”+双视点人物的叙事视点,通过小说叙事构建一系列艺术张力,展现丰富的情节内容,表达多层次的主题内涵,寄寓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营造小说庞大的精神世界,形成了融纪实、寓言、哲理于一炉的多样化风格。这一套“组合拳”的叙事功能是放射性的,收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效果。加缪从《局外人》到《鼠疫》《反抗者》的创作变化,展现出他着力思考、阐释的哲学对象及其论述的哲学体系由“荒诞”走向“反抗”的流变过程,构建起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及体系。也正是注入“反抗哲学”,形成加缪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他成为二战后欧洲乃至全世界几代青年的‘精神导师’”[7]扉页。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加缪作出这样的评价:“他(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7]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