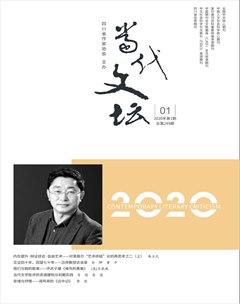对话传统:新世纪城市文学及特征
李志孝
摘要:中国新文学的城市书写有自己的传统,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无意之中“回应”着这种传统,并提醒人们联想起文学史的“先例”。不论是对城市的“欲望化”书写,还是“情感”书写,抑或是“他者”的城市经验书写,都是如此。但新世纪城市文学也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特征以及明显的缺失,表现在:宏大叙事日渐式微而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主流;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描写被雷同化、类型化的城市叙事所取代:典型人物的塑造被社会问题的呈现所代替;纪实性凸显而想象性不足。
关键词:新世纪城市文学;特征与缺失;承传与对话
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可以用“丰富”来形容,这种丰富性从其表现对象上就可以看出:都市情感、职场生涯、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女性人生、农民工等等,当然这之中有种种交叉。它反映了作家对人与城市的审美关系关注点的不同,也体现了城市书写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同步映照关系。也许从文学所描写的城市形象中,更可以看出当下中国的真实面孔以及隐藏其间的心灵悸动。
一 新世纪文学的城市书写
(一)欲望化的城市
中国作家审美心理中的城乡差别,在今天城乡互动加剧,乡村也已今非昔比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审视,但不可否认的是,“欲望”在城市中确实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让人惊心动魄。在新世纪文学的城市书写中,有大量的作品是表现都市人对欲望的追求与满足的。物欲、情欲、权欲,成为城市人生活的基本动力。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在这部作品中,权力欲望支配下的性欲、物欲,是故事演进的基本动力,整个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也都是由欲望来推进的。作品中的成功男人严守一,游走在众多女人之间,“力比多”似乎成了他生命的唯一。刘震云的另一部小说《我叫刘跃进》中的北京,也是一个物欲膨胀的都市,生活在其中的人物,也被物欲所控制,一个个都成了物质动物,难见人性的光芒。邱华栋大量的北京叙事更是凸显着现代城市的物化特征,现代化的大都市犹如一个物欲主义的释放地。著名批评家陈晓明曾这样说:“过去的小说家,不管是王朔还是其他任何作家,没有人像邱华栋这样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城市代码,他高频率地描写城市外表,那些豪华的宾馆写字楼、光怪陆离的卡拉OK舞厅酒吧按摩院、混乱的人流、蛮横的立交桥、庞大的体育馆、午夜的街道、牢笼一样的公寓……”①而“这些城市外表,具有坚硬的物质外形,无一不指向都市人的内心,搅动城市人内心的欲望”②。
这种欲望化的城市书写,也许与作家将城市看成是一个消费社会和享乐空间的认识有关。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新闻舆论界确曾大力宣扬中国已进入一个消费社会,而引导消费也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策略和杠杆。因而从1990年代开始,在卫慧、朱文等作家笔下,就已经出现大量的此类叙事,进入新世纪之后此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即如郭敬明的《小时代2.0虚铜时代》中的幻城,便是一个消费至上、欲望展演的舞台;张欣的《浮华背后》《夜凉如水》等小说,尽管没有那种无节制的欲望表达,但对上层社会奇观式生活场景的过度呈现,对普通人们所给予的激励也许仍是一种对功名利禄的追逐。鲁敏的《向中产阶级致敬》同样展现了社会上流行的物欲追求与相互攀比之风。而在城市文学的女性书写中,更是强化了欲望与女性之间的同谋关系:“化妆品时装内衣首饰鞋帽,从洗衣机到电冰箱到微波炉小型电熨斗水果削皮机豆浆机烧烤炉洗碗机……那些为企业商家带来微薄利润的日常用具家用电器,不再以革命的名义而是以女人的名义,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住房汽车从女人夜晚的梦境变成白天的现实;家具厨具洁具卧具玩具文具,也在家庭主妇饥渴与挑剔的追踪下迅速更新换代;就连写字楼的办公桌椅办公用品,也被设计成具有女性曲线的弧度,以女性的审美眼光作为借口部分实现了男人潜在的愿望。”③而城市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样也是或醉心于官场(如阎真的《沧浪之水》),或流连于商场(如张者的《桃李》)。作家所传达的都市经验和感受,指向的都是一种欲望化的文化心理。
这样的城市文学,让我们不能不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正如程光炜先生所追问的,“它是简单的雷同和重复呢,还是要打碎文学传统,而重建另一种文学秩序?”④也许他的另外一段话同样有道理,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中国的历史是以‘循环式的存在方式展现自己的面貌的……虽然文学的表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它自己的独特性,然而并未完全脱离文学史的轨道成为真正的‘另类。另类文学不乏夸张的先锋姿态,却总是以相反的效果提醒人们联想起文学史的‘先例。”⑤
(二)情感迷失的城市
都市情感是大量城市文学作品表现的一个主题,而这类作品中,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正如有学者所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几乎成了都市情感的主导,这里的情况一面是放纵和自由,另一面却是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安排;一面是前所未有的‘解放,好像突破了伦理的限制和压抑,另一面却是异常明快地尊重现实和非常明确地划定界限。在此之间,婚外之性的表现,不再是‘反封建或者‘自由的表征,而不过是如左拉或福楼拜小说中的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隐秘‘事件而已。”⑥在魏微的小说《化妆》中,女主人公嘉丽十年前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将自己的感情和身体献给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十年后,她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女人。当年的男人又一次出现时,她试图将自己“化妆”成丑陋的姿态向昔日的情人报复,但却陷入徒劳无功的境地,而受到伤害的只能是她自己。这是一个情意缠绵的虚假爱情的破碎过程,作家的敘述有一种女性主义的倾向,但其中反映的却正是现代城市中爱情的虚幻与可疑。方方的中篇小说《树树皆秋色》讲述了一个奸猾的学生与渴望爱情的大龄女教授的高级“调情”故事,他们在电话的两端上演着“欲擒故纵”的感情游戏,然而最后,故事的主人公察觉到了破绽所在,“事情的开始是那么自然,而到了后面却令她觉得诡异”。恰如残酷的社会现实一般,这个貌似浪漫的故事,早已注定了一个庸俗的结局。读者所期待的真情,不过是些虚伪的掩饰。在世俗的功利面前,学院的高雅与矜持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这样的胜利又能维持多久呢?读者所感受到的仍然是城市情感的游戏性质和女主人公所受到的伤害。在金仁顺的《彼此》中,相爱的夫妻,因对爱情纯洁性的执迷,而无法消解彼此心中郁结的过往。然而小说的悲剧性恰恰在于,当既有的婚姻破裂之后,真正的爱情并没有如期而至,小说的主人公周祥生和黎亚非这对因婚外生情而走到一起的男女,宿命般地又重复着第一次婚姻时的老路。欲望导致都市爱情本身成为一个奢侈的事情,围绕着金钱和得失展开的情感游戏让人厌倦却也无可奈何。众多作品给我们剖示的正是欲望时代的都市病相。
破碎的不只是都市爱情,人间亲情也一地瓦砾,让人不得不惊心于城市的冷漠与荒寒。刘庆邦的小说《骗骗她就得了》通过一个保姆的视角,呈现了都市家庭生活的某些场景。作品中的保姆陈书香被曹德海找来照顾久病在床风烛残年的表姑,但她发现表姑父曹德海却根本不关心表姑,在家里,除非表姑喊他,平时连表姑的房间也不进去,而且常常借故出差好几天不回家。后来她发现,表姑父还有一个“外室”,“肚子已经高高的了”。表姑父对表姑的冷漠和麻木,使陈书香慢慢明白了城里的一些事理:“在家时,陈书香并不知道什么叫苦。通过到北京伺候姑,通过姑对她说心里话,她才懂得了人的苦不是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是干的活有多重,而是在于人有心思,心思里的苦,才是真正的苦。”作品通过陈书香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都市生活的深处,“这是一种已经完全溃败的生活,这种溃败在都市的细胞——家庭中展开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不止是价值观的迷失或道德底线的洞穿,更可怕的是,在都市生活的深处,有一层坚冰铠甲覆盖在人心,那就是城里的冷漠与荒寒。”⑦在弋舟的短篇《平行》中,一个地理学教授在已经老去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追问什么是“老去”的问题,然而,他被冷漠的儿子送到养老院之后的经历,使他终于悟到:“老去”就是躺倒,与地面平行,也就是解脱。这些小说的故事,也许只是个案,但是,通过这些个案,都市人情感的真相却如山般压在我们心头。它让我们懔懔地反思,是人类出现了退化,还是现代生活异化了人性,让人连最起码的亲情也丧失殆尽?
读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让我们对今天的情感生活有一种紧张感和不安全感。事实上这就是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只不过阅读这类小说更加剧了这种感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怀疑,这是当下城市情感的全部吗?还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文学是否应在真实的生活之外,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有希望的理想的情感生活形态?
(三)“他者”的城市
新世纪文学中还有大量的描写城市外来者生活的作品,这些外来者是城市的“他者”,他们在城市的遭遇,展现的是城市的另一种形象,它坚硬、冰冷、龌龊、不堪,与那些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反人性的,它需要外来者提供劳动、服务,但却排斥那些为城市的繁华洒下汗水和泪水的外来者进入城市生活。而那些外来者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他们永远都是城市异乡者,是城市的“他者”。从这个意义说,城市是不属于这些“他者”的。
熊育群的中篇小说《无巢》中,农民工郭运在走下火车到广州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由一个质朴的乡村青年变成了杀人犯并自杀,原因是什么?正是城市的冷漠直接造成了悲剧的发生。面对穷凶极恶的社会,面对冷漠的人群,他彻底绝望了,对自己的生存绝望了,对社会绝望了,从绝望到愤怒、疯狂,一股强大的他所不能控制的情绪把他推向了一个极端。广州这个现代化都市的残忍、冷酷、无序,令人感到震惊,也感到愤怒。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城市,希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但他面对冷酷无情的城市,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以各种方式阻止他的努力,他只能是城市的一个孤魂野鬼。在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刘利的《奇迹》等小说中,城市规则,或者说资本家的规则,连农民工正当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也剥夺了。显然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他们的规则之中。在陈应松的《太平狗》等众多作品中,农民工在恶劣的环境下被强制性地进行着艰辛的劳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中,老板为了按时交货,要求工人没日没夜地连续加班5个昼夜,以致累死了一名工人。在杨小凡的《大米的耳朵》中,农民青年大米和耳朵曾天真地认为,“只要好好干,不信在城市扎不了根儿”,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弱肉强食的城市里,任何的无私和善良,都有可能导致自己的被淘汰。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城市任何一点哪怕是希望的曙光。也许这与作家对城市现代化的理解有关,但在作家的叙事中,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了今天的城市文明。这样的城市书写,我们在众多的“打工文学”作家如王十月、郑小琼、安子、林坚等人的创作以及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白连春的《我爱北京》、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农民而言,城市充满着诱惑,但他们的城市经历,又充满了创伤性体验,甚至就是一个噩梦。
即使是在那些表面上“成功”的人物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城市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正如《亲爱的深圳》中的女经理张曼丽,看起来是过上了白领的生活,有着豪华的住宅,早已不是当年的打工妹了,但他只能藏起自己粗大的骨节,连家里的实际情况也不愿让外人知晓,心中的酸楚只能自己去咀嚼。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同样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陈金芳不只是要进入城市,而且要在精神上“征服”城市,她也确实有一种永不休止的奋斗精神与改变命运的渴望。她也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左右逢源的投资艺术品行业的成功商人。然而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终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上层,一有风吹草动就从高处跌落。陈金芳最终还是被“打回原形”,城市对她来说还是一个噩梦。
当然,城市也并不只是噩梦。在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王手的《市场“人物”》、铁凝的《逃跑》以及姚鄂梅的《你们》等小说中,那些进入城市的“他者”也体验过城市温暖的一面。在這些作品中,作家并不一味地渲染底层的苦难,而是试图竭力去发现和理解这个时代都市人的生存真相。然而,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即使是那些怀抱理想主义的都市外来者,想要改变自身命运,也很难看到希望与可能。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主人公的命运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因为“底层”早已体制化为社会既有结构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那些逃离城市者,还是坚守在城市者,“他者”始终是他们的宿命,城市事实上还只能是他们的一个梦。
新世纪文学的城市书写当然不只是上文所说的欲望化城市、情感迷失的城市和“他者”所经验的城市,它比这要丰富和复杂得多。那些职场上的拼搏、官场上的角逐、家庭中的柴米油盐、街头里巷的飞短流长等等,也许更能表现城市生活的特征。而且也确有众多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所以,上文的论述不可避免地显示了一种片面性。也许那些最有价值的城市书写,还没有被我们及时发现和表达,但是通过上面提及的作品,还是让我们了解了当下都市的生活和精神状况,而且这样的文学书写还正在进行之中,我们有理由对其充满希望。
二 新世纪城市文学的特点与缺失
如果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新世纪城市文学与新文学的城市书写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题材选择、文本特征上,也表现在对城市的认识以及情感态度上,有人甚至认为,“新世纪以来关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的书写在深度和广度上并没有突破以前的同类写作。”⑧但是作家面对的城市经验和写作环境毕竟不同了,城市文学也有了与新文学传统不同的面貌特征,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与不足。而这种特征与缺失在与传统的比较中会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
第一,如果说,在现代文学阶段,文学的城市书写既有宏大叙事,也有日常生活叙事,且宏大叙事占有主流位置的话,那么,新世纪文学的城市书写却以日常生活叙事为主了,宏大叙事已日渐式微。
批评家杨扬在论及上海的文学经验时认为,以茅盾为代表的宏大叙事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分别代表了上海文学经验的两种类型。⑨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两种叙事类型,而在新文学史上,至1980年代中期以前,宏大叙事是主流的叙事方式,此后则日常叙事逐渐取代宏大叙事成为主体。左翼都市文學从阶级、革命、政治、经济角度入手,其作品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这是我们都已熟悉的历史。即使是以市民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老舍,其创作也常常有一个宏大的主题,比如《骆驼祥子》,就被研究者认为是一部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⑩而《四世同堂》更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觉醒国家意识、呼唤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作”11。至于“十七年”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已经被文学所放逐,在那些“工业题材小说”中,“作者以主导意识形态发言人的面目出现,对城市这一空间的体验同以对宏大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使读者获得的多是意识形态对城市的观念。”12以致在新时期初的“改革小说”如《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中,城市仍被置换成一个工业和行政的区域,城市生活感性化的一面仍被遮蔽。这类作品所秉承的还是1930年代《子夜》所创立的城市叙事模式。
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宏大叙事模式开始被改写,在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一系列作品中,日常生活与城市经验得到了“熔合”。城市生活的世俗景象全面出现在小说中,那些最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生存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最普遍、最普通的人物及其关系如夫妻、父子、婆媳、亲族乃至邻里之间的琐碎事项、矛盾纠葛、情感纷争等等,被原生态地呈现出来。这类创作展现了日常生活围困下的城市无奈,但却犹如打开了一扇窗口,让人们看到了城市的另一面。
到了新世纪,“城市文学”的特点正如雷达先生所言,“既不同于茅盾式的‘阶级都市,也不同于沈从文式的‘文明病都市,又不同于老舍式的‘文化都市,更不同于周而复式的‘思想改造都市,它主要表现为物质化、欲望化、实利化的‘世俗都市。”13而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全面占领了城市文学的书写领域。无需举太多的例子,就看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这部甫一出版就好评如潮,被称为目前最重要也是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的作品,充满十足的城市味道,然而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构架,也没有运用政治或道德视角,甚至也没有力图表现一个什么宏大主题,它写的就是家长里短、人情世态以及饮食男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幅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世相百态图。小说写了三个少年阿宝、沪生、小毛的成长,但连作者自己也认为未必就是成长小说。他甚至也不着意刻画某个人物的性格,作品突出的就是一种城市味道,一种城市人的生活姿态。金宇澄说:“作品讲自己知道的事情,作者和读者都在平等的位置上,作者是人群之一,喜欢说就说,在这样的位置上让读者得到感动、消遣就可以了,可以散漫,任何结构都可以”,因为“个人觉得‘宏大叙事和传统叙事的根基不符合,因此即使再折腾,也不会出彩。”14显然,作家是有意舍弃宏大叙事的方式而采用日常生活叙事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使读者得到“感动、消遣”。而且宏大叙事没有传统叙事(指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的根基,不会“出彩”。当然,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也不全是《繁花》这种写法,但不论是邱华栋描写北京人生存状态的“社区人”系列小说,还是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葛红兵《沙床》的上海书写以及吴君、邓一光、彭名燕、蔡东等作家抒写其对深圳这座城市感受的作品,就其叙事方式而言,都与宏大叙事相距甚远,书写日常生活成为主体。那种鲜明的理性意识和政治经济视角已经被强烈的个人感觉所代替,读者在其作品中看到的也是对城市越来越复杂的感受和困惑。当然,日常生活叙事在打破宏大叙事的僵硬模式,恢复城市日常生活本来面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和过度欲望化书写、过度自我追求的弊端。
第二, 在现代城市文学的书写中,不论是老舍笔下的北京,还是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都有非常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城市的地方风味十足。但新世纪文学的城市叙事却呈现出雷同化、类型化的特点,很难看到对城市的个性化书写。
其实,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历来都是失衡的,除了北京和上海可以在文学中立得起来外,其它城市,即便是那些现代化程度也并不低的城市如广州、南京、武汉、西安等,都没有被重笔书写。现代文学阶段是如此,当代文学依然。书写北京的作家,我们可以列出一串名字,远的如老舍,1980年代有邓友梅、陈建功、苏叔阳、刘心武等,新近则有王朔、邱华栋、徐坤、徐则臣等。他们的创作有较鲜明的北京城市特色,且有“京味”小说的称誉。上海则除了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之外,还有王安忆、叶辛、王小鹰、陈丹燕、程乃珊、腾肖澜等一批作家。“这些‘京派和‘海派的作家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城市意识,能够有意识地为自己的城市著书立传。北京、上海在他们笔下实现了斑驳陆离的文学建构,成为一种可以不断生产的文学想象园地。”15当然,除北京、上海外,在1980年代,天津卫的世情传奇、苏州小巷的世俗人生,也满带着各自城市特有的风情吸引过人们的目光。前者如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神鞭》《阴阳八卦》,林希的《天津闲人》《相士无非子》《高买》《神仙扇》;后者如陆文夫的《美食家》《小贩世家》,范小青的《小巷人家》《裤裆巷风流记》《顾氏传人》等。只是新世纪以来,天津、苏州这些城市的形象在文学中有些落寞。只有武汉在方方、池莉、彭建新等作家的书写中,依然延续着它的文学形象。
因此,我们看到,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城市书写总体上呈现出雷同化、类型化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慕容雪村不停地奔走于不同城市,他属于哪个城市?他笔下的成都与深圳又有哪些区别?安妮宝贝一度居住上海,但她的作品是否属于上海文学?抹去特殊的地标,我们很难分清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究竟有哪些差别,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上海、北京,相同的故事都可能发生。”16这种现象在网络文学的城市叙事中尤为明显。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的城市叙事从整体上看显然缺乏各自独特的城市文化内涵,作家们热衷于将目光对准城市的摩天大楼、咖啡厅、酒吧、霓虹灯、立交桥或者写字楼、公寓以及街道、居所,但却很难借此传达出城市所特有的情致韵味,城市给人一种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感觉。这在一些新兴的城市——如深圳,也许与它本身尚未建构起稳定的城市文化经验有关,但这对已经有悠久的城市文化传统和独特地域特色的城市则难以成为借口。
确实,随着这些年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城市正在失去原有的特色,在GDP成为唯一指标的发展模式下,对经济指标的追求成为每个城市的努力方向,人们所关心的也是经济利益和物欲滿足,心灵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而对于原有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片的老街区常常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大同小异的高楼,使得城市人也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这些确实给城市文学的叙事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作家对城市缺乏一种深入其中的切肤感受,难以对城市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肌理的深层把握,而常常被外部的千篇一律所迷惑。如何克服符号化、时尚化、单一化的弊病,而塑造出更为丰满、多元的城市形象,还需要作家们的不断努力。
第三, 与现代文学以至1980、90年代的城市叙事相比,新世纪城市文学缺乏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更缺乏鲜活、健康、可爱的城市人。
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那些堪称经典的人物形象。一部优秀作品的成功,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不论作品的构思如何新奇别致,情节如何离奇曲折、跌宕起伏,最终留在读者心中的还是生动的人物。那些精彩的情节在过后也许就会被人淡忘了,但人物却忘不了,他会深深地扎根在读者脑中,永远挥之不去。读老舍的小说,我们会记住祥子、虎妞、祁瑞宣、祁老人、张大哥、赵子曰;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记住白流苏、曹七巧;读曹禺的《日出》,我们会记住陈白露、李石清、潘月亭以及翠喜;读茅盾的《子夜》,我们会记住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等等。文学史上的这些形象,已经成为“共名”性的人物了,他们代表了现代城市文学的成就。甚至在1990年代,我们仍然看到了《废都》中的庄之蝶及其女性形象,看到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作为城市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他们已成为我们文学记忆的一部分。
而“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人物”17。正如孟繁华先生在分析鲁敏的小说《惹尘埃》时说的那样,这部典型的书写都市生活的小说,“是一部好小说,它触及的问题几乎就要深入到社会最深层,但是,放下小说以后,里面的人物很难让我们再想起,因为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的社会问题,而人物性格的塑造却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类似的情况在我们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18新世纪以来,读者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诟病不断,其中之一就是批判家在评论具体作家时多肯定,而评论整体文学时却多否定,认为这是一种自相矛盾,自打嘴巴。那么上面所说的情况也许就是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之一。因为确有大量的作品单独看来相当不错,但就人物塑造而言,普遍的情况却很难让人乐观。试想,在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中有多少可以让我们记住的人物?即便是那些开启过都市文学创作新风的作家,如王安忆、方方、池莉、王朔等,“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描绘过同时期的城市,近年的创作则显然更热衷于用‘往后看的视角,写城市的历史和个人记忆中的城市印象”19,其中的人物难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至于更多的“80后”“90后”作家的青春书写,其人物形象也模糊、单一。
这还只是一方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读者很难看到让人感动的可爱的人物。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是苦大仇深的底层,就是情感迷乱的小资,或者投机取巧的商人,抑或不择手段的官员,而这些人物又大都处在一种焦虑、惶惑、矛盾纠缠的内心挣扎中。内心充满光明、理想,富有诗意,既能正视现实又能仰望星空的令人感动的人物不是没有,但却难得一见。好像城市人已经完全被生活的浊水淘洗过了,失去了人类本应具有的梦幻。人物都处在一种利益的较量中,在现实的围困中被动地活着,甚至在泥淖中无望地挣扎,文学就缺少了引人向上的力量,更别说有对生命的形而上思考了。
第四, 新世纪城市文学更多纪实性,而缺乏想象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新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关注现实,与现实互动,成为新文学的伟大传统。现实主义也成为新文学的主流,那些非写实的文学创作甚至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如果说现代主义通过新时期的“恶补”已经相当程度满足了人们的期待,那么浪漫主义在中国却始终发育不良。就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而言,其非虚构性或报告文学特征异常鲜明,而想象性却难如人意。但是,想象毕竟是文学的基本特征,离开了想象力的文学无论如何都是让人遗憾的。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言,“对生活表层的纪实性表现,是当下城市文学难以走出的困境之一。”20
扫描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不论是王安忆、金宇澄等人笔下的上海,邱华栋、徐则臣等人笔下的北京,池莉、方方笔下的武汉,还是邓一光、南翔等笔下的深圳,其纪实性特征一目了然。作家常常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传达着对城市的经验和感受。不论是表现城市的坚硬与冷漠,还是温暖与诗意,都少有那种天马行空充满想象力的文本。这样的城市书写我们当然需要,然而看多了却也不免单调。我们同样希望看到用非现实的手法,超越现实主义的写作要求来创造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自然也不是彻底排除日常生活的琐碎,但作家总能以一种奇思遐想的方式书写自己的经验,给读者另一种阅读的惊喜。
有研究者指出:“作家的写作止于现象,止于大众的悲欢离合,和大众贴得太紧,缺少一个波德莱尔式的游荡者,缺少对大众的震惊体验。在城市里,人群是风景之所在,要像浪漫派作家对待自然风景一般审视大众。要有一个波西米亚人的眼光,在大众之中又疏离大众,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获得独特的都市体验,写出元气淋漓的城市文学经典之作。”21这是真知灼见。我个人认为:也许晓航的写作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思考。这位“60后”作家直到新世纪才开始驰骋于文坛,但他的一系列作品如《师兄的透镜》《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灵魂深处的大象》《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断桥记》《努力忘记日落时分》以及《被声音打扰的时光》等,让读者记住了他的名字。他的创作被称为“智性写作”,其小说也被认为是最具有城市意味的小说。他说:“‘智性写作就是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以不断扩张的想象力,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个超越现实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關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于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22他也确实不是用现实描述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城市体验的,而常常在一个虚构的城市空间中,通过略显夸张甚至荒诞的情节或人物,来发现和表现城市深处的秘密——都市男女的精神困境、人们在物质欲望和理想主义之间的苦苦挣扎、人性的分裂以及金钱主宰一切的价值观。“在我看来,恰恰是晓航表达出来的束手无策的无奈感,更深刻体现了我们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实。这才是让我们感到惊讶和震动的所在。”23晓航的一系列被认为富有“理性精神的想象力”24的作品,赢得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也为当下城市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惜的是,像晓航这样充满独特想象力的小说,在城市文学创作中少之又少。作家计文君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在现实中筑城花了三十年,我们用想象筑城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我想,耐心不仅是美德,还是能力。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城市文学保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想象中的城,慢慢在我们的文学中现身。”25
注释:
①陈晓明:《邱华栋“社区人系列”小说:生活的绝对侧面》,《文艺报》2011年12月16日。
②21王德领:《新世纪城市书写的模式化倾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③张抗抗:《作女》,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④⑤程光炜:《文学的今天与过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79页,第179页。
⑥徐刚:《城市小说和它面对的世界——新世纪十年城市文学一瞥》,《全球华语小说大系·都市卷》卷首语,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⑦孟繁华:《新文明的崛起与文学的变局》,《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
⑧郭冰茹:《关于“城市文学”的一种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⑨杨扬:《上海的文学经验——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⑩陈思和:《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骆驼祥子>》,载《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王玉林:《国家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呼唤——<四世同堂>文化解读》,载崔恩卿、高玉琨主编:《走进老舍》,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12苗变丽:《当代小说城市叙事的现代性研究》,《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13雷达:《雷达观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0页。
14钱文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金宇澄访谈录(下)》,《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
15张惠苑:《城市如何被文学观照》,《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16徐从辉:《网络与新世纪城市文学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
171820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19傅小平:《作家,如何与城市相遇》,《文学报》2009年7月23日。
22晓航:《智性写作——城市文学的一种样式》,《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23孟繁华:《发现城市深处的秘密——评晓航长篇小说<被声音打扰的时光>》,《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24邵燕君:《“智性写作”与“游戏精神”——晓航小说论》,《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25计文君:《想象中的城——城市文学的转向》,《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本文为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YJA751015)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