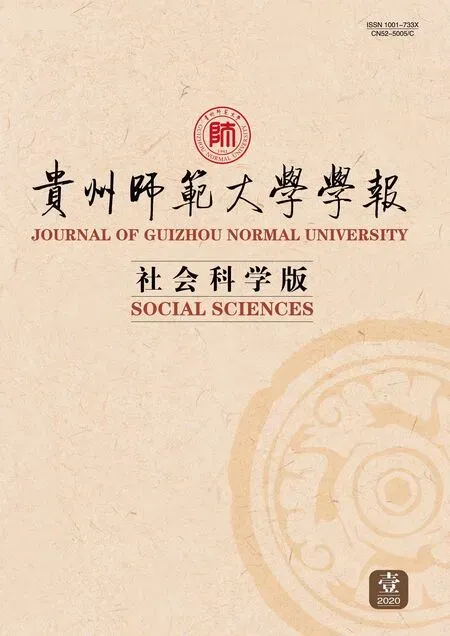出生入死:肖江虹小说的伦理追问
颜 军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阅读肖江虹的小说,“死亡”是一个必然会被注意到的现象。在肖江虹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中,几乎每篇都涉及到了“死亡”这一话题,其中多篇小说更是直接以死亡作为主题展开。《阴谋》(2007)中赵飞之死、《家谱》(2009)中许东生之死、《平行线》(2009)中保安之死、《天堂口》(2009)中火葬场里无名之辈们的死、《当大事》(2011)中松柏爹之死、《犯罪嫌疑人》(2011)中刘桂花之死、《我们》(2011)中徐老二和徐老大之死、《内陆河》(2011)中春树之死、《像风一样轻》(2012)中顺生和秋霞之死、《天地玄黄》(2013)中金大毛之死、《寻找1978》(2014)中庞德老汉的小狗之死,《求你和我说说话》(2008)中的王甲乙最终失语和《喊魂》中的范蚂蚁被打成植物人,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在肖江虹备受关注的《百鸟朝凤》(2009)和“民俗三部曲”——《蛊镇》(2013)、《悬棺》(2014)、《傩面》(2016)中,“死亡”这一话题同样得到了集中的呈现。显然,从“死亡”这一角度切入理解肖江虹的小说是很有必要的。死的反面是生,生与死是人生的一体两面。出于生而入于死,这大约是人人雷同的存在简史。死生大事,古往今来的文学都在书写这一母题。不过,对于肖江虹的小说创作来说,“死亡”不仅仅是作者创作的一个契机、一个事件,还是作者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伦理追问和价值判断的存在性基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能够理解肖江虹如此痴迷于“死亡”书写的缘由了。
一、未知死,焉知生
对生与死的自觉反思,正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性特征。何谓生?何谓死?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都是人生于世的根本性问题。《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虽说人鬼殊途、生死两岸,但人与鬼之间、生与死之间并不是分离的。在孔子这里,“事人”是“事鬼”的前提,“知生”是“知死”的前提。朱熹的解释很清楚:“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2]生与死、人与鬼,在古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人的不同存在状态而已。人人都有死,这种“有死性”是内在于人本身的。我们活着的时候被称为“人”,死之后则进入“鬼神”行列。“事人”要“诚敬”,“事鬼神”亦然。后来荀子在《礼论》中谈到这种生与死的礼法之时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始终一也。”[3]“敬生”与“重死”是合二为一的。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丧葬之礼的严肃与庄重正体现出这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重死”之道。孟子甚至在《离娄》中强调:“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4]“养生”是人情所在,人情所勉之下要达成并不太困难;“送死”是礼法所在,要做到不违礼法,“事死如生”,这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相较于“养生”而言,“送死”才是“大事”所在。
肖江虹2011年的作品《当大事》就讲述了“送死”这样一件“大事”:无双镇的松柏爹死了,在城里打工的松柏两口子忙于工作没有回来参加葬礼,在松柏妈的操持下,一群留守乡村的老者和嫩苔苔把松柏爹草草下葬。松柏爹给自己准备的上好的白杨木棺材并没有给自己的死赢得尊严,灵堂搭建得马马虎虎、道场完成得潦潦草草、棺材被卸成几块搬到坟地,一场本应隆重庄严的葬礼变得漏洞百出荒诞不经,悲剧变成了闹剧。李遇春指出:“这篇小说……通过讲述一个乡村老人艰难而尴尬的送葬过程,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的乡村葬礼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仪式,是如何在新世纪的社会经济转型中被一点点、一步步地蚕食或者吞没的。”“这篇小说仿佛是为我们勾画了一场最后的葬礼,它不单纯是一个乡村老人的葬礼,而是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消亡而描绘的最后的祭奠。”[5]生与死处于人生的两极,对死之重视映照的是生之价值,映照的是人之为人的那份尊严和神圣。钱穆指出:“死生本属一体,蚩蚩而生,则必昧昧而死。生而茫然,则必死而惘然。生能俯仰无愧,死则浩然天壤。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皆即往日俯仰无愧之生人。苟能知生人之理,推及于死后之鬼神,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5]现代社会,当死亡变得如此仓促和无足轻重之后,生的意义必然遭受到最根本的解构。作为“向死而生”的现代人,我们当何去何从?孔子强调:“未知生,焉知死?”我们今天可以反过来追问:未知死,焉知生?
死并不是生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死亡是生存的另一种展开行式。我们讲“盖棺定论”,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死了,才能对他/她的一生作出论断。如果人生是一个圆环,死亡就是扣紧这个圆环生的那头的最终环扣,通过这一扣,生与死进入了人生圆环的往复之中。肖江虹对死亡的伦理叙事,始终作用于生的展开过程。在2009年的作品《家谱》中,肖江虹就对这种死亡伦理作了揭示。故事讲述“我”在七月半根据家谱给祖先们写包时,发现家谱中某一页上只有一个叫“许东生”的孤零零的名字,这个“许东生”和家谱中的其他成员完全不同,家谱上其他成员的籍贯、经历、出生和死亡年月日时、死亡原因、安葬地都有详细的记录,唯独“许东生”这一页名字之外一片空白。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简史,家谱上每个名字后面的记录则是个人的生存简史。一个名字当然构不成一个人的简史,“许东生”留下的空白实际上意味着他的人生被“家谱”剥离、驱逐和抹除掉了。通过不断的追问,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缘由:作为“我”爷爷的爹的许东生,实际上是个被乡邻“乱棍击毙”的恶霸。家谱通过对“许东生”人生的留白,完成了对这个人最大的惩罚:这个作恶的人,在被乡邻击毙之后又被家谱杀死了一次,而且是永久性的。
谱系是维持传统伦理秩序的重要形式,生是谱系中的生,死是谱系中的死。立足于这种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传统,人们在谱系中找到了安抚寻得了永生。生前,有祖先神灵的庇护;死后,有后辈儿孙的缅怀。这是《家谱》这篇小说没有点明却试图召唤的伦理内容。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来说,这套谱系化的伦理秩序让人们的生生死死都有了依皈。然而,现代社会摧毁了这套秩序,人们生生死死的根脉正逐渐丧失。在《百鸟朝凤》中,肖江虹描述了这样一种正在去谱系化的生存状态,并对现代人生存的伦理困境作出了追问。小说中,唢呐匠人“游家班”的最终解体标志着维系乡土伦理秩序和精神生活的传统文化走向终结。小说主要人物游天鸣作为最后的唢呐人,既没有实现父亲游本盛的遗愿,也没有光大师傅焦三爷的传承。作品中写到游天鸣的痛苦:“那个黄昏,我守在父亲的坟边。从此以后,水庄再没有游本盛了,他和深秋的落叶一起,凄凄惶惶地飘落、腐烂。我在夕阳里想了好久,都没有想起我到底给了我的父亲什么。而我对于他,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失望。我的唢呐没了,游家班也没了,直到死去,他连一台送葬的唢呐都没有。”(1)本文所引《百鸟朝凤》的原文均出自肖江虹:《百鸟朝凤》,《当代》,2009年第2期,不再一一作注。当游天鸣在城里见到已经沦为门卫的师傅焦三爷及一帮不再吹唢呐的师兄弟们后,他完全绝望了:“我知道,唢呐已经彻底离我而去了,这个在我的生命里曾经如此崇高和诗意的东西,如同伤口里奔涌而出的热血,现在,它终于流完了,淌干了。”小说中的游天鸣是尴尬的,作为儿子,他没有安抚好父亲的死,作为徒弟,他中断了师傅的传承。工业生产的浪潮汹涌澎湃,城市滚动的车轮碾碎了乡村的土地,也碾碎了土地上生长的一切关系与秩序。游家班的唢呐匠们,这群吹响乡村婚丧嫁娶节奏的传统艺人,在现代生活的轮渡上迷失了自己。
谱系既是传统伦理秩序的表现形式,也是其内容本身。在谱系中生生死死,个体都能有所安抚;但在去谱系化的生存中,生没有本源,死没有归宿。在维系生死的新的伦理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人只能走在他/她和生活之间的裂缝之中。裂缝中的行走,可能有很多的错位,有人踩空了,有人掉下深渊了。不过,生命的尊严依然要去维护,或暴力的、或温情的,有种种方式。显然,在谱系伦理的背后,生命的神圣性更为根本。肖江虹在其作品中对这一个体生命尊严的伦理问题作了探索,如同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探讨一样,其展开方式依然从死亡这个事件入手。
《阴谋》(2007)、《平行线》(2009)、《我们》(2011)这三个短篇可作为同一个故事来看。三个作品讲的都是复仇。《阴谋》里面,下岗工人赵林的弟弟赵武拒捕时被警察沈飞击毙,赵林欲为兄弟报仇却误杀了保安。在《平行线》中,肖江虹把这个故事重新写了一遍,情节不变,甚至人物名字也基本相同。赵武的哥哥赵成拒捕时被警察沈飞击毙,赵武欲为兄弟报仇却误杀了保安。不过,在《平行线》中,肖江虹调整了叙事策略,叙事分别由保安和沈飞的视角展开,故事的复杂性和饱满度都有所提升。在《我们》中,这一叙事策略得到进一步的使用,不过主题依然是复仇。徐老大在外挖煤的弟弟徐老二音信杳无,徐老大赴煤矿寻找弟弟的过程中发现弟弟已经死于矿难,尸体还埋在矿洞里。徐老大找到矿主一家欲为兄弟报仇,却被赶来的狙击手击杀。这几个作品追问的伦理问题是亲情和法理之间的冲突。血缘亲情强调一种黏稠连续的伦理关系,现代法理强调的却是界限分明的区隔关系。复仇的合法性单一地建立在血缘亲情的伦理关系上,而复仇的失败源于强大的现代法理的阻止。不过,肖江虹的追问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这个层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在传统伦理和现代法理之外,肖江虹提出了生命伦理的问题。显然,《我们》中“我们”的存在困境也是我们的。
生命伦理的首要问题是生命的尊严。如果生命的神圣性是与生俱来的,那这份尊严必然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在《天堂口》和《寻找1978》这两篇作品中,生命的尊严问题得到了讨论。《天堂口》讲述的是火葬场里发生的故事。孤寡老头范成大是火葬场的火化工人,偶尔会遇到一些送过来的“很粗糙的”尸体:挖煤砸死的、广场上病死的、脚手架上摔死的……由于火葬场条件比较简陋,总之,“那些客死他乡的、煤矿爆炸透水的、吃低保的死了才会来这里,凄凄凉凉,冷冷清清,随便弄弄,就粗粗糙糙扔给范成大,有时候范成大也会问两句,说咋这样弄啊!连身衣服都没有。”(2)本文所引《天堂口》的原文均出自肖江虹:《天堂口》,《山花》2009年第23期,不再一一作注。在这些“无名尸体”火化之前,范成大总会细心地给死者清理身体,用几尺布裹上,念上一段《增广贤文》,再送入焚化炉。因为范成大有一个理念:“人老去了,应该干干净净的进去,因为那里是通往天上的入口。”《天堂口》不仅讲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彰显了一种生命伦理观。生生死死,不管是“有名”之人还是“无名”之人,只要是人,都必然会经历生与死,且没有谁能代替我们生、能代替我们死。他人之“死”也是我们的“死”,这种本质性的“死”是属于每个人的。在范成大的眼中,只有“死者”,并没有“有名”与“无名”之分。死者为大,一个人,即使活得很卑微,但没有谁有权力剥夺其死亡的尊严。范成大维护死者的尊严,实际上也是在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不知死,焉知生!
和《天堂口》的温暖不同,《寻找1978》讲述的是一个孤独的生命故事。庞德老汉有一条相依为命的黑狗,有一天黑狗被高速路上的车撞死了,老汉只知道撞死黑狗的车牌号后面数字是“1978”,于是,老汉就在收费站蹲守,想找到这辆“1978”,问个“子丑寅卯”。对庞德老汉来说,黑狗不仅仅是条狗,黑狗也有自己的生命。黑狗死后,老汉甚至给黑狗办了一场葬礼:“葬礼很隆重,坟堆不仅垒上了石块,庞德老汉还给他的黑狗诵了经。”[6]撞死黑狗扬长而去的车子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无视,这种无视实际上是对生命的背叛,是一种“原罪”。老汉的执念在于对黑狗生命的尊重,问个“一二三”的目的不仅是为黑狗申冤,还要为黑狗找回它生命的尊严。当然,庞德老汉是找不到“1978”的,他最多再重新养上一条狗。
肖江虹的作品执着于对人的存在的伦理追问。不管是对宗法伦理的探讨,还是对现代法理的思考,抑或对个体生命伦理的沉思,肖江虹都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有意思的是,肖江虹对“死亡”这一事件的书写似乎特别痴迷,他作品中的种种伦理追问,往往都建立在人物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死亡时做出的选择和行动之上。粗略来看,他笔下的死亡,要么是人在“现代”的死,要么是“现代人”的死,正是“现代”这一背景,让这些死亡事件变得突兀、破碎,甚而荒诞。肖江虹作品中的死亡事件和伦理追问,要放在“现代”这一大背景下才能体现出它的复杂性。
二、循环时间和区隔空间
一般来说,“现代”这一概念在18世纪就成为西方哲学探讨的主题之一。黑格尔认为,“现代”(moderne Zeit)就是“新的时代”(neue Zeit)[6]5。在黑格尔这里,“现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概念,用来指称不同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来的时代。黑格尔之后,“现代”的“新”的内涵不断被加强。我们熟知的被波德莱尔强调的“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概念在内涵上的扩大。波德莱尔认为现代的艺术作品处于现实性和永恒性的交叉点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8]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对美学和艺术的贡献此处不作讨论,和黑格尔比较而言,“现代”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个时代范畴,“现代”还具备了“瞬间美”的审美内涵,“现代”的本质在此发生了改变。不过,“现代”的“现代性”并不满足于只停留在审美领域,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那种消解神秘化(“祛魅”)的过程称之为“合理的”,并认为这是“现代”区别于传统的核心特征。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7]1韦伯之后,“现代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再也纠缠不清,有关“合理性”的各种标签也随之贴在了“现代性”的身上:主体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现代性”果然如波德莱尔描述的那样成了一个“时尚”的概念。进步与衰退、兴盛与没落、短暂与永恒、正义与罪恶,自20世纪之后,所有这些现象及其价值都成了现代事件。在对现代性展开反思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被屡屡提起:“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
不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讨论“现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与“前现代”比较而言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实际上,随着“现代”的突然降临,时间、空间、人等概念的内涵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护人们“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的传统伦理最终陷入了困境,然而诡异的是,陷入困境的我们还没醒过神来,却被告知“后现代”已经发生了。前一瞬间,我们还在泥田里过着刀耕火种的前现代生活,后一瞬间,在我们一条腿跨上田埂的那一瞬间,却发现田埂已经变成了公路,还没回过神来,有人猛然把一个手机塞到我们还没洗净淤泥的手上。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叠加现身,等着我们瘦弱的胃去消化这块成分复杂的压缩饼干。
肖江虹的书写没有回避这种时代的复杂性,相反具有相当自觉的“现代”意识,这正是我们前文提到的他的作品中多种伦理现象冲突的时代原因。在肖江虹的笔下,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复杂纠缠构成了其伦理追问的特定时空场域,各种死亡事件就在这错位了的时空场域里面轮番上演。
这种特定时空场域的纠缠,我把它称之为循环时间和区隔空间的纠缠。在前现代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把族人乡人等捆绑在一起。海子在诗歌《亚洲铜》里描述了这样一种与土地生死相依的情感:“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10]。生于这块土地,死于这块土地,生生死死都围绕着这块土地打转。以土地为中心,各种生存经验得以积累,各种伦理秩序得以建构。二十四节气是土地上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金木水火土是土地各元素的古老描述,八卦之一坤卦象喻“厚德载物”的大地……无疑,农耕文明的许多生存经验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而土地的相对封闭性又构成了一个比较稳定和固化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发生变化的不是空间本身,而是空间中的各种事物,对这些事物变化的各种描述最后却归结为时间的力量。因此,对源于土地的生存经验来说,时间成了构筑经验的最重要的因素。四季轮回、昼夜交替、圆缺盈亏,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时间经验,甚至被总结成“周流不息”“循环往复”的形上智慧。当土地上聚族而居的人们把祖先一步步神灵化之后,维系“乡土中国”的礼法也随之神圣化,其中对谱系的强调就是礼法神圣性的重要表征。谱系中生存着的具体的某个人并非是孤立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只是“我们”的影子,生前的“我”承受着祖先的荫庇,死后的“我”享受着后人的祭奠。祖先是过去之“我”,儿孙是将来之“我”,在世之我是现在之“我”,当“我”进入“我们”的“循环往复”的谱系之中后,“我”也就进入了永恒并实现了不朽。在这个意义上,“知死”是“知生”的前提,也是很多重要的伦理规范被建构的前提。无疑,等等这些最终都是建立在“循环时间”这一观念基础之上。
但是,随着“现代”的降临,我们祖祖辈辈不断重复的农耕生活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立在“循环时间”基础上的生存经验和伦理规范不断遭遇挑战,在新的经验和伦理没有完全建构起来之前,“我们”的生活必然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这一挑战,在根本上我们可视为“区隔空间”对“循环时间”的挤压和征服。
“区隔”是内在于“合理性”本身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以降,存在被遗忘,世界成了存在者的世界。特别是在笛卡尔之后,随着思维和广延之物的区分,一方面是主体意识不断被加强,另一方面是客体对象不断被分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越来越分明。最后的结果是,一切都降格成为存在者,存在之思完全蜕变成了存在者之思。世界丧失了深度,“所有的事物都陷在相同的层次上,陷在表层,这表层就像一面无光泽的镜子,它不再能够反射与反抛光线。广延和数量成了一统天下的维度。”[11]丧失了深度的世界成了一个平面的世界,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本书名所言:“世界是平的”。引发这一结果的原因,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存在之遗忘,但在具体的表现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生产的规模化显然是导致这种平面化的直接原因。麦克卢汉对此有很经典的描述:“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三千年的爆炸性增长。”[12]5结果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被称为“地球村”。这种切割是如何展开的?以钟表为例。麦克卢汉描述道:“作为一项技术,钟表是一种机器,它按照装配线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时间单位。经过这样统一的加工,时间就从人的经验节律中分离出来了。简言之,机械钟表有助于创造一个数量化和机械驱动的宇宙的形象。”[12]168这样的线性时间就是现代时间的典型形式。麦克卢汉还指出,这种“时间可以呈现出封闭空间或图像型空间的特性,……可以反复切割”[12]177。简言之,在现代社会,时间成为描述空间的重要方式,时间空间化的同时,空间也时间化了。我们用时区来描述地球,用轮船、汽车、飞机在各个时区间穿梭,最终,各种运输线路(水运、陆运、空运)和通讯方式把地球的空间布置成一张相互区隔而又紧密相连的巨网。城市就是这种平面化、网格化了的“区隔空间”的典型产物,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现代工业文明的“区隔空间”终归会取代传统农耕文明的“循环时间”,乡村终将消失,或者成为“城里人”的观光之地与挂在墙上的风景。这一世界变化正是肖江虹小说故事展开的大背景,其伦理追问也正是源于这一变化引发的种种困境。
《阴谋》《求你和我说说话》《平行线》《天堂口》等作品里的故事场景是城市里面的居民小区、桥洞、火葬场等,主要人物的身份设定是下岗工人、流浪汉、警察、火葬场工人等。人自身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都在这一城市场域里上演。《寻找1978》的故事发生在高速路上,这里面的寓意最为明显:高速路就是城市的动脉,深入乡村各处;乡村虽然还站在那儿,但已经不再属于自身了。庞德老汉的黑狗被“1978”撞死,这是乡村消失的预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即将涌起,而奠基于现代工业的经济发展引发的各种伦理困境也随之出现。作者通过这个简短的故事,试图对这一历史作出反思。在肖江虹另外的没有直接书写城市的多数作品中,城市始终作为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般的存在,最终影响并决定着乡村的命运。如《百鸟朝凤》《喊魂》《我们》等作品,如果离开以大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城市这一背景,就难以理解故事里乡村的没落和衰亡。不过,在肖江虹的作品中,“民俗三部曲”(《蛊镇》《悬棺》《傩面》)是对这一时空变化引发的生存困境作出反思的最深刻的作品。
《蛊镇》里面的核心人物叫细崽,一个六岁的孩子。细崽年纪小,但辈分高,村里老蛊师王昌林也要叫他幺公。细崽脸上有一块红斑,“不规则的一块红斑,差不多占据了整张脸,从额头上蜿蜒而下,漫过鼻梁,在右脸颊上夸张地铺开,一直流淌到脖颈”(3)本文所引《蛊镇》的原文均出自肖江虹:《蛊镇》,《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不再一一作注。,后来王昌林发现,这块红斑实际上是蛊镇一百年前的地图。细崽脸上的红斑因为和父亲进了一趟城,回来后就逐渐散去。当红斑(地图)完全消失之后,细崽也走向了自己的死亡。这个孩子临死之前,样貌变得非常苍老,“窄窄的额头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一张脸被枯败完全占领,深陷的双眼仿佛两个看不到底的黑洞”。细崽作为一个寓言式的人物,以自身之死完成了蛊镇时间的循环,故去-现在-未来在这个圆环里滚动,细崽是推动圆环的人或者就是圆环本身。城市是细崽的直接死因,细崽和父亲进过一趟城,却被其他孩子当成怪物,无奈回乡后,父亲给细崽承诺,脸上的红斑消失后就再带他进城,然而,细崽终归进不去那个他向往的城市。城市的空间容纳不了这个携带着循环时间的寓言,现代理性的手术刀把它不能理解的神秘的红斑切除了(“祛魅”的另一种方式),细崽的命运就只能被当成“怪物”(不正常的、不合理性的、会破坏城市秩序的)为城市所驱逐。小说末尾,王昌林和一帮老者重建了“地基还在”的蛊神祠。作者还是留下了希望,蛊镇并没有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那样最终消失。
和《蛊镇》把城市作为背景书写不太一样的是,《悬棺》直接书写了城市资本对乡村的侵略。《悬棺》以生死问题直接开头:“十四岁那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棺材。”(4)本文所引《悬棺》的原文均出自肖江虹:《悬棺》,《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不再一一作注。在小说中,这大概是燕子峡成人礼的表现方式。生和死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跨越,生有来源死有归属,生与死只是人存在的不同形式。在乡村,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可以谈论的,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很多人开始规划自己的死,缝制老衣、制作棺材、选择坟地,没有赴死的慷慨,没有等死的倦怠,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好像死亡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悬棺》里面的民歌大约表达了这种乡民对死亡的理解:“都说生来为了死,又说死是为了生。生生死死掉个头,好似睡觉翻个身。”这种建立在“灵魂不灭”基础上的朴素的死亡观念,让作品中的“我”在放置族人棺材的山洞里面见到了先人们(亡灵们)的各种生活场景这一事件得到解释。“我”因拥有了还没到来但必将到来的本己性死亡而进入了祖先们的世界,“我”的生与死的人生圆环也因此进入了祖先们的谱系循环之中,在此意义上,“我”之生并不完全属于我,“我”之死也并不完全属于我。在时间的圆环中,“我”因被祖先接纳进入这一循环,从而实现了自我人生的圆满。然而城里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稳定的秩序,资本的力量渗透到乡土的每一个角落:燕窝被掏走卖了,河流要建电站搞漂流来挣钱了,“养生送死”的仪式之一攀岩成了旅游的景观。“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在黏稠的时间长河上,乡村正在沉没,最终必将消失于城市条分缕析切割清楚的空间布局,滚滚而过的现代车轮甚至力图把埋葬古老乡村的坟墓也碾成畅通无阻的平地。
我们该怎么办?生存的时空场域已经改变,现代理性借助城市的发展即将完成它的统治。我们是系上石块和乡村一起沉没,还是保留希望去寻求新生?但不知死,又焉知生?《蛊镇》之后,肖江虹在《傩面》中继续讨论了这一伦理问题,并提出了“向死而生”的可能性。
三、向死而生的可能性
肖江虹在错位了的时空场域里面展开对人的生死伦理的追问。死亡作为人的存在的最大的局限性,如何克服“人之死”不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让主体哲学获得了根基,人随之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获得力量的人把一切都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客体)来看待,甚至把人本身也作为客体性存在来对待。福柯通过知识型的框架对西方文化进行考察,指出随着知识的基本排列发生变化之后,人作为一种近期的构思出现了,而这被构思出来的人也即将消失:“诚如我们的思想之考古学所轻易地表明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3]506实际上,在福柯看来,“人的消失”早就在尼采那里被设定了:“通过文学批判,通过某一种生物主义,尼采重新发现了人与神相互属于的时候,在那时,神之死与人之消失同义,超人(le surhomme)的允诺首先意味着人之死(la mort de l'homme)。”[13]446人“发明”了自己,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死亡,在此意义上,对于人来说,“人之死”其实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福柯指出,正是在这“由人的消失所产生的空档内”,人“才能思考”,思考他的生,思考他的死,思考一种新的开端的可能性能否“重新返回”。
肖江虹的《傩面》“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死亡”是肖江虹绝大部分作品的核心话题,不过,和这些作品比较而言,《傩面》对“死亡”的思考更集中也更直接。《傩面》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了两个人面对死亡时不同的选择和行动。一个叫颜素容,进城打工、身患绝症后返乡等死的年轻女子;另一个叫秦安顺,傩村最后的傩师,七十出头安然赴死的老人。在秦安顺眼中,颜素容本来是个“懂事”的姑娘,但进城打工回来后,却“像一朵妖艳的蘑菇”,把他吓了一跳。这朵蘑菇抽烟、喝酒、说脏话、与爹娘吵架,还追问秦安顺和他死去的老伴“做那事的时候”关不关灯,总之,这朵即将枯萎的蘑菇已经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愤怒和绝望之中,对这个世界丧失了敬畏之心。海德格尔指出,人的最大的无可逃避的可能性就是自己的死,换一个说法就是,凡事皆有可能,但只有死亡是确定无疑的。人人都会死,我们的生存其实就是“向死而生”的过程。既然死亡始终是难以避免的,为什么颜素容会陷入虚无状态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颜素容的世界破碎掉了,或者说颜素容丧失了她能够站立于其中的世界。一方面,颜素容对乡村是拒绝的:“装神弄鬼的秦安顺固然可恨,让颜素容更无法容忍的是这群乡下人的无忧无虑。这些人一路走来,贫穷、疾病、天灾人祸、生离死别似乎都抹不去他们没心没肺的烂德性。”(5)本文所引《傩面》的原文均参见肖江虹:《傩面》,《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不再一一作注。乡村的生活固然“无忧无虑”,但也“没心没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乡村人对其生活世界的那种顺应让颜素容难以忍受。或许是城市的经历让颜素容发现了自我,发现了自己可以抽离出乡村来看待这群浑浑噩噩的乡下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让颜素容具有了某种居高临下地俯视和藐视乡村的底气。生病返乡,是这朵蘑菇的潜意识之举,也是无奈之举。但是,拒绝了乡村的颜素容,也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虽然她“其实一直没有回来的念头,梦想是把钱挣足后,就在那个能吹海风的城市过完一生。可从医生把诊断书递给她那天起,回家的念头就愈发强烈了”。城市最终拒绝了颜素容,这朵长于山野的蘑菇,即使涂上口红穿上红裙,还是没有在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面找到自身的位置。
颜素容拒绝了乡村,但城市拒绝了颜素容。就这样,这个“懂事”的姑娘不可避免地掉进了城市与乡村的裂缝之中,她挣扎着,想理解自己的死,想为自己的一生找到安放之地。虽然她潜意识里还是想叶落归根,但她并不理解这“根”是什么。在和傩师秦安顺的相处中,颜素容慢慢从虚无主义的泥淖中爬出来了。
傩师秦安顺,做得最多的事除了雕刻傩面之外,就是跳傩,为离世之人“送死”。在傩村,人死了,“葬礼结束后,最重要的一堂傩戏就会上演。日子在头七,傩师会在坟前唱一出离别傩。……跳傩的自然是秦安顺,傩村最后一个傩师”。作为一个以“送死”为职业的傩师,秦安顺无疑是傩村见识过死亡最多的人。但所有的死都是他人的死,并不是自己的死,作为七十出头的人,泥巴已经堆到颈子了,秦安顺又当如何来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个事件呢?和颜素容不同的是,秦安顺并不惧怕自己的死亡。感觉到死之将近,秦安顺把傩神伏羲氏请上了神龛,然后跪伏于地,口中念叨着:“我祖伏羲,请听我语。弟子安顺,阳寿已及。生死有命,不敢强趋。凡尘已历,生死接替。敬望我祖,示我归期。”死亡是秦安顺自己的死亡,但如何死,什么时候死,这些却不是秦安顺能把握的。面对自己的死,秦安顺只能向傩神祈祷,请求傩神把死亡赐予自己。实际上,在秦安顺看来,如果死亡是一种权利,人本身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只有傩神才能决定一个人的死。死亡归属于神,来源于神的赐予。死是这样,生也是这样。生生死死,人只能去经历,去承受,但不能去决定。在《傩面》中,肖江虹用了较多的篇幅,书写秦安顺于恍惚中穿越时间的长河,像一个旁观者那样“看见”了自己父母的婚礼以及自己的出生。布朗肖在评价普鲁斯特的作品时指出,叠合的事件通过时间的转变能变成一个全新的现实:“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同一在场,被时间的流动隔开、无法兼容的多个时刻同时发生在一个感性的时刻。”[14]在这样一个重新建构的时间秩序中,我们通过事件之间的裂缝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秦安顺甚至忍不住叫了母亲一声,让时空那头的母亲不禁四处张望。不过,“母亲的眼神让他清楚了自己一直在找寻的那个神迹。按说,各有各的时序,各有各的经纬,不同时空在那一瞬间被接通了,这就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暗示。”出生是父母的赐予,死亡是傩神的赐予,“出生入死”的背后,都是“神迹”的“暗示”。叶落归根,落叶在“返回”中获得了自己的新生。对于秦安顺来说,落叶返回之根不仅是生命的谱系,更是一个充满神迹的世界。正如归乡傩里面所唱的:“一炷檀香两头燃,下接万物上接天,土地今日受请托,接引游子把家还。”这个世界是天地人神共处的世界,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世界,人的生与死是神灵的赐予,人的“还乡”也是神灵的赐予。在这个完整的神性世界中,人的生存是谦卑的,人对生死、对万物都保留着敬畏之心。在秦安顺这里,颜素容学会了谦卑和敬畏,也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的生与自己的死。
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Dasein),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世间万物构成一个关联性的整体。自笛卡尔之后被强调的主体理性,让人把自己和万物对立起来,人站在一面,万物站在人的对面,人借助主体理性把一切存在物都当成了自己的客体。结果是,存在被彻底遗忘,世间只剩下存在者。在这个存在者聚集的“世界”中,海德格尔认为,万物(包括人)实际上是一种聚合状态,是无世界的。在20世纪,这样一个存在者聚集的“世界”有各种其他称呼:“祛魅”了的世界,“单向度”的世界,“图像化”的世界,“商品”世界,“消费”世界,等等。人自身在这样的“世界”中失落了,人的原本饱满的生活世界丧失了它丰富的维度。作为“此在”的人,和万物本是一体的,但人渴望成为“超人”,然而,正如福柯指出的,“超人”的允诺意味着人将消失。
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生存于世,其无可逃避的可能性就是死亡,向死而生,这是人存在于世间必须去承担的东西。如何向死而生呢?海德格尔后期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看法。海德格尔指出:“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成其本质。人之所以能被称为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人能够赴死。惟有人赴死——而且只要人在这片土地上逗留,只要人栖居,他就不断地赴死。但人之栖居基于诗意。”[15]206我们都熟知,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这一说法来源于对荷尔德林诗的解读:“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对“神”作了特别的强调:“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惟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按其本质而存在(sein)。”[15]205如果缺少“神性”这一维度,人之“人性”也就丧失了“测度”的根据,“栖居”当然也无从谈起。在《物》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人作为能够赴死的终有一死者,其存在是和天空、大地、诸神共属一体的,这四方相互映射而各自成其本质,这种映射叫做“游戏”,世界就在这映射游戏中成为世界:“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者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之为世界。”[15]188显然,海德格尔想通过对世界的建构来实现人的自我救赎。
从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在《傩面》中,颜素容和秦安顺正好处于不同世界的两极。颜素容怕死,秦安顺赴死;颜素容骂天骂地骂神骂人、对世界毫无敬畏之心,秦安顺敬天敬地敬神敬人、对世界保持着宽厚谦和之心;颜素容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有坠入虚无主义深渊的危险,秦安顺的世界是完整的,天地神人四方的映射游戏成就了他的世界,这世界因此具有“诗意地栖居”的丰满性和超越性。在此意义上看,《傩面》就是一个关于人的救赎的故事,而这也正是其伦理性的体现。以此来看肖江虹的其他作品:或是展现世界破碎后人难以安身立命的那份不知所措,或是试图召唤神性与人性来缝合世界的碎片,以让人能有尊严地“栖居”在这大地上。正是这样一种为现代人的自我救赎寻找出路的姿态,让肖江虹的小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悲情意味。
被抛入现代这一时代大潮中,我们能否“向死而生”?如果能,那么“向死而生”的根基何在?这都是还会不断被讨论下去的话题。不过,在肖江虹的作品中,作家通过对神圣性的召唤,通过对人的尊严的维护,至少为现代人能够“向死而生”“栖居于世”保留了可能性。肖江虹围绕“死亡事件”展开的种种叙事,落脚点始终还是人的生存。知死,才能知生,这无疑是肖江虹在作品中反复追问的伦理问题。然而,随着现代性的降临,时空的变化如此突然如此让人措手不及,就算戴上了开过光的傩面,我们或许已没有机会和远遁了的诸神一起共舞了。或许,也不必如此灰心,书写的时刻,也许就是神迹显现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