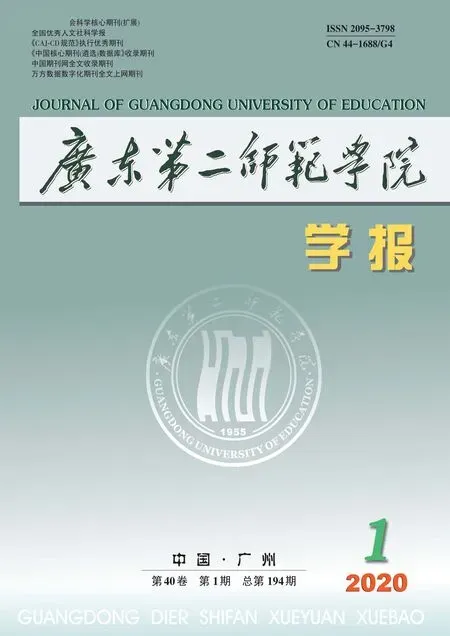从乐园到仙境:汉唐道教融创昆仑神话析论
罗燚英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10)
昆仑神话是中国古代两大神话系统之一,其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备受研究者关注。早在20世纪初,顾颉刚在研究昆仑文化时就曾指出“昆仑的全部事物笼罩在‘不死’观念的下面。”[1]由不死观念衍生而来的是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在道教产生以前,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就已在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关于生死观念的研究、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汉代墓葬的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具体可参考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侯旭东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蒲慕洲《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蒲慕洲《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的省思(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黄景春《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著作。。汉代道教产生之后,道教开始融摄昆仑神话来构建其神仙世界。台湾李丰楙曾将昆仑与王母置于六朝上清经派的方位神话构建之中加以考察[2],此一研究理路对本文颇具启发。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关注汉唐道教如何融合昆仑神话之乐园意象核心“神仙与不死药”,对其进行再创造,由此使昆仑成为地仙棲集的仙境、十洲三岛的重要神山,因之进而构造道教版本的昆仑神话。
一、昆仑神话的乐园意象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民族都曾有过乐园神话。乐园神话是人类理想生活的写照,不同民族都以自己的语言和故事,描述理想的生活。伊甸园、乐土、乐园、天堂、仙境、极乐世界、理想国、桃花源、大同世界、太平世界、黄金时代、乌托邦等等词汇均指向人类集体意识中的乐园神话,它们是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美好梦想。中国远古神话对仙境乐园有详尽描述,散见于先秦文献中,这些神话故事构成中国乐园神话的重要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昆仑与蓬莱两大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皆有乐园意象,各有其独特性:昆仑在西,蓬莱在东;昆仑在地中,蓬莱在海上;昆仑以神、巫为主,蓬莱以仙人、方士为主。“神仙与不死药”是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之乐园意象共有的核心①(2)①关于昆仑与蓬莱两大神话系统,参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第31-57页)、日本御手洗胜《神山传说と归墟传说》(《东方学论集》第2集,1954年)、王孝廉《仙乡传说——仙山与归墟的信仰》(收入氏著《中国的神话世界》,作家出版社,1991年)等文。本文所论以昆仑神话为主,蓬莱神话另参高莉芬《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一书。。
昆仑神话中关于乐园意象的描述散见于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其中以《山海经》《淮南子》最为集中,根据它们的记载,神话中的昆仑乐园具有以下特点:
1.凡人所不能及的远方异土。
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山海经·海内西经》)[3]294
2.乐园之神秘、与世隔绝来自不可测的高度和深度
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西经》)[3]294
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山海经·海内西经》)[3]298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淮南子·地形训》)[4]322-323
3.奇景异物
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瞂。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蜼、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山海经·海内西经》)[3]298-304
4.诸水之源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山海经·海内西经》)[3]297-298
5.内在结构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淮南子·地形训》)[4]328
6.神仙和不死药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山海经·西山经》)[3]47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内西经》)[3]294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山海经·海内西经》)[3]301
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大荒西经》)[3]407
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淮南子·地形训》)[4]325
昆仑乐园神话在宗教和世俗两个层面上传承和发展,成为后世仙境传说、游仙文学以及神魔小说的源泉。如《神异经·中荒经》称:“昆仑之山……仙人九府治所,与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玉童,女即玉女),无为配疋,而仙道成也。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5]东晋王嘉《拾遗记》卷10之“昆仑山”对“仙药”的特征和功效的想像更为具体和丰富,再加上“神仙”的描述以及昆仑山上的异树、异果、异兽的描写,呈现出异于道教昆仑仙境的昆仑乐园,体现了六朝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博闻洽见的特点: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四面风者,言东南西北一时俱起也。又有袪尘之风,若衣服尘汙者,风至吹之,衣则净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雾,著草木则滴沥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洒焉;以瑶器承之,如饴。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第六层有五色玉树,荫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烛。第三层有禾穟,一株满车。有瓜如桂,有奈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第五层有神龟,长一尺九寸,有四翼,万岁则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流精霄阙,直上四十丈。东有风云雨师阙。南有丹密云,望之如丹色,丹云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龙螭,皆白色,千岁一蜕其五脏。此潭左侧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肠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为脂。北有珍林别出,折枝相扣,音声和韵。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红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6]
汉魏乐府以及六朝隋唐游仙文学中的仙境意象同样存在对昆仑乐园神话的传承。如曹操《气出倡》云:“遨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7]346其《陌上桑》云:“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7]348一般认为,汉魏清商旧曲中的游仙文学,具体反映两汉的神仙传说,两汉的昆仑与西王母传说是先秦昆仑乐园神话的衍生。东晋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中反复出现昆仑乐园神话的意象:玄圃、昆墟、赤泉、三青鸟等,这可以直接追溯到《山海经》的昆仑乐园神话。六朝隋唐时期的游仙文学特别注意仙景、仙药、仙境等意象,昆仑为游仙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众多的素材,即便其中不少作品直接取材于道教的昆仑仙境说,然而究其根源皆可溯至昆仑乐园神话。
二、道教中的昆仑与地仙
与《拾遗记》不同,汉唐道教信仰中的昆仑乐园神话传承与道教宗教思想体系的造构密切相关,这是昆仑乐园神话在宗教层面的延展,也是汉唐道教对昆仑神话的再创造,其中之一体现在昆仑山与地仙说的结合方面。
在昆仑乐园神话中,昆仑是“帝之下都”。至汉代,昆仑成为仙人棲集之山。《汉书·王莽传》引《紫阁图》云:“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8]太一指汉代封祀之主神,黄帝则为黄老道所奉之尊神。太一、黄帝在汉代信仰体系中地位很高,昆仑作为他们张乐之处,可见昆仑仙境的重要。纬书《河图括地象》亦称昆仑山为圣人仙人所集之处[9]1095。后汉张衡《七辨》对昆仑仙境的描述,带有游仙的色彩,其文曰:“依卫子曰:若夫赤松、王乔、羡门、安期嘘吸沆瀣,饮醴茹芝,驾应龙,戴行云,桴弱水,越炎氛,览八极,度天垠,上游紫宫,下棲昆仑,此神仙之丽也。”[10]775
早期道教吸收昆仑乐园神话和秦汉仙说,将昆仑乐园转化为神仙治所。《太平经》卷120《不忘诫长得福诀》云:“神仙之录在北极,相连昆仑,昆仑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11]583《老子想尔注》亦称太上老君“常治昆仑”。魏晋之际,道教开始有意识地造构其神仙品级说,其中以葛洪提及的神仙三品说最具代表性。《抱朴子内篇·论仙》称“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12]20。这是葛洪在谈到李少君尸解时,引以为证的仙经内容,可见“天仙-地仙-尸解仙”之说在葛洪之前已然流行。《太平经》已有“夫上古圣贤者于官,中士度于山,下士虫死居民间”的说法[11]309,其中“中士度于山”对应地仙,而“虫死居民间”则近于尸解,此说与葛洪所引的神仙三品说近似,或者二说有相承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引《太清观天经》进一步说明了神仙三品说的内涵,即“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12]76所谓“中士得道,棲集昆仑”是道教对昆仑乐园神话和秦汉昆仑仙境说的重新诠释,将昆仑置于神仙三品体系中,使昆仑不仅仅只是地仙棲集之地,更是神仙三品说所蕴涵的“天界-昆仑-世间”之宇宙结构的中层。
道教修炼成真的境界及其阶次是汉唐道教教义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引《仙经》《太清观天经》来解释神仙三品说,说明汉末至魏晋时期神仙品级已经是道教关注的问题。在六朝隋唐道教教义发展的进程中,由葛洪引述并诠释的神仙三品说(天仙-地仙-尸解仙)始终是道教位业义的基础和基本结构。正如台湾李丰楙所说,“神仙三品说为六朝道教极具涵摄性、创发性的仙道思想,成为唐以后道教的神仙世界的主体。”[13]90而葛洪对神仙三品说的引述亦被六朝及唐代道教经典所转引和阐发。唐代前期的道教类书《大道通玄要》①(3)①《大道通玄要》不见于《正统道藏》,敦煌写本中存7件此经的写本。有关敦煌本《大道通玄要》的定年、具体内容、收录道经的考证、录文及其经教体系、义学思想,可参考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东京:福武书店,1978年)、尾崎正治《道教の类书》(收入敦煌と中国道教》(东京:大东出版社,1983年)、向群《敦煌本<大道通玄要>研究》诸文。卷14《仙品》引古灵宝经《自然经诀》云:“道言:修行得上仙者飞升虚空,体合无形,长与道同,永无数之劫也,七祖生天堂上仙。白日升天,有居上宫,封于名山,亦上仙之次也。中仙者,空中结宫室,或居昆仑、蓬来(莱)、钟山。下仙者,常栖诸名山洞宫,综领三界鬼神、地上生死之事。”②(4)②《灵宝经自然经诀》即敦煌本《灵宝经目》之《太上太极太虚上真人演太上灵宝威仪洞玄真一自然经诀》。《正统道藏》未收。此段《灵宝经自然经诀》引文见于罗振玉贞松堂藏敦煌本《大道通玄要》,本文所引据向群的录文[25]340。有关此经的研究可参考王承文的《敦煌本<灵宝威仪经诀上>考论》(收入氏著《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31-86页)。此段经文与葛洪的引述相比较,显示出一种直接承袭的关系。六朝灵宝经系自有其道派特有的位业义,如“十转”“二十七品”等,其中“二十七品”乃基于“三品说”而造构,而且《自然经诀》直接沿用了葛洪的三品仙说,可见古灵宝经对已有的仙品说既有直接吸收,亦有创发。唐代孟安排的《道教义枢》卷1《位业义》总结了自汉代至唐前期的道教位业义诸说,试图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其中不仅引述了《抱朴子内篇》所引《仙经》之三品仙说,还引述了《自然经诀》的三品仙说。此外,他也引述了《金箓简文》的三品仙说,即“地仙-飞仙-天仙”,并指地仙“游诸名山”,此说与葛洪之三品说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提及地仙时,往往有棲集昆仑、游诸名山的表述。换言之,“昆仑≒地仙”的对应逐渐地成为道教中人的常识,昆仑乐园神话也随之巧妙地被转化成为地仙棲集之仙境。
与地仙说密切相关的仙隐思想一度盛行于魏晋道教之中,得道者认为地仙远比天仙逍遥自在,昆仑则是乐土仙境的代表。道教仙隐思想与魏晋时崇尚隐遯的风气相因应。隐遯思想是魏晋之际的重要思潮之一,这是一种与名教、与现实政治相对抗的处世态度,由变乱的时代所促发。处于这种风潮之中的葛洪深受影响,《抱朴子外篇》首列《嘉遯》,充分显示其思想中的隐逸倾向。葛洪不仅将隐逸思想贯注于神仙三品说③(5)③有关葛洪的隐逸思想和三品仙说的形成,具体可参考李丰楙先生的《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之《神仙三品说的原始及其演变》一文。,使昆仑等名山成为地仙逍遥棲集之地,也将神仙三品说与金丹服食之法相结合,得道者通过服食剂量来自行决定留在人间还是升腾上天。《抱朴子内篇·对俗》云:“闻之先师云,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去留各从其所好耳。又服还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间者,但服半剂而录其半。若后求升天,便尽服之。不死之事已定,无复奄忽之虑。正复且游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复忧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间八百余年也。”[12]52葛洪《神仙传》所记传主不乏地仙之例,传文叙事中也一再强调地仙的逍遥和隐遁。例如《马鸣生传》曰:“(马鸣生)及受《太清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矣。”[14]167又如《白石生传》载白石生答彭祖所问:“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间耳。”[14]34可见,魏晋时修道之人多持仙隐思想,不欲升天为仙官,而愿为地仙逍遥于天下名山之间。
昆仑乐园本就是人们所向往的理想之境,其“乐园”性质与魏晋时期盛行的隐逸、游仙思想相契合,道教将昆仑乐园纳入神仙三品所对应的世界三级结构中,以地仙说诠释乐园神话,使昆仑之境充满了游仙之乐,并由此“造就了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神仙生活:游戏人间,逍遥自在,或棲名山,或升太清”[13]75。《抱朴子内篇·祛惑》中蔡诞的一段说辞反映了魏晋道教昆仑仙境说的具体内容,兹引如下:
吾未能升天,但为地仙也。又初成位卑,应给诸仙先达者,当以渐迁耳。向者为老君牧数头龙,一班龙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视之,不勤,但与後进诸仙共博戏,忽失此龙,龙遂不知所在。为此罪见责,送吾付昆仑山下,芸锄草三四顷,并皆生细石中,多荒秽,治之勤苦不可论,法当十年乃得原。会偓佺子、王乔诸仙来按行,吾守请之,并为吾作力,且自放归,当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诞还,云从昆仑来,诸亲故竞共问之,昆仑何似?答云:天不问其高几里,要於仰视之,去天不过十数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车,有珠玉树沙棠琅玕碧瑰之树,玉李玉瓜玉桃,其实形如世间桃李,但为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每风起,珠玉之树,枝条花叶,互相扣击,自成五音,清哀动心。吾见谪失志,闻此莫不怆然含悲。又见昆仑山上,一面辄有四百四十门,门广四里,内有五城十二楼,楼下有青龙白虎,蜲蛇长百馀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天鹿焦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其神则有无头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黄先生与六门大夫。张阳字子渊,浃备玉阙,自不带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绕之,鸿毛不浮,飞鸟不过,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鸟神马,幽昌、鹪·、腾黄、吉光之辈,皆能人语而不死,真济济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是闻诞此言了了,多信之者。[12]349-350
此段值得注意的有几点:其一,蔡诞的身份是地仙,为“老君”牧龙不勤,令其于昆仑山下芸草;其二,蔡诞所描述的昆仑景象如昆仑之高度和深度、其内部结构、昆仑山上的奇景异物、昆仑为五河所出等,显然皆源于《山海经》的昆仑乐园神话;其三,提及的仙人多属地仙之辈;最后,进入昆仑需带老君竹使符、左右契,《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左右契》,此应源于《老子想尔注》,属早期天师道的思想。至于老君竹使符应该也是早期天师道的一种符信,其原型是汉代征调所用的竹使符,亦省称“竹使”。《抱朴子内篇·遐览》曾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12]335,不过将道教符箓归于老君所造,是早期天师道的传统。此处的老君竹使符和左右契属同类性质的天师道符箓。由于《老子想尔注》中已经提出“老君治昆仑”一说,那么进入昆仑需老君之符信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王承文曾提出汉魏天师道对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葛洪之师即生活在三国吴和西晋的郑思远之时,江南“葛氏道”中即可能已开始融摄汉魏天师道教法[15]。尽管葛洪在《对俗篇》中批判蔡诞的荒唐之言,然而文中所谓“闻诞此言了了,多信之者”说明蔡诞对昆仑的描述正是葛洪时代人们对昆仑仙境所持的一种看法,而且里面还保留了早期天师道的道法元素。
三、道教洲岛传说中的昆仑山
值得关注的是,地仙与名山的结合对十洲三岛传说的道教化亦有所影响,昆仑随之亦进入十洲三岛的仙境体系,十洲之昆仑遂成为昆仑乐园神话的又一衍变。
十洲传说源于先秦时期形成的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两大系统。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东海有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战国末年,邹衍除了提出大九州之说外,还认为中国是被海所环绕的陆地,其上有五岳,陆地之外的瀛海则按方位被分为东、南、西、北四海。所谓“四海之说”在《山海经》中已经形成,邹衍只是把四海作为瀛海的四个部分。汉代纬书承袭《山海经》的四海说、邹衍大九州说、瀛海说及蓬莱三山说,形成一种以神话、宗教为基础的神秘舆图说,主要由海中之洲岛仙境构成。纬书《龙鱼河图》已有“玄洲在北海内”“流洲在西海内”“□州在南海中”等说[9]1155。李丰楙认为,“《河图》既已有‘西海’‘北海’的观念,则其他各洲也应分别布列于四海中。由此可以推知在《十洲记》撰成以前应有一较原始的河图形式的十洲记。”[16]130东方朔《与友人书》曰:“不可使尘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耳。”[10]265此处已将十洲、三岛并举,属神仙之境。十洲三岛之具体洲岛亦屡见于两汉的文献记载中。如西汉扬雄的《羽猎赋》和东汉张衡的《西京赋》都提到方丈、瀛洲、蓬莱;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出现“瀛洲、方壶、蓬莱”,蔡邕的《汉津赋》出现“玄洲”,枚乘的《游海赋》提及“长洲”。
魏晋以后,十洲三岛的传说在传承过程中不断产生流变。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曾记聚窟洲的的月支神香和猛兽、凤麟洲的续弦胶、炎洲火浣布。张华撰集《博物志》,其取材包括汉代纬书及汉晋之际的杂记,分类纂集,以示博学,其书异产、异兽类多处提及十洲物产。可见汉晋时期,十洲已是出产奇事异物的海外仙境。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卷十独记名山,以昆仑、蓬莱、方丈三岛为首,十洲之瀛洲和流洲(昆吾山)列入其中,其他诸洲则被员峤山、岱舆山和洞庭山所取代。员峤、岱舆是《列子·汤问》的渤海五仙山之二山①(6)①学界一般认为《列子》是魏晋时人造作的伪书。《汤问》提出的“五神山说”(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与“蓬莱三山说”应属于同一传承系统,二者对仙山的描述有不少共同的特征。《拾遗记》的名山说既有《列子·汤问》的影响,也结合了十洲三岛的传承。。洞庭山乃舆内名山,与吴越地区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道教灵宝派的重要符箓《灵宝五符》曾被大禹藏于洞庭包山之穴,其出世也在洞庭山。王嘉之名山体系以洞庭山殿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吴越地区有关《灵宝五符》的传说的影响。六朝道教融摄已有的十洲三岛传说,并使其系统化,进而作为道教海外仙境的主体。早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及《外篇》中就已经出现了长洲之林、炎洲风生兽和火浣布、昆仑神兽、神鸟和神马、聚窟洲异兽狮子等,说明魏晋时期道门中人熟悉十洲三岛的传说。《海内十洲记》的撰集则是道教对十洲三岛传说的整理和再创造②(7)②有关《十洲记》的撰者和年代,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以李剑国为代表,认为《十洲记》乃东汉后期道徒所作,至迟不会迟于魏晋[17];另一说是六朝人所作,持此说者颇多,其中李丰楙认为《十洲记》与上清经系密切相关,系东晋末年造作上清经的王灵期所做[16]134,王国良则认为其产生于东晋末期编造的《汉武帝内传》之后,《汉武帝外传》之前,理由是《三国志》裴注未引而《水经注》才加援用,可能出于宋齐之间[24]。从《十洲记》的内容来看,《十洲记》综合了纬书地理、魏晋杂记以及道教新说而成,因此本文认为六朝说更妥当。六朝及此后的诗赋、历代类书、小说、文集以及道书引用此书者颇多,可知此书流传甚广,影响亦大。。法国道教学者贺碧来指出,仙岛传说被《十洲记》编辑成书,其成书时间可能在六朝时期,并且可能先于上清经的传授[18]183。《十洲记》记述灵洲仙岛之境时,或泛称“多仙家”,或具体言明统领的仙官及其宫室,这些仙家多属地仙,“方丈洲”条更明确提出“群仙不欲升天者皆住此洲”。可见在六朝道教的世界结构中,十洲三岛与地仙对应。六朝道教将昆仑山纳入十洲三岛的仙境体系,也是基于神仙三品说之“地仙棲集昆仑”的考虑。
十洲三岛传说所包含的洲岛观念实际是指水中的陆地,蓬莱神话无疑是这种观念的最初形态,也是十洲三岛传说的基础。虽然在早期神话中,昆仑山既不属灵洲之列,也不是仙岛之一,但昆仑乐园神话具有“诸水之源”的特征,若从昆仑为众水所围绕的角度来看,昆仑也可以被视为水中的陆地,由此而衍生出“昆仑位于海中”的观念。东晋王嘉《拾遗记》即称昆仑山在“碧海之中”。六朝道教在造构系统的十洲三岛仙境时,亦将昆仑置于“西海戌地,北海亥地”。不过,《十洲记》虽将昆仑置于海中,但对昆仑仙境的描述却是综合昆仑乐园神话以及后起的昆仑仙境说:
昆仑号曰昆陵,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迴绕帀。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寔昆仑之支辅也。积石圃南头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阳去此四十六万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故名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一角有积金,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所。其北户山、承渊山,又有墉城金台玉楼相鲜,如流精之阙、光碧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景云烛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灵之所宗。上通璿玑,元气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20]册11:54
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十洲记》虽将昆仑山置于海中,却仍然保留昆仑神话的重要标志——“弱水”;其二,昆仑山的内在结构由三层变为三角:乐园神话之三层是凉风之山→县圃→太帝之居,十洲传说之昆仑三角则是正北阆风巅、正西玄圃堂、正东昆仑宫,这是将乐园神话的垂直结构转化为十洲昆仑的水平结构,不过三角之阆风巅、玄圃堂与三层之凉风山、悬圃之间的传承相当明显;其三,“天墉城”作为西王母治所的出现,《山海经》中王母居所有两处,一为玉山,一为昆仑之北,而昆仑乐园上也仅有增城。本文认为,墉城的原型应是昆仑乐园之增城,西王母治所之墉城说首先出现在六朝上清经派中,除了《十洲记》外,早期上清经《外国放品经》也出现了墉城说。北周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卷22《三界宫府品》承袭《十洲记》的构想,称“墉城金台、流金阙、光碧堂、琼华室、紫翠丹房,右在昆仑山,西王母治于其所”;卷23《真灵治所品》则征引《洞真外国放品经》称“昆仑墉城是西王母治所”[20]册25:59,63。唐末杜光庭则直接以“墉城”命名西王母所统领的道教女仙神谱——《墉城集仙录》。
十洲三岛传说亦见于早期上清经《外国放品经》。《十洲记》与《外国放品经》出世的年代先后目前很难确定,与《十洲记》略带小说叙事的特点相比,《外国放品经》具有更为鲜明的宗教色彩,体现上清经派的道教神学思想。叙述十洲三岛传说的集中在《外国放品经》卷下的《高上外国六品正音》。六国依次为东方呵罗提之国、南方伊沙陁之国、西方尼维绿那之国、北方旬他罗之国、上方元精青沌之国和中方太和宝真无量之国,十洲三岛散于六国之外,经文叙述异产异物较《十洲记》简略,洲岛的方位也有所变动。更重要的是,《外国放品经》不仅强调得为仙真,更通过持诵各国正音而得胡老、越老、氐老、羌老四方仙官降献来凸显上清经派的特色。至于昆仑山,《外国放品经》与《十洲记》虽在昆仑山的仙境描述上大同小异,但是《外国放品经》之昆仑山具有更深的教义内涵。首先,昆仑山位于中央太和宝真无量之国,这是道教对昆仑“地中”的诠释①(8)①关于汉唐道教的昆仑“地中”说,参见拙文《昆仑神话与汉唐道教的世界结构》[19]。。其次,以昆仑为藏经之地,即“玄文宝经、隐书古字,有千二百亿万言,在玄圃之上、积石之阴”[20]册34:28。昆仑为藏经之地,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已有记载,其文曰:“《仙经》曰:九转丹,金液经,守一诀,皆在昆仑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12]324六朝上清经典中常常提及昆仑山是藏经之所。如《真诰·运象篇第一》之南岳夫人魏华存的诰语称:“又云:‘《宝神经》是裴清灵锦囊中书,侍者常所带者也,裴昔从紫微夫人授此书也。吾亦有,俱如此写,西宫中定本。’问西宫所在。答云:‘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也,天真珍文,尽藏于此中。’”[21]早期上清经开首叙经典之出世时,常常提及经典生于太空之中,并书于玄圃之上、积石之阴。可见昆仑山对于上清经派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神圣经典出世及回归的神圣空间。最后,昆仑山上不仅刻题“三十六国音、诸天内文”,而且持诵的范围囊括了“诸天内音、外国三十六音、地下九垒之音”,这源于昆仑山所具有的“九天之澳灌,万仙之宗根,天地之纽,万度之柄”的神圣性[20]册34:28。
除了《十洲记》《外国放品经》对昆仑仙境的详细描述外,昆仑仙境在六朝其他道经中也有记载,但都较《十洲记》《外国放品经》简略。如《五岳真形图序论》节录《十洲记》,其中“昆仑山”条甚为简略,仅记载了昆仑山的基本概况。北朝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卷四《灵山品》引《洞真太霄隐书》所载的“昆仑”“钟山”仙境,与《十洲记》大体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六朝末道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②(9)②此经据日本学者吉冈义丰考证,敦煌文献中之《三洞奉道科诫仪范》残卷,与此书乃同本异名,并据此推测是书出于六朝末或隋代,最晚在唐初已问世[22]872。卷1《置观品》不仅解说了道教仙界的形成,并且列举了六朝时期出现的道教仙境诸说,其中提及的昆仑仙境属于十洲传说。其文曰:“科曰:夫三清上境,及十洲五岳诸名山,或洞天,并太空中,皆有圣人治处;或结气为楼阁堂殿,或聚云成台榭宫房,或处星辰日月之门,或居烟云霞霄之内,或自然化生,或神力造成,或累劫营修,或一时建立。其或蓬莱、方丈、圆峤、瀛洲、平圃、阆风、昆仑、玄圃;或玉楼十二,金阙三千,万号千名,不可得数,皆天尊太上化迹,圣真仙品都治,备列诸经,不复详载。”[20]册24:744-745
隋唐以后,道教对昆仑仙境的描述多保留十洲传说之昆仑的特征:外有弱水,形似偃盆,上广下狭,有阆风、玄圃、墉城、金台、玉楼等,北户、承渊为其支辅,乃西王母之治所。如唐末杜光庭《墉城集仙录·金母元君》载:“昆仑玄圃阆风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台,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塈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20]册18:168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保留昆仑为大地之中的传承,以昆仑山为十洲三岛五岳诸山的中心,但没有详加记述。北宋李思聪《洞渊集》所描述的神仙世界系统与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一脉相承,而且较之杜氏所记要更为详备,其中“昆仑山”条兼采《外国放品经》之说。此外,宋代道书《云笈七签》在卷22《天地部》和卷26《十洲三岛》中分别保存《外国放品经》和《十洲记》的昆仑仙境传承。唐代以降,道教斋醮科仪渐趋繁盛。宋代,用于祈禳济度的黄箓斋中出现以十洲三岛为亡魂所归仙境的拔度仪,即《黄箓斋十洲三岛拔度仪》①(10)①《黄箓斋十洲三岛拔度仪》撰者及成书年代皆不详。《道藏提要》认为,此仪“从词旨观之,似出于宋元间。”[22]375据李丰楙研究,北宋开始出现炼度的法事,流布于南宋,十洲传说的拔度仪基于同一需要而出现。南宋蒋叔舆纂集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五一至五六的《神位门》列醮座所设左右三班诸神名次近四百位,其中左班列“十洲三岛”之上真,与《十洲记》的十洲三岛相比,仅缺生洲、方丈洲、扶桑、昆仑。《黄箓斋十洲三岛拔度仪》当与《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的年代相近。同时,此拔度仪使用了整齐的诗歌形式,便于与道乐配合,此乃南宋道教风尚,故其撰成时间应在南宋时[16]165,168。。此经对十洲三岛之之妙景胜况的描述直接承袭《十洲记》等六朝道经,所谓“尘外十洲,尽是长生之境;海中三岛,无非不老之乡”[20]册9:743,可见十洲仙境说在道教仪式中的传承。
四、余论
昆仑由“神话乐园”到“道教仙境”的转变是昆仑神话在宗教义理诠释下的新发展,汉唐道教充分融摄昆仑乐园神话和仙境诸说,进而构造具有宗教内涵的地仙仙境及十洲三岛说。宋代道教还专门创设了十洲三岛拔度科仪,使十洲三岛说具有济生度死的宗教神学意涵。
若从道教世界结构说的角度来看,昆仑神话进入汉唐道教神学体系后,形成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层面的发展,即宇宙结构之“中”和道教仙境(十洲三岛)之列。前者源自昆仑神话之“大地中央”观念②(11)②关于汉唐道教如何将昆仑神话的“地中”观念融入道教,形成以昆仑山为中心的世界结构说,参见拙文《昆仑神话与汉唐道教的世界结构》[19]。,后者源自昆仑乐园神话。汉唐道教在承袭昆仑神话之核心观念的同时,不断赋予其宗教神学意涵,使这两个层面的发展逐步褪去神话色彩,进而成为道教神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在道教的具体宗教实践中,作为天人同构之大小宇宙中央的昆仑山、十洲三岛仙境之昆仑山往往成为道教神圣空间的象征,修道者在此特定时空中,通过象征性的仪式行为,实现自身与道的神秘融合。
作为神圣空间,昆仑山具有沟通三界的性质,此即伊利亚德所谓“神圣空间的一种最深层的意义”——“透过圣显,从一个层次穿越至另一层次,已然实现了,而且还有一道开口在此被建立起来,这道开口不是向上(通往神的世界),就是向下(通往阴间的世界或死亡的世界)。宇宙的三层次:天上、地上、地下,已在此相通了。”[23]昆仑在宇宙生成、天地运度之时,处于大地之中,并且下极地源,从而显示昆仑山可下通地下之境。而十洲三岛之昆仑则地处海外仙境,属地上之界。尽管昆仑神话中昆仑山已有沟通三界的特性,但是汉唐道教中昆仑山沟通三界的特性显然已超越了早期神话时期的天柱上通天、下极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汉唐道教构建神仙世界的三界结构时,一方面保留了昆仑山沟通三界的特性,另一方面则强调昆仑为地上仙境,而淡化其下通地下之境的特性,这一点可能与汉唐道教冥界说逐步完善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六朝时期酆都山的出现并最终成为道教冥界的神山代表;其二,以昆仑山为首的道教山岳所构成的各种神圣空间,皆具有典型的跨越、连接不同界域的特征,修道者借此建立的跨越时空的各种连接中(包括人体与外在宇宙的连接、洞天福地与人间俗世的连接等等),蕴涵着丰富的宗教神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