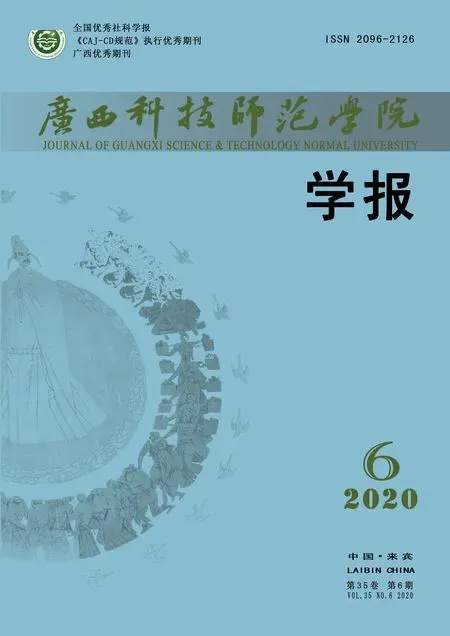后人类语境下的荒诞叙事历险
——以网络科幻小说《异人行》为例
鲍 远 福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网络科幻小说《异人行》原载于“火星小说网”,实体书由青岛出版社于2019年7月出版,它是青年女作家七马正在进行的“大图景奇幻小说”《人行世界》系列创作计划中的第一部。七马小时候游学国外,足迹遍布多国,见多识广,这让她的《人行世界》中包含了各种文化元素的碰撞与交流。《异人行》为读者讲述了一段处于“近未来”末世背景下地底异种人(白化的“蝼蚁人”)和地上普通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故事。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马波寻找姐姐曼波的“奇异旅程”而展开。谎话连篇、放荡不羁的少女曼波在十七岁生日当天捡到一本残破的故事书。她沉迷于这本记录着没头没尾故事的“书”,并和十二岁的弟弟马波一起凭借自己的想象把遗失部分拼凑出来。姐弟俩把这本微不足道的“书”命名为《恶棍》。不久以后,曼波因伤人罪被警察带走,从此失踪。五年后,高速公路连接的城市中频繁流传着同《恶棍》这本书里手法完全相同的犯罪故事,关于“蝼蚁人”的传说更是甚嚣尘上。于是,马波带着《恶棍》踏上了寻姐旅程。在这条通向世界尽头的公路上,马波相继遇见了会“拟声”的怪异女孩扮猫、精神失常的“煎蛋”、身世离奇的幻术师切·丹提、离家出走的女歌手泰卡、地下组织的猎手“鬼面人”古戎。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在高速路上驾车旅行,并遇到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此同时,鬼魅一样的白化怪物“蝼蚁人”、与《恶棍》故事情节如出一辙的犯罪传闻以及各种波诡云谲的人和事在马波遇到的旅行者们口中流传,构成了他们漫长、单调而又危险旅途中的唯一谈资,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神秘而荒诞的末日世界。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这个宏大的世界图卷徐徐展开,一个融合了堕落与抗争、黑暗与光明、罪恶与救赎的世界拉开了它的大幕。蝼蚁城的自相残杀,地下城与地上城的恩怨纠葛,普通人与“异人”的对立,处于夹缝之中的卑微者(扮猫、泰卡与小学徒)的挣扎,背叛者(曼波、鬼面人和“裂井三侠”)的复仇,强权者(城邦的统治者与蝼蚁城的维护者)的阴谋,帮凶者(莫莫、沌蛇和“黑化”的煎蛋/敦佐)的罪恶以及救赎者(半个上校、急王与大画师)的毁灭……共同交织成一曲荒诞悲凉的末世挽歌。
一、后人类语境下的荒诞故事
首先,《异人行》这种“大图景”式的未来场景和世界观设定融宏大叙事与荒诞结构于一体,给读者带来了极其震撼的阅读接受体验。这种带有“末世”特征的世界图景架构,类似于《未来水世界》《银翼杀手》《掠食城市》等科幻电影所建构的那种“启示录”或“异托邦”色彩,显示出鲜明的“后人类叙事”特征。“后人类叙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新“故事类型”。“这种故事类型以科幻类小说及影视作品为主导形式,以对未来技术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的逼真想象为基本特色,以生物基因改造的前景与危险、AI 技术与人类心智的合作与对抗、人类与其他生命共处与冲突等为典型题材,既试图表达对人类作为世界主宰和万物灵长的地位的怀疑,又在一种危机状态中重新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1]21 世纪前二十年的网络文学创作先后涌现出大量“后人类叙事”面向的科幻小说,例如:表现星际战争主题的《文明》(智齿著)、《小兵传奇》(玄雨著)、《间客》(猫腻著)和《银河之舟》(王白著),表现“太空歌剧”主题的《大宇宙时代》(zhttty 著)、《地球纪元》(彩虹之门著)和《修真四万年》(卧牛真人著),表现末世生存主题的《废土》(黑天魔神著)、《狩魔手记》(烟雨江南著)和《死在火星上》(天瑞说符著),以及表现人工智能或复杂形态智慧生命主题的《寻找人类》(RAYSTORM 著)、《深空之下》(最终永恒著)和《进化的四十六亿重奏》(相位行者著),等等。这些作品对“后人类”主题的诠释呈现了宏大的世界观设定,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性的复杂性,为网络文学20 年的发展历程增添了艺术韵味。《异人行》在网络科幻小说中属于“小成本”叙事,其内容的体量和主题的开掘都没有达到“鸿篇巨制”式网络小说的程度,也没有用精细的笔触去揭示人工智能、基因改造或是外星生命等“硬科幻”的主题和情节,而是以各种肉体和精神上都具有缺陷的“异人”作为叙述的落脚点,体现出作者希望通过在“近未来”场景中展示“人的异化”状况来揭示她对“人是什么”这一形而上问题的艺术探讨。魔幻、科幻与荒诞感仅仅是这个故事的外壳,而思想内核却是对人类现实生存境况中各种痛点与泪点的无情揭露。《异人行》旨在借助人性维度的多角度透视,为在现实生活中失意和困苦的人们提供心灵慰藉。读者透过另一重幻想中的世界体系来发现“人是什么”和人性的深度,作者借此反思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这构成了小说的核心议题。
其次,《异人行》虚构的未来世界充满了各种奇诡异常的想象性成分,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现实世界某种扭曲的“异域”或“镜像”。在小说中,有与地上屠城、新城互为犄角构成等边三角形的地下蝼蚁城,像钟面一样可以顺时或者逆时移动的钟面酒吧与尖叫桥。阑尾镇边海平面围绕的火山岛联通着地下蝼蚁城的出口,蝼蚁城的昼夜交替通过石英和名为“红雪”的神秘物质的反光来操控。沦为奴隶劳工的蝼蚁人睡在如同蚁穴一样的休憩场所……特别是在橘镇的钟面酒吧里,大画师设计的尖叫桥,其桥面以酒吧为中心,将桥体分为两半,可以像钟的指针那样转动,好似《哈尔的移动城堡》《掠食城市》等电影中那些长脚且会移动的城堡一般。种种奇思妙想在20 余万字的篇幅中徐徐展开,它们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幻想,而是充满着种种细节与真实的质感,很容易把读者带入“近未来”的末世场景中。这些末世情境的故事情节、画面描绘与场景设计不仅充斥着浓郁的魔幻色彩与荒诞意味,还像“网飞”的科幻短片《狩猎快乐》那样印刻着某种赛伯朋克艺术的美学质地。
再次,《异人行》的荒诞性还体现在其通过解谜叙述的方式构建的人类世界二元对立的生存状况。在橘镇,马波等人遇见了大画师,他是城邦世界以及蝼蚁城的设计者。他向一行人展示了一幅巨大的等边三角形地图,这幅地图出现了两个端点——地面世界上最大的两座城市屠城和新城,而另一个端点则讳莫如深。这个等边三角形是世界地图的简缩和隐喻,也是小说对“未来世界”无限可能性——“异人”世界以及其他的“后人类世界”的一种暗示。通过后文的解谜过程,我们知道这个端点指的是地下的蝼蚁城,它是城邦世界早先放逐罪犯和身心有残缺的人类的监狱。这种“地表—地下世界”的二元对立结构在科幻文艺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以回溯到科幻电影《大都会》(1927 年),后面有科幻电影《黑客帝国》(1999 年)。《黑客帝国》中的“锡安城”预示着人类对“恶托邦”梦魇——人工智能的反抗,为很多读者所熟知。而《大都会》中的“地下城”则可以称之为《异人行》中对抗性情节的鼻祖。影片中的地上世界繁华灿烂,人们在花园般的大都市里自由地生活玩乐,直到一个女孩带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闯入地表,地下劳工所在的那个残酷绝望的世界以及资本家的阴谋才被世人觉察。《异人行》沿用了《大都会》《黑客帝国》等文本的隐喻结构,只不过小说中的“地表—地下世界”不是刻板而机械的模仿。无论是被高速公路串联起的地上城邦还是由雪白的盐壁以及石英矿物构筑的地下蝼蚁城,里面生活的人物都血肉饱满,他们不仅会哭会笑,有喜怒哀乐,而且性格多样,躯体中隐藏着千差万别的人格与灵魂。在叙事的进程中,这些正常人类和“异人”的命运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幻想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它们虽然出现在“近未来”或“后人类”的语境中,却又时刻与现实社会的某些状况一一对应。作者眼光独到地为读者描画出这个与现实生活对应的“镜像世界”,它不仅折射了现实人类的生存境遇,也深刻地剖析了人性深处的隐秘世界。
最后,小说的标志性特征还体现在它的“反科幻设定”与叙事过程中俯拾皆是的“荒诞感”。小说中没有高科技设定,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后人类”群体,而只有一种“近未来”末世场景的简单设定,即由高速公路连接起来的众多城市组成城邦政府,以及高速公路地下那个暗无天日又不可思议的蝼蚁城市。被妖魔化的“异人”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蝼蚁城劳工,他们罹患“白化病”,只有区区三年的生命,还受到地上城邦政府与地下恶棍组织的双重盘剥。这种设定解构了传统科幻“美丽新世界”的现代神话模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及其组织体制中包含的人性“原罪”。小说无情地戳破了主流科幻叙事的审美乌托邦的泡沫,赤裸裸地呈现了一种未来的可能图景。在这种设定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卡夫卡(《城堡》《地洞》)、尤奈斯库(《椅子》《秃头歌女》)和加缪(《鼠疫》《局外人》)等现代主义作家笔下那种荒诞绝望的哲学迷思,也能读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树上的子爵》)和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沙之书》)等后现代主义大师所营造的那种魔幻现实主义悖论。
上述荒诞感与虚无感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小说中对半个上校达利与“裂井三侠”战斗场景的描述,既包含了作者对人类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无情戏谑,也隐含着某种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生存状况的思考。“裂井三侠”三兄弟为了对抗城邦政府不合理的税收制度而选择最激烈的反抗,半个上校则奉命带领孤军前来镇压。“裂井三侠”驱赶暴怒的牛群和蜜蜂冲击敌人,因此前来镇压的军队非死即伤,无一幸免。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半个上校注定会陷入失败的宿命中。他看透了城邦政府的虚伪,也认清了命运的无情,但为了维护军人的职责、荣誉和尊严,他仍然选择战斗到最后一息。于是,这场战斗就脱离了“正义/非正义”的伦理框架,演变成为一种荒诞的存在。战斗结束后,身负重伤的半个上校如此解释“他的战斗”:“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战斗。凡是战斗都是一场灾难。灾难从不给人时间准备,说来就来!但即便前面等着我们的是死亡,也只有战斗一条路。看不清意义的人生,永远都是场战斗!”半个上校对“战争”的解释充满荒诞色彩,也是最悲情和最深刻的反战宣言。他把战斗、灾难以及人生的荒诞感与虚无感联系起来,揭示了人生之中诸多的无奈与徒劳,犹如《西西弗斯神话》中的主人公,倔强而又绝望地把大石推向山顶,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滚落下去。小说中对“半个上校”身世的解释也充满荒诞色彩:半个上校由两个妈妈养育长大,她们都希望获得他的爱,以此补偿她们在半个上校父亲那里缺失的爱。为此,成年后的半个上校残忍地把自己的双腿铡断,并送给两位妈妈,以此来消弭两个女人爱恨交织的战争。
此外,同半个上校战斗的“裂井三侠”的故事也充满了荒诞意味,三兄弟阿门农、多米诺和莱昂的名字明示着某种神话隐喻色彩。特别是弟弟莱昂,他是一个患有痴呆症的弃儿,被两位兄长收养长大。他本来是一对不知名兄妹乱伦后的产物,其母“无脸人”生下他后在橘镇自杀,将他交给大画师,再由大画师丢给阿门农兄弟。莱昂的身世也出现在马波姐弟的故事书《恶棍》中。所以,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在现实与虚构的世界中相互交织,使得小说情节更加扑朔迷离。由此,小说为读者呈现了无休止的战争的残酷无道和人类命运的琐碎悲凉,并将两者间共存的荒诞存在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异人行》所建构的这个“大图景”世界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浪漫主义随想或“笔墨游戏”,而是在与现实生活偶然性与荒诞感的比照中获得了触及神魂的艺术质感与审美温度,以此来打动人心,引发情感共鸣。
二、多声部叙事文体的主题变奏
通览整部小说,读者会发现,《异人行》的篇幅虽然不长,却包含了十分复杂的“故事线”与情节结构,其原因是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以及她对多种文体范式的创造性套用。
第一,在叙述行为层面,小说的标题具有“拟歌行体”叙事的审美特征。“歌行体”是中国汉唐以来乐府诗的一种特殊体裁,其意义指向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与抒怀[2]。《人行世界》系列小说使用“XX+行”的标题模式,显然是作者对“汉唐古风”的一种修辞仿拟,我们不妨将其戏称为“拟歌行体”,因为其文本所凸显的叙事话语、叙述方式和情节模式仿佛是对汉唐乐府诗中的“燕歌行”“兵车行”“丽人行”“长恨歌”等体裁的创造性模仿。如前所述,汉唐乐府诗中的“歌行体”题材指涉的叙事内容大多是历史事实,如边境战事、塞外生活以及好友间的离愁别绪等,叙事是铺垫和出发点,言志抒怀与讽喻现实则是诗人情感表达的最终旨归。相比较而言,“异人行”诸篇题材所指涉的则是具有“启示录色彩”的“近未来”世界,即某种想象性事实。因此,这部小说标题所谓“拟古”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文体学意义,因为它不仅是对汉唐古典文体和文风的跨界“移用”,也暗示了其叙事行为所包孕的浓郁的“讽喻风格”。作者借助于构筑这一气势恢宏的“大图景”世界观体系,通过想象后人类世界中的各种“异人”“异事”与“异情”,表达她对未来世界与“未来的人性”可能性的一种态度。叙述者对于“异人世界”的见闻和感受,浓缩在作者的文本建构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体验。因此,“异人行”的“拟古”话语行为既是对小说思想风格的暗示,也是对文本的叙事内容和主题的明喻。
第二,在叙述本体层面,小说使用了“嵌套叙事”技巧创造出一个“层层镶嵌”的故事。“嵌套叙事”来自于托多罗夫的诗学理论,指的是叙述者“在其讲述的故事中讲述新的故事”,其原理就好比叙述者拥有某种神奇的“故事机器”,它可以不断地制造出更多新故事。“所有叙事都要使其陈述活动的过程清晰明白;但这样就必须出现新叙事,在那里,这个陈述活动的过程只是陈述的一部分。于是讲述的故事总变成被讲述的故事,新故事映照在被讲述的故事中,找到它自己的形象。”[3]《异人行》是“嵌套叙事”的典型体现。作者以小说中出现的虚构文本《恶棍》为焦点,并在叙述过程中有意地模糊《恶棍》中的虚构情节与故事中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甚至把故事中的现实世界与《恶棍》中的虚构情节的关系“置换”,从而生成一系列相互“嵌套”又彼此“戏仿”的“文本簇”。《恶棍》是儿时的马波和曼波无聊中拼贴起来的故事集,集合了一些残缺的虚构故事,分别讲述一些奇人异事,例如:“疤脸大盗”、“花儿”的故事、“无脸人”的故事、幻术师切·丹提的传闻以及有关扮猫身世的“胎记”故事等。这些故事游移在虚构和纪实之间,构成了一个彼此映射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网络”。此外,对于这本《恶棍》在小说故事情节建构过程中的“诗学功能”,马波的评价最为贴切,他曾对切·丹提说:“我那本是曼波拼贴的,他们手里的却是印刷装订好的册子,我那本是第一本,那本书根本不存在,或者说它存在。那些故事都是曼波凑起来的,无脸人的故事是她听过的橘镇传说,你的故事则是她搜集的报道。她把这些拼凑起来,形成了她的现实生活,‘恶棍’就是她,就是她的一切!我敢肯定,我姐姐曼波也是泥浆天使的核心人物。这些年高速路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泥浆天使还有她相关。”《恶棍》里的故事,有的是小说世界中没有对应的虚构,有的则是小说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实,有的是它里面的故事成为后来泥浆天使们犯罪的“前文本”。这些小说中的事实、“故事中的故事”以及虚构的叙事与《恶棍》的故事所形成的文本之间产生了“量子纠缠”,构成了奇异绚烂的叙事迷宫,为“嵌套叙事”的文本实践提供了崭新的审美接受体验。
第三,在叙述角色层面,《异人行》及其角色所虚构《恶棍》里的“故事中的故事”在叙事结构和内容层面彼此嵌套、环环相扣,既映射了故事中的现实世界人物和事件的复杂关系,象征着马波、曼波、扮猫、切·丹提等人的命运,也是另一层次的“元隐喻”和“元叙事”[4]。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小说故事世界中的角色的“述行语言”,向现实的读者“隐喻”叙事虚构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异人行》在叙述方式与故事结构的层面具有向《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交叉小径的花园》等“嵌套叙事”文学经典致敬的意味,其“故事套故事”结构的视觉形态也是对《黑客帝国》《盗梦空间》《故事中的故事》等科幻电影的跨文体“戏仿”。由此可见,它是以网络小说文体独有的叙事经验来建构和呈现叙事隐喻多重可能性的一次重要探索与历险,“元文本”的隐喻方式,“故事套故事”的叙事奇观以及多重文体经验的“复调式”回响在波诡云谲的叙事进程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主题变奏曲。
第四,小说还通过“末世+公路+悬疑小说”的交互性体裁构建了一个“多线程”的故事体系。“公路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主人公乘坐的路上交通工具所遇到的事件与景观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此讽喻现实人生、揭示生命意义的文学作品。《异人行》具有显著的“公路小说”叙述套路,它基本上沿着主人公马波的活动轨迹来建构小说的叙事空间,展开故事情节。小说的叙事路径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高速公路地理线”,从瓦肯镇启程,途经橘镇、旧车拍卖场、屠城、阑尾镇、新城的下城与上城,然后深入地下的蝼蚁城,最终回到地上世界。主人公马波在这一路呼朋引伴,接任务“刷怪”并寻找自己失散的姐姐曼波,一直向前延伸的旅途不仅记录了马波的见闻与感受,也为读者拼凑出这个“近未来”的末世画卷。同时,小说还套用了大量悬疑小说的叙事要素来展示“异人世界”的荒凉、残酷与神秘,揭示了命运的无常,生存的荒诞以及人性的复杂。小说以被妖魔化的“蝼蚁人”为叙事的“噱头”,展示了这个“大图景”世界的冰山一角,同时串联了曼波的失踪之谜、大画师与地上地下世界的关系之谜、扮猫的身世之谜、鬼面人的身份之谜、阑尾镇的形成之谜、城邦政府与蝼蚁城的共生之谜、蝼蚁人的终极命运之谜以及《恶棍》与小说中的世界关系之谜,故事内容环环相扣、叙事结构层层深入,形成了一个意义指涉的“莫比乌斯”之环。主人公马波的寻姐之旅迷雾重重,解开旧的谜题,新的谜题又接踵而至。主人公的连续性的“解谜”过程,不仅增强了叙事的张力,丰富了小说人物形象谱系的审美创造,也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神奇变幻的艺术世界[5]。借助于“公路+悬疑小说”的叙事模式,《异人行》在极短的故事篇幅中别出心裁地构建出多线程相互交织的复杂“故事线”,把一个简单的历险故事的叙事进程开发到了极致,并产生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审美效果。
综上所述,《异人行》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集合了多种艺术体裁和表意实践的“跨文体”叙事文本。因为它在文体上融合了不同的体裁,借助于有意无意中呈现出奇幻故事、反乌托邦小说、图文书①小说中内附了10余幅城邦世界的地图、标记和示意图,并配有简单的文字说明,补充了语言叙事表现力的不足,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直观依据,这也是一种体现“语图叙事”张力的文体实践。、魔幻现实主义、科幻电影、悬疑小说和网络游戏②小说的叙事进程明显可以被“转换”为地上城邦世界与地下蝼蚁城两个大型“游戏副本”,主人公马波的历险也可以被比喻为“冒险打怪”的游戏体验。等不同文艺体裁的多元结构,彰显出某种“百科全书式”文体的美学特征。
三、多元审美视域下的“后人类性”悲歌
在以“超长”和“注水”特征见长的网络小说中,《异人行》仅仅算得上是一部“小品”。但是,如此简短的篇幅却不仅囊括了丰富多样的主题,也成功刻画了数量惊人且各具特色的人物。除主人公马波及其小团队之外,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地上城和蝼蚁城的设计者大画师、阴险狡诈的卡车司机沌蛇、反抗城邦的“裂井三侠”、悲天悯人的半个上校、告密者兼作曲人水听、贩卖私酒的酒吧老板铁酋长、落魄的金融大亨急王等形成了立体多样的人物谱系,体现了作者出色的人物刻画功底。每一个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包含了丰富的故事;每一段只言片语的人物形象勾勒,都揭示了这些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善恶价值观的对立冲突与妥协被融合在人物塑造之中,并多侧面地展现出来,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意义雕琢和主题表现空间。
其一,小说中刻画了各种各样的“异人”或后人类形象,特别是小说对蝼蚁人的描摹,充满了神秘怪诞色彩。小说除了利用悬疑技巧描摹“蝼蚁人”,还不惜笔墨描绘正常人中的“反人类”或“非人类”角色,他们大多数是被异化了的普通人,如卡车司机团伙头目沌蛇、泥浆天使杀手莫莫等,他们身上种种卑鄙猥琐、阴暗狂躁、变态残酷的言行举止不仅令人畏惧而且让人不齿唾弃。即使是小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主人公之一曼波,作者也没有把她塑造成一个“拯救弱者于水火”的“圣母形象”,而是通过抽丝剥茧的叙述刻画了她性格的复杂性,揭示了其人格的瑕疵与裂隙,并通过她最终的毁灭来彰显人性的不确定性。因此,《异人行》并不像诸如《废土》《狩魔手记》《地球省》(龙一著)等大多数“近未来”科幻小说那样去露骨地描写道德崩坏的“恶托邦世界”,也没有着力去刻画某种看似和谐美好的“乌托邦社会”,而是截取了“想象性未来”的一个“断面”,以“公路小说”和“悬疑文学”的表现方式,借助城邦世界中的普通人与地下城“白化”蝼蚁人的敌对、纷争与互相伤害的情节,为读者揭示出未来社会中可能存在两个互相冲突的部分,即真实的人性与虚构的末世之间的审美张力。与此同时,小说也没有触及当代(网络)科幻小说(《三体》《地球纪元》《遗落南境》《安德的游戏》《分歧者》《饥饿的游戏》等)常见的“后人类社会”批判理论诸多宏大叙事的主题,例如:星际战争、宇宙社会学、生命政治、生存危机或“太空歌剧”等诸层面,而始终落脚于人性善恶与社会情境剧变之间的矛盾冲突,构建一种人文关怀的叙事维度,最终确立“人”的价值与意义。
其二,地下蝼蚁城白化了的蝼蚁人总会让人想起《大护法》中苟且偷生的“花生人”。蝼蚁人白化的病变皮肤与面相让地上的人们感到恐惧、恶心和鄙夷,因为这些病态的身体形貌表现的是地表人类想要极力隐匿的内心的罪恶、丑陋与阴暗的欲望本性。蝼蚁人在曼波的鼓动下想要和地上的人谈论合作以及他们寻求生存权的举动,就像小镇上的“花生人”长出了眼睛和嘴巴,让人类感到恐惧一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人类真正恐惧的并不是这些“异人”恐怖的外形,而是他们内心那些见不得光的罪恶欲望。对此,小说描述道:“传说蝼蚁人的身上带着病毒,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会死。而蝼蚁人也不会在人前露面。他们的存在方式就像是每个人人性里丑陋的一面,连自己都不想看到自己。”因此,当蝼蚁人希望走出地下世界并和地上人类和平相处时,才会受到城邦的当权者以及普通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心中的罪恶与丑陋,因此也不想给蝼蚁人生存的机会,所以他们启动了“水泥匣计划”,派遣军队用水泥封死了地下蝼蚁城的各个出口,也徒劳地希望将他们内心的黑暗与罪恶永远尘封于地下。然而,蝼蚁人的挣扎与反抗,地上的人们的阻止和镇压最终都是徒劳的,因为这个世界注定会在“最后一战”中土崩瓦解、鱼死网破。如前所述,即使是蝼蚁人的领导者曼波这样的叛逆者,也并不是正义的化身,她只想报复人类社会,以此宣泄她自小被父母和人类遗弃后在心中积压的嫉妒与愤恨。曼波既可怜又可恶,她是社会的弃儿,同时她也抛弃了这个世界,她把所有蝼蚁人的生命当作她向社会复仇的可悲工具。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把人物描写成单纯的英雄或者恶棍,而是揭露了其作为有人格缺陷的个体的多个侧面,这就避免了“扁平化”的人物塑造带来的呆滞感与单向度,使得网络科幻小说的人物性格刻画获得了复杂的延展性维度。
其三,在小说所刻画的这个爱恨交织的有些灰暗的故事背景中,也暗含着某种明晰的人性光彩,正因为如此,小说的情感基调才不至于那么低沉落寞,能够为读者带来人道的温暖,这体现在对半个上校以及急王的遗产继承人小学徒最终命运的交代。在蝼蚁人炸毁地下通道涌入地上世界后,半个上校达利果断地解散了屠城的军队,并拒绝参与对蝼蚁人的屠杀,这不仅表明这个身体残缺但人格健全的人勇敢与正直的品性,也暗示了他与城邦政府的彻底“决裂”。在半个上校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充满人性光辉的大写的“人”。半个上校是真正的英雄,他身上的人性光辉冲淡了小说悲剧结局的灰暗色调,给这个堕落的末日世界带来了某种慰藉与希望。历经艰辛来到屠城的小学徒则用急王的钱购买了被蝼蚁人烧毁了的半座屠城的废墟,他要建立一座大学,聘请屠城大学的教授教他读书。对于财产经纪人,小学徒只有一个要求:在废墟上的大学建成之前,打开所有的路灯,这样他就可以在路灯下面读书,而其他想读书却又上不起大学、点不起灯的贫苦学子也可以在他的路灯下读书。由小学徒倡议而开启的这些“废墟上的路灯”,成了人性之光的双重明喻,路灯不仅给人带来光明、指引方向,也象征了这个废墟一般的末世世界中依然有像小学徒这样初心未泯的赤子。他们懂得命运的艰难、获取的不易、拼搏的价值,所以他们才会非常珍视一切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并能够将自己的努力和坚韧转变为一面旗帜,指引着其他保持初心的芸芸众生,希冀他们也能在微弱的路灯指引下改变自己的命运,迎来希望的生活。在善恶二元价值观体系的话语建构之外,《异人行》别出心裁地塑造了半个上校、小学徒、泰卡甚至敦佐这样一些充满着赤子情怀的配角人物,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展示人性的复杂、卑微与伟大,向纵深方向拓展小说故事情,建立了一个富有深度且又感人至深的审美乌托邦,唤醒了读者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在一个青年作家身上,我们虽然看到了她对人性复杂的犹疑心理,但也能切实领略到其借助于深厚的艺术修养与普世价值关怀所彰显出的人格魅力与人文情怀。
其四,小说展现人性复杂性的另一个方式是它集中地描绘了各式各样的“后人类的毁灭”。例如:城邦的权谋者(屠城和新城的城主)死于曼波复仇的大火,卑微的蝼蚁人(杀手“微声”和其他无名者)死于自相残杀,为众人抱薪者(扮猫、急王)死于困厄,权谋的帮凶者(大画师、古戎)死于暗杀,作恶多端的恶棍(沌蛇)死于马波的反杀,甚至在背地里谋划一切的终极大Boss 曼波最后也死了……一场终极大战过后,绝望的废墟上只剩下理想破碎的追梦者、逃避现实的自我放逐者以及面对无常命运的幸存者。在这一出末世悲剧中,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正义与无道一起在混乱中毁灭。善恶有报的政治伦理并没有在这部小说中获得叙事正义的支持,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叙事伦理所透露出来的荒诞虚无和焦灼绝望却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震撼感,它不仅增强了小说作为一部反科幻、荒诞未来主义的叙事文本的“艺术成色”,更体现了网络科幻小说在主题思想和艺术价值追求方面所作出的大胆突破,极大地拓展了当代网络文学的审美表现力。
四、结语
“即便是天使,也看不见人们心里的苦难。……蒙眼天使的意思其实是:神也不长眼!”因为,“现在这个人人自危的艰难世界,没人顾得上尊重和照顾别人”。这是小说中最能击透人心的话语。很明显,《异人行》通过20余万字的篇幅、带着极大的诚意为我们展示了“蒙眼天使”所看不见的各种人间悲剧与苦难,重新唤起我们对于“人是什么”的思考。由此看来,小说虚构的故事虽然是“近未来”的“末世”,但它的情感指向却是真实可感的现实世界。七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蕴含朴素哲理的未来故事,这个故事有着荒诞与魔幻的外壳,但却隐藏着一颗悲悯而人道的内心。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仇恨、爱恋、责任、权利和道义所做的种种决断与取舍,既蕴含着西方式的理性思考,又潜藏着东方式的天道情怀。作为一部网络科幻小说,《异人行》为读者提供了一曲多声部交响的后人类生命恋曲与人性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