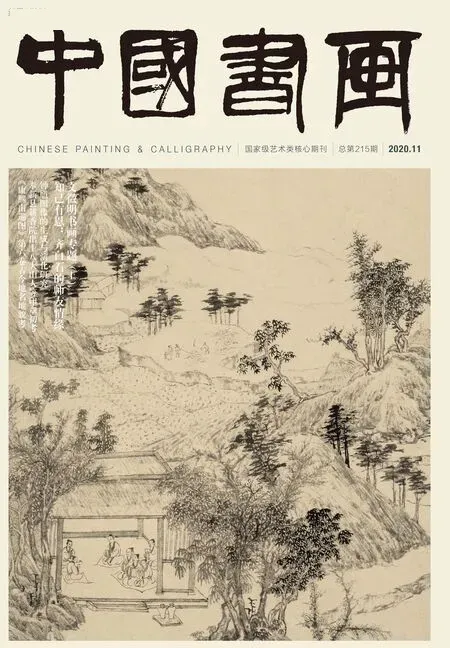一次对王铎的重新勾勒:基于《王铎年谱长编》
◇ 薛龙春
编纂一部数据翔实可信的王铎年谱,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王铎一生的仕宦、行踪、交游及艺术活动,也能为治明清文化史和政治史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20世纪初,日本出现现代展厅与书法展览,模仿以王铎为代表的“明清调”(即巨轴行草书)的作品以强烈的视觉性大获成功。这刺激了日本书家开始对王铎进行研究,其年谱方面的成果,首推须羽源一1975年在《书论》杂志发表的《王铎年谱(稿)》,1992年,村上三岛主编《王铎の书法》五大册,也收入福本雅一所撰《王铎年谱》。这两部年谱以部分王铎书法作品以及藏于日本的《拟山园选集》诗集(清顺治十年刊五十四卷残本)为核心资料。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书法展览也蓬勃兴起,王铎及其他明末清初书家如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也受到普遍的青睐。1993年,有关单位在王铎家乡孟津举办了一次王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高文龙、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附录了简要的《王铎年表》,成为大陆学者王铎年谱(表)编著的开端。随后的一些相关出版物中也都附录王铎的简要年表,但这些成果未能全面超越日本学者。
2007年,张升编纂的近20万字的《王铎年谱》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作者出身历史学,他使用正史、实录及野史著作,也从时人的诗文集中辑得部分数据,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王铎的认识。但该谱也存在一些不足:一、对各版本的王铎诗文集,以及诗文集未收诗文、信札与题跋等未能进行充分的辑录与考订,纳入年谱的诗文作品有较大局限;二、对于王铎传世书画作品的搜集明显不足;三、对王铎行踪及社交圈的考察较为粗疏。
总体上看,已经出版的《王铎年谱(表)》,不是使用文献不足,材料捉襟见肘,就是未将王铎作为文学艺术家这一特殊的谱主身份来对待,未能充分反映王铎文艺活动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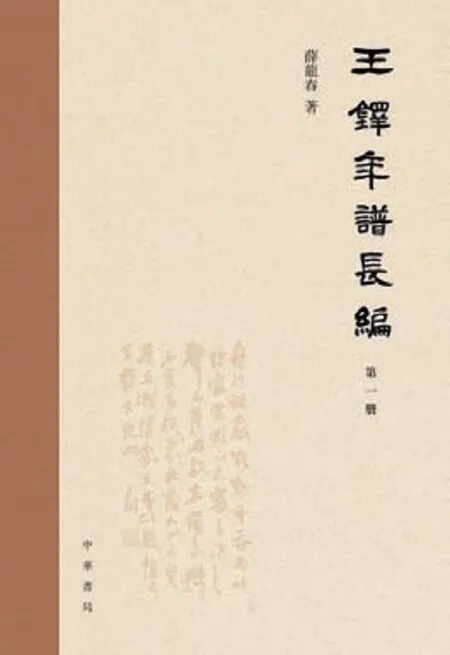
《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中华书局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2006年春,笔者开始研究王铎与晚明书法,决心系统搜集各种相关数据。日积月累,资料日丰,在撰写相关研究论文的同时,也整理与考订这些资料,重新撰写王铎年谱。本书力求全面展现王铎一生的行迹、活动、交游与艺术活动,约略而言,着力点有四:
一、本书使用了明清若干版本的王铎诗文集,如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年(1653)刊《拟山园选集》诗集,这一版本比日本所藏残本多出了整整二十一卷。天津图书馆藏《王觉斯初集》黄居中钞本、河南图书馆藏明崇祯刊本《拟山园初集》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拟山园选集》残本,收录了较多王铎早年的诗文,对于我们钩稽王铎50岁以前的生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书也对30余种传世的王铎诗文手稿进行辨识、采录,并力图考证写作时间,纳入谱中。笔者还仔细爬梳王铎周边友人百余部诗文集,以及清初各类总集、选集,其中的相关材料经过选择,皆编入相关年份。本书所使用的诗文集有不少较为罕见,如国家图书馆藏张镜心《云隐堂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张文光《斗斋诗选》、上海图书馆藏张鼎延《嶰谷巵言》、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郑之玄《克薪堂诗文集》等。本谱还广泛利用各种地方志,除了人物传记之外,也从中辑出不少相关的唱和诗、序记、碑志、往来书札等。
二、以图像数据而言,王铎的书画作品,《王铎书法全集》仅收360余件,《王铎书画编年图目》收500余件,且真赝杂厕。本书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有关机构与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国书刊及国内外拍卖会图录中搜集到1000余件可靠作品,既包括卷轴扇册等正式“作品”,也包括书札、题跋、签条、诗文稿等日常书写,兼及刻帖、碑板、版刻序跋等经过编排、加工的手迹,其中有近半数难得一见。每条尽可能详其形制、材料、尺寸、著录情况、收藏地、内容,并释读题识、跋文与印鉴。如故宫博物院藏王铎书札60余通,上海图书馆藏王铎书札20余通,香港近墨堂藏王铎致戴明说30余札,这些重要的数据素不为学界所知。又如刻帖,过去学界熟知的唯王无咎刻《拟山园帖》、张鼎延刻《琅华馆帖》,但梁羽明刻《银湾帖》、薛葳生刻《日涉园帖》、张缙彦刻《论诗文帖》、李化熙刻《二十帖》等其实皆有拓本传世,除了保存部分王铎书作外,刻帖的主体部分都是王铎与友人的书札,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三、本书力求考订王铎诗文、书札、题跋中所涉及人物的确切身份。有些通过诗文集与地方志就可以获得信息,有些则颇费考索之功。如台北石头书屋藏王铎《楷书卷》,卷中并无明确的上款,但笔者注意到第五行高出左右半格,起首两字是“遂兄”,并根据序文中提及此人在芜湖征税,考证出这件作品乃为王思任所书。王思任字遂东,崇祯初年曾以户部主事榷关芜湖。又如,上海崇源2009年春拍有一件王铎书作刻帖,题为《予患难中,千里提携,千古义人,爰用作歌》,从《拟山园选集》诗集七古卷四《千里过存》中“我爱季千里,无能度其美”句,知“千里”姓季,又据五律卷二十一《千里榷广陵闸不及相送》,知其人曾榷关扬州,查《(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于扬州钞关下发现季之骏之名,因知千里即季之骏。本谱共考证出各类人物数百人。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问题从未被解决。
四、大量无纪年的诗文与书画作品,笔者也极力考索、推求,纳入相关年月,如此,则零散的材料与信息便成为有组织的结构。将王铎不同形式的作品进行信息勾连与综合排比,常常可以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如济南文物商店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款识云:“天启乙丑孟冬,夜漏二鼓书,时同韩官岑、南思敦、温与恕、余望之,酒后胡涂,满纸葛藤,可笑也。涵一老先生大词宗教我,嵩下樵王铎。”涵一即陕西三原焦源溥,此作书于1625年十月。北京大学藏《王铎手书残稿》有《焦涵一诗集序》,中有“涵一与余相遇于十年之前,长安舍中,同南中干烧蜡谈诗”云云,思敦、中干都是王铎同年进士南居仁的字,故知此序亦作于此际。又,私人收藏王铎《与涵老札》,无纪年,中有“诸老谕以画者,俱未敢领。……兼之天寒研冻,又无暖室,故如此。然老先生一画,虽手足肆应中必欲为知己一涂污之”之语,据“诸老”“天寒”亦知作于此时。这三条材料在年谱中组织于一处,其作用非零碎状态可比。系统的数据搜集与排比,不但使得以年谱的形式全面揭示王铎的生平、仕履、行踪、交游及艺术创作活动成为可能,也为勾勒王铎的同僚圈、乡党圈、艺文圈等不同的人脉网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光阴荏苒,匆匆十年。面对成稿,笔者自知学植浅薄,必有失当与错谬之处,诚望发现错误的读者,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