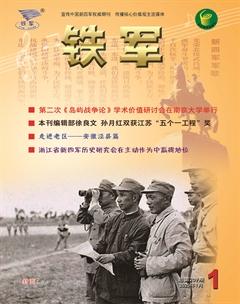心灵底片
边震遐

编者按:7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第三十九军等新四军传承部队,和其他部队一起,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开赴朝鲜,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发扬铁军精神,经过3年浴血奋战,打得美军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乖乖签字。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豪情,打出了新中国60多年的和平岁月。几十年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幸存者的回忆揭开了尘封已久的悲壮故事,当年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依然让我们心潮澎湃;这些“最可爱的人”展现出来的崇高信念与钢铁意志,再一次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与亲历者一起走进那烽火连天的激情岁月里。
人们在生活中,会留下很多师长亲友的照片,天长日久,有的照片难免渐渐褪色,而留藏在心灵中的底片,尽管岁月消逝,却依然鲜明清晰。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战场,分配在东线的第九兵团政治部工作,常听到机关干部们称颂智勇双全的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将军。我是新兵,曾遗憾没能在新四军东进时期,看到陶勇率部在苏中歼倭的雄姿;也没能在渡江大战中,看到陶勇击伤敢于向我们挑衅的老牌帝国战舰“紫石英”号的壮举。但是,在朝鲜战地,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位传奇名将的风采和魅力。
有一次,我作为一名摄影记者,随着陶勇上前线。我们的吉普车在敌机重点封锁区“鬼门关”的北缘停了下来。面对盘旋的敌机和挂在空中的照明弹,防空哨兵要我们把汽车隐蔽起来,等到拂晓时刻通过封锁区。
秘书问,为什么非要等到拂晓? 哨兵说,拂晓的时候,敌机对地面目标看不清楚,比较安全。陶勇听了跨下车,踱了几步,问防空哨兵:“绕道行不行? ”哨兵说,绕道要多走200多公里路,也有“鬼门关”。
“那就冲过去!不能在这里干等几个钟头。”陶勇迎着照明区一挥手,拿定了主意。秘书和警卫员互相望望,明知危险,都没有说话。驾驶员却皱紧了眉头,显然是在为首长的安全担忧。
陶勇看了看手表,走到驾驶员身旁,斩釘截铁地说:“你坐到一边去!”驾驶员知道陶副司令的脾气,不吭声,带着一脸的无奈,乖乖地让出了自己的驾驶座。陶勇身边的人都知道,还在苏北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部队缴获了第一辆摩托车,他不顾连连摔跟斗,当天就学会了驾驶,以后就敢在火线上穿梭飞驰。就这样,陶勇亲自驾起了吉普车。
小车拖着滚滚烟尘,奔腾跳跃,车上的伪装树枝纷纷甩落路旁,挡风玻璃和引擎盖板反射着照明弹的强光。敌机很快发现了目标,竟钻到照明弹底下进行观察。啸声震痛耳膜,机翼闪着寒光。驾驶员和警卫员探身到车外,及时报告敌机动向,陶勇就根据情况不断地改变着车速。
“俯冲啦!”驾驶员和警卫员同时喊。
敌机怪啸着凌空直下。陶勇一踩刹车,随着机枪的连射声,只见一串串子弹冒着蓝色火苗,噼噼啪啪地打在前方路面上;当又一架敌机刚进入俯冲并开始发射火箭弹的时候,陶勇却猛踩油门,让小车像快马着鞭似地向前窜去。只听得轰轰两声,两枚火箭弹远远地落在车后爆炸了。
敌机连续攻击没有奏效,便在路面上投下了凝固汽油弹。陶勇拉低帽檐,圆睁双眼,咬紧牙关,镇定地将方向盘向旁一打,小车灵活地划了一个半弧形,紧贴着路沿,避开燃烧液的高温中心,又向前飞驰了。热浪扑进车厢,燃烧液沾在车轮上,像长了火的翅膀一般,扇动着,扇动着,带着呼呼的声响。连续飞驰了好几百米后,燃烧液才被车轮的离心力所甩净。
就这样,我们终于胜利地冲出了被照明弹映得通亮的封锁区,除轮胎烧了一点外,谁都没有损伤一根毫毛。
到了安全地带,陶副司令这才把汽车傍着山根停下来,擦去满头大汗,脱下帽子扇着凉风。随即,他又同秘书和警卫员一起,帮驾驶员检查了汽车,加足冷水,又用脚踢踢车胎,用手拂拂飘到鼻子跟前的焦臭味,笑着说:“没啥没啥,小意思!”说着又像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样,搂着驾驶员和警卫员的肩膀,认真地说:“回到机关,可不能向司令员告状喔!”原来,司令员对他喜欢亲自开车并爱开快车的事,曾经多次提出过警告,他怕再一次“挨剋”。这正是陶勇的性格。他既有雄狮般的勇猛,还有着长者的温厚、孩子般的天真。
我开始认识陶副司令,是在1951年夏天。那时,中朝军队经历了5次大战役,一直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我们的兵团机关从咸兴地区移到了江原道的一处深山里。有一天,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通知我到司令部去,说是陶副司令有事要“请教”。我背起照相机,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司令部驻地。经哨兵指引,我在茂密的松林中找到了陶副司令的住所。瞧,这简直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别墅:茅草盖顶的小屋连着防空室,门前有一方清除了杂草的平地,旁边筑了花坛,种上了色彩斑斓的野花;一棵矮树上,还用废电线拴着一只小猴子,正在攀缘跳腾。来到小屋门口,我就听见了一片噼噼啪啪的木器撞击声,夹杂着人们的阵阵欢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人围着一张小小的康乐球桌,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围观当拉拉队。其中有个打球人劲头特別大,嗓门特別高。他穿着衬衫,挽起袖子,一边打球,一边叫喊:“瞄准——击发——命中!哈哈!”
这个快乐的球手,正是陶勇,我们的兵团副司令。将近一年的恶战苦斗,虽然使他明显地消瘦了,而胜利,却又使他变得年轻了。我走上前去,向他敬礼报到。他一见我,怔了一下,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嘿!小鬼,你是摄影记者吗?”我红着脸说还不算正式记者,刚开始学习。
“哦,现在不算正式记者,以后就是正式的了。”他说着,把我拉进了他的住室,从桌上拿起一架小型照相机,“你给我讲解一下这玩意儿的性能和射击要领,好不好啊?”
原来,作战部门根据陶副司令经常深入部队视察阵地的需要,给他新配了一架缴获的照相机。他见我有些拘谨,便笑着说:“请大胆指点。你总比我先学一步,先学为师嘛!”
从此,我这个刚刚入门的见习记者,就成了陶副司令学习摄影的“辅导员”。有一天,辅导完毕,开午饭了,陶副司令留我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兵团参谋长覃健。桌上两菜一汤,唯一的荤菜是两个荷包蛋。陶副司令夹一个荷包蛋在我的碗里,怕我推让,又用筷子使劲地将荷包蛋捣碎;接着把另一个荷包蛋分成两半,和参谋长一人半个。
“小鬼,你到底几岁了?”陶副司令突然笑着问道。
“不是告诉过你了吗?18。”
“肯定打了埋伏。”覃参谋长在一旁插话。
陶副司令虎着脸接上说:“应当忠诚老实嘛!把生辰八字报给我听听,说假的,小心我打电话査你的档案。”无奈,我只好报了出生年月。副司令一听,哈哈大笑了:“参谋长在这里,你还能骗得了!按科学算法,不足16岁嘛。”忽然,他止住笑,逼问:“唔,你是怎么混进部队的?”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心头怦怦直跳。
他看见我羞红了脸,忙又改口道:“快吃饭,不用紧张,保证不开除你的军籍!不过,虚报年龄可要改正过来。年纪小参军打仗并不丢脸,我当兵那年也只有16岁,如今当了兵团副司令,周总理、陈老总见了我,还叫我小陶小陶的,我才不卖老哩!”吃完饭,陶副司令又亲自给我削苹果,一边侃侃而谈:“革命需要人才,人才不够,只好从实践中培养嘛。不少同志20來岁能当上营长、团长,十五六岁的娃娃为啥不可以学当记者?我没有上过正规军事学校,过去贪玩,不用功,靠领导管得紧。有回不肯参加学习,陈老总要派警卫班把我绑了去学习。后来也就自觉一点了……”说着,把削好的苹果塞进我手中,“你这娃娃兵,可要好好学习,唔!”
我心里热乎乎的,低着头啃苹果,一边却在品味着这些甘霖般的话语,温暖得就像在家里一样。
1953年初夏,前线比较平静。兵团政治部特邀朝鲜画家洪圣哲来兵团驻地,创作油画《打击侵略者》。陶副司令知道这事以后,就打电话给政治部主任谢友法,要求将画家洪圣哲请到司令部去,就把画室安在他的住所旁边,说要亲眼看画家画画。《打击侵略者》刚画成,陶副司令又来电话命我去拍照,除了为他和画家与画作一起拍照外,他还接过我的照相机,特地为我和画作拍了照片留作纪念。洪圣哲通汉语,激动地赞叹说:“想不到……战功赫赫的陶将军会这样喜爱艺术,真让人感动啊!”
有一天,志愿军总部和各兵团的高级将领们到我们兵团驻地开作战会议,陶副司令又要我去拍照。我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高级将领,慌了神,端着照相机,东边转转,西边站站,好容易鼓起勇气,走到将领们跟前,取好景,迅速按下了快门。不料,刚松过一口气,这些老干部忽然指指点点地议论了起来,只听得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像吟诗一般地吟道:“好个娃娃记者,听声音,咔嚓一下倒清脆;看镜头,上面还罩着一个盖!”
指挥员们都乐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窘得我无地自容。这时,陶副司令摇摇手道:“别笑,别笑,娃娃记者初次见到这么多大首长,难免会紧张。请大家原谅,多多原谅!”一边走上前来,站到我身旁,看看拍摄场面,为我鼓劲壮胆:“唔,这个角度不坏。沉住气,重拍一张。”说完,表示抚慰地摸了一下我的头,走回到指挥员中间去了。李志民也微笑着安慰道:“小鬼,不必紧张嘛,我们又不吃人!”
欢声笑语,使我振作精神,终于完成了任务。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回忆起来,总像发生在昨天,我仿佛在陶勇将军的亲切关怀下,还刚刚摆脱童稚状态。十年浩劫中,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将军,未能为国捐躯海疆,却被林彪、四人帮害死在一口水井中,令人悲愤!陶勇将军猝然离世,专案人员也抄没了我所珍藏的大量照片,但他们无法抄去我心灵中的底片。陶勇将军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