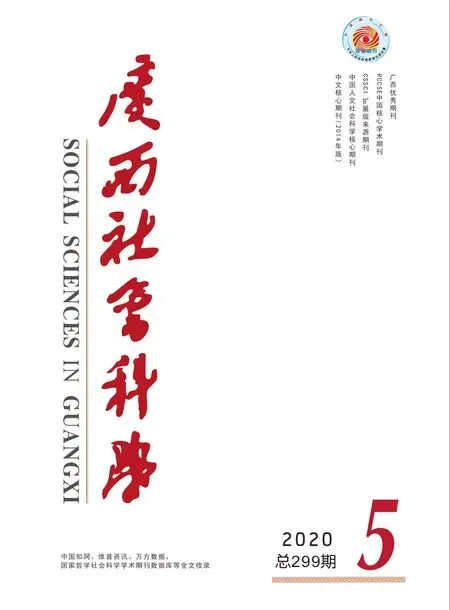“气韵”与“Aura”:谢赫与本雅明的艺术观比较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气韵”与“Aura”分别是中西方诗学认知艺术的核心范畴之一。“气韵”是谢赫提出点评绘画作品的“六法”之一,自六朝后成为评判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标准。“Aura”的有无是本雅明区别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圭臬。机械复制时代的浪潮湮没了艺术品的“Aura”,“开启了艺术世俗化、大众化、政治化的进程”[1]。“‘Aura’产生于纯然容纳的艺术直观,正与中国画家聚精会神的观物方式相合。”[2]而“气韵”是中国古人以直感体悟人与物的生命意志与情调的门径,故“气韵”与“Aura”有一定会通之处。
对于“Aura”,学界将之翻译为:韵味、光晕、灵气、灵氛、灵韵、灵光、辉光、气息、气韵、神韵、神晕、氛围、魔法等[3]。周海宁认为,凡是翻译中含有光的,是抓住了Aura本来的含义,而含有韵、味、气等,是融入了中国古典美学概念[4]。从尚有争议的翻译中也能看出“气韵”与“Aura”可通约的地方。
当前学术界分别对“气韵”和“Aura”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如彭吉象在其主编的《中国艺术学》中指出,“刚中寓柔,动中寓静,静中寓动,所谓动静不二、刚柔相济才是中国‘气韵说’的内核”[5]。如方维规在《本雅明“光晕”概念考释》中考辨本雅明开始论述“光晕”概念的时间,剖析了本雅明文中出现“光晕”的几段文字和“光晕”概念的本义与转义。但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对两者进行区别性和趋同性的对比研究还十分之少。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尝试爬梳中西方学者对“气韵”和“Aura”的阐释过程,从自然观与神学观、作者向与读者向、心觉与视觉三个方面对谢赫与本雅明的艺术观进行比较,希望能对我们认知中西诗学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有一定的理论启迪。
一、自然观与神学观
气韵一词肇始于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6]其中,“气韵生动”是谢赫品评绘画的第一原则,对后世的画论、书论和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气韵”由谢赫提出,但“气”与“韵”在谢赫将两者结合起来之前就有深厚的美学意蕴,是谢赫文艺思想的源泉。
“‘气’范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个兼务‘形质与本体’、描述生命和心灵的基本范畴。”[7]《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8]也就是说,同样的声音会云集响应,同类事物的“气”可以相互感知,中国古人以形象可感的“气”来理解抽象的人、物的属性或自然特点。“‘同声相应’者,若弹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是也”[9]。“宫”“商”皆属于“五音”,此处的“声”即“韵”。谢赫连合“气”与“韵”也许是受到了《周易》的影响。
“气”是人与自然相通的精神本体,也是自然生命化的形象表征。《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有言:“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10]自古以来人能意合自然,一切生命的根本源于自然的阴阳之气。天地四方的九州,人体的九窍、五脏和十二节,都能体合自然之气。《黄帝内经·灵枢·刺节真邪》指出:“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11]“真气”禀受于先天,后天的人气须摄入自然的“谷气”。人体受孕于自然,顺应自然之气才能茁壮成长。《国语·周语》认为:“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而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12]自然是一个能自我调理的有机体,以土聚成高丘,水汇成江河,以高低之势差疏导地气,使得土壤凝聚不崩塌而万物得以安居,地气不沉滞淤塞而水流不失序,百姓活着的时候有财可用,死的时候有地可葬。自然孕育生命,人以生命化的形式把握自然。自然之气的调和是人气得以持存的先决条件。“‘气’包含有宇宙之元气与生命之血气,‘韵’也包含创作主体之精神风貌与作品的节奏韵律。”[13]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与作品的节奏韵律须与自然生命之气相和合才能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
与谢赫相似,本雅明也吸收了“Aura”的本义来执持西方艺术的本体。“德语Aura,是指(教堂)圣像画中环绕在圣人头部的一抹‘光晕’,这是Aura的本义,与‘神圣’之物相对应;本雅明用‘光晕’形容艺术品的神秘韵味和受人膜拜的特性,这是Aura在本雅明那里的转义。”[14]本雅明将Aura的神学意旨延及艺术品的品鉴。罗奇利兹认为,本雅明的艺术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5—1925年。这个时期本雅明“试图纠正审美传统”,“以神学主义重新建构起未被认识的浪漫主义的内涵,即弥赛亚主义”[15]。第二阶段为1925—1935年,本雅明的思想转向“社会革命干预的政治美学”[16],但他的这种转型是不彻底的,正如赵勇所认为的,本雅明的思想“形左实右:摇摆于激进与保守之间”[17]。比如,本雅明在提出“Aura”的美学概念时,还保留有神学主义的思想残骸。
本雅明于1930年写的《毒品尝试记录》中细致地论述了“Aura”:“首先,所有事物都能显现真正的光晕;它并不像人们所臆想的那样,只与特定事物相关。其次,光晕处在变化之中;说到底,物事的每一个变动都可能引起光晕的变化。第三,真正的光晕,绝不会像庸俗的神秘书籍所呈现和描绘的那样,清爽地散射出神灵的魔幻之光。真正的光晕的特征,更多地见之于笼罩物体的映衬意象。”[18]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本雅明似乎要与神学主义划清界限,反拨Aura本义的三个特性——特定性、恒定性与神性。但他后来以决绝的姿态走向唯物主义阵营,恰恰证实了他诠释的“Aura”所先天具有的神学基因。
本雅明在1931年完成的《摄影小史》中这样阐述“Aura”:“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19]这里,本雅明的思想又表现出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面,以描述性的含混词句论说“Aura”,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相悖逆。综合本雅明对于“Aura”的阐释性文辞,可以观照本雅明二律背反的思维面相,“一张是我(指犹太教信仰),一张对布莱希特(指马克思主义)”[20]。“一方面,这种经犹太神学改造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革命理论注入精神和神圣的质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崭新维度;另一方面,本雅明对政治弥赛亚主义的伪救赎性质的疑虑和他笃信的衰落史观又一再将他拉向犹太神秘主义的末日拯救。”[21]本雅明给具有神学本义的“Aura”注入艺术美学的内涵,旨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语境下“让实物脱壳而成,破除‘灵光’,标示了一种感知方式,能充分发挥平等的意义”[22],进而摧毁法西斯审美意识心态,通过审美政治化的途径救赎人类。
通过追溯谢赫与本雅明的思想来源,可以镜照两者不同的艺术思想。谢赫的“气韵”以人气意和自然之气,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达到气韵生动的意境。而本雅明既借鉴又反叛、超越“Aura”的神学意义,从救赎犹太人走向救赎全人类,赋予救赎神性维度。二者一合一离,展现了中西分别崇尚自然与宗教神灵的不同思维取向。
二、作者向与读者向
就“气韵”和“Aura”的作用对象而言,“气韵”侧重表现作者的主观精神参与或作品所呈现的作者的知情意,“Aura”侧重表现读者的接受状况,“Aura”的消失前后预示着艺术的受众由精英转变为大众,艺术品对于鉴赏者的价值由膜拜价值转变为展示价值。谢赫与本雅明提出的美学概念的作用客体不同,从表面看是两人接受的思想资源不同,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西思维范式的差异。
在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气”或“韵”共出现了十一次,分别是:(1)(序)“气韵生动是也”[23];(2)(评卫协)“颇得壮气”[24];(3)(评张墨、荀勖)“风范气候”[25];(4)(评顾骏之)“神韵气力”[26];(5)(评顾骏之)“天和气爽之日”[27];(6)(评陆绥)“体韵犹举”[28];(7)(评毛惠远)“力韵犹雅”[29];(8)(评夏瞻)“虽气力不足”[30];(9)(评戴逵)“情韵连绵”[31];(10)(评晋明帝)“颇得神气”[32];(11)(评丁光)“乏于生气”[33]。除“天和气爽之日”的“气”指“天气”外,其余的“气”或“韵”都意指人物或景象的内在精神品格或艺术家主体精神在作品的气化显现。“‘气’与‘韵’结合成为‘气韵’概念后,它不仅仅指对象的精神之一含义,同时开始涉及画家主观精神问题,而在以后的绘画发展中,‘气韵’含义便更多地由对象方面的内容转向画家主体精神方面,进而落实到具体的艺术传达中。”[34]
文学艺术创作与作者的主体精神发生勾连,可以回溯到曹丕的“文气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可移子弟。”[35]曹丕认为,“气”是文章的主导源,分为清气和浊气,不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得到,父亲无法传授给儿子,兄长也无法传授给弟弟。曹丕强调“气”的先天性,先天禀赋的“气”决定了文章的内在精神。同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指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36]刘勰认为,文章八种风格的变迁,可以通过后期的学习达到。作者的才情气力来自先天的气质。气质使志向充实,志向决定语言的表达,文采的收放自如与作者的性情相关。换句话说,先天的“气”决定了文章的语言表达。徐复观认为,韵在六朝是“在人伦鉴识上所用的重要观念。他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间,从形相中可以看得出来的”[37]。这在六朝古籍中大量可见,比如《世说新语·向秀别传》曰“拔俗之韵”[38],《世说新语·卫玠别传》曰“天韵标令”[39],《世说新语·高坐别传》曰“风韵遒迈”[40],《晋书·桓石秀传》曰“风韵秀彻”[41],《宋书·王敬传》曰“神韵冲简”[42],《齐书·周颙传赞》曰“苦节清韵”[43],《梁书·陆杲传》曰“风韵举动”[44],等等,皆是形容人的形相所展现的气质。综合曹丕及其同时代的刘勰对于“气”的理解,谢赫对于“气韵生动”的审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作者内在精神的“气韵生动”,第一品的画家能将自我生动的气韵传神地呈现于作品中。“韵”在同时代的古籍中出现大量用来描述人物的气质品性的语用案例,所以在理解谢赫的“气韵论”思想时,须将画家的气度与作品的神韵结合起来考察。
本雅明从读者反应的角度言说“Aura”的蕴意,诚如前文本雅明对“Aura”的定义一样,他从观者与审美对象的距离进行论述。他的弥赛亚主义思想以拯救犹太族人为旨归,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着意于拯救人民群众,他的思想来源都与接受者有关。本雅明选择站在大众立场,除了神学主义和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外,还有反法西斯主义迫害的因素在其中。德国法西斯主义势力残酷杀害犹太人,抱有犹太教神学信仰的本雅明以大众审美为突破口,通过将审美政治化,拂除法西斯主义政治的弊害,从而挽救犹太族人,拯救大众。哈贝马斯认为,“对于作为从属于自律领域的艺术,纳粹的宣传艺术完成了它的解体,但是在其政治化的背后,它确实是在为赤裸裸的政治暴力美学化服务。它用操纵性的手法制造出膜拜价值,从而取代了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膜拜价值。膜拜符咒的打破是为了让它全面更新;大众的接受变成了对大众的暗示”[45]。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法西斯主义势力将政治审美化的险恶用心,即为法西斯的血腥暴力行径提供艺术上的合理性支持。法西斯美学以对集权统治者的膜拜为中心,本雅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Aura”等美学范畴以艺术品对大众的展示价值取代膜拜价值,同样以审美政治化的方式反拨法西斯美学主张,消解法西斯美学强加于民众的膜拜价值。
“气韵”与“Aura”的生产者与接受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不单是谢赫与本雅明思想来源的差异,更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以“气韵”为中国文论的索引,综观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史,大多文论都涉及艾布拉姆斯所提及的艺术批评的三个坐标——作品、艺术家和世界,却鲜有文论专门论及读者、观众与听众。以“Aura”为切入点,博览西方艺术理论批评史,却发现了接受美学这一朵以读者反应为原点的阆苑奇葩。笔者认为,正是中西古代文化运行机制的不同,才形成两种不一样的文论格局。
梁漱溟认为:“中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间之两异的精神。”[46]中国古代文学有重文轻小说的传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47]。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主体是士大夫,士大夫是“治人者”;而小说的创作主体通常是稗官或“引车卖浆者流”,稗官“指卿士之属官,或指县乡一级官员之属官”[48],这些人皆是“治于人者”。从创作主体而言,中国“严尊卑”的文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重诗文轻小说的传统。同样地,绝大多数读者都是地位卑下的贱民,为一般有身份的文论家所不耻,所以读者之维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盲点。
反观西方,民主思想肇始于雅典的民主政体,伯里克利这样描述民主政体的性质与特征:“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49]民主政体为民主思想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民主思想在政治上层建筑表现为民主政体。同时,民众法庭为民众发挥自身社会影响力奠定了法制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民因此而成为‘政体的主宰’”[50]。民主政体的存在使得人人平等,在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作者与读者是地位平等的,读者的审美反应得到文论家的重视,读者向度的文艺批评理论也得以建构。
综上,将作品之“气”与作者之“气”贯通源于曹丕的“文气说”,谢赫在《古画品录》将之运用于画家品级的评定。从曹丕及其同时代的刘勰可以瞥见谢赫“气韵论”的作者向问题;本雅明的犹太教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和反法西斯倾向使得他必须立足大众这一接受群体的立场,以迎向“Aura”的消逝的姿态摧毁法西斯主义美学大厦。在此基础上,在中西方文化大背景下比较中西方文论的读者向度有无的问题,可以发现,“严尊卑”与“民主”“平等”思想的差异造成中西文论的取向差异。
三、心觉与视觉
从“气韵”与“Aura”所调动的感官而言,人体需要“心觉”品悟艺术品的“气韵”。所谓“心觉”,即“神遇”,“就是心灵的直觉,是外在感觉迅即转化为心灵的直觉,以人的内在感性直觉和理性直觉的综合感悟力、穿透力去把握对象的实质”[51]。而“Aura”凋谢后,传统绘画凝神观照的品鉴方式变成回归视觉的蒙太奇式的“震惊”体验。谢赫与本雅明品评艺术品方式的差异,不但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而且也是传统与现代审美的差异。
五代荆浩在谢赫“气韵”的影响下提出绘画六要:“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行,备仪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音,搜秒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飞因笔。”[52]“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即作画前胸有成竹,以心运笔,才能将“胸中之竹”变为“手中之竹”,使画作充满活泼泼的生气。“韵者,隐迹立行,备仪不俗”即“在绘画创作上,既不要备取庸俗的法则,在形象塑造上,也不能有造作而不自然的痕迹。如此,则画中的‘韵’味才能得到。”[53]具体的形象须去除伪饰,抽象的法则须气通自然,不陷于尘世流俗。综上,艺术家凭借心觉取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对自然的觉知神会是中国人艺术创作的起源,那么,在鉴赏名画时也应当以心觉体合作品所传达的气韵。在感悟画作时,人从外在感官出发,逐渐进入内在心灵,以性灵的虚静制住世俗纷纷扰扰的动,“涤除玄览”,对作品凝神观照,以心相通,方能洞见艺术的真谛。
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背景下,“Aura”的消散使民众对艺术品的观赏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对传统艺术的凝神观照变为流于视觉表面的消遣,即专心与散心的区别。观照艺术品需要专心,要“入乎其内”;而欣赏照片或电影则不需要劳神地去专注,可以凭借散心的消遣方式感受作品。“这种散心的感受之道,在现今一切艺术领域都愈来愈明显,这也是感受模式重大转变的征兆;而在电影中已找到了最佳试验场所,影片的震惊效果正符合这种形式的感受。”[54]技术的变革如摄影与电影的出现决定了散心的观赏方式。而散心的视觉体验使艺术接近了大众。艺术品的膜拜价值被散心的感知方式取消,代之以实现民主与平等的展示价值。散心的艺术感受消解了“法西斯主义者将首领崇拜强加给民众,如此来压榨百姓”[55]的仪式价值,是本雅明作为共产主义一分子以艺术政治化回应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的感知方式,具有革命性意义。不过,本雅明也对这种浏览方式提出自己的隐忧,建议以触觉补充视觉:“在历史的重要转型期,人类感官必须面临的人物向来都不仅仅以视觉渠道为主,即不只以关注的形式为主,反而需要在触觉感受的引导之下慢慢适应。”[56]综上所述,“Aura”的消逝使散心的鉴赏模式成为可能,这种模式使艺术走向大众,解构了传统艺术的膜拜价值和法西斯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但这种以视觉为主的官能欣赏也应由触觉加以弥补。
心觉与视觉的艺术知觉差异,取决于创作者布局意识与展演模式。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布局凝聚着艺术家的意识,而这些意识的“有”又会通道心的“无”,以“无”之道意合自然法则,故以心取象,同时又“隐迹立行”。创作者体合自然气韵的巧思要求鉴赏者以心觉知。而本雅明认为,“相片中的空间不是人有意识布局的,而是无意识编织出来的”,“只有借着摄影,我们才能认识到无意识的视象,就如同心理分析使我们了解到无意识的冲动”[57]。而了解这种无意识冲动的感官任务却移交给了眼睛,人类的手为图像复制的技术所解放,同时也放逐了心觉这种凝神观照的感受方式。“画作邀人静观冥想,在画布面前,任想象驰骋。电影便不能如此,看电影时,眼睛才刚捕捉到一个影像,马上又被另一个影像取代,永远来不及定睛去看。”[58]绘画以静置的方式展示方能让人感悟生动的“气韵”,摄影与电影以复制或蒙太奇的方式操演却破除了“Aura”。本雅明在拥抱机械时代的复制艺术的视象感受时,也在为心觉的落幕感到惋惜:“连续不断的影像阻碍了观众心灵的任何联想。其创伤性的影响力便是由此得来。电影如何其他撼动人心的事物一样,需要特别用心专注才能掌握。”[59]
四、结语
虽然处于不同时代,直面的艺术现状也不相同,但是谢赫与本雅明分别立足中西方不同文学渊源,提出对后世艺术理论具有深远影响的诗学范畴。谢赫的文艺观肇始于中国古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气化美学、联结作品之气韵与作者之气的关联性思维和心觉的体悟方式。以气连合天与人的自然观必然形成中国古人联系性思维范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从作者的气韵把握作品的精神意涵也就自然成了这种思维在艺术品鉴上的显现。而“气韵”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需要以心直寻、妙悟和熟参,决定了心觉的领悟方法。本雅明则不然,其文艺思想源于神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崇尚犹太教的信仰决定了“Aura”消失的救赎维度,而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理想又决定了“Aura”消逝所拯救的对象——大众。机械复制技术与大众文化的庸常性又决定了视觉散心的审美接受方式。谢赫的“气韵”与本雅明的“Aura”在崇尚的根源、作用对象和接受方式具有诸多真理性联系与差异。所以,“气韵”与“Aura”作为中西文论的代表性关键词,两者的比较研究为人们进一步认知中西文化的异同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