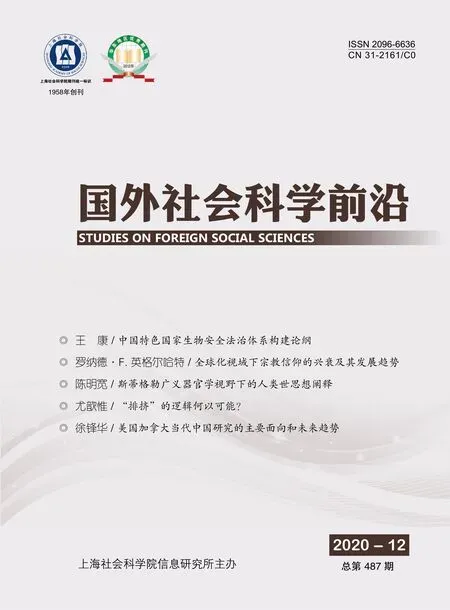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论纲 *
王 康
内容提要 | 新冠疫情暴露出了我国现有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的种种不足,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机制面临巨大挑战。对此,要采取“整体化+类别化”的规制模式,尽快落实《生物安全法》规定的基本制度,并由其统率和协调各单行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伦理准则、国家标准等,共同构成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要遵循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分类监管、严格责任、国际合作等基本原则,形成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保障机制、生物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风险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风险管理机制、恢复和补救机制、生物安全防御机制、法律责任机制等制度保障体系。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生物主权、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促进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推进生物安全全球合作共治,增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它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要求,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彰显着风险责任理念的法律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后,与疫情防控、生命科技风险密切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就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国际社会一度出现该病毒“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认为它是人工合成并泄露的,甚至是“基因武器”。1Areeb Mian and Shujhat Khan, Coronavirus: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BMC Med., vol. 18, no. 1, Mar. 2020. 国际著名医学刊物《柳叶刀》在2020年2月19日发表了来自8个国家的27位科学家对该阴谋论的谴责声明:“在这次疫情中,相关数据迅速、公开且透明的共享,正受谣言和错误信息的威胁。……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疫工作,别无它用。”Charles Calisher, et al.,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 Lancet, vol. 395, no. 10226, Mar.2020, pp. e42-e43.这些谣言已经在科学基础上被多次正面驳斥。2《 英媒:美科学家驳斥“人造新冠病毒”谣言》,《参考消息》2020年2月16日,http://www.ckxx.net/guoji/p/209085.html;汤波:《为什么新冠病毒阴谋论在技术上不成立?》,《 南 方 周 末 》2020年2月2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77355。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已经对SARS-CoV-2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了分析,结果压倒性地证明了其可能来源于野生动物。参见前注《柳叶刀》刊文。但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具体源头,在科学上仍然没有清晰的定论,主流意见只是倾向于非人工合成并泄露。K. G. Andersen, A. Rambaut and W. I. Lipkin, et al, 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 Nature Medicine, vol. 26, 2020, pp. 450-452.在疫情防控中,病原体基因鉴别、疫苗研发、药物临床试验等生物科技手段发挥了重大作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机制也在加速推进。2020年2月14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1新华社:《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20年2月15日。科技部随即发文要求加强实验室病毒管理,确保生物安全。2文件名称为《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参见许雯:《部分药物已经初步显示良好临床疗效》,《新京报》2020年2月16日。国家卫健委2020年7月6日发文要求“加强实验室监管以防新冠病毒泄露或人员感染”。3《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中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20〕534号)。生物安全问题在疫情防控、社会治理、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治理体系,意义重大。
在《生物安全法》进入立法程序42018年9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规划中将《生物安全法》列入第三类立法项目。参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9/10/content_2061041.htm。之前,我国已经有学者研究了生物安全法的基本理论,但主要侧重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法律治理。5有代表性的文献,参见蔡守秋:《论生物安全法》,《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明远:《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孙文广:《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子灿:《生物安全法:对生物技术风险及微生物风险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15年。在2019年4月召开的《生物安全法》立法论证会上,来自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的几位专家就立法目的、调整范围、核心概念、基本框架、主要制度、法律责任等核心问题进行了交流。6全国人大环资委环境资源立法研究基地于2019年4月27日组织立法咨询闭门会议,对该法起草中的重大问题征求专家意见。部分专家意见,参见杨朝飞:《〈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刘旭霞:《〈生物安全法〉应突出生物技术安全防范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崔国斌:《〈生物安全法〉应重点管控生物技术研究和商业化应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王康:《〈生物安全法〉立法定位及对基因技术的风险控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刘银良、薛达元:《〈生物安全法〉应把握立法重心和相关法律规范的衔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国家生物安全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学者从不同视角分别对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原则、框架、路径、制度等问题提出了见解。王晨光提出了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优化的逻辑问题,7王晨光:《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优化的逻辑及展开》,《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常纪文、莫纪宏、于文轩分别对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提出了具体建议,8常纪文:《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学习时报》2020年2月17日;莫纪宏:《关于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若干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于文轩:《生物安全保障的法治原则与实现路径》,《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秦天宝、侯东德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基本原则和制度,9秦天宝:《〈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侯东德:《生物安全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薛杨等提出要在《生物安全法》引领下全面推进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安全的体制机制。10薛杨、俞晗之:《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这些及时的文献为我国生物安全法律规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建言。
虽然作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核心的《生物安全法》已于2020年10月1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但是在这一体系的构建理念、内容、框架、路径等方面还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现状及其面临的新挑战出发,结合我国法制背景、条件和趋势,讨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理念遵循、目标体系、基本原则和构建路径,以助力于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完善。
二、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面临挑战
(一)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新形势
当前,生物安全问题在国际范围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复杂多变,这给生物安全治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人类已经步入风险社会,全球性生物风险(global biorisk)已经多次发生,仅在公共健康领域,自进入21世纪以来,SARS、H7N9、H1N1、MERS、Ebola以及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都引发了全球恐慌。这些严重的生物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全球性、突发性和反复性,并且绝大部分与人类活动有关,而非单纯源于自然演化。
生物安全不仅关系社会民生、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还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当前,生物恐怖主义、基因武器已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虽然《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生物武器,并要求销毁既存的生物武器,倡导以和平方式利用生物科技,但并未能制止生物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美国炭疽攻击1Frederic P. Miller, et al. (eds.), 2001 Anthrax Attacks,Alphascript Publishing, 2010.等事件的发生,也证明生物恐怖主义业已成为现实的威胁。这种新型的生物威胁和重大突发公共健康危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虽然尚未在国际范围内造成急迫威胁和恐慌,但是居安思危,国家必须尽快并最大程度地增强生物防御能力。
在新形势下,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也不例外,同样面临着巨大挑战。此前一段时间,我国生物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其中,生物遗传资源流失2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出十分严峻。据统计,我国流出的森林植物资源总计已达168科392属3364种。资料参见中国网,http://guoqing.china.com.cn/zhuanti/2016-05/11/content_38428882.htm。、人类基因数据非法出境3资料显示:“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企业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非法收集和攫取行为仍时有发生。对人类遗传资源的攫取形式也由自行收集,扩大为通过与国内机构或专家合作,由国内机构或专家收集后输出境外;出境途径也由携带基因样本出境转变为通过互联网将基因数据发往国外,手段更为隐秘。”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起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送审稿)〉的说明》,2012年10月30日,http://www.gov.cn/gzdt/2012-10/31/content_2254379.htm。上个世纪末我国人类基因流失情况,参见王康:《基因权的私法规范》,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2页。来自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5月起约一年内,我国共发生基因数据跨境传输925余包次,4391家境内单位疑似存在基因数据出境行为。参见钱柳君、娜迪娅:《4391家境内单位疑有基因数据出境行为》,《南方都市报》2018年8月17日。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披露了在2015—2018年对涉及人类遗传资源违规行为的6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参见唐唯珂:《人类遗传信息违规出境处罚公开 基因大数据安全性拷问》,《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0月29日。、基因改造生物非法扩散4王康:《基因责任论:基因改造生物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11~28页。、外来物种入侵(alien species invasion)5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参见生态环境部:《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0年5月18日,http://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202006/P020200602509464172096.pdf。、实验室病毒泄露6例如,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实验室因操作违规,导致SARS病毒泄露并发生小规模疫情(北京和安徽两地出现SARS确诊病例9例,医学隔离862人)。等问题已经被多次曝光。2018年底,更是发生了备受谴责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我国在生物领域同样面临着国家安全风险,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biodefense strategy)和防御能力尚需加强。
无论是维护人民健康、社会安全还是国家安全,都要求加快推进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在科技、法治等方面形成严密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在本次重大疫情防控的时刻,习总书记及时提出了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目标和方针举措,意义深远。
(二)我国现有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框架
在2020年10月17日《生物安全法》通过之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搭建了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框架,但缺少一部综合性的生物安全法。现行法主要集中于环境生态保护、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动植物检疫与国境检验检疫、病原微生物与实验室生物安全、传染病防治与突发重大公共健康事件应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和人类基因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现行法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呈现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不同位阶,在内容上包括实体和程序规范、技术准则和伦理指南。
在环境生态保护领域,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等法律渊源。1本部分所举法源,仅列最高法源的名称。例如,对于最高法源为法律(狭义)的,一般不再列出其项下的行政法规(实施条例等)。对于部门规章、国家标准等,标注原发布机关或部门名称,若有修订,则标注最近修订的部门名称及时间。
在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目前主要包括《种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陆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渊源。
在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领域,目前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药品安全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渊源。
在动植物检疫与国境检疫领域,目前主要包括《海关法》《动植物进出口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渊源。没有专门用于管理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或法规,有关条款分散在各个法律中。
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领域,目前主要包括《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其项下的部门规章《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审查办法》(科学技术部,2018)、《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国家卫计委,2016)、《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卫生部,2009)、《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卫生部,2005)、《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农业部,2005)、《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国家卫健委,2020)等,以及国家标准《WS233-2017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国家卫计委,2017)、《WS 589-2018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标识》(国家卫计委,2018)等法律渊源。
在传染病防治、突发重大公共健康事件应对领域,目前主要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家畜家禽防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渊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还印发了《医学检验实验室管理暂行办法》(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0〕27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发布了规范性文件《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2版参见国卫办科教函〔2020〕70号)。
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领域,目前主要包括行政法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其项下的部门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部,2017)、《农业转基因生物(植物、动物、动物用微生物)安全评价指南》(农业部,2017)、《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部,2017)、《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农村农业部,2019)、《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部,2017)、《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海关总署,2018)等,以及国家标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通用要求 实验室》(农业部,2016)、《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签的标识》(农业部,2007)等法律渊源。
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人类基因技术规制领域,现行规范主要是一个行政法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以及几个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有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科技部,199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2001)、《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卫生部,200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卫生部,2003)、《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卫生部,2003)、《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2015)、《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国家卫计委,2016)、《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科技部,2017)、《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等。
此外,我国1993年正式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1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 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该公约,1992年11月7日批准,1993年1月5日交存加入书。,2000年签署《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00. 该议定书于2003年生效。我国于2000年8月8日签署,2005年4月27日国务院核准,2005年9月6日正式成为缔约方。。为了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和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的支持下,我国在2000年发布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3该框架重点关注了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尤其是转基因生物的风险管理、产业发展,以及生物安全管理国家能力建设。参见《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课题组编:《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南。不过,在目前我国的法律秩序中,该框架并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
(三)我国现行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不足
作为几十年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本次疫情考验着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并在事实上已经暴露出了我国生物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不足。4对此,习总书记已经明确作出了判断。参见新华社报道:《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20年2月15日。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本次疫情显示我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不足。参见章轲:《生态环境部答一财:疫情暴露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不足》,https://www.yicai.com/news/100524777.html。例如,在本次疫情发生初期,对未知病毒风险评价的科学性欠缺(风险识别出现严重错误,多次声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关疫情信息的风险沟通真实性、充分性不足(甚至瞒报、漏报,打击合理的质疑声),地方政府未能主动采取及时、有效的应急防控措施(没有科学合理的应对预案,对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诊断迟缓,隔离措施不到位,床位、药物、物资等严重短缺),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疫情控制时段。当然,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及时采取了有力的防控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从表面上看,某些政府部门、主管机构的生物安全风险意识相对薄弱,地方政府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普遍不足,突发公共健康危机应急预案不具可操作性,应急医疗资源储备不足,是出现上述问题的部分原因。但实质上,真正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不完善,包括突发公共健康危机在内的生物风险治理能力、治理措施在整体上相对薄弱。在2020年10月17日《生物安全法》通过之前,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框架,但是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协调性不足。
首先,规制体系不够健全。因为缺乏一部专门的生物安全基本法,各个法律法规相对零散地存在,甚至部分规定存在冲突,所以没有构成有机统一的法律治理系统。
其次,规制范围存在空白。现行法律法规主要集中于环境生态与自然资源保护、传染病防治(及其项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出口商品及动植物检验检疫、畜禽疾病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遗传资源及基因技术监管等领域,缺少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基于各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兴生物科技风险(如生物合成、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基因武器)等专门法律法规,生物安全评估等国家标准不够全面。
再次,规制内容有所缺失。现行法未能充分贯彻科学、理性的生物安全治理理念,风险监测预警、风险评估、风险交流、治理能力建设等机制有所欠缺。
最后,规制效果实效不足。由于缺少一个权威的协调和决策机构,主管部门众多(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自然资源、科技、卫生、农业、教育、海关、国防)且权限职责模糊,风险管理系统先天不足,加上法律责任机制相对薄弱,监管主动性不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执行力差强人意。
在2021年4月15日《生物安全法》实施之后,以上不足在生物安全基本法的基础上得以适当弥补。但是,国家生物安全协调机制的建立、现行法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分级分类规制措施的具体化、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治理的体系化等重要法律改革,都有待完成。考虑到以上种种不足的根源尚未消除,当前依然应在理念、目标与路径等方面,着眼于生物安全的事物本质和全球性生物风险的新形势,进行系统性的讨论。
三、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思想遵循与法律理念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一部系统性、基础性、综合性的《生物安全法》的制定恰逢其时,未来应以其为核心进一步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是法治国家、法治文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法治表达。构建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遵循,以总体国家安全观1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可能和军事、经济、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等其他国家安全领域发生交错。为指导,以风险责任理念为法理基础。这一构建理念,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要求,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彰显着风险责任理念的法律价值。
(一)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要求
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理解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政治要求。2020年2月14日,习总书记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2新华社:《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20年2月15日。2020年3月2日,他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继续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新华社:《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人民日报》2020年3月3日。生物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社会福祉并行不悖,要统筹协调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发展和生物安全之间的关系,做好风险防控。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尤其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在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中,一方面要着力于增强生物防御能力,以应对来自外部的生物攻击;另一方面要把重大疫情防控纳入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出现的突发严重公共健康危机和难以想象的新型生物风险。
(二)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
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理解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制度功能。习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3新华社:《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20年2月15日。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威胁和生物风险的能力,涉及科技、管理、法治等方面。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角度来看,预防和控制重大新型传染病、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攻击、防范外来生物入侵、预防生物技术滥用、确保生物实验室安全、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基因资源,都要求进一步增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生物安全治理的法律政策、组织系统和能力建设要有机结合,政府部门要具备生物风险意识,形成生物风险管理和生物安全法治思维,确保生物风险识别、预警系统和应对措施持续有效,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三)承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角度,来理解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历史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大国担当精神,符合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趋势下,生物风险极易跨境蔓延,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多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健康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生物安全问题属于全球治理领域,应在联合国体系下完善全球治理法律规则。我国正深入推进全面开放格局,应积极与国际社会共享生物安全治理的教训和智慧,推动形成科学、透明、公正、共治的生物安全国际治理体系,最终有利于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4王慧慧、侯丽军:《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的全球安全。
本次疫情防控,客观上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机会。WHO高度赞赏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肯定中国为全球抗疫争取时间、提供经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5WHO Director-General's statement on IHR Emergency Committee on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Jan. 2020,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statement-on-ihr-emergency-committee-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on 21 February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on-21-february-2020;WHO Director-General's speech a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Feb.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20年4月18日,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柳叶刀》也在社论中指出,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1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864-3/fulltext.中国除了及时向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以及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疗等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技术方案,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力支持,并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以支持其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工作。现实已经证明,用无畏、牺牲、忠诚精神铸就的生物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疫情防控、生物安全国际治理的范本。中国正在以切实的行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四)彰显风险责任理念的法律价值
要从风险责任理念2关于风险责任理念的初步分析,参见王康:《基因改造生物环境风险的法律防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的角度,来理解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法律价值。所谓风险责任,是指在社会系统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面前,为预防损害(包括损害危险)发生和实现社会共存目标,而对风险成本进行公平分配的责任体系。它包括初始性责任分配和恢复性责任分配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为法定义务,主要通过立法者的一般衡量,以法律上的高度注意义务为分析工具,实现分配正义。后者体现为包含侵权责任在内的综合性救济机制,主要通过裁判者的个案判断,以损害的公平归责为评价目标,实现矫正正义。风险成本包括对不确定性损害风险的预防负担,以及风险现实化后的恢复、补救和赔偿等损害救济责任。前者是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阻却负担,后者是对风险现实化后的救济负担。当投入了足够的风险预防时,可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减轻损害;当所投入的风险成本在函数曲线图上与所避免的损害相会于一点,就达到了一个风险预防的理想均衡状态;当无论投入多大的风险预防成本,仍然不能避免或减轻损害,这就是一个悲剧性社会行动。当一个被许可的悲剧性社会行动发生时,损害的启动者和承受者都将付出代价,受害人无疑值得同情,但行为人却不具有法律上的可谴责性,此时综合性社会救济体系应妥当地发挥作用。
风险责任理念倡导尊严、安全、团结和共同责任,这是其最重要的法律价值。在生物安全领域,风险责任理念的要义在于它并不拒绝生物风险,在追求生物科技、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利益与机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防范、避免或救济可能的损害及其危险,并且公平地进行风险分配。由此,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优政策是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形成风险责任机制,在促进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同时,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生物风险进行充分的预防,以最大限度地确保生物安全。
四、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主要目标
栗战书委员长指出,我国《生物安全法》是一部“体现中国特色、反映新时代要求的生物安全法”,致力于“防范生物风险、促进生物技术发展、支撑国家生物安全体系”。3参见栗战书在2019年7月10日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有关内容,参见王比学:《栗战书主持召开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强调 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 保障和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以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摘要,《人民日报》2020年5月26日)。《 生物安全法》第1条对此进行了具体陈述:“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应对生物威胁,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是总体要求,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根本目的,保护生物资源、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防范生物威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主要任务。这一目标定位,既贯彻风险预防原则,维护国家安全、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也强调促进生物技术发展,着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值得肯定。
这一目标体系,体现了对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统筹协调。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要协调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这是生物安全国家治理的主线。一方面,维护国家生物主权、国家生物安全,防范对国民健康、福祉以及经济、政治、国防方面的安全的威胁,应该是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首要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文件都确立过生物主权、生物安全、人类健康等法律原则。1Preamble, Article 3, 8 & 15,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在促进人类健康目标上,不仅促进国民健康安全,也要促进全球健康安全。另一方面,促进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创新发展也应该是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重要目标。生物科技虽然也带来了种种生物风险,但拥有强大的科技工具(如检测手段、药物、疫苗等)对解决这些不断变化的威胁又是至关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它。我们应该在促进生物科技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生物风险预防,并通过公正的风险沟通和文化融合促进形成妥当的生物风险认知,形成生物安全治理中的风险责任机制。
概而言之,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目标,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生物主权、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促进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推进生物安全全球合作共治共享,增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二)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法学研究者再次提出了一些有关生物安全立法基本原则的见解。常纪文提出应建立损害预防优先、科学管理、公众参与、损害者负担、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2常纪文:《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学习时报》2020年2月17日。莫纪宏主张贯彻以人为本、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基本人权、保证技术风险可控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法治原则。3莫纪宏:《关于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若干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于文轩认为生物安全立法应坚持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并建议在科技安全保障方面以人文关联补足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生态安全保障方面以保障总体国家安全为主旨、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4于文轩:《生物安全保障的法治原则与实现路径》,《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秦天宝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风险预防原则、全程控制原则、分类管控原则和多元共治原则。5秦天宝:《〈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主张,虽然观点表述不一,但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例如都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公共参与原则。
考虑到生物安全在外延上的广泛性,生物安全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有所侧重,因而必须注意生物风险的类别化治理。同时,考虑到在全球性生物风险的新形势下,生命科技风险、公共健康危机成为最重要的生物安全治理对象,而这些新事物具有更复杂的风险情境和特征,也具有更多的负外部性,就要求对其采取全方位、全流程、全领域的风险防范、安全保障措施。在这些措施中,严格的法律责任才是最重要的生物安全法律保障机制。因而,笔者主张,为实现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治理的目标,构建我国生物安全法治体系,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彰显风险责任理念,遵循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分类监管、严格责任、国际合作等基本原则。以下分别作一简要论述。
1. 风险预防原则
习总书记在谈国家安全时,引用《三国志》中的话说:“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1习近平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这就指明了在生物安全法治中贯彻落实风险预防原则、风险管理措施的重要价值。
风险预防原则的内涵为:只要可能存在损害或损害之虞,就不能以没有科学上可以证实的肯定性证据为由,而不采取或延迟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风险预防原则不同于指向确定性损害及其危险的“预防为主原则”,它体现了对待具有不确定性的生物风险的审慎立场。哪怕对这种可能发生的生物安全损害的性质、因果关系、范围和大小等具体因素知之甚少,同时也不能或很难进行可能的量化评估(此时,“预防为主原则”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只要依据一定的技术分析或科学论证可以认定存在产生损害的可能性,并且根据风险社会感知状况一般公众在价值判断上难以忍受此种损害可能性,就应该适用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领域早已被广为采纳。现有资料显示,联合国大会1982年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最早涉及风险预防措施(special precautions)。2Art. 11, art. 12(b), UN GA RES 37/7,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Oct. 1982.1987年第二次保护北海国际会议发表的宣言要求采取风险预防措施(precautionary approach),并初步对风险预防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ecautionary action)作了初步表达:“甚至在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科学证明之前,也要如此行动。”3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rth Sea in London on 24 and 25 November 1987.在1990年第三次保护北海国际会议发表的宣言中,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这个简洁而明确的术语才被正式地表达出来。4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rth Sea in Hague on 8 March 1990.风险预防原则的内涵在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15中得到了正式、明确的经典阐述,5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宣言中的原则15即为风险预防原则:“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取预防性措施。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的地方,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推迟采取防止环境退化的费用低廉的措施的理由。”后来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中得以特别明确(要求防范基因改造生物“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和“对人类健康的危险”)。6Art. 8(g),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 该条款规定:“制定或采取办法以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体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即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对其继续予以重申和贯彻,在第10条第6款中将所要防范的风险描述为“潜在的不利影响”7Art. 10,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00. 该条第6款内容如下:“在亦顾及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的情况下,即使由于在改性活生物体对进口缔约方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所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方面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亦不应妨碍该缔约方酌情就以上第3款所指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问题作出决定,以避免或尽最大限度减少此类潜在的不利影响。”,这就比里约宣言陈述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更容易得以认定,从而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下形成一个纯粹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有强意义和弱意义两种理解。强意义的风险预防原则实际上是零风险原则,它要求风险事件的启动者或制造者必须提供该风险事件没有任何危害的证明,否则相关行动就不能进行。这是对确定性的一种太过理想化的描绘,事实上很难做到让任何事件都是零风险的。《世界自然宪章》有关风险预防的表述有强意义的倾向。1Art. 11(b), UN GA RES 37/7,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Oct. 1982). 宪章在第11(b)条中指出:“在进行可能对大自然构成重大危险的活动之前应先彻底调查;这种活动的倡议者必须证明预期的益处超过大自然可能受到的损害;如果不能完全了解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活动即不得进行。”弱意义的风险预防原则并不要求做到零风险的确证,仅要求在风险事件全过程中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不采取或推迟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对风险预防原则的经典陈述,即是在弱意义上作出的。通常所说的风险预防原则就是弱意义的,它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对待。风险预防原则并不要求作零风险确证,仅要求在风险事件全过程中不能把缺乏充分的科学肯定性作为不采取或推迟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
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现行法中没有真正贯彻。甚至,在实际立法中已坚定地贯彻了实质等同性原则。2参见《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2007年12月1日卫生部令第56号)第8条、第19条和第26条。该办法被《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2013年5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号)废止,后者第15条和第22条也提及实质等同性,但却在第23条中将“转基因食品”排除其管制范围。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除在第69条要求“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外,并未对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的安全(风险)问题作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对待;第151条进一步明确转基因食品监管是该法的任务(该法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彻底遵循了实质等同性原则。当然,强制标识制度也意味着通过知情同意机制而对这一原则的部分缓和。《 环境保护法》中的“预防为主”原则,主要指向具有确定性、可以量化的损害及其危险,在本质上是“损害预防”原则,而非以科学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预防”原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3条第2款的定义虽体现了风险意识,但没有明确地将其上升为风险预防原则。当然,在对风险预防措施的法律规制中,要考虑消极风险的类型(根据不同性质给出禁止、限制、允许的理由)、严重性(对可能的损害范围与大小的评价)、概率(对因果关系等不确定性的评价)、可接受性(对风险感知等价值意义的评价),以及成本效益分析(对可行性的评价及风险预防成本的合理分配)等几个核心要素。
2. 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要求在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中保持开放和透明,只要信息可及性、参与公正性能够得以保障,就可以有效祛除谣言和恐慌(就像本次疫情时期出现过的那样),生物安全治理才可以顺利进行。
在有关生物安全的风险交流、风险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可以为决策的正当性提供社会基础,也有利于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开展。公众参与是以公正、充分的风险交流为前提的,这就要求风险规制者应培养公众对待风险的理性和宽容心态,在作出风险决策之前还需要获得特定公众的知情同意。由此,公众参与原则就具有提前知情同意的内涵,对形成理性的风险社会感知、促成科学的风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公众参与原则与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关联。“社会信任是解释科学与现代技术的社会接纳程度的关键因素”,而它又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的途径来重塑或改善。3[意]鲁西亚·马蒂内利、[波兰]玛戈扎塔·卡巴兹、[西班牙]文森佐·帕沃尼:《转基因食物:不确定性,信任与责任》,别应龙译,《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公众对风险交流和风险决策的参与,可以进一步增加社会信任程度,塑造对风险可接受性的共识,有效地弥合科学不确定性与社会对安全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公众参与原则在我国现行法中虽有体现,但并不充分和具体。《环境保护法》第5条即对此予以宣告,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未予反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则明确规定了“信息共享,公众监督”原则,要求在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重大事项上应当邀请利益相关者参与。4该方案要求实施信息公开,推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共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信息。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工作中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开,并邀请专家和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参与。参见中办发〔2017〕68号。在新的法律秩序中,要对公众参与原则的地位和程序保障进一步强化。
3. 分类监管原则
生物安全治理的核心是危险度评估,而生物风险事件类型多样,因此应根据危险性的不同性质、等级,进行分级分类监管。依据在于:一方面,生物安全是一个内涵相对确定、外延模糊、内容宽泛的系统,涉及重大突发公共健康危机(疫情)、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外来物种入侵与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实验室生物安全、微生物耐药、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等不同领域。在法律治理体系构建时,必须根据生物安全风险的事物本质提取出共性要素和整体特征,才能为体系构建提供科学依据和事实基础。另一方面,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系统的法律工程,内容庞杂,难以通过一部法律构建出完整的法治体系。因此,顾及生物安全在外延上涉及事项广泛,考虑到“结构 - 功能”的内在相关性,在生物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构建上,就必须区分不同的生物安全领域,基于其个性化特征进行类别化描述和规制。《生物安全法》中的生物安全分部门监管和协调机制,就是一种不得已而为的功能主义考虑的体现。这是在现实条件下,可以采取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兼顾但实用主义优位的妥协策略。
4. 严格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是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措施执行力的根本保障。正如WHO《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指出的,有效的生物安全规范是生物安全保障活动的根本,应建立国家标准来明确国家和单位在防止标本、病原体和毒素被滥用方面应负的责任,规定主管部门在发生生物安全事件时的介入程度、作用和责任。1WHO, 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 3rd ed., Geneva,2004, p. 47.严格责任原则除了要针对生物安全损害提供侵权责任规范,还要在公法或社会法上提供责任规范。此外,严格责任原则还要求针对生物安全事故,设定适当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并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增强其威慑力。
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现行法中有所体现,但在法秩序上呈现得并不全面、一致。在我国生物安全管制法中,有两个以违法性为要件的责任条款(即《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第28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52条),但它们并非真正的关于严格责任的规范基础。《环境保护法》第5条即明确规定了“损害担责”原则,并将具体责任承担问题指向了侵权责任法。在作为国家政策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中,“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再次被强调。2该方案要求体现环境资源生态功能价值,促使赔偿义务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赔偿义务人因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需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参见中办发〔2017〕68号。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专门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不仅为常态的环境污染损害提供救济,还特别对生态损害责任作了具体规定。不过,民法典目前的条款,还不能完全解决具有多类型、多样态、多领域的生物安全损害救济问题。
严格责任除具有法律责任的内容外,还具有伦理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意蕴。2013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3该倡议全文,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cn/xw/zyxw/yw/201304/t20130428_3829951.shtml。倡议还称,科学家要负责任地开展转基因技术开发及应用,在增进转基因科学知识,推进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同时,积极关注技术应用的社会和环境效果,预见技术的潜在风险,自觉规避技术的负面影响。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科学家应对由自身努力而取得的成果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决策咨询、风险管理、科技传播等事务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转基因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科学家应在审批决策过程中坚持审慎负责的行为,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坚持公正理性的立场,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坚持诚实坦率的态度。保持对技术伦理的敏感性,自觉思考技术开发和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呼吁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科学家所处的特殊位置及角色,使其应具有两方面的责任担当,一方面体现在使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表现为感知不公正和避免风险的自觉性。诚哉斯言!在未来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框架内,应将生物技术伦理准则适度地法律化。
5. 国际合作原则
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要协调好共同安全(全球治理)和自身安全(国家治理)的关系。一方面,推进生物安全全球合作共治,是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目标之一。以SARS-CoV-2病毒为例,无论它是自然发生还是非自然发生的,都可能迅速蔓延至全球各个角落,在联合国体系下的生物安全国际共治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最终要落脚于增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否则以上所有目标都将沦为空谈。要科学和理性地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只有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提升,才能更好地参与对全球生物风险的国际共治,推进全球生物安全共享,最终有利于“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早日实现。
五、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模式与路径
我国应构建以《宪法》为根基、以《生物安全法》为核心的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宪法》序言和多个条文涉及生物安全,为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生物安全法》应为综合性法律,是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一般法、基本法,是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栗战书委员长曾对我国《生物安全法》进行了定位,指出它是一部“内容全面、结构完整、重点突出,具有基础性、系统性、综合性、统领性的生物安全基本法”。1此为栗战书2019年7月10日在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讲话内容,参见王比学:《栗战书主持召开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强调 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 保障和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在《生物安全法》的统率下,各单行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伦理准则、国家标准相互协调,共同构成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另外,鉴于生物安全领域的相对宽泛,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也是庞大而散乱的,应采取功能主义立场下的“整体化+类别化”规制模式。
(一)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规制对象和范围
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规制对象是生物安全。生物安全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应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否则可能失去立法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基础。
在生物安全的内涵上,既指生物安全状态(事实描述),也指生物安全措施(原则、技术及实践),又指生物安全能力(生物安保能力、生物防御能力),更包括生物安全价值(目标、风险感知)。《生物安全法》所称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在生物领域能够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具备保障持续发展和持续安全的能力”。所谓生物因子,是指“动物、植物、微生物、生物毒素及其他生物活性物质”。这就把生物安全定义为一种国家能力(“在生物领域能够……具备保障持续发展和持续安全的能力”)、一种状态(“在生物领域能够保持稳定健康发展,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它以生物风险防范(“有效应对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为出发点,以生物领域“稳定健康发展”为价值目标,并致力于保障“持续发展和持续安全”的国家能力。
在生物安全的外延上,“生物”包括人类和其他生物,“安全”既包括实验室安全(包括危害性生物制剂、病原体和毒素管理)、公共健康、动植物疫病防控、环境生态安全、外来物种入侵、出入境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等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现代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技术及其与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风险、遗传资源管理、生物恐怖主义、生物黑客、生物武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在生物安全的形式上,表现为技术安全、伦理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等不同类型。在英文中,生物安全有biosafety和biosecurity两种表达。WHO在《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中,用biosafety来描述那些为防止发生病原体或毒素无意中暴露及意外释放而采取的防护原则、技术以及实践(侧重于技术安全、生态安全),用biosecurity来描述为防止病原体或毒素丢失、被窃、滥用、转移或有意释放而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侧重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1WHO, Laboratory Biosafety Manual, 3rd ed., Geneva,2004, p. 47.虽然WHO在该手册的中文版中,将biosafety和biosecurity分别译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不过在立法上还是很难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法制情况和立法成本,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可以将二者一并纳入。
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应采“大生物安全”的概念,2王康:《〈生物安全法〉立法定位及对基因技术的风险控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由此形成其相对宽泛的规制范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下,生物安全属于较为宽泛的国家安全领域。根据习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多个领域,生物安全则是新增的内容,但不是可以和上述安全领域并列的事项,而是一个相对包容、相互融合的综合性国家安全领域,与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具有叠加或交叉关系。
(二)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构建模式
鉴于生物安全领域的相对宽泛,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也是庞大而散乱的,应采取功能主义立场下的“整体化+类别化”规制模式。
结构与功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生物安全法律治理也同样处于这样的状态,为更好地获取有效的制度功能,就有必要对生物安全领域和法律治理的内部结构关系予以关注。“整体化”体现了生物安全法治系统的本质构成和全局特征,有助于彰显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价值目标、系统功能;“类别化”则着眼于不同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本质和个性特征,例如通过具体的制度保障措施,来落实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整体化”的规定性,有助于提升法律制度的实效。《生物安全法》(具体是指其中的一般规定)就是“整体化”的体现,其他单行法则是“类别化”的体现,二者的结合可以超越整体的模糊性和个别的有限性。
当然,此种功能主义立场下的“整体化+类别化”规制模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整体结构的体系美观性(例如,《生物安全法》只能放弃对生物安全法治领域的事项的面面俱到)。不过,这一规制模式却较好地凸显了立足于具体结构要素的体系功能性,从而聚焦于我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生物安全治理事项(例如,遗传资源安全、生物科技风险、重大公共健康危机)。
由此,考虑到生物安全领域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生物安全治理相关的现实法制背景、社会条件,可以对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作“横切面”“纵切面”两个交互的维度进行构建。“横切面”是指作为个性的不同领域的生物安全治理事项及其法律法规体系,“纵切面”是指作为共性的生物安全的规制理念以及全流程风险防范、监管措施等制度保障体系。在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构建的技术路线上,“纵切面”聚焦于风险责任理念和制度的体系凝练,“横切面”着力于风险责任理念和制度的具体铺展。纵横交错的构建方法,有助于立体、全景的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形成。
(三)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形成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法制背景、立法进程和未来趋势,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三步走”,并采取总分结构的表达模式。
第一步,尽快贯彻落实《生物安全法》的基本制度。《生物安全法》自2018年9月列入第三类立法项目后,在大约两年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全部立法程序。1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后,习总书记于2019年1月21日指出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参见习总书记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此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生物安全法》确立为2019年立法任务,并将其定位为“基础性、系统性、综合性、统领性的生物安全基本法”。参见前引栗战书2019年7月10日在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2020年4月,《生物安全法(草案)》第二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10月17日最终顺利通过。《生物安全法》中的一般规定,是这个法治体系的总纲,其下应分不同领域或对象予以规制。《生物安全法》在“提取公因式”的基础上,规定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责任以及其他普遍适用的规则。《生物安全法》将重大突发传染病与动植物疫情防控、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保障、外来物种入侵防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微生物耐药应对、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武器威胁防御等作为规制范围,值得肯定。考虑到对现行法规制盲点的填补,《生物安全法》分则特别规定一些具有迫切性的重大领域监管制度,但对微生物耐药问题仅列入规制范围,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规制条款。
第二步,处理好《生物安全法》与《传染病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关系。这些法律已经提供了有关公共健康、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野生动物保护、突发事件应对等制度,但应在新的生物安全治理形势下予以及时修改,以形成“健康协调、有序衔接”2参见前引栗战书2019年7月10日在生物安全法立法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制度体系。
第三步,在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在现有行政法规、规章的基础上制定《基因技术法》《生物医学技术法》《遗传资源管理法》《生态损害补偿法》等新的法律,并由主管部门适时补充形成或完善各个领域的生物安全治理技术规范(如生物安全评估技术规则等)和伦理准则,以形成严密的技术保障机制。
(四)国家生物安全制度保障体系的构成
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下,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生物安全制度保障体系。这个制度保障体系,由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保障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决策和执行系统建设、技术保障、资金和物资支持)、生物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风险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公众参与、信息交流、教育培训、对外合作)、恢复和补救机制、生物安全防御机制、法律责任机制等组成。
应增强以上制度保障体系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要通过合理设置组织领导机制、明确不同领域的主管部门之间的权限关系、设定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来避免主管部门不愿主动履行监管职责,甚至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
在这个制度保障体系中,关键是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保障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决策和执行系统建设、技术保障、资金和物资支持)的合理构建。《生物安全法》建立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下的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1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生物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由健康、农业、科技、外交等国务院主管部门和有关军事机关组成,职责是“分析研判国家生物安全形势,组织协调、督促推进国家生物安全相关工作”;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下设专家委员会,为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研究、政策制定及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建立相关领域、行业的生物安全技术咨询专家委员会,为生物安全工作提供咨询、评估、论证等技术支撑。参见《生物安全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其中,“国家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是隶属于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的咨询机构,不具有独立的生物安全决策权力。为更好地体现生物安全治理(尤其是有关突发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应对)的专业性、效率性、权威性、实效性,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而非“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其主要成员为主管部门负责人、技术专家),使之成为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决策和执行中枢。当然,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生物安全重大事项(例如针对生物恐怖主义、生物武器)拥有最终决定权。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下设独立的国家伦理审查机构(由主管部门、技术专家和公众组成)、科学咨询机构(由技术专家组成),负责制定生物安全治理的伦理规范、技术标准。
为应对潜在的生物恐怖威胁,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要及早形成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推进生物安全防御系统工程建设,提升生物防御能力,确保国家生物安全。
六、结 语
在全球性生物风险面前,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治理机制面临巨大挑战,新冠疫情已经暴露出了我国现有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的种种不足。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机协调,没有形成严密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甚至还存在冲突,实效不足。因而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下统筹考虑,在生物安全领域进行系统的体制安排和制度创新,集中于以《生物安全法》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生物安全法治保障体系。
要采取“整体化+类别化”的规制模式,应在完成系统性、基础性、综合性的《生物安全法》的制定任务后尽快落实相关的制度,并由其统率和协调各单行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伦理准则、国家标准等,共同构成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要遵循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分类监管、严格责任、国际合作等基本原则,形成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保障机制、生物安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风险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风险管理机制、恢复和补救机制、生物安全防御机制、法律责任机制等制度保障体系。
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生物主权、生物安全和人类健康,促进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推进生物安全全球合作共治,增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这一法治体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要求,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彰显着风险责任理念的法律价值。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中,中国特色国家生物安全法治体系有理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前瞻性的制度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