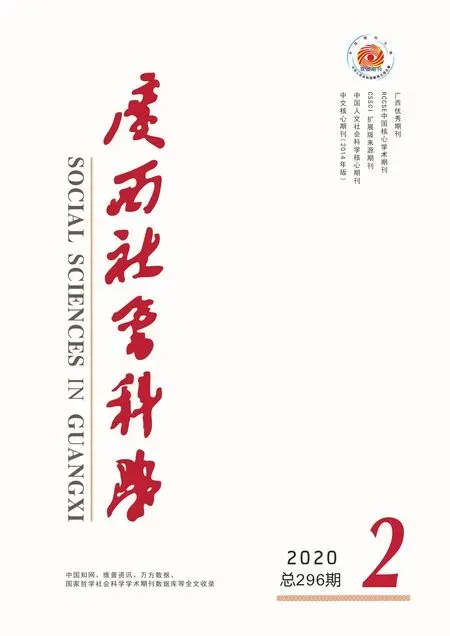马华文学的在地经验与空间表征
——以黎紫书小说创作为例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近年来,马华作家黎紫书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集《野菩萨》、长篇处女作《告别的年代》甫一上市就备受好评,更是受到王德威、董启章等学者、作家的推介。作为华文作家,黎紫书小说与常见的离散主题书写不同,她并不总是站在“域外之境”来书写个体的离散命运,而是将她的创作题材扎根于马华本土,以“域内人”的身份通过在地经验关注个体命运的转向。同时,她在小说中善于营造空间意象,将人物置放于现实与想象的空间之中。无论是从文本的内部还是外部来考察,黎紫书的小说都具有明显的在地经验与空间表征。
一、在地经验的文学言说
马来西亚华人从枝叶飘零到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这一变化必然包含个体对身份认同的转变,华人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政治、种族的夹缝中逐渐找寻自身的位置,扎根在蕉风椰雨的马来西亚土壤中。从心向中华到心向祖国马来西亚,离不开在地经验的言说与表达。“地方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把世界视为含括各种地方的世界时,就会看见不同的事物。我们看见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关联,我们看见意义和经验的世界。”[1]人文地理学强调个体与地方之间的经验关系,在地经验即主体在地方性文化空间中所感知的经验体系。面对马来西亚多族群聚居的文化特征,马来西亚华人从坚守中华文化到更多地吸收在地性经验完成文化身份的多元融合,在坚守中有转变,在转变中又充满“不为外人道也”的辛酸。
黎紫书作为新生代的马华作家,自身的文化属性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华文化,而是融合了扎根马来西亚的多元在地经验。这种在地经验与自身文化属性的抵抗、融合的过程,始终贯穿着黎紫书的小说创作,成为其小说中隐而不显的深层文化表征。纵观黎紫书笔下的个体命运书写,人物看似活动在中华文化构筑的文学空间场景中,实则又通过细密的生活场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元文化。“马华小说随着中国文化运动而萌芽出现,它已成为华人面貌的一面镜子,与华人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2]在方北方、原上草等作家的笔下,早期马华作家始终坚守着中华文化的属性,他们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的言行举止、生活信仰与大陆作家笔下的人物别无二致。而在黎紫书笔下,人物的文化身份开始变得游移,更多地吸收了大马在地文化的诸多特征。
经验的获得与感知是个体身份认同的直接来源,其间,在地经验的作用尤为重要。“人的记忆深处,隐藏着未经伪装和粉饰的认同态度及情感向度。”[3]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现实的生存境遇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黎紫书笔下的人物总是充满焦虑与压抑,他们始终生活在逼仄狭小的空间里,忍受着孤独与怪诞。小说里人物的生存境遇当然是作者的想象,但这虚构的想象必然取材于现实的在地经验。自马来西亚建国以后,种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矛盾一直都在动态的发展中,尤其是1969年发生的“五一三”族群冲突事件,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地位逐渐退据失守,生存空间被挤压而处于边缘化。然而族群政治带来的压迫并没有让华人屈服,马来西亚华人不甘放弃自身的文化属性,教育成为文化阵地的最后堡垒,他们借助社会力量出资,自建华校,其中艰辛,可想而知。那些漂洋过海、历经动乱的马来西亚华人,曾经与当地人一样怀揣着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的喜悦,以主人翁的姿态想要奉献“祖国”,但随着一连串的政治事件、种族冲突,他们内心充斥着“沦为二等公民的自卑感,有的甚至渐渐失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勇气,而兴起候鸟的心态”[4]。种族倾向性政策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一度成了被“祖国”抛弃的浪子。因此,马华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华人总是生活在荫翳、低矮的天空下,承受着爱与死的挣扎,这一切都与马来西亚华人的现实境遇息息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更加积极、多元的种族政策,新经济政策更是推动大马经济的腾飞,华人的生存境遇得到较大的改善。
作为小说家,在地经验最终要转化为文学经验,这种转化总离不开所生存的社会空间文化对作者思想观念的建构,作者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取材、构思、风格、氛围。生活、成长在中国的作家,决不能创作出生动反映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小说;从未来过中国的马华作家,也只能凭借想象和错置的时空体验来虚构“中国生活”,这正是在地经验对作家制约和规训的体现。马来西亚华人被排斥、被挤压、被歧视的历史经验,在黎紫书的小说中被塑造成一群瑟缩在边缘角落的小人物,他们以女性居多,如小说集《出走的乐园》《野菩萨》中的女性,她们敏锐地感受着身边的风吹草动,内心世界柔软又粗粝,在爱情面前柔软得如同湖水,她们渴望爱、渴望关怀、渴望在恶劣、冷漠的环境中有个栖身之所。她们曾经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于男人的手中,希望男人许诺的爱情为自己构筑栖息的“巢穴”,但命运总是日复一日地带来苦痛,来自日常生活的琐屑与窘迫,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敌对,最终她们在男性的背叛面前又狠毒如同恶妇。她们总是充满惶恐,背负着历史的重负和家族的秘密,呼吸着湿热的丛林弥漫出的瘴气,挣扎于内心世界的苦痛深渊。黎紫书塑造的女性成长之路已经脱离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沿用的批评标准,性别对抗与性别差异在文本中退居其次,黎紫书要呈现的是更加普遍的人性世界,即女性在她们所生存环境下遭受的苦难,以及应对苦难时内心世界的独特体验。
作家的在地性经验鲜明地塑造作家的写作风格并标识出小说人物、环境所在的文化属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马来西亚华人学子奔赴我国台湾地区留学,他们以“侨生”的身份“登录”台湾,在错置的时空里,想象与现实交汇,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疑虑与反思。身处现代化的台北,漫步在灯红酒绿的街头,当他们张望着满街店铺、广告上熟悉的方块字,理想中的传统“中国性”与现实境遇相背离,而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母国文化却又时时发出召唤。在黄锦树、李永平笔下,马来西亚在地经验与我国台湾在地经验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小说文本中,马来西亚的在地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不竭的创作动力,他们以边缘人的姿态“确立一种更恰切的言说文化乡愁的发声位置”[5]。李永平笔下淫雨霏霏的婆罗洲、张贵兴笔下充满爱欲和暴力的热带雨林,在台湾文坛造成不小的轰动。同样是以汉语写作,在台马华作家对母国在地经验的书写标识出鲜明的马来西亚文化属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台湾地区读者对神秘的蕉风椰雨、热带丛林故事的猎奇和向往。
黎紫书在她的文学书写中则小心翼翼地、敏感地、飞蛾扑火般地驰骋着奇幻的想象,她的小说中体现出更为多元的文化标识,不同于其他的在台马华作家。李永平写归去来兮,在大河上下寻找、重塑自我身份,他的书写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思考。其他马华作家在错置的时空里以“望乡”的姿态书写母国,也往往包蕴着浓墨重彩的私人情感,而黎紫书则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如果说在台马华作家书写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望乡”,黎紫书则是扎根本土,书写日常生活的众生哀乐。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里,黎紫书将细腻的笔触伸向马来西亚华人日常生活的角落,在柴米油盐中塑造了隐忍而又坚毅的杜丽安形象。在她眼中,没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正在马来西亚土地上为着生存而负重前行的人更值得书写。但她追求的又不仅仅是对表层个体生活的描摹,在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生活“常态”的变体,人物始终生活在压抑、阴郁的氛围之中。黎紫书营造变形的、魔幻的空间来刻画她们的内心世界,书写异常脆弱、备受摧残的女性生存境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标识出其独特的写作风格。
二、空间表征及其隐喻
“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握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6]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学的空间转向为人瞩目,空间理论不仅影响了地理学、建筑学,也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方向。文学文本中长期被忽视、被遮蔽的空间问题和空间书写重新受到重视,巴赫金较早对文学中的“时空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分析古希腊传奇小说中的传奇时间时,他指出:“在文学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7]一直以来小说被视为时间的艺术,作家的叙述行为需要时间,故事的开始、过程、结尾需要时间,文本完成后的流通、阅读也需要时间,而空间问题则被无意识地忽略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为后来的批评家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角度,也启发了学者对空间的关注与探索。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场域,还是实践意义与价值的对象化载体。”[8]在其空间理论的奠基之作《空间的生产》中,他阐述了现代社会空间生产活动的政治、文化内涵,空间实体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会同样生产出其价值意义。列斐伏尔提出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空间三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rional space)。空间不再只是客观的、有实意的物自体,而成为既是实践的、又是抽象的文化载体。其中的空间表征对文学理论批评开拓了新的角度,学术上所言的“表征”一词即指“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9],其意是通过文化实践赋予对象以价值和意义。
文学是时空的艺术,文学书写可以艺术地创造多元的文化空间,“它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现空间的生存意蕴”[10]。优秀的小说家善于借助空间的构筑来凸显文化内蕴,以此推进情节和人物的发展。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艺术地建构了“大观园”“太虚幻境”两个虚实空间,太虚幻境指向欲望与神隐的世界,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早已被安排好,人人各安其位、各有其命。而大观园则指向现实的、行动的世界,在大观园的空间中,金陵十二钗的极爱与极恨都是早已注定了的命运的铺展,这两个艺术空间异中有同,最终都走向毁灭与虚妄。大观园的现实空间被赋予深层的文化内涵,它是红楼儿女们活动的生活空间,它以花园式的构造承载人物的日常生活“表演”,其中的季节变换、植物枯荣、夏月秋虫无不暗示着人物命运的走向,同时它又蕴含着园内儿女们日常的生活体验,大观园的围墙隔开了两个迥异的空间,大观园外是世俗的空间场域,大观园内则是众多贾府儿女们悲欣交集的生活空间。曹雪芹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刻意以空间建构为目的,但作品一旦完成,空间自然而然地衍生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从空间角度切入反而更有助于理解作者的“荒唐言”与“辛酸泪”,成为打开小说秘密之门的一把钥匙。
黎紫书在小说中十分擅长营造空间意象,其空间意象的建构具有鲜明的文化表征,并非或有或无的人物活动的点缀。她营造偏远的、丛林深处闭塞的小镇,营造充满情欲宣泄的“五月花”妓院,营造阴暗的充满昆虫、幻想的阁楼。此外,黎紫书小说中的空间并非实体性空间而是蕴含着文化、历史想象的建构。尤其突出的是她对历史空间的重构,通过小说叙事,历史在她笔下有着不同的空间形态。
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艺术地构筑了“五月花”这一空间,“五月花”曾是一座妓院,它见证了两代人的命运,最终衰老成一座人去楼空的“古迹”,只剩下“你”在其中昼伏夜出,寻找母亲生前留下的秘密。“五月花”在小说中是重要的空间意象,是黎紫书精心构筑的隐喻世界。这一空间意象在她的小说序列中不止一次出现,短篇小说《推开阁楼之窗》中,“五月花”是一座旅馆,主人翁小爱则生活在这座旅馆的阁楼上,她试图与爱人一起逃离,最终却无望地看着男友丧命。无论是妓院还是旅馆,“五月花”都是丰富的意旨所在,它是人物集合之所、欲望之所,是家,是禁锢,是梦想,也是绝望。当刘莲在“五月花”旅馆中生下私生子“你”,而“你”穷尽一生在破败幽暗的“五月花”里寻找即将消逝的家族秘密时,“五月花”空间则成为迷失与寻找的空间隐喻。妓院和旅馆都是私密的、流动的场所,妓院是放纵欲望之地,人们在此宣泄欲望、转身离开。密闭的空间上演着情欲的故事,它充满暧昧与虚幻,在昏暗的氛围中照见众生的野蛮相。而“你”在衰败的妓院里出生、成长,“五月花”之于“你”则成为家宅的象征。关于家宅,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作过精辟的解读: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11]。但对于小说中的“你”而言,家宅则充满不确定性,它不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感受不到亲情的抚慰,它是冰冷的、幽暗的、衰老的所在。五月花垂垂老矣,它将无数隐秘的、情欲的故事都镶进墙缝中,摇摇欲坠,“你”就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你”的“寻找”注定是残酷和无望的。在五月花中感受时空错置带来的微弱感应,试图把握某些稍纵即逝的瞬间以打通与母亲、爱人、家族之间的联系,最终却都是徒劳。黎紫书借助空间呈现了人在“无根”状态下的精神世界,阴暗的阁楼藏污纳垢,被分割的时空像碎片一样,人生从来都不是完整的,总充满惶恐、焦虑,在一次次漫无目的的寻找中耗尽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黎紫书小说中的人物与飞蛾别无二致,都是生活的俘虏。
“黎紫书总在自己阴暗的空间中,过滤着社会人生中的毒汁,用那阴冷浓稠的毒汁告诉世人,在这个污浊世间中有着那让人透不过气的郁闷、沉闷、阴暗和无奈。”[12]她钟情于营造压抑的、封闭的空间场景,她时常构筑一座边陲的小镇,它们偏居于一隅,似乎与外界隔绝,时间变得凝滞、臃肿,一切流动的事物都失去了意义。在《国北边陲》中,“这小镇像褪壳过程中的蟒蛇,大多华人已经弃守,等不着它蜕变”[13]。这是一座人迹罕至、被四周茂密的森林笼罩的小镇,“我”的返回是为了解开家族关于死亡的秘密。“我”结束了流浪就是为了试图解开家族每个人都必将在30岁死亡的魔咒,神秘的小镇、神秘的家族、神秘的咒语,小镇在此成为神秘的救赎空间。黎紫书小说的魅力正在于她深入挖掘了人生存处境中的“非常态”“神秘态”以及碎片化、混乱化的本质。《国北边陲》里,莫名其妙的“非正常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家族成员的头上,而“我”的寻找注定无功而返,因为“我”绝望的发现,死亡的魔咒在家族的历史之中,我无法穿透时空的迷障抵达过去,因此死亡与痛苦是无法改变的,“我”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篇小说里,“我”在封闭压抑的空间中产生心理的扭曲变形,小镇阴冷、幻影重重,黎紫书总是安排她笔下的人物不断地逃离、寻找、回归,最终在自我放逐中焚毁。
小说《蛆魇》是黎紫书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作者营造了极其阴郁、可怖、阴森的空间氛围,在黏湿的独属热带气候的丛林中,“我”感受到寂寞像毒蛊一样侵入骨髓。而“我”的家宅正处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通过“我”的眼睛,最终发现了家族的禁忌:爷爷的暴虐与性变态,每每强迫孙子为自己口交,而母亲则是放荡的面孔,在辗转无眠的深夜让智障的儿子为自己排解寂寞。这是一篇有关家族禁忌的小说,乱伦、人性的扭曲变形统统被压抑的、阴森的空间所笼罩。最终“我”可悲的发现“这世间没有一种罪名能够以死解脱啊!我脱离了那终究腐烂的躯体,却发现真正的腐烂并非来自肉身”[14]。黎紫书善于营造变形空间中的扭曲心理,有时是外界空间对人物生存空间的挤压,有时是人物不可避免地坠入异质性的空间中。这些空间仿佛是另一种真实,如果说现实空间是人生存活动的场所,那么黎紫书建构的异质空间则昭示着人物幽微难名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黏湿的热带雨林,还是时光凝滞的小镇,在这样的空间里,一切众生的哀乐都变得无关紧要,历史在这里停住脚步,无论时间如何变幻,封闭的铁门似乎永远不会洞开,人物开始焦虑、扭曲,试图冲破束缚的藩篱。黎紫书温柔地触及人物的内心,又暴烈地看着他们飞蛾扑火般的焚毁,她借助空间的营造完成人物命运延宕的书写。
三、以小博大:再造的历史空间
芸芸众生此时此刻的瞬间叠加一起,造就了历史的丰厚与深刻,时间以奔流的姿态前进,被它甩在身后的就是历史。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必然面临一个问题,那便是以何种姿态去呈现历史?如何从历史中开掘生命的状态、发掘个体命运的丰富性、照见人性在不同空间情境中的幽暗明昧。对于马华作家而言,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是一部丰厚的大书,他们从枝叶飘零到落地生根,在多元文化、政治、种族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求得生存。他们从大陆逃难至南洋,生活在英国殖民体系之中,又历经日军侵略、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似乎每个阶段他们都承受着历史所赋予的重担,华人的在地经验、历史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华作家创作的渊薮。
书写历史是大胆的行为,因为历史一旦成为历史,我们就再也无法重返当时的情境,对历史的书写总要经过书写者意识的过滤,更恰当地说,历史就是观念史,真正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作家再现历史的行为就像挥舞着艺术的魔法棒,因为历史的重塑不只是以呈现事件为目的,而是为了尽可能艺术的感受历史丰满的细节,感受个体命运在历史夹缝中所承受的丰腴的痛苦,感受情欲、人性、暴力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极端境遇中变得癫狂而扭曲。客观化的冰冷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作家则要淬炼出历史的“温度”。因此,同样的历史素材经由不同的作家意识观念的过滤、拼接、重组,最终呈现出迥异的历史画卷。在张贵兴、李永平笔下,历史总是被情欲化、暴力化,尤其是对马共的历史书写。马共是马来西亚华人内心撕裂的伤口,在马来西亚国内,这段历史一直处在幽暗的角落,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马共成立,它积极参与了马来西亚境内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日本投降后,却转而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武力镇压,此后,马共开始遁入苍茫的热带雨林中,直到1989年投降。马共躲进丛林将进半个世纪,他们行踪隐秘,给外界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他们在热带丛林中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以至于当马共走出丛林与执政党和解的那天,出现了上万人前去观看他们扛着武器从雨林中走出的历史场景,随着他们一同走出雨林的是那段漫长的、充满暴力与哀戚的历史。
事物越神秘越能够刺激想象,而想象往往重构了历史具体的细节,历史不只是正史上冷冰冰的不带情感的叙述,而是芸芸众生最凡俗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历史的肌理。在不同的作家眼中,历史呈现着不同的面孔。张贵兴、李永平笔下的历史充满情欲与暴力的因子,他们不去呈现历时性的宏大的历史整体脉络,而试图呈现历史的某个横切面,呈现个体经验下的历史境遇,因此爱欲交织着血与暴力,雨林成为浓墨重彩的历史活动舞台。对张贵兴而言,“进入雨林,仿佛婴儿回到母亲的子宫,殷殷吮吸,不再苦恼”[15]。而在黎紫书笔下,马来西亚的热带丛林成为极富文化内涵的隐喻性空间,她习惯于将历史空间重构于人物生存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人物的爱欲在历史空间中变得扭曲,甚至精神错乱,但那些宏大的词汇,有关阶级、斗争、暴力对抗的色彩变得疏淡。黎紫书总是在看似轻描淡写、寥寥数笔之间将历史事件的轮廓勾勒出来。
在小说《州府纪略》中,黎紫书以多人视角叙述了主人翁谭燕梅与黄彩莲的一生,身为戏子的谭燕梅曾风光一时,她与闺蜜彩莲在动乱的岁月中相互帮扶,历经日军侵略,最后两人加入了马共,因为一个男人,两人的关系一度破裂,但最后彩莲在日军的攻击下为救爱人而牺牲,谭燕梅则带着彩莲的孩子重新回到了小城。儿子长大后,适逢马共投降,燕梅带着儿子一同前去观看,想找寻她故去的记忆。在这篇小说里,黎紫书想象性地再现了马共的历史活动空间,她用爱情的外衣重塑了马共的历史形象。借由想象的通道,作者重现了自我意识中的马共丛林史。黎紫书有意淡化历史的意识形态特征,马共不再是妖魔化的象征,历史空间通过环境、细节等描写得以再现,神秘的热带丛林展现为真实可感的生活画卷。
黎紫书对历史空间的营造体现在她对日常生活细节刻画的功力上,历史总是隐匿在生活场景之中,对生活场景精准的刻画正是对历史场景的反映与再现。物象在她的小说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黎紫书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感性捕捉生活场景,街道、牌楼、商铺、广告牌、电影院、饮食、家具等时常在她的小说中扮演着“言说者”的角色,它们言说着历史的细节,保存着鲜活的历史记忆。在《告别的年代》里,黎紫书描写了锡埠的生活场景,主人翁杜丽安“每天下午在大华戏院上班,卖五点、七点、九点和周末半夜场的票。白天她得忙着帮忙苏记把炒粉、糖水、芋头糕、炸芋角和咸煎饼等糕点一一准备好,放到三轮脚踏车加蓬改装的摊子上”[16]。正是在琐屑的生活场景中,历史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激烈的革命、血腥的暴力,有的只是世俗生活及世俗人生。
《告别的年代》是黎紫书的一部野心之作,历史事件在她笔下甚至成了她叙事的形式之一。小说的起始页并非从常规的“1”开始,而是以“513”作为小说正文的起始页。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5月13号是令人铭记的日子,1969年5月13日这一天爆发了种族之间的冲突,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这场冲突阻碍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感。他们置身于多元文化、种族之中,却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华人对本土的归属感在独立前后达到最高点,然后渐渐衰弱。”[17]很长一段时间,马来西亚华人处于被边缘、被压制的地位,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无不影响着马华作家的文学书写。黎紫书将“513”作为小说的起始页,在小说中她并没有直接描写“五一三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通过陈金海意外猝死,街头出现骚乱、杜丽安惊慌失措中被钢波营救,勾勒出“五一三事件”的面貌。“于细微处见历史”是黎紫书历史书写的策略,也是她的历史观。历史空间在这里成为人物日常生活的舞台,在琐屑的生活描写中,映照出“大”的历史。
总之,黎紫书的小说以在地经验的言说为基础,她善于营造浮光掠影的梦境,以及阴郁、可怖、压抑的异质性空间,人物在她笔下总是处于焦虑、敏感、孤独的状态。作为新生代的马华作家,她没有刻意规避历史书写,而是将沉重的历史事件熔铸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以“物”的描写感知历史的氛围。她将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境遇、内心世界做横向的剖析,始终关注人在特定空间文化氛围中的生存状态。爱欲、孤独、寻找、流离、失根,成为她小说中恒久的命题,黎紫书用她的笔感知芸芸众生生命的坚韧,不断探寻特异历史空间中日常生活所潜藏的私密的人性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