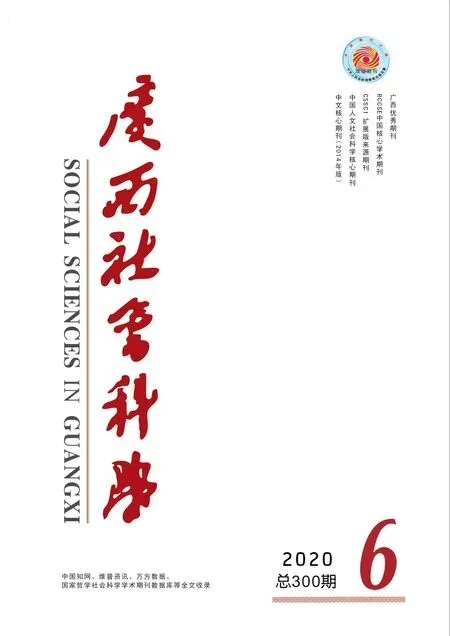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乡土想象的三种形态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文化认同的主观性使知识分子们在想象中国乡村时既形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1],又由于各自视野、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使得银幕上的乡土想象呈现出不同形态。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将“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定义为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风景画是指进入乡土小说叙事空间的风景,承担着多种叙事功能。“首先,它以特有的自然形象呈现出某一地域的‘地方色彩’,其次,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隐含的精神结构的象征载体或对应物,由‘场景’或背景换位或升格为与人物并置的叙事对象,从而获得相对独立存在的意义。”[2]风俗画指的是乡土小说中对乡风民俗的描写所构成的艺术画面。风俗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具体生活事件,对乡土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风俗又因地而异,“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风情画较前面两者更多带有“人事”与“地域风格”内涵。电影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依据这一逻辑起点,根据电影中对“三画”呈现的多寡将银幕上的乡土想象划分为三种形态,即“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和“诗意剥离后的生死场”。
一、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进入
“三画”交织形成浓郁的“地域色彩”与“风俗画面”。但是,在一些影片文本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三画”逐渐从电影的叙事空间中退场,乡土电影也随之蜕变为“农村题材电影”。如果将乡土社会视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存在,那么从社会形态上看,“乡土”蜕变为“农村”源自他者的进入,他者在这里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
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得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版图依然是乡土而古旧的,直到土地改革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猛烈冲击了乡土中国,顽固的宗法制关系被阶级关系所取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他者进入乡村,促使“乡土”向“农村”蜕变。“土地改革的目标在于解除束缚农民的‘封建家长制’枷锁,因为整个地方社会都被缠入这种特殊社会联系的复杂形式之中,要用合理而富有战斗性的阶级团结的方式来取代旧的传统的束缚。然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却阻碍着中国农民轻易地挣脱封建家长制的束缚,拆散旧的基础,土地改革的进程冲击着传统的生活结构,极大地造就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复杂多变的模式。”[3]“十七年时期”电影很典型地展现了这一蜕变,《我们村的年轻人》《李双双》等影片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乡土中国稳定的宗法血缘开始被阶级关系所遮蔽。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旧者,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新的经济形态开始逐渐深入乡村社会,尤其新时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生产方式的进入不可逆转,市场经济大潮在席卷了乡村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巨大波动,金钱取代乡土伦理成为乡民价值判断的尺度,而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思潮也对乡村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些对于古旧完整的“乡土中国”来说的他者,在进入乡村后导致“乡村”向“农村”的蜕变,也由此生成电影中“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的乡土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并不是乡土社会的对立物,只是在一种新的形势下他们过于突出,并确实对乡土世界产生了一种冲击。
(二)乡村生活作为背景
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乡土想象中,“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着力于以当代农民的生存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又可以被称之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创作,因为它们失却了作为狭义乡土电影的重要美学特征,即对风土人情和地域色彩的描绘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餍足。仅仅是对“乡”或者“土”或者人情的展示尚不能构成诗性乡土电影的全部,只有具备“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艺术质素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乡土电影。他者的进入使得电影中的乡土想象的一极缺乏对“三画”的描绘,侧重于展现当代农村生活,反映社会风貌,其叙事热点有“反映国家政策对农村影响”、“乡村日常生活”、“乡村法制、教育、医疗事业建设”、“城与乡的冲突”等,具有浓郁的社会学意味。
王德威认为“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4]。“文革”结束后,重返阵地的电影艺术家们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一批优秀乡土影片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最先以严厉的声调控诉了极“左”路线对人性和人们生活的戕害,这便遥指一种“政治潜意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政治理念的强力灌注使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革”产生的根源,清算“四人帮”倒行逆施对人民的危害,“伤痕电影”便成为新时期电影的肇始。这些影片中的乡村风景秀丽,可是统观整部影片却只见风景而不见风景画,村庄只是叙事的背景,并未进入编导的意识层面,影片也缺乏对“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绘,电影中的乡土想象只是“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伤痕”控诉后这一叙事热点便转而展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实施情况,《咱们的牛百岁》《柳暗花明》等都以热烈的声调讴歌乡村这片热土。而进入21世纪后,面对国家专项资金扶持,乡土想象中开始出现惠农政策的身影,例如《公鸡下蛋》《村官过大年》《沉默的远山》《荔枝红了》等,统而观之,这一类乡土想象往往“三画”色彩匮乏,以客观的语调叙述国家政策对乡村的影响。
“农民的日常生活”是“客观叙事下的乡村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叙事热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与民俗风习的变迁。改革开放后,赵焕章的《喜盈门》以诙谐幽默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当代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卷,通过家庭里妯娌长短的故事展示了我们民族尊老爱幼的伦理传统,影片中洋溢着迷人的乡土气息,风情画与风俗画相交织,但是风景画逐渐退隐至不见。20世纪90年代的《男妇女主任》、21世纪的《暖春》也是这样的影片文本,影片故事和人物的生动有趣,侧重于展现当代乡村生活,但“风景画”的消失使影片失却了某种审美标记,促使电影向农村题材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高速发展的城市相比,农村的法制和教育事业建设依然问题重重,解决好这些问题便成为农村、农民和国家的共同诉求。反映在影像中,“农村法制、教育事业建设”就成为重要的叙事热点。《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天网》三部影片的叙事主线都是“村民告村长”的故事,虽各有侧重,却反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法制事业建设中的问题。此外《一个都不能少》《背起爸爸上学》《美丽的大脚》《上学路上》《山那边》等影片从不同视角反映了农村的教育事业发展问题。“这些影片以人物的质朴、生活气息的浓厚以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生活化的关系,一方面呈现了当今真正的现实境遇和社会现状,一方面呈现了这些人物的人格基础和环境现实,体现了一种真实和质朴的力量。”[5]
(三)隐蔽的他者:城市文明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中乡土想象中的城市似乎是“不在场的”,一个缺席的他者,但实际上作为乡村的对立面、现代文明的代表、一种可以为村民提供命运转变契机的情节因素,城市在乡土想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乡土想象中一个隐蔽的他者。乡土想象中的城市往往被处理成两种形象,一种是光明的能指,一种是道德的深渊。
伴随着经济改革、思想解放的号角,人们大踏步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现代化被作为新时期以来一个光明目标,预示了富裕幸福生活的来临。而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能指,代表了迥然不同于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更理想更美好更上进的文明生活,因此,乡土电影中开始出现农村青年对城市的向往与追求,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激烈冲突。如果说《哦,香雪》中女孩子们对现代化的朦胧追求表现在对火车汽笛声和铅笔盒的神往,那么电影《人生》则将现代化的象征物具体到城市。高加林对县城的向往象征着农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尽管巧珍美丽、善良、纯真,无私无畏地爱着加林,他依然在理性的驱使下选择了黄亚萍,两位女性分别代表着乡村和城市,而高加林的选择体现出了对乡村的背弃与对城市的向往。跳脱出对作品“痴情女子负心汉”道德批判的窠臼,尽管高加林最终城市梦碎落魄回乡,但是从这个“于连式”人物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新一代农民所具有的奋斗竞争精神。还有一类青年,虽然选择留在了乡村,却依然使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而他们圆梦之地,便是作为“开放”和“光明”象征的城市。如《野山》中的禾禾在城里实现了之前屡战屡败的改革愿望;《咱们的退伍兵》中的二虎在城市里参军六载,退伍后利用人脉和技术办了焦煤厂,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老井》中为了打井不知折损了多少汉子,孙旺泉经过科学培训后才打出了老井村第一眼井。
城市以他的开放与文明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权力与金钱的相对集中又使得城市成为道德的深渊,罪恶的代名词。《惊蛰》中的关二妹好不容易逃离乡村,却在她向往的城市里经历了爱情和生活的双重破灭;《秋月》中在城里打工三年的牛宝回乡第一件事便是与秋月离婚;《高兴》中的五富受尽城里人的白眼,迫不及待地渴望还乡。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与人的异化使乡土社会通行的伦理道德规约在城市成为一纸空文,而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常常遮蔽了人性,因此城市在乡土想象中又常常被处理成“被道德遗忘的角落”。
二、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
(一)乡土特性与乡愁理念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重刊的序文里说道:“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6]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乡村便处在这一特具的体系的支配之下,而这一特具的体系即依靠血缘、地缘、姻亲关系和传统习俗的纽带来维系彼此的关系。
乡土是对一方水土的眷恋,离土之后,乡愁便由此而生。土生土长又终老于乡村的乡下人是不会有乡愁的体验的,因此,乡愁往往与知识分子及其书写对象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影片的创作者们往往是和土地没有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大都有乡村出身或下乡劳作的经验,这使得他们身上都保有那种与土地特有的血肉联系。尽管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出了乡村,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走进或者回到城市,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孤独与疏离又使得他们感伤的思念着回不去的乡村。即使是城市出生城市生长的电影人,也往往会深受乡土中国的浸润,因此,中国电影人的乡土想象及其生成物乡土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郁积于怀的乡愁的抒发。电影的特性决定了影片内容会突出强调戏剧冲突,但在一大批乡土电影中我们依然不难窥见编导对乡土田园的歌咏与眷恋,因此“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的形态是中国电影的乡土想象的重要一极,它所指涉的乡村不仅仅是一处地理位置,一个客观叙事的背景空间,也是观照者的心灵家园和灵魂的栖居之所,一处有着内在的生命与激情的存在。
(二)灵魂栖居之所
在乡土想象的“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形态里,创作者在乡愁的观照下对乡土倾注了大量强烈的个人情感,影片中的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相互交织,形成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而根据乡村在叙事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乡村是世外桃源,美景与人情相得益彰;其二,乡村是外来者的避难与拯救之地,其三,乡村是游子的精神家园。
受美学传统的影响,对田园生活的深情歌咏占据了我国电影中乡土想象的重要位置。“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并不是某一个时期、某一个类型或某一代导演的偏爱,而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7]胡炳榴1981年拍摄的《乡情》便是一个典型文本:田秋月通情达理让儿子寻亲,又亲自陪着女儿进城,面对她曾经舍身相救的匡华和廖一萍,她并没有以恩人的身份自居,反而悄悄回到乡下。田秋月博大的举止令整部影片具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儿,而这优美人情与风景相得益彰:田桂和翠翠去公社登记时,导演以大远景展现了春水初生,春风十里的江南水乡,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和碧绿的田野美得如诗如画,整部影片如同一曲风景、风俗、风情相交融的田园牧歌。
在乡村的第二种角色中,乡村作为外来者的避难与拯救之地的功能与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山下乡运动鼓舞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乡村,他们在“文革”中受尽苦楚,乡村以自己的温厚与善良成为知识分子们的避难与拯救地。《牧马人》中的“资产阶级”弃儿许灵均被折磨20多年,受尽人世煎熬,但在敕勒川里,热心的乡民无私无畏地保护、关爱他,辽阔悠远的草原风光感染着他,敕勒川成为许灵均的人格重生之地;《青春祭》中的李纯到云南德宏盈江县傣寨插队,家庭四分五裂,求学生涯突然中断,乡村生活艰苦不堪,初到傣寨的李纯无疑十分痛苦,这也是一代知青真实写照。但是傣寨的美景和人情很好慰藉了李纯心灵的创伤,云南傣寨之于李纯,是精神救赎之地,是理想净土家园。这片美丽的土地给了李纯少女初恋的体验,成长的顿悟,使她恢复了爱美的天性,树立起新的生活的信念,也确认了乡村的避难与拯救功能。而乡村的第三种功能,往往通过“游子返乡”这一桥段来实现。
(三)游子返乡
乡土是游子“挥之不去的记忆和眷恋,是铭刻着艰辛和殊荣的长卷”[8]。返乡是他们时时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执念。在乡土想象的创作主体群中,尽管创作者已经和土地没有了直接的联系,但是身处城市文明的浸润下,精神上的返乡使他们能更好地思考两种文明的本质并找到书写点。游子返乡是“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这一形态的典型叙事模式,游子只能通过返回家园才能获得一种诗意栖居的在家感,一份灵魂的安妥。因此,《南方的岸》中的易杰回城后开了粥粉铺,生意兴隆,但海南的那片椰林时时搅动着他的心,最终他又踏上了南下的轮船;《飞来的仙鹤》中的白鹭曾经在松嫩平原遭受过身心的折磨,但当她重回这片仙鹤翩跹、水丰草美的芦苇地时,她情不自禁地随白鹤一起舞动,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
谢飞导演的电影《黑骏马》借游子还乡的故事表达了导演/知识分子对草原/传统文明的思考。阔别十二年后白音宝力格终于回到了家乡。再次回到家乡的白音宝力格从索米娅身上看到了老额吉的影子,开始思索草原文明的意义。知识与现代文明的熏陶使白音宝力格不能容忍草原上原始的习性和自然的法律,因此他选择离开,去寻找当时更纯洁更美好更文明的人生。时过境迁,曾经的社会进步理想在市场经济浪潮汹涌的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质疑和反思,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了乡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于是,白音宝力格的回乡就有了双重的意义,既是对当初错误的忏悔与感激,又是对草原/原始/乡土文明的确认。白音宝力格的返乡,是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人对乡村心灵家园的回归。
三、诗意剥离后的生死场
在某种意义上说,“诗意剥离后的生死场”和“乡愁关照下的心灵家园”实际处于同一个层面,但是它对乡村的展现却在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向度上展开,如果说“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回望的是温情脉脉的乡村的话,那么诗意剥离后的生死场中展现的乡村却是令人震悚的。这一形态中同样具有三画,但是与前者相反,生死场想象中的风景荒凉、风俗丑陋、风情麻木,乡土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人性的光彩与黑暗都被置于前台,对悲凉乡土上的苦难描写构成了这一形态的最主要特点。
(一)食与性:生存止于活着的黑暗图景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食与性是人类的两重本能,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只有满足了生存的基本需要才能谈及伦理道德规范。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下的人们可以易子而食,而性饥渴甚至会冲决最基本人伦,因此,不能以简单的道德价值判断来批判生死场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生死场想象是创作者观照乡村时剥离诗意之后的景观,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创作者往往通过食与性的纠缠来展现物质匮乏下生死场的蛮荒和粗野,而在精神匮乏的展示上,则通过对乡下人生存状态与陋习的精细描绘而展现。
焦渴贫瘠的土地和以原始劳作方式耕作其上的人们成为生死场想象的典型图景,食与性的满足便是人们欲求的全部。《老井》中的孙旺泉为了让弟弟娶上媳妇忍痛放弃心爱的巧英,入赘寡妇喜凤家;《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颂莲在母亲的逼迫下退了学,嫁到地主家当小老婆;《红高粱》中的年轻漂亮的九儿被父亲以一头大黑骡子做交换,嫁给了麻风病人。乡土中国超稳定性的结构对人起着巨大的禁锢作用,个体很快会被环境同化,如曾经觉醒过的萧萧在十年后也按照族规给儿子娶了一个大媳妇;菊豆屡次提议逃跑,都被杨天青闷声闷气的否决;颂莲进入陈家大院后试图假孕争宠。封建男权社会的顽固与强大使偶有的越矩者很快被剿灭,如《白鹿原》中的反抗者田小娥最终身死神灭,被一座六角青砖塔牢牢镇压,永世不得翻身。在这压抑而了无希望的乡土世界里,灵魂麻木又衣食无缺的人开始寻找精神的消遣,于是影片中出现了丑陋民俗与黑暗人性交织的骇人画面:《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陈老爷为妻妾制定了一整套得宠就可以点灯、敲脚的规矩;《桃花满天红》中的老爷爱着桃花一张“桃花面”,为博美人一笑而重金请满天红演皮影戏,扬言死后也要桃花陪葬;《白鹿原》中的白孝文吸食大烟、滥赌无边,最终耗尽父亲辛劳一生积攒下的田产。正如萧红所说,“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乡村千百年来凝滞不变的生活方式与封建伦理的规约造就了乡民精神麻木的生存状态,他们在“铁屋”中熟睡着,即将被闷死而不自觉。置身于生死场中,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使人们的生存仅止于活着,个人的尊严与意志彻底流失殆尽,无论是以食换性或者以性换食都是那样心酸又令人绝望。
(二)死亡:乡村意义的流失
生死场本质上生成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匮乏所产生的焦虑、躁动甚至绝望将人陷入一种无边的生存困境中。在某种程度上人成了处境的困兽,当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抵挡来自生死场处境的压力时,死亡便成为最终的解脱。因此,在乡土想象的生死场形态中,死亡是最寻常的事件。《温故一九四二》中的老东家在逃荒途中目睹亲人一个个死去;《湘女潇潇》中的寡妇巧秀娘和铁匠相好,按照族规铁匠被打断双腿,巧绣娘被沉了塘;《黄土地》里的翠巧企图渡过黄河投奔延安,却被黄河水吞没;等等。
克尔凯郭尔说:“绝望是精神或者说是自我的一种疾病,而且,绝望就是永恒和自我的丧失。”[9]而死亡,正是强烈绝望的结果,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解脱。换言之,生死场处境是人们滋生绝望的温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死场想象中充斥着那么多以死亡为结局的故事。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空虚形成了生死场之上人们心灵的巨大空洞,但乡土社会超稳定性的结构使生活近乎凝滞不变,因此空虚便推动人们将生活中发生的一点小事尽情发酵膨胀,而长期的匮乏与空洞也滋生出种种人性之恶,由此酿成鲁迅所谓“几乎无事的悲剧”[10]。《血色清晨》取材于拉美魔幻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但是“影片核心的被述事件: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不再是一种魔幻,一种荒诞不经的偶合与残忍,而正是一场至为残忍的愚昧对文明的虐杀”[11]。红杏被张强国退了婚,因为新婚之夜“床单上啥也没有”。红杏的哥哥李平娃和李狗娃必须一雪前耻,捉拿红杏的奸夫。于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李明光在众人甚至是一片默许的眼光中走向了死亡,导演用高速摄影将凶杀的场景展现得极其残忍与荒诞,给人以极为强烈的视觉与心理冲击。愚昧贫穷、性的饥渴与人性的黑暗最终导致了这场以四条年轻生命的惨烈死亡为代价的无端惨案的发生。死亡,是生死场处境之中生命意义流失的最终极呈现。
四、结语
“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诗意剥离后的生死场”是三种想象中国乡村的方法,“客观叙述下的乡村生活”是“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退场之后的乡村图景,而“三画”的消隐不辨源自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进入,这一形态侧重于乡村生存状态的展示,或是展现改革的状况,或是揭露乡村法制、教育问题,导演对乡村的个人感情倾注较少,身处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无疑承受了更多转型的阵痛,因此这一想象形态中的典型叙事模式是展现现代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而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无疑激起了农村青年热切的向往。“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是影片创作者温情回望乡村时创造的乡土想象,唯美的乡村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场所更是影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物的心灵的栖居之所。“心灵家园”形态的乡土想象典型叙事桥段是“游子还乡”,只有还乡才能更好地认识家乡,认可家乡,从而实现精神还乡。“诗意剥离后的生死场”在某种层面上是“乡愁观照下的心灵家园”在另一个向度上的推进,乡村之美被剥离而呈现出令人震惊的丑陋与荒凉。“生死场”生成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而匮乏产生的绝望将人逼入绝境,死亡便成为这一形态的基本特征。内容和形式规约着三种乡土想象的形态与精神特质,但观照对象的相同成为它们最为深层的关联,从中我们可以窥到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与社会变革的多重合力对知识分子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