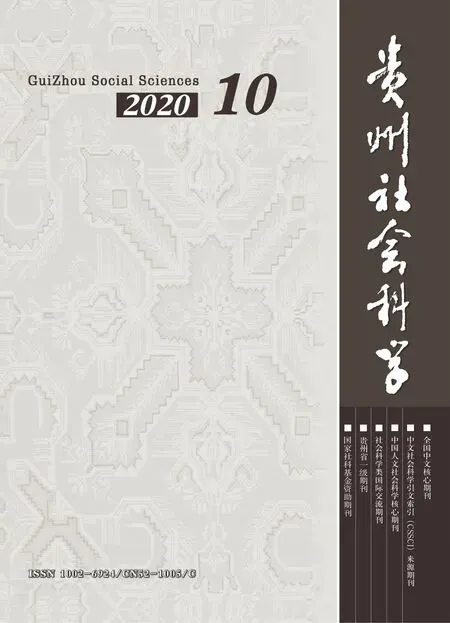环境史视野下的咸海危机研究
刘合波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冷战时期,对大自然的开发不仅包含着人类试图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美好想象,也包含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斗等历史背景。因此,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征服大自然来彰显国家的力量,成为衡量各自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重要尺度。大自然的开发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的一时繁荣,但不计后果的开发也往往会造成生态环境长期、大范围的恶化,福祉也随之演变为灾难。其中咸海在短短几十年里由繁盛走向枯竭的变迁史,就是苏联在冷战形势下对大自然过度开发所造成悲剧的缩影。历史上的咸海曾是世界上的第四大内陆湖,拥有近7万平方公里的水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咸海浩渺的湖面及丰饶的水产,使人类围绕咸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生活多样性的代表性地区之一。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及其解体后的国家对咸海补给河流——阿尔河和锡尔河的过度截流,以及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原本广阔的咸海水体产生了多次裂分,最终走向了不可逆的枯竭。
近年来,咸海的枯竭引发的生态灾难与严重的社会后果,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咸海危机形成的原因、过程与后果,以及咸海的恢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国外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主要是从生态学、地质学、环境学、海洋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咸海危机进行了分析;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已有成果主要侧重于咸海危机的警示意义及对咸海的治理等。①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虽已较为深入,但对于咸海危机的中的冷战因素分析较少,从环境史视野对该问题的探讨也不够深入。随着环境史在研究时段上的不断外延及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冷战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冷战环境史也成为环境史、军事环境史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也为研究咸海危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②本文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通过研究咸海危机来考察冷战时期苏联对大自然的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变迁,以及国际社会对咸海的拯救,以此来阐明冷战时期以迄于今日的长时段人类开发自然带来的环境问题之历史教训及其现实意义。
一、苏联对中亚的农业开发与咸海的枯竭
地处中亚的咸海流域,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并不适合耕种农业,因此早期居住在咸海流域的居民就有对咸海的两条补给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进行改道与开发利用的历史,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灌溉系统。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河流改道计划,尚未对咸海造成大的影响。③在俄国扩张、殖民的过程中,这些早期发展灌溉农业的历史记忆被传承下来。但在运用大规模的现代技术之前,这些灌溉农业的发展规模非常有限,并不是影响咸海状况的决定性因素。④对咸海枯竭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主要出于冷战需要在实施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过程中建立的灌溉系统。
(一)冷战背景下的“处女地计划”与“白金计划”
1954年以前,苏联的粮食生产区主要集中在降水充足的传统农业区,然而苏联人口的增长及其对动物产品需求的增加,使传统地区的收成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⑤这是苏联在横向上扩大耕地面积、纵向上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来提供更多农产品的现实需求。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处于冷战的高潮阶段,双方除了意识形态、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竞争之外,农业生产力的比拼也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要面对国内的粮食形势与来自美国的冷战压力外,苏联还要通过农产品援助来维护与东欧国家的同盟关系,这些都是苏联扩大农产品生产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国内的粮食安全、冷战发展态势都使粮食在苏联的国内外政策中处于中心位置。⑥赫鲁晓夫认为,迅速增加粮食供应的唯一途径是大幅度增加播种面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犁开以前未开垦的大片土地。1954年2—3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和开发未开垦和闲置土地》的决议,这标志着战后苏联农业政策的根本转折。推动农业发展的“处女地”计划随之被推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处女地和闲置土地被大规模开垦,小麦和其他作物开始在这些干旱和半干旱的土地上种植。⑦为了启动这项计划,65万人被移民到哈萨克斯坦,其中包括咸海地区。由于开垦脆弱的土壤所造成的破坏,造成了这些被开发的“处女地”广泛的退化和沙漠化,这是最终造成咸海危机的基础。⑧
除了粮食之外,苏联更重要的意图是希图依靠大规模灌溉来获取棉花并进行出口。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的棉花生产国主要是中国与美国,在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美苏对抗的背景下,苏联既要解决300多万士兵的军服问题,也希望能从棉花生产中获取更多的财富,因此棉花生产成为苏联的一项军事与战略需求。苏联政府认为,中亚等加盟共和国气候温暖,人口众多,是“白色黄金”的理想产地。⑨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为实施开垦边际土地与种植棉花的“白金”计划,开始有组织地利用现代技术对位于咸海流域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个加盟共和国进行大规模的开发。⑩但中亚位于半干旱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就需要解决灌溉问题。事实上,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开发这个项目唯一需要投入的就是实施一个大规模的灌溉计划。为了对这些半干旱地区进行灌溉,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被苏联认为是填补不断扩大的水渠灌溉网和棉田最理想的水源。因此,苏联截流了咸海的这两条补给河流,通过对这两条河流进行改道(修建运河)、建设水库,在中亚地区建立起了错综复杂的灌溉网络。
随着庞大的灌溉网络的不断蔓延,中亚地区的灌溉面积不断扩大。从1960年到1990年,中亚的土地利用面积从350万公顷增加到750万公顷,棉花产量猛增,该地区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棉花生产区。随着“白金”计划的逐步推进,棉花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产量也迅速增加。值得关注的是,苏联时期依靠大规模的灌溉来获取棉花并出口的这种理念,对乌兹别克斯坦影响深远,乌兹别克斯坦对出口“白金”获取财富的认知,是其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乌兹别克斯坦大约有一半的农田用来播种棉花;到1990年,种植棉花的面积扩大到了约三分之二;土库曼斯坦也在不断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从1960年到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原棉产量从100万吨提高到了170万吨,土库曼斯坦的棉花产量也从12.2万吨增加到了42.3万吨。在30年间,咸海地区的棉花产量总体上实现了近两倍的增长,为苏联提供了90%的棉花。除了棉花之外,发达的灌溉系统还使该地区为苏联提供了40%的大米。由此来看,灌溉农业为苏联的棉花独立与粮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单一的棉花种植与过度、无效地用水,河流改道与上游水库的修建,导致严重依赖阿姆河和锡尔河补给的咸海水位不断快速下降,最终导致了咸海的枯竭。
(二)补给河流的过度利用与咸海的枯竭
1960年,咸海的表面积为6.75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亚洲的里海、北美的苏必利尔湖和非洲的维多利亚湖,是世界第四大内陆水体。咸海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湖,其补给水源最主要的是阿姆河和锡尔河,因此咸海的水位平衡基本上是由这两条河流的补给和净蒸发来维持的。有研究表明,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咸海水位的变化可能小于4.5米。从1911年开始使用仪器对咸海进行观测,到20世纪60年代初,咸海的水位非常稳定,最大水位变化小于1米。
但在苏联采取开垦“处女地”的垦荒运动、种植棉花的“白金计划”之后,大规模的灌溉需求打破了咸海通过河流补给与水的蒸发实现水位平衡的稳定状态,咸海的海平面急剧下降,海岸线开始大幅度后退。尽管自1960年以来,咸海储水量的变化有气候方面的原因,如1970年代的一系列干旱年份,特别是1974—1975年的干旱使得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水量变小,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消耗性用水。有学者认为,在改造河流的灌溉计划中,卡拉库姆运河是最近几十年造成咸海流入量减少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1954年开凿的卡拉库姆运河是苏联最大最长的灌溉渠,也是苏联时代最大的工程壮举之一。卡拉库姆运河穿越土库曼斯坦南部约1370公里,将水从阿姆河输送到里海(Caspian Sea),运河的修建改变了这个沙漠地域的农业面貌,但也改变了咸海稳定的储水量。据统计,卡拉库姆运河向350万公顷牧场和近100万亩农田提供灌溉;在土库曼斯坦,有超过60%的粮食、果蔬与肉类产量及接近一半的棉花与牛奶产自卡拉库姆灌溉区。此外,运河还支持发电,为沿线城镇的工业和生活用水提供水源,部分地区还可通航。但由于大量蒸发、渗透及用水管理不善,河水浪费极其严重。到1980年,灌溉用水占到了从阿姆河和锡尔河取水量的84%,其中62%的水由于蒸发和渗入地下而流失。而所有这些流经卡拉库姆运河的水,包括排水沟的水,咸海都无法利用。此外,阿姆河上游的努列克(Nurek)大坝和锡尔河上游的托克托古尔(Toktogul)大坝的修建,使中下游的水情恶化,总流量较少的锡尔河的情况更为棘手。
无法得到充分补给的咸海,水量迅速减少,海岸线越推越远,逐渐开始向更小的水体单元分化。从1961年到2011年的50年间,基本以每10年为一个阶段,咸海从1961—1970年第一个阶段的缓慢衰退开始,以后每个阶段的减少速度都变得越来越快。1987年,咸海裂分成北部的小咸海和南部的大咸海两个水体(锡尔河流入前者,阿姆河流入后者)。咸海的裂分进一步加快了水位的下降,尤其是大咸海,1989年的海平面有3.6万平方公里,而2011年则仅余0.6万平方公里。至2011年,整个咸海水位和储水量达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海平面缩小到1万多平方公里,水体体积减少到92立方千米,分别只占到1960年的15%和8%,近6万平方公里的原海底已经干涸。对于咸海的迅速干涸,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就宣布咸海在生物学上已经死亡。曾经依靠当地丰富的鱼类资源进行消费和贸易的社区,现在距离海岸线有100多公里,整整一代人甚至都没有见过他们父母曾赖以为生的“大海”。阿姆河和锡尔河河水的过度使用,最终导致咸海走向枯竭,出现了咸海危机。
二、咸海枯竭下的生态灾难
就环境的载体而言,咸海枯竭本身就是一场灾难,而由此引发的危机远远则超过了咸海枯竭本身。从环境史的角度看,咸海危机除了包括咸海的枯竭之外,主要是指咸海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生物种属的变迁和对人类健康与生存条件的威胁。咸海海平面下降、海水盐分升高及咸海荒漠化问题,都大大改变了过去咸海长期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盐度水平及气候条件,导致了生物种属的变迁。咸海的枯竭对18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咸海流域的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不可逆的消极影响,饮用水的减少、高盐化及污染造成的水质下降,使当地流行病肆虐。生存条件的变化,以及咸海的枯竭带来的捕鱼业、航海业的急剧衰退,使咸海地区很多人流离失所,成为“生态难民”。
(一)生态环境的恶化
咸海退化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海水盐度的升高和咸海沙漠的形成。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河水正常流入咸海的时期,咸海的含盐量大体保持在每升10克的水平,约相当于海洋盐度的三分之一,这是咸海能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然而自1961年以来,咸海的补给水越来越少,海水的盐度也越来越高。1989年咸海的盐度是1960年的2.8倍;到2004年,大咸海的盐度达到每升80—100克;2011年更是超过了150克,已经是1960年的15倍多。
咸海盐度几倍、十几倍的增长也反映了咸海快速走向干涸的进程,随着咸海海岸线的迅速退却,加速裂分的咸海海底逐渐为盐土、硬壳盐岩所覆盖,地球上第四大内陆水体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一片干燥、被污染、有毒的盐沼,最后形成了特殊的、巨大的开放式盐沙漠——咸海沙漠(Aralkum)。这些富含碱性的盐是盐尘风暴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干涸的海床缺少植被的固着作用,沙尘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并因此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邻近的耕地造成盐污染。咸海地区的生态危机覆盖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北部和哈萨克斯坦西部的肥沃土地,整个地区都成了最严重的环境灾难的牺牲品之一。咸海盐度的不断攀升与咸海盐沙漠的形成,改变了原来咸海生物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咸海物种种属的重大变迁,也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健康,造成了海洋生物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此外,该地区的气候也受到了影响,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冬天则越来越冷。来自西伯利亚的风,曾经被咸海所缓冲,现在则可以自由地穿越海床,带走大量的尘埃,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咸海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
(二)生物种属的变迁
最初在咸海有至少180种无脊椎动物,在咸海盐碱化之前,来自淡水、咸水和含盐大陆水体的物种占主导地位。咸海曾有20种本地鱼类和14种引进类型,本地鱼类主要是在淡水中繁殖,鲷鱼、鲤鱼等是主要的商业捕捞鱼类。咸海周围的湿地是多种动物的栖息地,咸海沿岸的图加德森林构成了一片绿洲,成为许多鸟类的筑巢场所。其中生活着包括60种哺乳动物,300多种鸟类和20种两栖动物。就植物种属而言,到20世纪60年代,咸海的植物种属主要包括24种高等植物、46种藻类植物。在长期的进化与物种引进的过程中,咸海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群落与较为完备的生态结构。
早在1961年,咸海动物就出现了退化,但当时引起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引进。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咸海退化的速度加快,海水盐度的不断升高成为影响咸海生态的主要因素,咸海的无脊椎动物群也因之经历了两次大的生存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咸海中的淡水、半咸水动物种群首先灭绝,海生物种、源自海洋的广盐性物种以及内陆咸水动物物种存活了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咸海变成了一个高盐湖,由于无法进行有效的渗透调节,海生物种逐渐消失了。咸海的盐碱化也进一步导致了寄生动物的枯竭,随着寄主的消失,与寄主生命周期相关的寄生虫也逐渐消失。对锡尔河和阿姆河的管制以及它们流量的减少已经改变了咸海鱼类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它们的繁殖。1971年首次出现了盐度对成鱼造成不利影响的迹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鱼类的自然繁殖完全遭到破坏,商业捕鱼量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咸海里的鱼类绝迹。大自然生态圈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链条网,一种生物种属的缺失,往往带来整个链条的断裂。上述海洋动物群落的消失引发了连锁反应,以海洋环境为栖息地、以鱼类或无脊椎动物为食的水生和半水生动物,如食鱼鸟类、水禽、两栖动物、水蛇,甚至水生昆虫的数量都急剧减少,一些淡水物种和河流、森林物种灭绝或完全离开该地区。此外,伴随咸海水面面积的减少和化肥、杀虫剂、除草剂、棉花落叶剂的使用造成的剩余水体的污染加剧,也使水禽的种群也大量减少。
在咸海的动物种属逐渐消亡的同时,植物种属也几乎开启了同样的进程。辽阔的阿姆河三角洲原本有丰富的生态系统,但咸海的退化对其损害严重。咸海海平面下降导致了地下水水位下降,这加剧了沙漠化的蔓延,由柳树、沙枣、油松、盐雪松和芦苇等乔木、灌木和高草构成的大面积湿地都遭到巨大破坏,耐盐碱植物和耐干旱植物迅速取代原有的植被群落。在20世纪60年代初,包括水草在内的淡水或半咸水水生植物开始消失。到20世纪70年代末,物种急剧减少,在高盐度的影响下,芦苇面积减少了一半;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咸海盐度逐渐升高,芦苇就基本消失了。新形成的、快速盐化的浅层生境被嗜盐物种如刺角藻、沟草等植被迅速覆盖。但随着盐度的进一步增加,这些物种也逐渐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末,咸海的植被只剩下了能够耐受每升50克盐度的蔓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经植被较为丰富的咸海,最终被盐生植物所取代。长期以来形成的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生境被破坏,由多种植物及水体形成的栖息地随着咸海的枯竭而消失。海洋动植物的叠加消失,进一步加剧了咸海危机。
(三)咸海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影响
咸海生态环境的恶化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多重的,除了对咸海本身之外,咸海衰退也给咸海周边数十万平方公里内的数百万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咸海地区水质的下降、咸海沙漠的形成,使咸海地区各类疾病流行,极大地威胁着当地民众的健康。咸海枯竭及其导致的大量生物的灭绝,使过去咸海地区的居民赖以为生的职业衰退或消失了,这给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进而加剧了咸海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咸海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之一,是饮用水水质的下降。咸海水体的减少使海水盐度增高、造成盐沉积并渗透到地下水中,由此带来了饮用水盐度的增高。到20世纪90年代,咸海地区每升饮用水的含盐量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上限的四倍,这导致了肝脏与肾脏疾病、腹泻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增加。水质下降的另一个表现是饮用水受到了细菌污染,这导致了结核病的流行,在前苏联各地区中咸海地区的结核病发病率是最高的。在一些城镇,10万人中估计有400人患病。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res,缩写为MSF)估计,到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左右,咸海周围地区居民每10万人中有100—150人患有结核病。水质下降对于孕妇和婴幼儿的影响尤其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调查显示,该地区婴儿平均死亡率为7%,而毗邻前海滨的几个地区的婴儿死亡率为8%至10%以上。这一比例是前苏联国家水平的3至4倍,是美国的7—10倍。除此之外,棉花杀虫剂、落叶剂等有毒化学制剂的沉积和进入灌溉系统造成的污染,也是水质下降的重要原因,这导致了伤寒、病毒性肝炎和痢疾的高发病率,进一步恶化了咸海地区的公共卫生形势。
咸海枯竭产生的盐风暴也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咸海地区形成盐风暴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北风或东北风,这对整个咸海周围区域都会产生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咸海西部哈萨克斯坦的于斯蒂尔特高原(Ust-UrtPlateau)和咸海南端的阿姆河三角洲地区,后者是沿海地区人口最密集、经济和生态最重要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质学家和咸海专家的研究显示,每年单是风沙就从咸海干涸的海床吹走大约4300万公吨盐。当地卫生专家认为,无数吨暴露在空气中并被空气传播的盐和灰尘,是造成咸海附近地区高度呼吸道损伤和疾病、眼部疾病,甚至可能是导致喉癌和食道癌的一个因素;而盐和灰尘中所含有的残留农药和重金属,都对人类和其他动物产生了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咸海的生态环境危机不仅对咸海地区周边居民的健康造成了威胁,还导致了当地民众赖以为生的产业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干旱和沙尘使农作物减产,带来了粮食的安全问题;靠近咸海的三角洲和沙漠地区的畜牧业由于沙漠化造成牧场面积减少和生产力下降,地下水水位下降,适合放牧的自然植被被不能食用的物种取代而受到破坏。除了畜牧、农业受到重创之外,捕鱼业、航海业等行业也都随着咸海海岸线的不断后退而日渐衰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当地居民部分或全部失去了以前的收入来源,到21世纪初咸海的北部地区仍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最贫穷的地区。环境的恶化还造成了“环境难民”,199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独联体难民和移民问题会议上,与会各国认为干燥的咸海盆地是当时最糟糕的生态灾难,估计有几十个地区、10万多人因环境灾难而流离失所。谋生手段的缺失、公共医疗体系的脆弱及不断恶化的环境,咸海地区的居民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有研究指出,到21世纪初,有500万人生活在一个日益恶化和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中。在无数的研究和报告发表之后,专家们认为重建工作是不可能的,应该把重点放在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上。
咸海的枯竭带来了水质下降、盐风暴、物种变迁、疾病流行及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咸海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也对生态系统中的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已陷入危机中的民众的营养状况、当地的经济和医疗体系、区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咸海危机的影响溢出了咸海枯竭本身,生态环境危机超越了中亚各国的边界而成为国际性的问题,这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切。
三、各方拯救咸海的努力
从1960年往后,咸海萎缩的速度逐渐加快。随着咸海海岸线不断后退、咸海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当地居民各种疾病的流行与传播,苏联、咸海流域各国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拯救咸海、改善咸海地区居民的健康与生活条件进行了研究,并试图通过设立项目和制定拯救计划,来恢复咸海的生态环境。从拯救咸海的过程来看,参与方从最初的苏联逐渐转向咸海流域国家的联合,进而扩大到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拯救的内容,也从恢复咸海及其生态逐渐延伸到对当地居民的人道主义救助上。
对于咸海的修复,首要的任务是解决咸海水体的补给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学者就开始研究咸海出现的问题及过去一个世纪里咸海海平面高度的波动,并于20世纪70年代指出了拯救咸海的必要性。苏联政府也注意到咸海萎缩和中亚地区灌溉用水出现的问题,因此曾制定了多项计划试图挽救不断萎缩的咸海,如计划通过修建长达几千公里的运河,从西伯利亚的诸条大河引水注入咸海。但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加棉花的产量而不是为了拯救海平面不断下降的咸海。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用一种灾难来代替另一种灾难”。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解体前,苏联不断关注咸海的海平面下降、咸海的生态环境与生物状况变化及咸海萎缩对社会的影响,也对这些问题组织了学术研讨、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如1977—1985年莫斯科地理研究所就主导研究了从阿姆河和锡尔河调拨灌溉用水的后果。当时的咸海沙漠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盐沙漠刚刚开始发展,咸海的恢复似乎是现实的。但类似的项目只是停留在进行研讨的层面,还远没有提上进行拯救的议事日程。因此,咸海不断持续地萎缩。1982年,阿姆河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向咸海补给河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普遍认为,将咸海恢复到1960年之前是不可能的。
有研究认为,1991年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从前苏联继承的最大的环境遗产就是咸海的枯竭。苏联解体后,中亚新独立的各国不得不面对咸海枯竭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1993年3月,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总统联合成立了“解决咸海盆地问题委员会”,希望通过获取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捐款来解决咸海问题。在世界银行的领导下,先后有131个外国特派团和国际专家代表团访问了咸海,讨论了咸海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并编写了报告和发表了文章,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导致具体行动的产生。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咸海的局面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仅处于讨论阶段,咸海的形势仍在继续恶化。在1987年咸海分裂为大小咸海之后,2005年大咸海进一步分裂为东部和西部两片海域,次年咸海西部又出现了再次分裂。咸海的盐度也随着咸海的收缩而不断上升,这对生活在咸海中的鱼类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并摧毁了沿海的港口和渔村。直到2006年,哈萨克斯坦政府才在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下,最终完成了小咸海的部分修复,使小咸海的盐度下降到一些本地鱼类可以生存的水平,渔业也开始复苏。但大咸海的恢复依然遥遥无期。
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咸海的海水补给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部分恢复和保护阿姆河三角洲及其湿地成为优先选项。1998年,在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下,为期5年的“水与环境治理项目”开始在咸海地区实施。随后,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全球环境基金开始实施“咸海湿地恢复工程”,通过在三角洲和咸海干涸的河床上建立人工池塘和湿地,部分生态系统已开始恢复。自20世纪90代初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对阿姆河和锡尔河进行生态研究和监测。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咸海盆地科学咨询委员会”,试图为在科学家和决策者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协助国际水资源分享协定的谈判和执行,以及为河流三角洲的恢复与咸海的稳定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除此之外,德国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地区和国际组织,都与中亚国家在水资源的利用、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进行了合作,这些都为咸海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尽管国际社会对咸海地区的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生态的恢复与保护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但生活在咸海地区的500万民众的健康问题却长期遭到忽视。199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咸海环境与地区援助项目”,向环咸海灾区提供援助,其中的援助重点主要是营养、健康教育、水和环境卫生等方面。1998年4月23—2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救助儿童会等组织发起了主题为“减轻生态灾难的后果:妇女、儿童、健康和环境”的会议,呼吁应大力倡导民间团体参与目前和未来的发展决定,将今后的努力应集中在注意妇女和儿童的状况,特别是健康和营养方面。同时,必须促进对腹泻病、急性呼吸道感染、疟疾、麻疹、营养不良及其伴随症状的预防,为医院、学校和药房提供清洁的水,对孕产妇和儿童疾病提供标准化的服务程序和治疗等。
在实际的医疗援助方面,自1998年以来,无国界医生组织就一直在该地区开展工作,向居民提供医疗援助,并对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进行研究,他们呼吁更多的国际组织加入到对咸海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来。针对咸海地区流行的结核病,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覆盖大片沙漠的380万人口中推广现代结核病短期化疗(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缩写为DOTS)技术,其中登记治疗的病例超过6000例。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积极努力下,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国家结核病政策。尽管如此,治疗病人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如因距离遥远而无法进行有效、正常的监测等。目前,联合国和各机构正努力改善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民生,减少健康和环境风险。
从前苏联、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独立国家,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恢复咸海的水位、生态环境,对咸海地区的生态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如1998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所指出的,尽管咸海地区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要有效地实施救助,必须充分地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由此可见国际援助的愿景与实际成效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国际社会对于完全恢复咸海的态度也并不乐观。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关于咸海盆地的2000年展望,认为中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但同时也认为在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咸海盆地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对咸海盆地的2025年展望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2025年咸海盆地将拥有健康的人口,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和谐地生活在一个安全、健康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中,城乡人口收入也将高于2000年。但这一愿景还面临诸多挑战,如资金、跨国界水资源的分配、不断增加的人口的用水需求、政治方面的议题等,这些因素都使恢复咸海的任务面临重重困难。
四、结 语
咸海危机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咸海补给河流的过度改道、拦截蓄水、引流灌溉与对水的管理不善造成的。咸海在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海岸线急剧后退,尽管苏联、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及国际社会都提出了种种方案和拯救措施并加以实施,但咸海还是走向了不可逆的枯竭,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社会危机。
在巨大的改变自然的运动中,这些运动尽管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却在短时期内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暂时繁荣的代价是整个生态体系的崩塌与变异,甚至消亡,并带来了地域文化的消失。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遏制、争夺与竞争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流,人与自然的动员,是双方满足冷战需要的重要举措,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成为研究冷战时期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咸海的枯竭是美苏冷战产生的诸多环境问题的代表。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发展走向与选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影响了冷战格局,尽管这些问题在相关方面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冷战时期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也呈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思想的极端发展,为适应灌溉的需要而在全球范围内修建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承载着美苏等国家的冷战意识,以水坝修建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绿色革命在全球的推广与在第三世界的全面铺开,都展现了技术对环境变迁的巨大影响。从现代农耕方式的层面看,咸海危机并不是孤例,从东非高原的维多利亚湖、中非的查德湖,到美洲的墨西哥湾、美国的莫诺湖等等,依赖灌溉的现代农业带来了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及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对水资源的污染等问题,从而造成了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与严重的社会后果。
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阶段来看,咸海危机只不过是冷战时期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资源开发和利用而导致的环境灾难的案例之一。咸海的枯竭,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消亡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削弱,过度开发与缺乏预见性甚至不计后果地破坏(不论有无意识),都带来了古老文明、文化的消亡。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存在都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物种或环节的消失,都会产生“蝴蝶效应”,只不过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需要若干年后才由隐性转为显性。咸海生态系统几十年的急剧变迁表明,在生态环境的链条中,居于生存金字塔顶端的人类采取的剧烈改变自然的活动,是造成环境变迁的主要根源,如果任由这种方式发展下去,类似咸海的灾难将会持续在地球上出现并蔓延。
注 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Andrey G. Kostianoy, Aleksey N. Kosarev,The Aral Sea Environment, New York: Springer, 2010; M. G. Bos, ed.,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rrigation, Drainag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Aral Sea Basi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M.G. Bos, et al.,Water Requirements for Irrig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Dordrecht: Springer, 2009; Michael R. Edelstein, et al., eds.,Disaster by Design: The Aral Sea and its Lessons for Sustainability,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Siegmar-W. Breckle et al., eds.,Aralkum - a Man-Made Desert: The Desiccated Floor of the Aral Sea (Central Asia), New York: Springe, 2012; Ian Small, Noah Bunce, “The Aral Sea Disaster and the Disaster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2, (Spring 2003); Andrey G. Kostianoy, Aleksey N. Kosarev,The Aral Sea Environment,New York: Springer, 2010; Philip Micklin, et al., eds.,The Aral Sea: The Devastation and Partial Rehabilitation of a Great Lake, New York: Springer, 2014。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徐海燕:“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亚生态环境问题——以咸海治理和塔吉克斯坦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杨恕,陈焘:“咸海——危机和前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1期。
②关于“冷战环境史”的概念、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等,参见J. R. McNeill, Corinna R. Unger, eds.,EnvironmentalHistoriesoftheCold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刘合波,“史学新边疆: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内容与意义”,《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
③Herbert Wood,TheShoresofLakeAral, London: Smith, Elder & Co.,1876, pp.98-99。
④Paul Josephson ed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Rus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71。
⑤Martin McCauley,KhrushchevandtheDevelopmentofSovietAgriculture:TheVirginLandProgramme1953- 1964,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6, Preface, p.xi。
⑥Michael R. Edelstein, et al., eds.,DisasterbyDesign:TheAralSeaanditsLessonsforSustainability,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p.112-113。
⑦Martin McCauley,KhrushchevandtheDevelopmentofSovietAgriculture:TheVirginLandProgramme1953- 1964,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6, p.79。
⑧Michael R. Edelstein, et al., eds.,DisasterbyDesign:TheAralSeaanditsLessonsforSustainability,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p.113-114。
⑨Siegmar-W. Breckle et al., eds.,Aralkum-aMan-MadeDesert:TheDesiccatedFlooroftheAralSea(CentralAsia), New York: Springe, 2012, pp.432-435。
⑩咸海流域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伊朗等7个国家,只有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沿海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