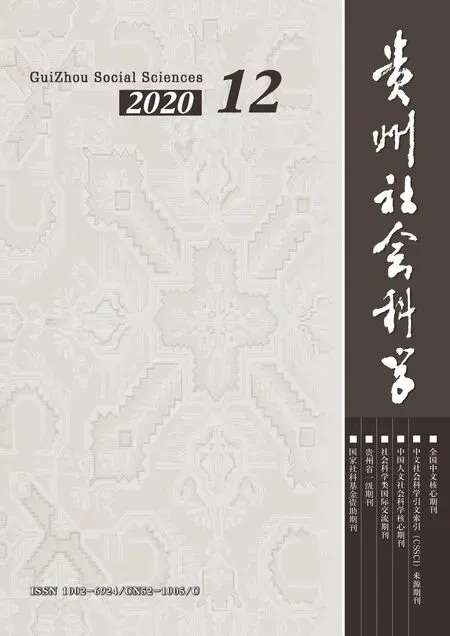何以斗而不破?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抗争运动刍议
张新军
(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
在古代世界各地,阶级冲突普遍存在。为什么英国能够平稳地实现社会转型?塞缪尔·亨廷顿总结了社会转型的三类方式,一是上层社会主动改革,采取变革方式(transformation),一是由下层社会主导社会变革,采取取代方式(replacement),还有一种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合作完成,采取替代方式(transplacement)。[1]英国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展现的就是替代方式。莱因哈德·本迪克斯认为,英国复杂的社会斗争经历了从断裂到再整合的过程,始终保持着很大程度的体制连续性。[2]汉南对历史上英国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赞赏有加:“英格兰的相对稳定带给其居民有长期保障的财产安全。因为国家的权威没有争议,政权也无颠覆之虞,百姓遇讼,乐于求诸法院,而不是私以武力相决。”[3]国内学者对于中世纪晚期英国抗争能够取得长效成果的研究最为杰出的是钱乘旦、陈晓律和侯建新三位先生。其中侯建新先生以主体权利为突破口,结合权利与法律保障的关系论证了英国农民的精神力量积累,为英国由中世纪晚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4]钱乘旦先生和陈晓律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联袂推出《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在“卷首语”中,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阐发了英国何以平稳走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英国发展道路”——追求自由平等的激进与稳重守成的保守融合相济。[5]笔者依据文献资料,通过个案分析,揣陋分析并总结出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抗争运动的突出特点,不当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市场化导向社会的确立是统领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的总体因素
1215年约翰王签署的《大宪章》对于英格兰的经济体制有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安茹王朝的国王们承前启后持续地强化中央王权,在客观上为建设统一市场奠定了制度保障。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派特别是米塞斯等学者把国家政府视为寻租和干扰市场自由运行的角色,但爱波斯坦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对维护经济发展,建立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中央集权可以削弱阻碍市场整合的各类因素,比如领主私自开设市集、领主的庄园司法特权。[6]另一方面,英格兰强化了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如何判断中世纪盛期特别是1215年《大宪章》签署以后的英国经济体制,以下三个要素可以参考:一是市场主体是不是多元且平等的,而非单一的王室垄断,或地方领主局部区域垄断;二是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三是交易价格是不是按照商品供需产生。中世纪西欧各王国的封建制度决定了它们的经济体制只能是习惯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从各级封君与其封臣之间乃至包括农民与他们的直接领主的经济来往来看,封臣对其封君的供赋基本上是固定额度,大体上都属于习惯性的,超过某个习惯规定的额度,就需要按照市场价格采买。在中世纪早期,买卖活动大概不够活跃,王室及其封臣几乎都是靠自己过活,领主经营自营地,农民耕作自己保有的份地。13世纪以后,特别是《大宪章》之后,随着王室和各级领主的消费增长,买卖活动日趋活跃,普通农户也逐步卷入日常买卖交换。英国农村很早就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7]当时英国的商品市场同样很开放。中世纪伦敦的谷物交易非常活跃,以至于私人谷仓都得按周出租。自1211年以来某一地区产出的丰歉不会影响小麦市场价格,自12世纪以来关于财产交易的记录就显示,英国的土地和房屋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自13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法庭案卷记录也表明,农民之间的土地市场交易很活跃,人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用地的买卖。[8]
增设市场反映出参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交易的频繁化。在1215年之前,地方领主只有获得王室特许状方可开设市场。[9]119《末日审判书》记载了最早由王室颁发特许状建立市场是索福克郡的罗格·比高德( Roger Bigod)的凯尔塞尔( Kelsale)市场和罗伯特·马尔特(Robert Malet)的艾耶(Eye)市场。在13世纪之前,王室很少颁发开设市场的特许状,在1066年到1154年间,王室颁发同类特许状总共只有19例,其中还有3例是伪造的。安茹王朝早期,依据王室特许状建立的市场寥寥可数。布里特耐尔的研究表明,“被授权的市场只占实际存在市场的很小比例”。王室的“特许状卷档”( the Roll of Charters)自1199年开始建立,表明授权建立市场的特许状正在增多,王室正式登记开始。[10]文献显示,1198—1483年间,英国王室大约授予了2800份市场特许状,其中超过一半是在13世纪前3/4阶段授予的;这些市场只有少数开设在城镇,多数开设在乡村。[9]119当然,地方领主为获取一份开设市场的特许状须向王室缴纳5马克的金钱。[11]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地方领主私设市场,因为开设市场一方面获利多多,另一方面,通过开设小市场,可吸引那些穷人和非农业人员来做营生,借此亦可展现领主对其依附农民的“慈爱”和“族长风范”(paternalism)。[12]
二、抗争诉求在体制内解决
中古以来英格兰佃农抗争目标之所以能够实现,首先在于他们的抗争是一种体制内的抗争。所谓体制,就是现存社会的根本组织结构及其所运行的规则和程序。S.N.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写道:
……我们强调了政治过程的竞争——“斗争”的方面。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就在同一过程之中,在各种群体之间也会产生某些共同的规范、某种程度的共识与一致意见。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和冲突的调节、处理适当规范的形成和制度化,自主的(亦即非政治性的)机制和政治性的、官僚制式的机制这二者,同时发展出来了。尽管这些不同类型的机制很不一样并且互相冲突,但它们又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规范的制订和精致化,以及这种通道的制度化,与政治斗争和政治过程、与统治者的政策直接联系起来了,并且成了它们的重要内容。[13]307-308
首先,农民抗争不以推翻中央王权为目标。在14世纪中期之前,农民直接负担中央王权的赋税较轻。正如当时有首民谣云:“赋税害得我们苦,就是没病也亡故,国王所得很有限,原来落入贪夫手。”[14]这种抗争目标是植根于英格兰社会对王权的认识观念中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即便是传说中的侠盗罗宾汉——他代表着当时社会中的反叛力量,都表现出对国王的忠诚与尊崇。在“罗宾汉事略”里,国王是以绿林好汉的朋友形象出现的:国王大嚼着好汉们偷来他自己的鹿肉,他最后还是这些好汉的恩人。[15]92即便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1381年起义,起义的农民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出过改朝换代的要求。不过,戴尔认为,起义者此举反映了他们直接颠覆领主权威的愿望,以谋求村社的独立和自治这样可实现的目标。[16]216,217,219相反,起义队伍对国王显示了更不寻常的信赖,这种信赖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之上。农民将自身的困苦皆归咎于除国王之外的其他廷臣。这种社会观念决定了农民抗争不可能演变成对中央王权大规模的对抗,同样中央王权也很少血腥报复抗争的农民,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内的抗争不可能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1381年起义失败后不久,中央王权对农民的镇压很快结束,而且后来处理那些起义的农民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非常有分寸的。大多数起义领袖和普通起义者都被赦免,甚至很多起义发起人不仅自己的家产未被褫夺,而且还“官”复原职,仍然身居乡村的某些职位。
其次,农民抗争不以否定地方权威为目标。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农民“要求在封建统治内的而非在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地位。他们并不完全排斥领主的权力,而愿意继续负担服役和缴纳赋税,但这些捐税的性质和程度应有严格的限制和确定性”。[17]424体制内的抗争就是基本上不触动中央王权与地方领主的政治架构,依照习惯法赋予自身的权利与领主抗争。等级社会的农民一般都接受等级特权的观念。对农奴阶层而言,他们直接的要求就是能够和自由农民享有同等的身份地位、同等的地租水平。对普通农民而言,他们只接受领主享有惯例赋予的特权,而且他们对自身的权利格外珍视。领主的特权是历史形成的。在9世纪至10世纪,农民对领主的要求是,保护比自由更为需要。[17]382但是领主对农民保护的重要性到11世纪和12世纪就显得次要了。[18]在日常抵抗斗争中,农民的抗争对象大多集中于王室和领主的官员们,农民特别憎恨那些官员们随意关押和敲诈开释费(extortion of money for release)[19]
复次,农民抗争坚守有限剥削的底线。农民反对领主超出惯例进行盘剥的特权。1381年农民起义期间,许多地方领主或其代理人遭到杀戮,财产遭到抢劫,正是领主过分盘剥农民的结果。起义领袖之一勃尔发出“当亚当耕种夏娃编织的时候,谁是上等人?”的呼吁,有个贵族听到这个呼声,发出绝望的感慨:“假令叛徒成功了……那末……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就都完了,英国将成为沙漠”。[15]116乡村农民接受领主特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领主的法庭上,领主将收取来的罚款据为己有,在农民的眼中,这是合情合理的。[20]他们对领主的要求只是有条件的接受。以1381年起义中农民对地租的要求为例,农民要求每英亩田地只缴纳4便士地租,“从前之价少于此数者,此后亦不得增加”。[15]126但是当自身已经享有的权利遭到威胁时,他们会毫不妥协,奋起抗争。既接受习惯法规定的领主特权,又坚持习惯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决定了英国农民的抗争是一种体制内的抗争。
英国农民抗争目标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权和地方治理结构,经济上坚守领主有限剥削的底线,因此,这是一种体制内的抗争。修订惯例是这个进程的核心,农民与领主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一种新记忆的开始。这其中统治阶级的妥协是抗争走向和解的必要条件。领主的妥协避免了新一轮的仇恨,由于领主的妥协退让,社会没有陷入复仇的循环之中。
庄园制的衰竭是农民与领主冲突双赢的结果。虽然英国农民抗争的对象都是一个个具体的领主,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庄园制,但是那些束缚在他们身上的诸多惯例实质上就构成了庄园制。诺斯指出:“庄园制的本质在于,在某种意义上,庄园主执行着政府的职能,只有当政府权力(不仅是政治影响)归属于贵族和封地时,我们才能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1]31从这个角度上讲,庄园制度的衰竭也就意味着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庄园制度的生成与早期封建制度的形成应该是一对孪生姊妹,甚至是一体的。出于安全需要,农民和领主形成投托关系,他们的行事规则基本处于习惯之下,各种习惯交织成一种“无为”的制度。那些五花八门的习惯既限制领主也限制农民。当然,对农民限制的比重应该更多于领主。到了中古晚期,庄园制的内外大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外部,整个社会较早期安全许多,因此农民对安全需求的迫切性大大降低;在内部,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不仅影响着普通大众,就连王室强制征取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对此时的农民而言,庄园制是窒息其经济活力的枷锁。受制于当时人们的觉悟和观念意识,他们不可能把自身的苦难归咎于庄园制,而是就事论事,于是在乡村社会,不时地会出现农民与领主斤斤计较的场面。长达数百年的抗争,农民在一庄一社的获胜案例表明,他们不断努力肢解侵蚀着庄园制度。农民抗争不在于废除或“改革”庄园制,而是导致庄园制绩效越来越低效。在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影响之下,随着工资和租金支付的劳动效率日渐胜过强制劳动的效率,欧洲大陆上的庄园制和农奴制(serfdom)从12世纪起便开始了衰落的过程。[22]到了中世纪晚期,庄园“不再是一个经济活动单位,而变成了一个收取地租和其他货币的体制”。[23]
放弃庄园制是中古晚期领主阶层主动而为的。庄园制的终结是以频繁的市场商品关系取代传统习惯经济而结束的。至于这些变革是否增进封建贵族的利益,内森·罗森堡和L.E.小伯泽尔说:“答案在两可之间”。他们转而又指出:“不过,这些变革并非孤立发生,放之于更大的历史背景,我们或许会得到更明确的答案。这些变革出现于欧洲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时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显然会促进土地实际价值的提高,这有利于封建贵族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出现在欧洲城市化过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上层阶级如果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活动没有任何联系,将注定走向衰落。”[21]80在庄园绩效衰败中,鲜有领主家道中落者,倒是有许多领主积极卷入社会转型的洪流中,他们其中的很多人参与地方市政管理——毫无疑问,中央王廷的官员们是大贵族充任的,如领主亚当地产广袤,一度担任过林肯市长。[24]实际上,更多的领主在失去领主权后,并没有丧失对财富的进取心,而是以私人协议或以议会立法,同一个又一个地主交换地块,形成了一个个连成一大片的大地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耕作效率。[25]81那些领主不仅在自身阶层之间进行交易,而且与富裕起来的农民(乡绅)也有频繁的交易。15世纪的英国观察家对于欧洲大陆上的领主与农民缺乏交往感到非常不解。[25]86中世纪晚期到近代前期,英国领主贵族们放弃直接经营自营地以后并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他们并没有坐吃山空,而是将积累下来的资金投资于采矿、运河及道路等事业。[25]96
三、为承认而斗争
承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学者霍耐特提出来的,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内涵框架基本得以完成。在该著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中,霍氏总结了社会冲突不外乎有两种模式,一是为自我保护而斗争,一是为承认而斗争。[26]前一种模式表明,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消极的个人自由权利,简言之,就是别人不要妨碍我的自由权利;后一种模式,就是要争取积极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在获得前一种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声索一种更积极的、按原有习惯规定所没有的权利。目前我国学界对“承认理论”的认识理解尚待进一步求索,然而,它的分析框架无疑对探究英国农民抗争的特点具有启发意义。
那么,英国农民要求领主承认什么呢?承认已存的“非法”事实,即英国农民争取的是承认尚处于“非法”的权利。进一步讲,农民所争取的权利是既有事实,只不过这种事实被领主看作是非法的,这种事实在时间上已有一定的久远性,往往是领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违反事实的无奈默许。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民多为理想甚至是空想而斗争。一言以蔽之,一个是为承认而斗争,一个是为理想而斗争。这就是二者的差别,这种差别往往也决定了斗争的剧烈程度。
社会冲突理论家科塞认为,冲突越是围绕着现实问题发生,则其激烈性越小;越是围绕非现实问题发生,情感介入越多,冲突就越为激烈。[27]农民要求领主承认他们已经获得但尚未获得法律保障的权利。中古英格兰农民对领主的抗争,不是要建立什么大同社会,而是都与自己的身份、与自己的生产生活非常紧密的事务,租役问题是直接关乎自己的生产生活。这种抗争,目标是现实可触摸的,绝对可以激发农民为之抗争的激情。因为一旦成功,立刻就能在自己的生活方面彰显其效果。“权利的观念暗示着对其他个体的承认”,[28]30“未经承认的自由哪有价值,未经认可的权利又所值几何?”[28]48-49“自由或权利的内涵中一定包括彼此的承认。” 圭多·德·拉吉罗多次重申“承认”在西方民众追求自由与权利中的地位与影响。[28]1承认的前提就是此前已经形成的事实,只不过在习惯法上还未予以认可,尚处于“非法状态”。这也昭示着抗争目标的可实现性。也就是说,农民如此抗争是要让领主承认现状——农民可能早已不履行劳役,可能早已抛开庄园法庭的登记而转让土地,可能早已不经领主的同意而出嫁女儿等等那些早已荒废的规定了。同样,1381年起义中农民要求乡村自治的愿望,在戴尔看来,这是一种在国王直接权威之下的村社自治的理想,并不完全是不合实际的。因为乡村自治的组织机构已经存在于乡村,而且在没有领主和律师(lawyer)参与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发挥其功能。[29]
农民抗争运动在观念和实践上又产生了一个悖论,即如何理解农民的守法与“非法”要求。遵守习惯法是全社会的共识,那么农民的那些“非法”行为又是怎样转变为合法要求的呢?在18世纪前的法律观念世界中,自然法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自然法的内核就是正义,如果惯例不正义,那么惯例就是非法的。当然,这需要时间。惯例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可能因某些情势而作出调整。实际上,在中世纪庄园法庭的司法实践中,庄园法庭往往不是“依法(习惯法)”裁决的,而是按照自然法的正义原则,在当事者之间进行调节协商谈判达成协议的。如苏顿(Sutton)的亚当(Adam)拥有1威尔盖特(30英亩)地,死后留给老伴和两个儿子。老伴玛蒂尔达(Matilda)到法庭上要求小儿子罗伯特(Robert)遵守当时的习惯。佃户陪审团却要求继承惯例对长子继承制作出改变,由于缴纳了40先令的罚款,这个改变的惯例就被通过。玛蒂尔达被告知让他的长子威廉下次到庭。这个案例说明,某些案件有时候可能因缴纳一笔罚款,就可以使一项惯例以新的内容确立。这个案件大概会让以权利为取向的现代法学家大为惊骇,亚当的财产原本应该由罗伯特继承,而法庭竟然剥夺了罗伯特的此项权利。博尼菲尔德(Bonfield)的研究表明,在庄园法庭上,这类争端解决的方式更多地是妥协折衷而不是判决。[30]533又如,沃切斯特(Worcester)主教地产的收入来自17个庄园,它们位于沃切斯特郡(Worcester)、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沃威克郡(Warwickshire)。由于农民的抵制,许多惯例几乎为具文。1444年约翰·卡朋特(JohnCarpenter)任主教时期 ,其承认费(recognition)从1433年开始即受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460年仍然没有支付,后来就干脆放弃了征收的企图。普通罚款CommonFines(英国首要的款项)与领主的司法特权结合在一起被列入到法庭案卷中。如同过户费一样,这个普通罚款也是一笔数额不菲的现金,通常是几先令,按每十户集体收缴,由于这项罚款在1302—1303年整个地产中有17镑,看来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欠款一栏里有一句清晰表达的惯用语:“因为农民拒绝支付。”[31]11-33在受“正义”精神支配的自然法观念推动下,普通人也逐渐认识到那些被盘剥的惯例是“不义”的,虽然在领主阶级看来,农民的那些抵制行为和赖账是“非法”的,但在农民不断抵抗中,那些倾向领主利益的习惯仅仅只是习惯而已。时移势易,人们甚至认为那些被盘剥的习惯没有依据,当然彼时的人们是以忘记或不承认的做法来回应的,这也昭示着抗争目标的可实现性。
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领主与农民双方均展现了灵活的妥协性,双方所妥协的结果体现在惯例的修订内容上,惯例被时人视为法律,也就是说,农民争取到的权利凝结在惯例中,权利即得到法律保障。相互妥协的英国民族品格奠定于1215年的《大宪章》,其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个让步”。[32]农民与领主在化解冲突中同样能够展现出灵活的妥协性。“自由或权利的内涵中一定包括彼此的承认,这又暗示着必然存在特定的相互交往。”[28]1罗德尼·希尔顿发现,早在 10 世纪,诺曼底的村庄就从地区集会中选举代表参加农民大会,此外,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以下做法,即农民与村社管理机构之间就劳务、捐税和权利事项进行谈判。[33]农民要求“公平”地租,而不是否定所有地租,他们只是抱怨和拒绝支付过高的以及与奴役性身份相联系的地租捐税,对于领主的司法权则是承认并接受的。
在14世纪中叶之前的“地租斗争”中,通常领主获胜,但在14世纪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农民能够通过谈判而加强自身地位时,暴力抗争就没有必要。斗争导致的地租水平下降,农民阶层的资本积累也就成为可能。在哈特菲尔德(Hatfield)主教的地产上,一部分农民拒绝接受高过现有的每英亩1先令的地租,领主不得不退步,以免他的土地无法出租而导致撂荒。1355年,主教允许基乐比(Killerby)的租户们继续持有“1便士农场”(Pennyfarm),持有前提是:这样的条件必须保密,不能让其他农民知晓。[34]3016世纪的一部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领主对农民的看法:“这帮群氓太富有了……他们懂得没有顺从,没有法律,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乡绅。……他们给我们指定应得的地租。”[31]11-33雅克·巴尔赞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意味着没有通过贸易培养而成的自制力和妥协的习惯。”[35]正如兰德斯所说,欧洲统治者和力图有所作为的领主为寻求增加税收,不得不利用参政权、自由权和特权——简言之,讨价还价——以吸引参与者。他们必须说服人们参加纳税人的行列。而且,免除物质负担和赋予经济特权,常常导致政治让步和自治。在这里,创造性来自下面,这恰是欧洲模式的本质特征。其中暗含的是权利和契约意识——谈判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自由与经济活动安全的获得。[36]
有妥协方可达成契约。1280年,波顿修道院长声称他的那些维兰除了肚皮以外,一无所有。那些维兰对此予以否认。修道院院长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耕牛,还强迫维兰们缴纳塔利税和林地放猪税,并强迫他们承认维兰身份。维兰们团结起来抵制住了修道院长的要求。[37]237最后,这位修道院长众怒难犯,只得收回成命。1374年,一个农奴与托马斯伯爵通过谈判承租了伯爵的庄园,条件是前两年免掉6英镑,以后他每年才缴纳2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租金。[38]14世纪时,乡村农民抵制劳役的抗争随处可见。如在弗里克斯顿(位于萨福克郡)的农民罗伯特·博雷尔否认他的农奴身份,就被指控“忘恩负义”,触犯了一系列罪状:未经许可就结婚,并且拒交一个羊羔和废弃他的房屋。弗里克斯顿修道院庄园的女院长在1377年召开特别法庭,由修女们和阿尔德比(位于诺福克郡)修道院院长、管家和其他世俗官员组成。他们与博雷尔达成一个“协议”。博雷尔承认自己是农奴身份,在“没有受到强迫”的条件下宣誓予以认定,并且同意遵守原来的习惯,遵守婚姻管理规定,重建他的房屋。他必须找到保证人,保证人必须亲眼看见他履行他的义务,若保证人作伪证的话,每人就要受到5镑之罚。“协议”一方的女修道院长则豁免他的总计达53先令4 1/2便士的罚款。[16]210本案中,在接受领主大部分要求之下,博雷尔也至少被免除了50余先令的罚款。1379年,伍斯特修道院领地的一个庄园上的农奴集体拒服劳役,修道院长扣押了他们的牲畜等财物,以示惩罚。但这帮农民仍不屈服。1381年,在《迈尔恩德纲领》取消农奴制的消息传来后,他们坚定了拒服劳役的决心,而且还打算暴动,吓得修道院长取消了外出参加宗教会议的行程。1381年农民起义失败后,这里的农民仍然坚持斗争。1385年,再次发生了农奴拒服劳役的事件,修道院长以扣押农奴牲畜来威胁农奴,但苦于“帮凶”不够而无法付诸行动。1386年,格洛斯特修道院罗姆斯莱村的农民,在两个维兰的领导下,拒绝向修道院长宣誓效忠,并且声称他们不再是修道院长的农奴。双方冲突自头年10月持续到次年3月,到复活节时,其中一个领袖被捕死于狱中,另一个领袖失踪,冲突才告结束。15世纪时,英国切尔特纳及其附近五个村的约120个农民(大多数都保有半份地)要求女修道院长降低他们的货币地租。这些由劳役折合成的货币租共计107镑7 1/4便士。从1445年起农民拒绝交纳这笔地租,从1451年起到次年,双方开始谈判。后来修道院长又请了领主及其扈从前来“仲裁” ,协商的最终结果是农民的租额从10镑7 1/4便士降到6镑13先令4便士。[37]54-73
四、结 语
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社会,农民抗争活动是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结局多为失败,即便成功也往往沦为王朝循环。13世纪初期特别是1215年《大宪章》签署之后,英国从习惯经济和命令经济融合的体制中发展出市场化导向的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不仅培育出国民的谈判协商和契约精神,而且尽可能地以市场方式化解社会冲突。这种社会体制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抗争的趋势。英国农民抗争不以推翻中央王权和地方治理结构为目标,坚守有限剥削底线,要求领主阶层承认他们既存的“非法”事实,英国社会没有像其他地区动辄爆发出阶级大搏斗的震荡局面。英国农民以体制内的途径和方式解决他们最为现实的问题。这正是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抗争行进着一条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轨道之所在。古代不同地区农民抗争运动所处的社会体制背景及其抗争特点不同,决定了这些抗争的不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