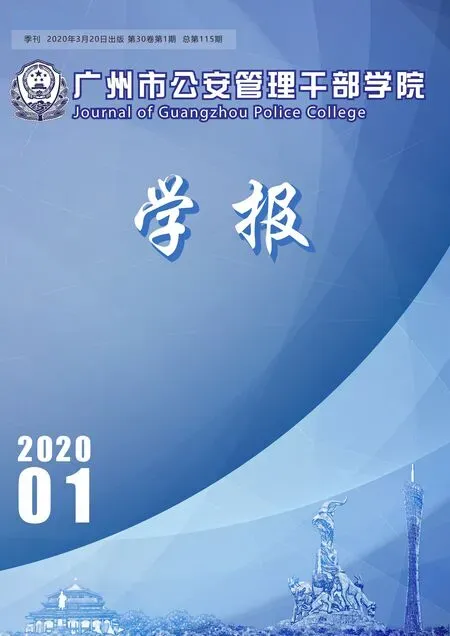浅析盗窃案件的取证思路
张豫辰
盗窃案件证据的提取和固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中仍有些许不足之处,或疏漏某些关键证据的提取,或盲目的收集证据造成效率的低下。因此,有必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盗窃案件的取证体系,从而优化警务资源配置,提高盗窃案件的办案效率。首先是对盗窃案件有个整体的认识,由现阶段盗窃案件犯罪分子作案的特点入手,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盗窃案件证据链所需的各个部分。
一、盗窃案件概述
(一)盗窃案件的概念
盗窃案件,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一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犯罪案件。秘密盗窃,是指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该财产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经营人而占有该财产的行为。一般盗窃案件需要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入户盗窃、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是行为犯,只要存在上述四种行为即可直接认定为盗窃。[1]由于盗窃案件的数量大、侵害范围广,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较大,因此,做好盗窃案件的取证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盗窃案件的几种常见表现形式
1.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内容。具体来说,入户盗窃是指行为人进入居民日常生活的住所实施盗窃的犯罪行为。由于入户盗窃属于行为犯,因此,只要证明存在盗窃行为即构成盗窃罪,无需证明盗窃数额的数目。其中,“户”是指能供他人家庭生活居住的且与外界相对隔离封闭空间,常见的“户”包括牧区人民居住的帐篷、封闭的农户院落、租住的房屋、渔民当做房屋长期居住的渔船等,但不包括公共场所。比较特殊的是,集经营和生活一体的处所,只有在生活期间可视为“户”,在生产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能视为“户”如白天作为商店,晚上用来居住的房屋。此外,入户盗窃不同于入室盗窃,实践中应当注意辨别和区分。侦查阶段将“入户” 归在“入室”,是因为在客观方面犯罪分子实施盗窃的地点均为封闭场所,在侦查手段和侦查方法上具有共性。[2]
2.扒窃
扒窃是指盗窃他人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携带的财产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进行了限定和扩张。扒窃侵害的不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还有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公共场所是指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开放,满足公民对社会活动需求的场所,如商业广场、公园、图书馆等。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向公众开放的场所可视为此类活动期间的公共场所。携带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实际的统治或占有,包括受害者带来的身体和附着在身体上但放在受害者身边的身体,并且可以被身体直接接触和检查。
3.携带凶器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内容。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进行盗窃时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可用于实施暴力或形成暴力威胁的器具。如果盗窃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使用上述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胁则直接构成抢劫罪;如果在盗窃结束后为逃离现场或拘捕而使用上述凶器则转化为抢劫罪。
二、盗窃案件的特点
(一)现场一般留有明显的翻动或暴力破坏的痕迹
盗窃犯罪分子进入现场的手段多为破(撬)门(窗)、拧锁等,一般都会改变或破坏现场的原有状态,为了搜寻财物又多会撬砸锁柜、抽屉等,在相应位置上会留下指纹、撬痕和翻痕。[3]有时犯罪嫌疑人慌乱之中会将犯罪工具和随身物品遗留、丢弃在现场或附近区域,有的犯罪嫌疑人为图方便将现场的合适工具带走以备下次作案使用,还有的由于疏忽或无反侦查意识会留下指纹或DNA 等微量物证。这些痕迹会反映出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个人特征,甚至是地缘特征。除扒窃案件外,绝大多数的盗窃案件的现场都留有较明显的痕迹、物证。
(二)盗窃方式、手段多带有习惯性
在司法实践中,盗窃犯往往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某些地区擅长攀爬入室,某些地区擅长暴力破门入室。往往为流窜作案,并且实施多起。盗窃犯罪分子在长期、多次盗窃过程中不断的积累经验,完善作案手法,最终形成成熟、固定、具有特定的作案手法。这种较为稳定的作案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盗窃目标、时间具有相似性;二是盗窃手法、盗窃工具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三是潜入、逃离现场的方式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等等。[4]
(三)有团伙作案的趋势
时代的发展,盗窃案件的犯罪分子的反侦察意识也在不断地提高。为了降低暴露的风险,提高得手的成功率,犯罪分子现阶段往往进行多人协同作案,事前踩点人员与作案人不同,现场作案人与场外盯梢人相互配合,既提高效率又利于赃物的快速转移。
(四)流窜作案形式日益明显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便民设施逐渐完善,多样性的交通方式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为盗窃犯罪分子流窜作案提供了条件。在一地实施几起盗窃案件后转移战场,使自身行踪不易被侦查机关掌握,大大加深了破案难度。因此,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多采取流窜作案方式。
(五)犯罪行为具有隐秘性
盗窃案件类型繁多,盗窃手段方式多种多样。但是,“秘密窃取”都是盗窃犯罪的重要行为特征,也是盗窃案件的基本方式。因此,绝大部分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没有正面接触,少部分案件虽然有正面接触,但都是嫌疑人乘被害人不知情的状况下盗走其钱财或物品。等被害人发觉被盗时,犯罪嫌疑人早已逃之夭夭。盗窃犯罪的这一特点,使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很难找到目击证人,这就给打击盗窃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盗窃案件的取证思路
盗窃案件的证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架构,分别是案发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及其鉴定意见、辨认笔录、客观记录犯罪某一阶段过程的现场周边的视频监控资料、收赃人的供述(或证言)及其辨认笔录、赃物及其价格鉴定意见、作案工具及对其辨认、鉴定等材料、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及其辨认笔录。侦查人员在此类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一方面,要有保全证据和尽可能将相关证据链条收集完备的意识;另一方面,对于收集到的所有证据通过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以协助侦查行为。[5]
(一)及时勘验、检查现场,获取痕迹、物证[6]
1.制作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
如现场方位、概貌图,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相、物证照相,现场勘验检查情况分析报告等。
2.提取遗留物品
如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遗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犯罪嫌疑人穿戴过的手套,犯罪嫌疑人携带物品的附着物等。
3.提取痕迹物证
重点有房屋或其他封闭空间出入口的指纹,犯罪嫌疑人可能接触过得物品上的指纹,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经过的地面、踩过的物品上的足迹,锁、防盗门等钳剪、撬压、拧打痕迹,室内衣柜、抽屉上撬压痕,车辆轮胎痕迹等。
4.生物物证提取
如疑为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烟头、口香糖,疑为犯罪嫌疑人擦拭过的纸巾,疑为犯罪嫌疑人饮用过的水杯、饮料瓶,现场遗留的血迹、绷带等。
5.调取、复制周围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法定证据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防范意识的提高,各城市公共场所基本实现视频监控覆盖,甚至有的农村地区也开始建设视频监控工程。对于发生设有视频监控设备场所的盗窃案件,如商场、银行等,侦查人员可依法向相关场所管理部门调取或复制案发时段的视频资料。盗窃现场的录像资料完整记录了嫌疑人作案的过程,属于直接证据,可以大大缩短破案时间,为及时寻找和控制嫌疑人提供支持。相关现场的录像资料串联还可以为调查嫌疑人进入现场途径和离开、逃跑路径提供侦查思路。视频中提取的嫌疑人的照片结合天网工程可直接搜索出嫌疑人的详细信息。
(二)深入调查访问,获取犯罪线索
1.访问的主要对象
发现人、报案人;被害人及其家属;首先到达现场的公安民警;被害企事业单位财产的所有者和保管者;现场附近及犯罪嫌疑人来去路线沿途的知情人。
2.调查访问的主要内容
(1)被盗财物的存放及日常保管情况,如被盗财物平时置于何处,何人负责保管;日常保管的方法以及是否有相应的交换班制度等。如果是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还要了解财物的保管、交接制度,存放处日常保卫工作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2)被盗物品的特征主要包括被盗物品的体积、数量、样式、品牌、型号等方面的内容,特别要了解被盗物品具有哪些细微特征,足以与其他物品区分开,如特殊的划痕、特殊标记等。如果是特别贵重的物品,如纪念币、古董等,则最好能够提供相应的信誉卡、照片以及收藏证书等。
(3)被盗现场的原始状态。对被盗现场在盗窃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的具体情况进行访问,了解在盗窃发生之前,现场各种物品的摆放情况、人员的活动情况等,特别是一些陈旧的痕迹物证,需要了解案发之前有没有存在,什么时候存在的;有无报警系统及其工作运转情况等。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通过与勘查现场时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从中发现案发现场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进而来分析、判断犯罪分子在现场中的详细犯罪活动过程和具体行为。
(4)发现被盗的经过。大多数盗窃案件,都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发现的,而人们在发现被盗时,往往是先进入现场进行一定的查看和清点,进而才决定是否进行报案。因此在调查访问中,要尽可能的询问发现被盗的具体经过,包括何时发现被盗、如何发现被盗的,发现被盗后有何人进入过现场、到过哪些地方、触动过哪些物品等。
(5)案发前后的可疑情况。着重了解在被盗前后,有无无关人员在现场附近逗留、窥视等,有无人员特意打听财物存放情况、有无反常迹象;如果是企事业单位被盗,还要了解哪些人对被盗财物熟悉、熟悉的程度、有无怀疑的对象及怀疑的根据等,案发前后有无发现可疑的人,其体貌特征如何,与本单位内部哪些人员有接触等。
此外,应当尽力查找现场目击证人。在现场及周边寻找目击证人,问明所见到的详细情况,并留下证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方便日后取证;同时,还应当及时调取声像资料,如监控录像,目击者拍摄的作案过程录像,并开展模拟画像工作,如根据事主口述画像,目击者口述画像等。
(三)全面分析案情,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
根据现场调查和考察情况,确定考察方向和范围。
1.内盗外盗分析
主要通过作案时间的选择,出入口是否明显,有无破坏痕迹,现场是否翻动和被盗财物是否准确,作案手法的习惯性,技术性和遗留痕迹来分析。要注意分析发现内外勾结作案。
2.惯偶犯分析
惯犯有长期积累的经验,作案时沉着老练,作案技术高,一般带有习惯性动作,盗窃得手后常伪装现场,破坏和销毁现场痕迹物证,以逃避侦查。偶犯作案缺乏经验,胆小,作案计划周密,但临场常会紧张、慌乱,盗窃手法和技术不高,在破坏障碍中易出现多余和重复动作,不敢久留,有些财物甚至都来不及拿走。要注意少数心理素质好的偶犯,也可以做到手法熟练和胆大心细。
3.本地人和流窜作案分析
根据现场遗留物进行分析,判断是外地还是本地产品;从被盗盗窃的财物分析,看被盗是较为笨重、难以变现的财物还是只盗窃现金或金银首饰等体积小、易携带的贵重物品。此外,有交通工具装运所盗财物逃离现场的多是本地人作案;从串并案来分析,如果并案的几起案件发生在不同的多个地区,则多为流窜作案,如果都发生在范围不大的同一地区,则多为本地人做案;从作案地点看,本地人由于对当地熟悉,一般选择隐蔽的地点,不易被人发现,流窜作案一般选择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等方便转移的场所;从作案手段和过程分析,本地人作案则多有伪装现场或清扫现场痕迹物证,流窜作案破坏程度一般较大,不在乎留下痕迹物证。
结语
盗窃案件作为一种在我国多发的刑事案件,不论是对民众的物质还是精神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治理盗窃案件是为了更好的预防盗窃案件的发生,这就需要使盗窃案件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收的制裁,这就离不开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来服务于审查起诉。为了使盗窃案件证据链条更加牢固,就要求我们树立一套清晰的取证思路,从而严密刑事法网,使盗窃案件的犯罪分子不敢犯、不能犯。当然,本文虽提出了一种取证思路,但仍需不断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它应该建立在对其基本原理和运作方式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逐渐成为一种能够有效发挥系统效应的“生命有机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