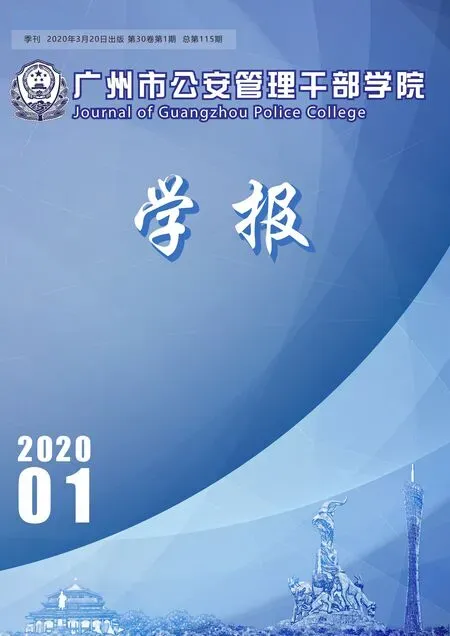新时代背景下社区警务探索新路径
王麒睿
社区警务诞生于第四次警务革命。自2002年3月中国公安部正式提出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各地区对社区警务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如火如荼。其中,涌现了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典型治理模式。然,新时代背景对社区警务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生活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新兴科技如互联网、大数据等要求社区警务工作的开展需与时俱进。新时代背景下,社区警务的探索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新时代对社区警务的新要求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追求“美好生活”作为社区警务出发点,社区警务的开展要注重人民的主观感受。无论是治安防控还是提供服务,其出发点都是为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归属感。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作为社区警务落脚点,社区警务的开展要因地制宜,如城乡结合部与外来人口流动频繁社区警务开展的侧重应有差异,实现差异化社区警务模式。
(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应秉持此理念开展警务活动。“共建”要求打破传统仅以公安为主导的社区警务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堡垒作用,破除部门之间的壁垒,共建社区合力。具体如:将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警务实现双向融合。“共治”要求社区警务的主体不只是社区民警、派出所,而是形成多元共治机制,如引入居委会、居民、志愿者、社会公益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社区。“共享”要求社区警务的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三)新兴科技的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不断涌现。社区警务的开展需跳出传统模式,借助新兴科技之力升级社区警务模式,更好的实现“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社区警务宗旨。例如,传统社区居民信息以纸质版收集保存,不易查阅不易久存。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居民信息的收集更全面、利用更便捷、保存更方便。新兴科技将会让社区警务的开展迈上新台阶。但,新兴科技不能完全替代社区民警开展社区走访等具体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还需社区民警与辅警、居民等形成合力,而不是以冰冷的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二、钳制:社区警务发展的阻力
(一)社区警力在质与量双维度上有待提升
从数量维度看,社区警力不足。第一,“由于公安机关层级较多编制有限,机关占据了大量的编制,加之空挂、长期借调等原因,派出所的警力较少,民警在岗率不高”[1];第二,目前各社区基本实现一个社区配备一名社区民警。社区民警在处理社区警务时还要承担派出所值班接出警、巡逻防控、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任务,占据社区民警在社区工作的时间,难以保证社区工作的全面、高效、高质量开展;[2]第三,社区警员的晋升机制、福利机制、工作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客观因素影响社会新力量加入社区警务队伍,担任社区民警的后备力量热情不高。
从质量维度看,社区民警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第一,社区民警的年龄结构不合理。社区民警年龄偏大,其工作热情和接受并运用新科技的能力不足;第二,对社区民警的培训欠缺针对性。实践中,“对社区民警与其他警种的民警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培训”[3],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较少,社区民警仅能通过工作实践的方式积累经验。此种经验积累方式对岗位的固定性要求较高,且不利于社区警务工作短期内取得实效,更不能实现社区警务的与时俱进;第三,社区民警还需提升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矛盾调节能力、群众组织能力。在科技提升工作效率的情况下,社区民警的工作重心更应侧重深入社区、入户走访、调解纠纷等依赖民警主观能动性的工作。
(二)基础设施配备不齐全
在社区警务室设立问题上,目前各地已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但有社区基于党建角度将社区民警与社区党务工作人员合室办公,没有设立独立的警务室。这一做法有待商榷,易产生“社会群众治安信息反馈渠道闭塞找不到反馈信息的单位、找不到社区民警的弊病”[4]。除此,已设立的社区警务室存在面积狭小、硬件设施不足及简陋等问题,如盾牌、警棍、钢叉等警械配置率较低。部分驻村农村警务室基于地理限制,使社区民警深入社区存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的阻碍。[5]
(三)考核机制失灵
我国社区民警绩效考核常以出警率、立案率、破案率、逮捕率等的降低为硬性量化指标。然而,社区警务重在预防犯罪,对犯罪的预防工作、降低犯罪危害程度工作等都无法计入硬性量化指标。例如:“社区警察通过努力将由于海洛因成瘾而持刀抢劫的罪犯改变为仅吸食少量大麻的社会闲散人员,”这可以被视为社区警务工作的“成功”,但是却无法计入考核标准。[6]以此观之,预防性工作便丧失了激励机制;其次,基于社区警务的差异化供给,不同社区的治理方法、管理难度差别较大,以统一的绩效指标评价社区民警的工作水平显失公平;最后,实践中有社区创造性地提出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标准。这一考核机制是对传统考核机制的突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需引起重视。如:居民满意度为主观感受,不同居民因文化水平、社会地位、世界观等不同而对社区民警工作的认可度不同,因此难以量化的标准很难具有说服力。除此,居民满意度测评时是否要采用回避机制、由何种主体主持测评更具有公平性、如何避免测评过程弄虚作假等问题都对新考核机制提出了挑战。
(四)公民对社区警务认同感不强
社区警务的定位是服务型警务而非管理型警务。其虽然发挥了预防犯罪、维护治安环境的作用,但实质上要树立服务意识,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然而,实践中公民对社区警务认同感不强,一方面是基于部分民警把社区警务落实为在社区中开展警务,走入了“社区+警务”的误区,把“社区警务室”变成了派出所的“派出所”。[7]这样的社区警务工作仅浮于表面,欠缺实质功能;另一方面在于民警深入社区、入户走访频率低。社区民警由于承担较多非警务职能,分散警力,深入社区时间有限。社区居民基于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以及“陌生化”的邻里居住关系无主动沟通的积极性。因此社区民警与社区居民之间欠缺沟通机制,社区居民对社区警务的开展认同感较低。
(五)社区防控机制有待完善
新时代背景下,社区防控要从“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持续发力。第一,现有“人防”中警力不足。单纯依靠社区民警之力难以形成有效的“人防”,社区防控需汇聚辅警、保安、网格管理员、楼长等共同力量;第二,“物防”设备不齐全。“物防”设备具体如智能门禁、对讲门、火灾报警系统、防攀刺、防拉栓等,现有“物防”未能因地制宜地利用已有科技产品;第三,“技防”落后。现有防控机制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在信息电子采集、信息共享平台搭建、治安危险预警、社区舆情监控等方面仍有空白。
三、突围:社区警务发展新路径
(一)社区民警队伍内部建设
社区民警队伍建设要着力解决四大难题:警力不足、素质较低、设施简陋、考核失灵。解决内部建设问题是开展其他社区警务工作的基础与前提。
1.充足社区警力。增加社区民警的数量、实现警力下沉并非充足社区警力的唯一方法,多元一体、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日益受到实务推崇。实践中,部分社区提出“1+3+N”的专群联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对原有公安系统的人力资源调动影响较小,也利于缓解公安各级警力不足问题。提倡“1+3+N”模式首先要发挥社区民警的领导作用,其次要着重挖掘社会力量,不断扩大“N”的范围形成群防群治局面。例如:推动律师法律援助进社区、志愿者活动进社区、心理辅导员等,重在融入社会力量。
2.提升社区民警素质。一方面,要增强社区民警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矛盾调节能力、群众组织能力,充分发挥社区民警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要增强社区民警学习、应用新兴科技的能力。例如应用大数据进行社区危险性研判、个人信息数据采集、分类、检索等。除社区民警自身努力外,公安分局也要提供保障机制。首先要尽量保证社区民警工作的稳定性,减少无必要性的岗位调动;其次,要具有针对性的对社区民警进行培训,推广实践中的典型治理模式供社区民警学习,增加社区民警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最后,建立好社区民警衔接机制,以经验丰富的社区民警带领、指导年轻新上岗的社区民警,形成社区民警间“传、帮、带”的习惯,避免因人事调动导致社区工作断层甚至工作水平倒退的不利后果。
3.完善基础设施。社区警务室作为社区警务的核心,首先要有独立的办公空间,相应的办公设施如办公桌等务必配齐;其次,相应的警械器具如盾牌、警棍、钢叉等应按警务人员数量配备齐全;最后,支持社区警务室引入科技产品,如视频监控、摄像头等,把社区警务室打造成信息站、服务站。完善基础设施既是为社区民警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后盾,也是让社区居民求助有门、乐于求助,形成社区警民间良性互动。
4.革新考核机制。相较于传统的硬性量化指标,新考核机制应采取弹性考核、综合考核体制。首先,要制定新的《社区警务考核办法》,让激励办法更加明确、具体,发挥引领促进作用;其次,建立“分局+社区+群众”的三方考评体系,必要时可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估组织运用大数据客观做出评价;再次,延长考核周期。基于社区警务投入大、见效慢的特点,考核周期长度应适宜,例如实务中部分地区以一年为考核周期;最后,建立定性、定量双重指标。一方面,社区警务中用于审核评估的公报既要有符合社区特点的定性指标,又要包含看得见摸得着的定量指标,以便于不同社区间工作量的对比;另一方面,在考核内容上应当综合评估各单项工作的绩效后根据定性的指标进行评价。例如,无论社区民警在特定考核周期内的单项工作绩效何如,都要参考定性指标如居民满意度来做综合性评估。[8]
(二)以民为本,服务意识建设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区民警的定位应是“社区工作服务者”而非“社区工作管理者”。服务意识可从以下角度构建:第一,警务工作前置,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9],力争实现“让数据多跑,居民少跑”的目的。将警务办理事项前置到社区警务室,在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增进了社区民警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利于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警务的认可度;第二,推行“错时工作制”[10],使社区民警的部分工作时间与居民下班时间重叠,提高社区民警入户走访率,为社区民警与社区居民的双向沟通提供时间保障;第三,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方式。通过线上社区警务平台的搭建,实现信息采集、服务回访、群众沟通、宣传教育等简单基础性工作,针对复杂问题,仍需采取线下传统方式深入社区予以解决。
(三)科技支撑,防控体系建设
社区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需依靠“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来提质增效。基础信息的采集是防控体系建设的根基,在居民信息基础上的分析研判则是对传统社区警务的延伸和发展。
规范基础信息的采集首先要注重全面性,全面性要求采集的信息在质量上真实,在数量上广泛。其次,要提高数据的精准性。即及时更新居民信息,保证已收集到的信息的可用性;最后,要增强数据的可用性。[11]即通过分类建档的方法整理归类并存储备用,“打破数据提取难、传输难和共享难的局面”[12]。在基础信息的采集方式上,要将普通电子采集和自动化数据采集相结合。自动化数据采集如监控视频、智能门禁、电子围栏、WIFI 围栏等,[13]搭建高效精准的数据采集平台。
在搭建起精准有效的基础信息数据库的前提下,社区民警需对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预测探究辖区内风险地域、风险时段、风险人员等要素的空间分布”[14],从而可以有针对性的部署警力、开展社区警务工作。让社区警务向预防型、预测型警务转变,实现社区警务工作有的放矢。实践中,泸州市的“多功能楼栋门禁系统”便是在智能采集信息基础上做出的预测性研判,值得各地学习与推广。泸州市公安局在社区居民楼安装智能门禁系统,社区民警利用该系统可以精准掌握社区内流动人口和特殊人口信息,并在后台进行标注,“系统会对标注房屋水电异常、标注人群出入楼栋异常情况自动报警”[15]。此种新型智慧警务便是以新兴科技为支撑的具有创新性的治理典范。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的转变都对社区警务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固步自封,只会让社区警务与时代脱轨、与人民脱轨。与时俱进,从理念上革新、从技术上更新、从模式上创新才是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社区警务的新路径。新时代背景下,社区警务要从组建多元体制“人防”、完善基础“物防”、革新运用新兴“技防”,创造出社区警务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