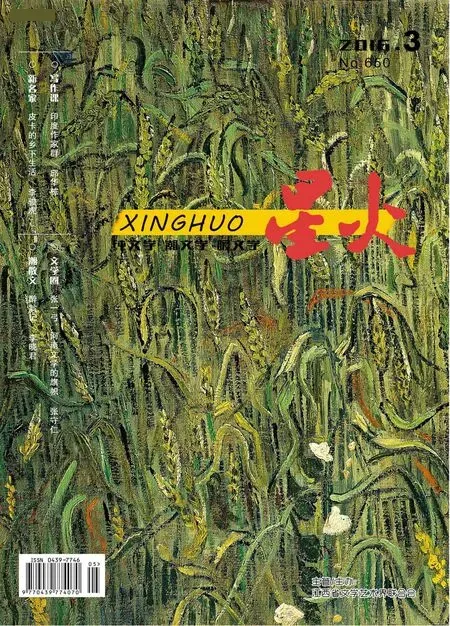清明雨迟
郭林强
太阳自从早上打了个照面之后,再也没有出来过。站在地面往上看去,只是隐隐约约能在布满云的天空上,看到一个竹筛般大小的光晕。云昏暗得发青,浓一块,淡一块的,乍一看,还以为是一片深浅不一的秧田,想伸手去挂平,却又触不到。
对岸一片片的油菜,都开着灿灿的小黄花。种得早的油菜,上面已经结了不少菜籽葫芦,菜籽葫芦吊在油菜秆上,可爱得很。晚上聚集在油菜上的露珠还没有散去,黏在油菜叶子的毛绒之间、褶皱里头,就好像只要太阳不出来,油菜地里,就一直是早晨。若是有个爱瞎跑的孩子出现在油菜地里,一株一株的油菜准会被他弄得摇摇晃晃起来。这一摇晃,油菜上的露水一下子就变得活跃起来,汇聚,加重,从叶片上滑落下来,一半落到了地上,一半落到了孩子的身上。落到衣服上的露水,很快地渗入到衣服里头,然后慢慢晕开;布的颜色变深了,看起来就像是染布时没将颜料调匀一样。湿迹起初只是一两片,后来,片与片之间连了起来,到最后,整个衣袖,或者整个裤脚,或者是全身的衣服,都被露水给占据了。皮肤能感觉得到,每一根棉花丝之间的缝隙,都充满了这来自风里的甘露。孩子离开时,身上沾满了金黄色的花瓣和花蕊,他没有发现,紧随在他身后的粉蝶,发现了。如果能把从空气中回归到大地的水,都唤做雨,我想,这,应该是清明下的第一场雨了!
天上忽明忽暗,雨看着要下了,却又不知道还得等多久。清明这天,不管是家里带小孩的老人家,还是田地里劳作的人,心里都比往日要急切一些。
老人家坐在家里哄着摇篮里半醒半睡的孩子,他们把脚搁在摇篮下面一踢一收,有节奏地晃动着摇篮,隔一段时间就朝屋外的天上看一眼。看完天,老人家又望一望晾在外面的衣服,心想:“这天是疯子天,没准什么时候雨就下下来了。下雨了,田地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又没带蓑衣,那儿也抓不到可以拿来挡雨的树。”
年轻人到了田地后,发现自己昨天整平了的秧田被谁家的牛踩了几脚,被踩得乱七八糟的,就着急忙慌地跑回家去取木板,打算重新再挂一遍秧田。在回家的路上,他遇上了个迎面走来的人,虽然隔得很远,但也认得出是村里的熟人;等走得近些了,他们都稍微放慢了步子,好有足够的时间来打个招呼。他们谁也没有停下来,只是趁着两个人的距离还足以让对方听清自己,闲话了几句,然后又各自忙各自的去了;他们虽然没有聊上几句,但是彼此都已经把自己想说的事情说得差不多啦。那个熟人方才也是刚到田里不久又反转身回了趟家,原因是他们家的公猪找不到了;他到家后就带着孩子到处找,把村里村外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最后还是他的老母亲在邻居家关着母猪的猪圈里把猪给找到的;这猪一找到,他就立马往田那边赶了。
雨是急不得的,它下不下是天的事情。天不下雨,你就是把村子里的土地庙、荣四公庙和所有的老井都拜遍了,天也不会动容。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天色没有改变多少,大家却变得比之前懒散了,大概是因为内心与天上的乌云僵持了太久,时间一长,就倦了,就松懈了。他们慢慢地挪动自己于田间,如同吃了老鼠药的蚂蚁之于南瓜叶,打不起十二点的太阳的那股劲头出来。后来有些人就干脆把农活搁置在一旁,三三两两坐到田边开始聊天,估摸着反正天黑前能把事情做完就行。
有一个汉子和一个老汉坐在一个土坡上闲聊,当他们聊到隔壁村一个寡妇改嫁的故事时,都笑了起来。旁边本想赶完工尽快回家的小伙子,听到这边的热闹,也忍不住放下手里的活,到水沟里把手洗干净了,凑过来听一听。小伙子迫不及待地往他们那儿走过去,还没等走近,估摸着还有个一丈多路,小伙子就脱下一只鞋扔到西面的汉子旁边,之后单脚跳了好几步,挨着汉子坐在了那只鞋子上。他挪了挪屁股,感觉自己坐稳了,就开始一边听着汉子和老汉聊天,一边给自己卷烟了。他从左边裤口袋里抽出一张印着双喜字的红色烟纸放到半蜷着的大腿上,又从右边裤口袋里抓出一撮晒干的烟丝放到烟纸上,等右手的食指把烟丝摊均匀后,就拿手指卷出了一支烟送到口里。因为心里着急,卷烟的时候并没有区分烟纸的正反面,结果把双喜字卷在了里头。说实话,看着他口里叼着的那根白色的卷烟,人们不自然地就会联想到戴孝的妇女在头发上绑的那个白布条。不过他才不会想这么多呢,注意力全都在旁边两个人的谈话里。他没带火,就问旁边的汉子要,汉子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口袋也是空的,就拿胳膊撞了一下右边的老汉。老汉说:“我右边这个口袋里有盒火柴,我手太脏,全是泥巴,你帮我拿一下。”说完,老汉就把右边的屁股抬起来扭转到汉子这边来,不巧,那盒火柴刚好在老汉转身的时候掉了出来。汉子伸过手捡起火柴盒,正准备打开给小伙子划一根火柴,小伙子说:“太客气了,还是我自己来吧!”小伙子说完就从汉子手里接过了火柴盒,他一边抽出火柴抽屉,一边问:“刚刚你们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啊!眼睛都笑得眯成那样。”老汉就又从头开始讲方才讲过一遍的故事。小伙子一边听一边划着火柴,当火柴快送到烟边上的时候,他听到了“寡妇”两个字,生怕接下来会漏掉什么细节,整个人都屏住呼吸定在那里,就连点烟的动作都停顿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忽然听到老汉讲故事的声音里头夹进了一丝微弱的“呲呲”声,他回过神,发现手里的火柴被一滴水给浇灭了,那“呲呲”声正是火柴被浇灭时发出的。小伙子心想:“哪里来的水啊?旁边的田里都没有人玩水,谁抛过来的水啊?”他抬起头,疑惑地朝天望去,没想到这时又有另外的两滴水落到了他脸上。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被这水的来源困惑着。直到旁边的汉子说下雨了,他才恍然大悟,知道方才的水滴原来是这憋了一天的清明雨。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等了一天的清明雨真真切切地触及到了皮肤的时候,小伙子反而不认识这雨啦。就好像有一张窗户纸隔在雨和这小伙子之间,非得有另外的一个人来把这张窗户纸捅破,下雨这件事情才变得明了。大概是等雨等得太久,和雨的距离反倒显得比平日里还要长。
三个人着急忙慌地爬起身来,大声地朝四边的村里人叫嚷着:“下雨啦,下雨啦!”这时候,清明雨才真的下下来了;较比去年的清明雨,今年的,迟了。
一刻钟前还打不起精神的那些人,一见雨下下来了、风刮起来了,变得有些慌乱。他们本想把剩下的尾巴工作给结了,没想到今年的雨来得异常地突然,异常地大。他们知道,要是把余下的事情都做了,身上的衣服非湿透了不可;于是就胡乱收拾一下农具,把装谷籽的空麻袋掏出一个窝窝,披到头上挡挡雨,往家那边小跑过去了。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觉得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下午干活没有把时间抓紧点,后悔自己坐到田埂上去和别人攀谈,不然就可以把那些活儿的尾巴完完全全地给做没了,也不至于明天还得挑个时间专门再回田地里一趟。
村子里头,老妇人们正在厨房做饭。雨没下大的时候,她们也没察觉,当瓦上滴滴答答的响声盖住了灶里头硬柴燃烧时爆裂的声音时,她们才恍然知道雨来了。她们立马放下手里的锅铲,急忙跑出去收衣服。有的老妇人脚下踩着的还是三寸金莲,步子一迈急了,身体就左右打转,看起来有些滑稽。谁知道这雨说下就下,等老妇人们发现有雨的时候,雨早就下得和鼓点子似的。不过好在衣服都在家门口,冲出去胡乱一把抓回来就行。她们把衣服晾到屋里的竹篙上,就回到厨房抓紧做饭。她们知道,田地里的儿女,过不了多会儿肯定都回来了,饭得快点准备好。豆子般大小的雨滴落在青瓦上,溅起了水雾,与炊烟融合,朦胧一片;湿柴烧出的浓烟散不出去,呛得妇人们咳嗽不断,咳嗽声透过泥墙,传到了外面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这声音本来无足轻重,却因吓走了冒雨偷吃剩饭的流浪狗,而显出几分趣味。
家里养了牛的,从田地里回去的时候,都顺带着把放养在外面的牛牵回到牛栏里。也不知道是西边邻居的哪个邻居的哪个邻居的哪个邻居(村子并不大,这样表达完全就能覆盖到村子里的每一个人了)回家时,走到塘坝这头了才发现自己把草耙落在了田边,不过雨太大,他也不好再回去拿,就打算明天早上早点起床再去收回来。虽说做好了明天再去拿的计划,但心里还是担心草耙会被别人给捡走。他这回去的一路啊,都像丢了魂似的,路过塘坝头的时候,就连系在旁边的牛也给忘了。后来西边邻居的哪个邻居的哪个邻居,带着那根落在田边的草耙来还他,他心里才算安定踏实下来了。西边邻居的哪个邻居的哪个邻居走的时候,对他说:“我这次回来得晚,发现你家的牛还在那边拴着呢!”他听了,跺了跺脚,说:“对哦!我居然把牛给忘了,我这就去牵回来,哎!全被这个草耙弄得分了心了!”他从门背后拿出一把伞,撑开,从昏暗的屋里走了出去。这一天对他来说好像并不是特别顺利,他没想到自己出门没几步,就被门口石头上的青苔给滑倒,摔了个四脚朝天。他爬起来,低头看了看衣服的前头,又转过头来,看了看衣服的后头,心想,别人要是看到自己身上泥巴的样子,肯定知道自己摔了跤。他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生怕别人会笑话自己,毕竟这么大个人了,还摔跤,听起来也的确怪羞的,于是立马小跑回屋里去换衣服。
湖边的草坪上,低矮的婆婆纳开满了小蓝花,花儿浸在雨雾里,坠着几分情韵,就好像是从哪位打人间路过的仙子挽着的花篮里一不小心掉出来的仙物一样,在等着人间貌美的女子过来采撷。草地上很空旷,只有一头牛还在雨里头淋着。这牛是水牛,从它头上那长长的角和宽大的背部就可以看出来。水牛喜水,经常会到河里去饮澡,这天上下的几点雨,它是不怎么在乎的。水牛仍旧伸出有力的舌头把一卷卷被雨水清洗过的新鲜的草卷食到肚子里去,像没下雨一样。不过,水牛旁边那只寻食的白鹭,就没有水牛这么淡定啦,它是有些怕雨的,但之所以没有飞回到东边山上的窝里去,可能是因为它和人们一样,也被天气玩弄了吧!起初也觉得这天不会下雨,而雨一下下来,就大得让它归不了巢了。不过白鹭还是很机灵的,雨下大了,它就躲到水牛的肚子下面去避雨。水牛吃完一处的草,慢慢走到另一处去,白鹭也跟着走到另一处去;牛绕着牵鼻的木桩,一圈一圈地啃食着新草,白鹭也一圈一圈地跟着。好在黄牛吃草时走得慢,白鹭只需踏一踏那两只纤细的腿,就能赶上黄牛的步子,要不然,黄牛肚子下面也不是个好的躲雨处。后来,那人过来把牛牵走了,白鹭就只好窜到一旁的高草丛里,像站在屋檐下的老妇人一样,盼着雨势减小。
这被雨一折腾,天地之间好像换了个世界一样,一切都变得热闹了起来。不过要说最热闹的地方,还得数村子前面那口远不止半亩的荷塘。雨下下来,大些的时候,就感觉是天上掉下来的丝线,上面连着天空,下面连着荷叶,云成了缠绕着丝线的大纺锤,和云朵形状相似的荷叶,成了吊在大纺锤上的小纺锤。雨水沿着丝线滑到荷叶上,要先在荷叶上打个转溜后,才落到荷塘的水面上。雨势小些的时候,在瓦上汇集不起来的雨水,在荷叶上能;雨水在荷叶里越积越多,越积越重,把荷叶的一侧压得越来越低,当雨水多到荷叶再也承受不住的时候,就一下子从荷叶里头冲了出来,涌入荷塘,成为荷塘里水的一部分。聚集的雨水没了,荷叶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身姿一挑挺立了起来,这一个清扬的挑,扬起了几颗像乳牙一样的小水珠子;此时正好从旁边游过的鱼儿,误把这小水珠子认为是被雨水冲下来的虫子,跃起身跳出水面,张开嘴去迎接,自然是扑了个空。鱼落到水面,溅起碎碎的水花,散开的珠子比刚才荷叶扬起得要多得多,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打旁边游过的别的鱼,也会为了这扑朔迷离的水珠子,犯同样的傻。你若是不知道这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又怎么能分得清那水面的涟漪,是鱼儿的率性,还是雨滴的荡漾呢?
雨水滴落在荷叶上,声音是有些沉闷的。若是细听,多少会有些差异:雨滴落在大些成熟些的荷叶上,声音像击鼓一样;落在刚刚舒展开的荷叶上,声音里面透着些小钹的质感;落在刚冒出来的荷尖上,声音就与手指抚过古琴的琴弦时发出声音无异。整片池塘就是个天然的乐器组合,不管雨下得多大,荷塘都会像正月初四的“保护出神”一样,热闹非凡。
这突如其来的雨,把大家的节奏一下子打乱了,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因为这雨躲回了家里。不信?你看秧田里的稻草人!不信?你看看渡船上那把伞下的摆渡人。
摆渡人上午接了不少的客人,客人离开的时候都是直接把钱扔到摆渡人站着的船间里。每次天气好的时候,摆渡人都是等到傍晚收桨回家时,才把零钱从船间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清明这天,他见天变了,就早早地把钱收了起来,一方面是怕纸币被淋湿了,另一方面也是预计到今天不会再有客人来了。他掂量掂量一下袋子,感觉比昨天重得多,就知足地把袋子挂到船头甲板下的一根竹销上。收拾完钱,他把船桨摇起来搭在两侧的船舷上,然后俯身从船舱边拿出两根近一丈长的竹篾和一块方形的密网。他把两根竹篾交叉着放在腿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苎麻细绳把这两根竹篾从中间牢牢地绑在撑篙的一端;之后他把竹篾用力弯过来,将两根竹篾的两头分别绷在了密网的四个角上。他做这个是为了拿来捕鱼虾的,故乡那边把这种工具叫做“罾的”。下雨时,很多虫子之类的都会被冲到水里,再加上河水被搅动了,水里鱼虾的食物,会比平时丰富许多,鱼虾自然也会比平时更活跃啦。这时候,往罾的里头放上一些诱饵,然后把罾的沉到水里,过会儿再提起来,罾的里面就会有不少的鱼虾。摆渡人是很会经营生活的,这雨天捕到的鱼和虾,可以带回家自己吃,吃不完还可以卖给第二天坐船的船客。大些的鱼可以放到水桶里养着,第二天拎到船上卖给爱吃鱼的人;小些的鱼虾,要是当天找不到买客,他就会把它们放到灶上去烘干,当做干货卖,毕竟,秋天的虾干春天吃,春天的咸鱼秋天吃,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有时候觉得,清明不下点雨,似乎还有点不成样子。印象中,家那边的清明大多时候还是会下雨的,或早,或迟。有时候是一整天的蒙蒙细雨,飘个半天,也不见得能在瓦上聚成水流,就和早上的露水差不多,别看路面湿漉漉的,你若是拿脚往上面踩一踩,那打湿了的泥巴连鞋底都沾不上去;有时候,忽晴忽雨,谁也琢磨不出个规律来;有时候呢,天空晴朗了一上午,才出现几朵昏昏沉沉的云百无聊赖地把天空盖住,待到中午时分,云朵把雨水酝酿得差不多了,也就放开了手,把雨给下了下来。
总之吧,该来的总是会来的,清明雨到底是逃不脱的。也许清明那天还真的没有下雨,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那一年错过了清明雨。清明是个节气,是天地之间万物欣荣的一种气象,也许会比日历上的日子早上一两天,也许会晚上一两天,这都是没有关系的。清明节前一天的雨也是清明雨,清明节后一天的雨,我也承认;只要是那一场雨,那一种感觉,我都会把自己的感观毫无保留地交出去。毕竟,我爱清明本身,胜过清明的各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