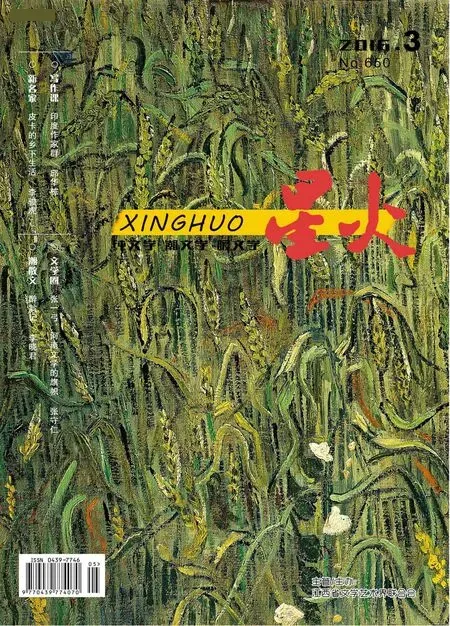上海姨奶
陈 武
上海姨奶
姨奶只是身在上海而已,我相信,她的心从来都不在那儿,她的心应该永远停驻在苏北一个叫南城的小镇。
姨奶早年背井离乡去到上海,自然是为了谋生。听姨奶说,1949年前,她在一位大学教授家烧饭。后来,那位教授举家迁往美国,邀请她一同前往,被姨奶谢绝了。后来,教授的一个女儿也留了下来,还经常来看望她。姨奶说,那时她三十多岁,女儿还小,放在老家,由妹妹(我外婆)一家照看。而她的丈夫则在更早的时候,死在侵华日本兵的刺刀下。
那时的上海是摩登的。虽然姨奶祖籍杭州,父亲曾是商会会长,但后来家道中落,从苏北小镇来到上海的姨奶只是一个家政服务员,上海的繁华对她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吸引力;除了干活,闲下来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家,想自己的孩子。在上海几十年,南京路淮海路就去过屈指可数的几趟。女儿十二岁的时候,姨奶生活安定一些了,才把孩子接到身边,直到女儿十七岁出嫁。
姨奶没有文化,不识字。据外婆说,姨奶不怎么喜欢念书,当时家里供她们念书是有经济条件的;而自己则喜欢学习,上了三年私塾,识了些字,不然就是睁眼瞎。
不识字的姨奶1949 年后就在新村里烧“老虎灶”——就是烧开水卖。姨奶住的新村是上海新建的居民区,是一个一居室,集厨房卫生间和卧室于一体的小套。在上海,这般麻雀虽小但功能齐全的一居室已被称为一套房子,并且,这样的套房已经相当奢侈了,因为更多的上海市民那时还住在棚户里,阁楼里,亭子间里,或者打地铺。姨奶隔壁的小强家,和姨奶同样大的房子住了一家五口。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家的自行车每天都要挂在屋里的墙上,而身材矮小的小强外婆每天都在浴缸上面铺板睡觉。可见,姨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住上这样的一室户应该是十分了不起了。
这样一套房子,不管是对于晚辈,还是亲戚,都是奢侈品——房子对于当时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许多大龄青年结不了婚,没有房子是主要原因。于是,姨奶的房子便具有了某种公益属性,她的外孙结婚,她的某个朋友的儿子结婚,都曾借她的房子一用。外孙则在她的房子里住了很多年,直到分到房子搬走。
也许有人会问,一位在上海打工的普通劳动者,建国初期,她是如何分到这样一处房子的?事实上,建国初期,上海市政府针对广大群众居住困难的问题,相继建起了多个工人新村,比如普陀区的曹杨新村,徐汇区的日晖新村。这些居住区的建立,解决了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部分住在棚户区的劳苦大众的居住问题。这是1949 年前的工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姨奶作为城市平民,在那个年代分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也许并不奇怪,这恰是底层百姓地位提升的体现。
我对姨奶的记忆是从她六十多岁开始的,那时她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看自行车。大概是政府照顾吧,她看自行车收的钱不用上交,全归自己。那时,一辆自行车收费两分,一月下来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比上班拿工资的要强很多。不过,对于姨奶来说,她必须天天看自行车才有收入,她没有退休金保障,直到白发苍苍,还舍不得放下那份收入,还得靠劳动养活自己。往往,手里攒下点钱还要贴给孙一辈结婚。
大概我五岁的时候,姨奶从苏北把我带到上海,过了有半年的光景。模糊的记忆里,我曾帮她捡过菜场的菜皮喂鸡,还用缝被子的针绑在木棍上扎烟屁股,然后撕开烟屁股,把里面的烟丝积攒起来,寄给抽旱烟的外婆。那时候,上海多是竹篱笆围墙;挤公交车像打仗;一次姨奶有事,把我托给一位邻居阿姨,她带我到小吃店吃了碗馄饨……儿时和姨奶在上海的时光现在俨然成为梦中的场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多次写信给福州军区,姨奶被确认了烈属身份。她的儿子在1949 年的金门战役中失踪,三十多年后,被追认为烈士。那年,我从部队回来探亲,特意到上海看望她老人家,她从一个饼干盒里拿出一张盖有叶飞将军私章的入伍证明书给我看。这时,我方才知道姨奶牺牲的儿子名叫许宏波。姨奶说,当年他在部队是卫生员。姨奶的烈属身份得到确认之后,得到了政府的各项关怀,每月享受烈属的抚恤待遇,街道逢年过节还上门慰问。姨奶曾对我说,儿子虽然走了,但我还是享了儿子的福。
姨奶虽然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比在故乡多,可是她从没有把自己当成上海人。她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多年,没有学会上海话,只会一句上海方言的“谢谢你”。她甚至对自己孩子身上的小气颇有意见。她心心念念的还是老家。只要老家有人来上海,她总是买上很多东西托人带回去,并且嘱咐好给张三李四,怕弄错了,还让人在每份东西里放上字条。姨奶特别喜欢回老家走走看看,住上一段时间。我当年居住的城市其实离姨奶的老家还有二百多公里,可是对于姨奶来说,到了苏北就好像是到了家了,因为苏北地区的淳朴民风和人情风俗十分相近。有一回,姨奶在我家住了一年多,父亲单位许多人都以为她是我父亲的母亲,父亲笑笑默认。姨奶最后一次回老家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了,本来我只是去看望她老人家,结果姨奶坚持要和我一起回苏北。我无奈,只好带她一起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长途车的车况也很简陋。姨奶跟着我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一路颠簸晃荡,着实让人心里捏把汗。
有一年出差,我拐到上海看姨奶,那时,姨奶住在上海吴泾一个条件简陋的敬老院里。一个房间挤得满满的,住了好几位老人,姨奶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所有的个人物品只能放在一个床头柜里。姨奶见到我很高兴,也很意外,因为之前她不晓得我会去看她。那年,她已经近九十岁了。那是我从部队退役到地方的第一年。我拿出一百元钱给姨奶,姨奶说了句“还给我钱”,就高兴地收下了。她知道,这是我的一片孝心。由于还有其他事,我在姨奶的床边只坐了半个多钟头,我还拿出相机给姨奶拍了一张相片——霞光透过窗户,照在满是银发的姨奶的脸上,姨奶微微笑着,坐在床边的姨奶在一片红色的光晕中显得瘦小。后来胶卷拿去冲印,这张照片竟然没有洗出来——这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
在黄昏的敬老院,我不知道这是我和姨奶的最后一次交谈,我只记得她老人家关心地问我有没有女朋友。虽然我是特意去看望姨奶,但实在是太匆忙了,好像姨奶还没有把我的脸看清楚就要匆匆离别了。我也没能了解姨奶的更多一些信息,更多一些状况。我和姨奶告别的时候,姨奶没有一句挽留话,相反,她怕耽误了我的时间,叫我走吧走吧;可是从她的眼神里,我分明读到了眷恋,读到了不舍。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是我和姨奶这辈子最后一次说话。
姨奶住进吴泾卫生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从苏北赶到上海只看到她睡着的样子。一个月后,她老人家仙逝。当晚,我在电台主持的节目中谈到了姨奶,忍不住失声痛哭。姨奶在我小的时候带过我——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能够深切感受到姨奶是真正疼爱我的人。或许,在她的心灵深处,她无意识地把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寄托在了我身上。
多年之后,也许是一种缘分,也许是一种巧合,我从苏北辗转来到上海定居,并且我上班的单位离姨奶当年居住的小区就一步之遥。为此,我写过一段话:
姨奶,您知道吗
每天路过日晖影院的时候我都会朝那里深深注视
我多么希望时光倒流,再看到您打着围裙看车的身影
姨奶,现在影院老放“穿越”电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您也能“穿越”一次
在日晖影院的门口让我再望见您
姨奶,告诉您
日晖一村的地上现在建起了日晖新城
而我常常会利用午休
去日晖新城寻找您的影子
姨奶,我恍惚觉得自己是“穿越”而来
而您却失约未至呵
外公的凌霄花
小镇,被夏日的一阵疾风暴雨涤荡之后变得异常清澈。雨水把道路上的泥灰全部冲到了下水渠中,露出了光洁的鹅卵石般被车辆和行人磨平的石路。山上下来的水也汇集到下水渠中,发出水冲击和拍打石壁的声响。从山上淌下来的水是非常干净的,在山涧两边,许多妇女正在用木槌敲打着衣服,洗好后随便一拧,便把衣服摊在山坡上。空气中满是植物的气息,那是山坳里特有的气味,各种花草树木挥发的气味。抬头见山,只见山的半腰处有一弯云,但,挡不住迅速升腾起来的太阳。
看着天晴好了,宅院里的妇女和孩子又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把下雨前晾晒在太阳心的凌霄花从屋里移到院子中央,或展开芦苇席,将凌霄花平铺在上面,或直接把花朵撒在院子的青石板地上。而更多的花还在枝头。在小镇,在家家户户的围墙上,都爬满了凌霄花的枝蔓。长了几十年的枝蔓,遒劲,沧桑,有力,具有刚与柔兼备的美感。而像喇叭一样开着的红色花朵,鹅黄花蕊,依然是天真的模样,依然透着一股淡淡从容的香气——那是一种不骄奢的香气,一种更加正直的香气,一种接近平民的香气。此时,我不需要去查什么百度,我更愿意从字面和她自身的姿态去读懂她,去体会她,去注视她——凌霄花。此刻,我还非常地佩服我们的祖先给这株花起了个如此贴切的好名——请用心去抚握“凌霄”二字,那是由地而生,却接着天界仙气的凌性草本呵。
是的,凌霄花正是肩负济世的使命而来;作为一味中药,在与疾病的抗争中,她扶正压邪,她扶佑生灵。而外公当年把凌霄花从外地引到小镇种植,本来的想法是极简单纯粹的。外公本来就是个爱花之人,不仅喜欢赏花,还喜欢种植各种花草,且颇有心得。外公爱花,不仅是他生活情趣的体现,也是他艺术爱好的延伸。外公酷爱书法绘画,且造诣很深,解放后因此当上了美术老师,退休之后,还被当地文化部门请去当书画顾问。当年,江苏电视台的《艺林漫步》栏目还专访过他。由此可见,外公喜欢花草并不是偶然的,这和他的艺术旨趣和性情禀赋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他与凌霄花相遇,并把她带到小镇却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一次远足的意外发现和喜欢,小镇就不会有家家种凌霄花,满镇皆凌霄花的盛景。
知道了凌霄花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之后,凌霄花在小镇才算是真正传开了。凌霄花成为了小镇人家收入的正当补充。各家各户,都找外公讨要凌霄新发的幼苗带回去种植,外公总是有求必应。渐渐,凌霄花在小镇长出了规模,长出了名气。不仅美化了环境,有的人家还把凌霄花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墙根有一点空地就种上,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钱,老人的抓药钱。
外公岁数大了,自己不能爬上爬下摘花晒花了,就把采摘凌霄花的任务交给暑假在家的孙辈。忙一个夏天,卖给药材收购站花干的钱正好可以交新学期的学费,余下的,就留着过年给孩子们扯布做新衣裳。记得那年暑假,我搭邻居的便车去小镇看外公外婆。到了小镇,我也承担起采摘凌霄花的光荣任务。凌霄花爬在高墙上,垂下来的花朵伸手可摘,而更多的花儿开在墙头上,于是,需要搬来竹梯,把梯子戗在墙上,然后爬上去,把开了的花朵一个个摘下来。摘下来的花朵一定要抓紧时间晾晒,否则就会捂烂了。夏天,太阳烈,可雨水也多,花朵开了就赶紧摘下来,有几日好太阳一晒,就保险了。晒干的凌霄花到了药材收购站,一过秤就是钱。
最近,我又去了趟阔别很多年的小镇,小镇的变化很大,原来是一个完全以天然石材建筑起来的古老山镇,现在混合了各式材料和样式,和其他地方一样,正进行着拆旧建新。访遍古镇,在一些现代的院落里,已经找不到凌霄花的踪影,而在数百年以上的古老斑驳的院落里,凌霄花弯曲的向上攀援的顽强枝蔓还在。现在是初春,凌霄花还没抽芽,相信到了夏天,凌霄花还会一年一年如约绽放,在她盛开的红艳艳里,我会看见已离开我们很久的外公的笑容。
父亲的厨房
水杉树笔直地伸向天空,天空照样是蓝的,知了在某一棵树上叫着,偶尔有风吹过,树叶发出声响,透着夏天的某种恬静。水杉树下摆着一个红褐色的四方小桌,小桌上已经放好一瓶还没有启盖的啤酒。父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他在炒菜——夏天里的菜,有青椒炒毛豆粒,有青椒炒土豆,有西红柿炒鸡蛋。这些都是夏天家里最常吃的菜。此时,父亲应该正在炒另一道夏天里大家都爱吃的菜——小公鸡炒毛豆,因为透过厨房的纱窗,菜的香气已经在长着水杉的没有围墙的院落散开了。“小公鸡要选没叫的,一斤左右的。”父亲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
父亲有早起的习惯,即便星期天不上班,他亦起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床呢,父亲的菜已经买回来了。那时候,买回来的鸡都是要自己杀的,父亲买菜回来的头一件事就是杀鸡。父亲会接一碗冷水,水里放上少许盐,把鸡抹了脖子,鸡血就淌在碗里。中午烧鸡的时候,鸡血结成了块状,倒在锅里,和鸡一起烧,味道很好。
菜场就在农垦大院的马路对面,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菜市场。过来卖菜的都是附近西郊的农民,菜的品种很多,都是一早从自家菜地里摘的,很新鲜。父亲喜欢在固定的摊点买菜,喜欢人与人之间熟悉友好的感觉,父亲买菜基本不还价。有时候母亲和他一道去菜市场,见母亲还价父亲总是向她使眼色,意思让她别还价。父亲宁愿在价格上吃点亏,也不乐意影响到他构建和营造起来的那份和谐。
过去,城市和乡村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城市根本上是从乡村变形而来。在门前屋后种些瓜果蔬菜,养几只鸡,是十分普遍的。在物质并不充裕生活相对贫瘠的年代,城市家庭的微型农耕和养殖,确实可以改善生活不少。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种过蔬菜,养过鸡,甚至还专门种植过平菇。
记得那年,父亲从市里的一个食用菌研究所买来菌种,按照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指导,在平房前面的空地上向下挖了一个半尺深十平米左右的浅坑,然后把菌种和打碎的棉花籽搅拌在一起,平铺在坑里。在放入棉花籽之前,需要在坑里先撒一些石灰用于防虫。最后,在坑的上方铺上塑料薄膜,定期喷水即可。大概十天半月,菌种就开始生长。不久,在父亲烧的汤里,就吃到了自家种的平菇。父亲对平菇的第一次认识,来自防震棚里一个老树根长出的一大簇不认识的菌类。父亲把树根上的菌子用刀削下来,问隔壁学农业的邻居,邻居说,这是平菇,可以吃啊。于是父亲就把菌子送给了他。后来,这个树根又长出了许多菌子,即平菇,于是,父亲用来烧汤。那汤的味道现在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绝不是现在广泛种植的平菇的味道可以比的。
孩提时并不懂得父亲买菜烧饭的辛苦,也不懂得在厨房里变出花样的难度。父亲为了给餐桌添彩,在夏天的雨后,会鼓励我和妹妹去采木耳。其实,在无所事事的暑假,我是很乐意去采木耳挖马齿菜的。在农垦大院道路的间隙处,马齿菜长得非常茂盛;在许多锯过的木桩和朽木上,木耳也是随处可摘。采后的马齿菜需要沸水汆熟后晾晒,和猪肉放在一起,是过年包包子的好食材;木耳更不用说,作为营养丰富的食用菌,放在西红柿蛋汤里是再好不过了。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亲从想着烧什么怎么烧,提高到问我们想吃什么。父亲在拿着帆布袋出门买菜前,总要问一声,今天想吃什么。一般来讲,只要菜场里有的卖,父亲总会买回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有时,我们点的菜没有买到,父亲还颇带歉意,总是要解释一下。有一年,我看到电视里面人家吃火锅,便向父亲提出吃火锅的想法。家里并没有火锅,父亲就去单位食堂借了一个被铜质火锅淘汰的铝质火锅。买来羊肉,剁成大块,加上胡萝卜,放在火锅里炖煮。由于是第一次吃羊肉火锅,没有经验,羊肉烧得很膻,我吃两块就作罢。由于没有木炭,火锅烧的是没有充分燃烧过的木块,火锅一边烧,一边冒着呛人的烟灰。吃完饭,一家人脸都熏黑了。
在家里,厨房一直是父亲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过去,我下班回家,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在三楼的厨房朝我招手,打招呼。一晃,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厨房里再也找不着父亲的身影。父亲,我多想和您在厨房里,一起再偷偷地抽一支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