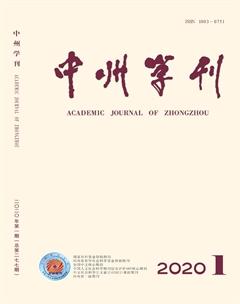近代城市居民公共卫生意识的转变与嗅觉构建
李永菊
摘 要: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较差,民众对脏乱环境的嗅觉感知并不敏感。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同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观念,并将改变公共卫生认识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国之大事,于是脏乱的环境开始承载“疾病”“落后”等更加丰富的医学内涵和政治想象,人们对脏乱环境散发的“臭味”愈加敏感。通过公共卫生运动和身体入微的体验,近代中国人对“臭味”的嗅觉感知能力逐渐被建构起来。
关键词:近代;城市卫生;臭味;嗅觉感知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1-0135-05
关于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视角较多侧重于卫生现代化的成果和意义,而对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体验和感官习惯缺乏必要关注。①尤其对脏乱的环境引发身体不适,基本上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探究的现象。事实上,对环境的身体感知不仅是国人的日常生活,更是近代国人建构与想象现代国家和现代身体的重要基础。本文试图以嗅觉感知为切入点,分析近代来华外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对中国城市脏乱环境的不同言论,探讨近代国人对“臭”的嗅觉感知是如何被不断叠加和改变的。
一、明清时期的城市卫生状况与国人的嗅觉感知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虽多,但是关于环境脏乱以及恶臭引发身体不适的描述较为少见,记载的缺失并非说明城市的卫生状况良好,事实上,明清时期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极为糟糕,普遍存在随地便溺、乱扔垃圾、臭味难闻的现象。根据邱仲麟对明清北京城卫生状况的研究,明代京城居民随意倾倒垃圾、随地便溺已成习惯,明初虽有管理律令,清政府亦屡次整改,但是积习难改。明清时期北京城漫天黄沙,满街人畜粪秽和泥泞,空气亦是恶臭难闻。②作为首善之地的北京城都是如此,其他城市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地区也普遍存在乱倒垃圾、随地便溺、排水沟失修和河水污染等公共卫生问题。③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居民习惯于将粪便、污水等生活垃圾倒进城市河流之中,导致河道堵塞、河水脏臭。另外,由于城市街道道路不平,疏于维修,居民在街道上乱倒污水、粪便、垃圾等,致使城市道路两旁的排水沟成为污水沟或臭水沟,在气温上升时散发出阵阵恶臭。清代嘉道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的发展,江南地区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愈加严重,主要表现为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狀况不良,每到天热时节,秽臭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泛滥猖獗。④
既然中国古代城市公共卫生如此之差,为什么史料中却少有记载?很显然,对于当时的官员和社会精英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值得记载的,由于这类事业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显然不能成为国家和官府的施政重点,地方政府不会花费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地方政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担负起维护公共卫生的责任,这类事业往往由民间力量主持承担。但是由于各地民间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不一,再加上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公共卫生的维护很难实现制度化。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文献中,中医典籍有不少关于臭味的记载,如秽气、恶气、腥气、膻气、病气、尸气、疫气。中医认为“臭”容易致病,“凡脏腑之情,遇香则荣卫通行,遇臭则荣卫凝塞”⑥。这一观点倒是符合现代公共卫生知识中臭气致病的理论,不过与西方社会着力消除公共环境的恶臭相比,中医则主张通过养内的个人行为以避秽。由于“六淫不正之气”和“沟粪恶浊气”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⑦,不可能完全驱逐或消失,所以面对各种不正之气,传统医学主张“污秽恶臭,固宜远避”⑧,通过宁静淡泊、饮食起居规律等办法增强自身正气,以抵制各类秽气。这类养内避秽行为显然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国家和政府行为,当然除非发生大规模疫情,否则国家和官府较少关注公共卫生问题。
总之,在古代社会,环境脏乱既非重大的钱粮和治安问题,也非政府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而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因而,人们对此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如何增强自身正气以适应和抵抗各种异味。由于没有其他外来卫生观念的比照与借鉴,国人在共同的生活情境中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气味。正如古人所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二、近代中外城市居民的嗅觉感知差异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外国人进入城市生活,他们难以忍受城市环境的气味,开始较多地用“臭”来描述其对环境的直接感受,这类记载见诸于当时的各类报刊、游记和报告中。如光绪年间的天津,“城内地基很低,一下雨,城墙之下积水成河。一到暑日,各处污水沟臭气冲天,热气引发多种流行病,致使丧命无数”⑨。清朝末年的北京,“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架、人和牲畜的尸骸”⑩。清朝末年的上海,“垃圾粪土堆满街道,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宣”B11。清末民初的沈阳,“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脏乱和不卫生的。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1905年前,奉天并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B12。
1863年以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海关医官的报告对中国城市街道的垃圾清理和厕所粪便处理问题有过不少讨论。如梧州海关医官麦当劳(Roderick J. J. MacDonald)就说中国人把垃圾和死掉的动物弃置街头,听任“腐败之气污染空气”B13。北海海关医官罗瑞(J. H. Lowry)说:“根据我们西方关于卫生法则的观念,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活在这样肮脏的环境。”B14汉口医官瑞德(A. G. Reid)惊讶地发现,汉口的厕所周围充斥着强烈的恶臭,然而如此恶臭的厕所不只旁边有私人住家,“甚至还紧邻生意兴隆的餐馆”B15。除了上述几个城市,福州、宜昌和烟台等地的海关医官也都有提到类似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上可见,近代来华外国人的关注点主要是环境肮脏、污水排放及垃圾清运等问题带来的各种臭味。
来华外国人的游记和报告中有关城市臭味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身体体验,无疑有“真实”的一面。对于经过现代卫生观念洗礼的外国人而言,视觉上的“脏”和嗅觉上的“臭”引发他们不适的感觉。但令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些问题似乎只困扰外国人,身处其中的中国人似乎不觉得这有任何不妥,他们惊讶于中国人的嗅觉怎么如此不敏感,完全感觉不到难以忍受的臭味。如英国传教士雒魏林(1838年开始在华传教)说:“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嗅觉器官似乎不太敏感,因为当外国人在中国城市的任何一地受到令人厌烦的臭气的冲击而几乎被击倒时,本地人却几乎没什么反应,无论在家还是在外。”B16为何来华外国人对脏乱环境的臭味难以忍受,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却显得习以为常?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身体感知差异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理构造形成的,而是因为不同文化认知使人在体验相同环境时拥有不同的医学知识和卫生习惯,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嗅觉差异。
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工业社会,逐渐具有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并建立了相应的卫生制度和卫生法规,在西方的知识脉络中,脏乱导致疾病是重要观念。B17依据现代医学知识的细菌理论,垃圾和污水等腐败物质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是一种霉素,一旦被人类吸入就会患病,只有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身体才会更加健康。因而,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市政建设重点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培养市民良好的卫生习惯。西方人对气味的感知自然比较敏感。其实,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之前,中世纪西欧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如教会认为沐浴是“性道德败坏之源泉”,“洗澡在群众中则更是罕见”。B18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城市迅速发展,居民卫生习惯日渐养成,“现代身体”逐渐被建构起来,西方人对臭味的身体感知能力愈加敏感。
中外城市居民的嗅觉感知存在差异,说明了身体感知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可建构的文化现象。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身体构造并没有本质差异,恰恰是不同的文化和认知造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嗅觉感知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对气味有着不同的解读。近代以来来华外国人将现代卫生观念和细菌理论带到了中国,并以现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标准评价中国城市卫生,而此时恰是帝国主义势盛、白人种族优越感高涨的时代,来华外国人将其对中国城市环境的看法上升到先进与落后的层面,在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负面评价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焦慮和压力,并由此导致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建构国人的嗅觉感知。
三、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体验与嗅觉建构
近代以来,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认同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观念,这一方面源于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的负面言论,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环境臭味的直接感官体验。
对气味的认知不可能从人的嗅觉体验中抽离出来,感官体验会直接影响人对气味的认知。近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游历,他们对西方城市的干净整洁留下了深刻印象,“道路最宜洁净,西人于此尤为讲究,其街道上稍有积秽,无不立予扫除”B19。另外,国内各国租界的街道干净整洁,与租界外的脏乱无序形成了鲜明对比,“上海各租界之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收拾”,“试往城中比验,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B20与西方国家和租界的干净整洁相比,中国城市的景象是路边随意便溺,脏水随意乱泼,垃圾越堆越高。这种明显的感官体验对比给近代城市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压力,产生了处处不如西方的自卑心理,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国家的强盛和城市整洁卫生的内在关联。
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公共卫生上升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成为关涉民族兴亡国家兴亡的国之大政。B21强国与卫生的关联开始被不断强调,如1906年有一篇文章《要强种先得讲卫生》在《京话日报》上刊出,“开口就说强国,合口就说强种,要强国先得强种”,“要强种先得讲求卫生”。B22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强国与卫生的内在关联,对臭味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臭味”暗示着无序、落后与贫弱,环境恶臭从习以为常的现象变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国人意识到脏乱臭与封闭落后的内在关联,就希望通过除臭以达到对洁净的渴望。洁净意味着有序、强盛、文明和进步,对洁净的期待反映了近代国人强种强族、摆脱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洁净成为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实现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此时,除臭作为清洁卫生的重要手段开始有了新的意义,成为实现国家民族富强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和官府应尽的职责。
在广泛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和公共卫生教育中,国人的嗅觉感知和身体习惯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政府到学校,从医学界到宗教界,从社团到报刊,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公共卫生运动。根据余新忠的研究,中日甲午海战以后,“具有近代意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中”B23。1905年国家卫生行政机构成立,清洁“不再被视为个人的私事或某种特定行为和当政者值得称道的义举,而被看作应有行政强制介入的普遍的公共事务”B24。1916年卫生教育联合会成立,主要职责就是教导人民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以及预防传染病等事宜,开展一系列公共卫生教育运动。当政府把近代公共卫生视为国之大政,环境恶臭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除臭从民间的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的公共事务。近代公共卫生运动中的重要内容,诸如清扫街道、改造厕所、净化河流,有效处理污水与废弃物等都有助于清除环境臭味。
除了官方强制性地推行卫生行政外,民间社会也积极参与进来。其一,民国时期,中国民间社团尤其是众多医疗卫生社团通过报刊、书籍、演讲、卫生展览、征文比赛、实物模型、戏剧表演、图片标语等途径积极传播现代公共卫生观念。B25其二,在教会医院和教会医学校中,一些医学传教士纷纷传播现代卫生学说、开展疾病诊治和预防工作。其三,民国报纸杂志在公共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报道,如《申报》除了真实客观地展现公共卫生发展的状况之外,还积极主动地向民众灌输公共卫生观念。B26
一旦对“臭”的认识发生变化,很多传统的生活习惯开始受到批评,原本习以为常的气味开始变得无法忍受,民国时期各类报纸杂志纷纷对中国各地的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批评并提出相关建议。北京作为首善之地,其卫生状况受到较多关注,据1918年《顺天时报》载,粪夫每每任意“将洗粪桶秽水乱遗道途,以致臭气不堪,一般行人莫不痛恨”B27,报界呼吁警察严格管理。1926年《晨报》刊登《设立公共厕所之必要》一文B28,1930年胡百行撰文“为北平特别市卫生局进一言”B29,都是希望能够改变北京胡同里到处都是尿粪垃圾、臭气熏天的问题。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多知识分子和医界人士也展开尖锐的批评。1923年梁实秋来到嘉善县,“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B30。1929年,周卓人描述了其初抵安庆的观感,“大街小巷,尿粪遍地,种种不卫生之处,屈指难数”B31。黄尊生认为,乡村“没有所谓公共卫生”,“到处都是鸡粪狗粪猪粪垃圾泥土”,即便都市,如武汉、宜昌、重庆、九江、安庆、芜湖等,“其污秽,其黑暗,其鄙陋,其荒凉,实在与乡村无多大区别”。B32
总之,在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强势话语下,政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政策,民间社会开展各类卫生教育运动,近代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除“臭”运动,细菌、卫生、洁净的知识得以传播,近代国人对臭味的感知能力更加敏感。公共卫生推行的过程,即是改变身体感受能力的过程,除臭的过程,亦是培养身体感知能力的过程。从对“臭味”的习以为常到对“臭味”的极为敏感,近代国人的身体感知能力在公共卫生推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所以近代国人对“臭味”的身体感知并非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在近代中国卫生教育运动的推行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培养而成的身体技能,就如同欣赏音乐、绘画、品茶和品酒,都需要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才能获得感受能力。
当然,近代国人身体感知的建构主要发生在城市居民之中,生活在传统乡村的民众较少受到公共卫生运动的影响,这恰恰说明了身体感知并非完全的生理现象,而是经过建构的文化现象。下面以除臭剂和消毒水为例加以说明。除臭剂和消毒水等商品大多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在各类广告宣传中,被披上了“卫生”“健康”“进步”的圣衣。除臭剂和消毒水主要出现并流行于通商口岸或其他城市,这些城市居民拥有现代公共衛生观念和现代医学知识,产生了对洁净的渴望和需求,使用除臭剂和消毒水意味着拥有了洁净、健康、科学和进步。而对于传统中国乡村居民而言,他们缺少公共卫生观念,也较少有对“臭味”的政治联想,除臭剂在乡村社会不仅没有市场,还引发了嗅觉上的反感。在一些穷乡僻壤,人们称消毒水为“臭药水”,他们的身体感官是这些药水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不适,“偶有一家之用,则附近邻居,每嗅其气,必致怨恨”B33。可见,所谓的“臭”与“不臭”,不仅仅是一种嗅觉感知,更是一种由文化认知导致的感官变化。面对同样的商品——消毒水和除臭剂,由于其背后的认知意义不同,不同人们的感官体验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城市与乡村对待除臭剂的态度差异,不仅仅取决于除臭剂的味道,还取决于对除臭剂背后反映出的洁净、卫生与文明的认识。
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不仅是学习现代科技和制度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身体感知能力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蔡天民在安庆发现有人把粪缸放在门口墙脚、天井院子或厨房灶边的,心中发生一种奇想:以为这里人的嗅觉机关当有特别构造,不然,如此的“荷风送香气”,我们皆要“掩鼻而过”,总偏“食思其间”,消受得起,可不是“逐臭异禀,得天独厚”么?B34这段话不免让人想到前文提到晚清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雒魏林的言论,当外国人在中国城市的任何一地受到臭气的冲击而几乎被击倒时,本地人却几乎没什么反应。晚清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居民感受能力不敏感的疑惑,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居民对乡村居民身体感知能力的怀疑,都反映了人的嗅觉感知能力是可以建构的。在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从西方国家到中国的通商口岸,从中小城市再到乡村社会,对臭味的身体感知逐步如涟漪般展开,近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身体感知能力不断建构的过程。
四、结语
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政策以及民间社会开展各类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很多国人的身体感知能力经由身体的体验和想象逐渐被建构起来。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城市居民抑或乡村居民,其对臭味的感知能力因其对现代公共卫生的认知差异而不尽相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嗅觉的身体感知是在一定的认知背景下经由想象形成的文化感官,是近代国人在挽救民族危亡之际,经由现代西方话语和国人身体入微的切身体验共同建构而成的。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非要恢复传统社会的卫生状况,而是认为不能对由西方社会构建出来的符合现代性想象的嗅觉感知熟视无睹。不可否认,除臭清洁工作在公共卫生和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但当我们完全拥抱西方话语对于气味的定义,将会阻碍进一步理解和探讨国人的传统身体体验。明白这一点,将有助于抛开现代性的观念偏见,警惕长久以来内化到身体的感官经验,更好地感知不同文明的身体体验和不同文化的丰富质地,同时有助于思考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利益和广告媒体是如何建构甚至掌控“现代人”的身体感知等现实问题。
注释
①③⑤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②邱仲麟:《风尘、街壤与气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11月第34卷第1期。
④余新忠:《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⑥⑦⑧顾世澄:《疡医大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版,第664、665、664页。
⑨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前编》,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513页。
⑩皮埃尔·绿蒂:《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马利红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B11转引自《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B12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伊泽·英格利斯编:《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和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B13B14B15转引自李尚仁:《帝国与现代医学》,中华书局,2012年,第244、241、242页。
B16转引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B1719世纪30—40年代在英国由埃德温·查德威克(1800—1890)所领导的公共卫生运动被视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滥觞,肮脏导致疾病正是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观点。
B18王杰:《中世纪盛期西欧市民阶层医疗卫生观念变化的原因初探》,《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13期。
B19《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第1版。
B20《租界街道清洁说》,《申报》,同治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第1版。
B21转引自黄兴涛:《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63—78页。
B22《要强种先得讲卫生》,《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第1版。
B23B24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9、72页。
B25孙娟、吴百欣:《跨越边界: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新视角》,《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6期(下)。
B26李洪茹:《民国公共卫生研究——以《申报》为中心(1927—1937)》,安徽财经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B27《警察宜注意卫生》,《顺天时报》1918年9月7日。
B28《设立公共厕所之必要》,《晨报》1926年11月8日。
B29胡百行:《為北平特别市卫生局进一言》,《医学周刊集》1930年4月第3卷。
B30梁治华:《南游杂感》,《清华周刊》1923年第280期。
B31周卓人:《安庆市卫生建设概论》,《安徽建设》1929年第8期。
B32黄尊生:《中国问题之综合研究》,启明书社,1935年,第92—115页。
B33《臭药水之功用》,《新黎里》1924年5月16日。
B34蔡天民:《谈谈安庆市上眼前要改良的十桩事》,《市政月刊》1928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