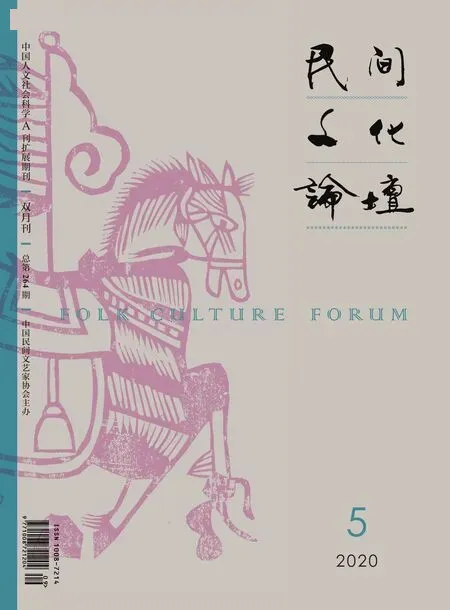社会变迁中的家庭生活
—— 对山西省T 县B 村的考察
刘正爱
以家庭为主要线索,采用历时分析和共时叙述相结合的方法,利用1949 年前后的土改档案、1966年《阶级成分登记表》、1960 年代以来的村庄档案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家户红白喜事礼单和田野调查资料,基于家庭规模、家庭经济、婚姻及互助等内容,我们考察了山西农村家庭的生活变迁,进而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状况。①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来源于2010 年11 月、2013 年6—7 月,2018 年3 月笔者对当地的田野调查,以及在此期间搜集的村庄档案。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而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家庭无所不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教育、习俗均寓于家庭之中,因此,家庭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有关中国汉族农村社会变迁与家庭生活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例如,王沪宁调查了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12 个省份,所完成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家族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②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曹锦清等人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也涉及到农村社会变迁中的家庭文化。③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启动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相应成果以《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形式陆续出版十余本,如陆学艺主编的《内发的村庄》、孙兆霞等著的《屯堡乡民社会》等。近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出版的多部社会史研究也对山西农村社会的研究有所推进,如行龙主编的《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及其所著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等。此外,该研究中心编的《社会史研究》辑刊也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三谷孝主编《中国内陆农村变革与地域社会:山西省临汾市近郊农村的变迁》也是有关山西农村社会变迁的社会史研究文集,但书中只收录了两篇有关家庭或家族的文章①该书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研究成果,与家庭或家族相关的文章是:田中比吕志的《高河店社区家族结合的历史变迁——以茹氏为中心》和张爱青的《高河店的嫁妆的变迁》。。相比于华北地区的其他省份,关于山西农村社会和家庭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希望为这一项工作尽微薄之力。
一、村庄概况
本研究所关注的B 村位于山西省晋中T 县东北约15 公里处,隶属T 县XB 乡。截至2018 年3 月,B 村共650 户,总人口1796 人,均为汉族,全村有6 个村民小组。全村土地总面积为4024 亩,人均面积2 亩多,土地主要用于林业,占80%以上,农业用地约占10%,其余约10%为宅基地、养殖业等用地。B 村是山西省苗圃菜蔬基地,林业主要以种植树苗为主,农业有大棚种植、玉米、西瓜等。2012 年时,B 村人均收入约8000 多元,2018 年增加到13000 元。
B 村是杂姓村,有张、李、赵、孟等68 个姓氏。张、李、孟为在地户,其中以张姓人口为最。据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张姓557 人,李姓219 人,赵姓80 人,白姓75 人,孟姓57 人。除了张、李、孟氏外,其他姓氏主要是长工落户,投亲靠友,逃荒移民,20 世纪90 年代的水库移民以及近年在附近打工而在本村置房者。B 村张家是民国年间晋中地区四大家族之一②其余三个家族是:东里乔家(著名乔家大院主人的故里)、北洸曹家,以及上庄王家。。除经营和制作药材外,张氏家族还曾经营钱庄,在外村和县城开多家店铺,经营范围甚至扩展到俄罗斯以及北京、天津、承德、张家口、上海、广州等地。B 村人重视教育,1949 年以前,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就近上学,村里曾经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人们仍对张氏家族的几个堂号津津乐道,举人巷的修身堂是T 县老字号药铺广升誉最大股东ZTY 的堂号,其家产富裕,名声远扬③其他还有松龄堂(店铺主要在北京和东北)、修身堂、六一堂、二合堂、宝山堂、谦德堂、志忠堂、玉秀堂、守义堂等。。张家曾拥有祠堂和祭祀组织,在村中各项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家庭规模
1949 年以前,地主、富农占有T 县的大部土地。抗战时期,抗日县政府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组织生产互助。1946 年,T 县的解放区首先实行土地改革,有52 个行政村的7082 户,共28890 人参加土改,分别占全县总农户和农村人口总数的38%和26.5%,分配和调整土地121860 亩,占全县总耕地的24%。1948 年T 县全境解放后,又在新解放区全面进行土地改革。1950 年11 月初至年底,T 县组织土改复查,复议阶级成分,颁发土地证,整顿组织,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之后,农村经过生产变工互助,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完成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生产关系变革。1980年以后,T 县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①T 县志编撰委员会,《太谷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86—87 页。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改变了B 村大多数家庭的命运。以张家为例,自明清以来,张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后来一些富家子弟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但在后来的土地改革中,破败户幸运地被划为贫下中农,而那些勤俭节约,持家有道的大户人家却难免地主之名,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就这样,有的由富变穷,有的由一无分文变为有地有房。土改还彻底瓦解了原本就已经衰弱的宗族组织,从根本上改变了B 村的家庭、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1949 年以后,宗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B 村的宗族组织彻底消失,这种消失意味着因外力导致人们对家族和家产生新的认同。土改政策虽然主张公平分地,但这种公平只是贫雇农之间的公平,土地和财产超过一定范围的人被打成地主,财产没收,净身出户。如张氏宗族的主要人物ZTY 在B 村的家产土改时全部被没收②据《阶级成分登记表》载,ZTY 家“土改前有地100 亩,房屋823 间。大车1 辆,轿车5 辆,汽车1 辆,骡子4 头,羊儿40 只,枣林一个(50 根),扇车1 辆。农具俱全,箱柜共100 支。商业买卖有9 处,太原、T 县、交城、北京等地”。当年一位李姓人家为修身堂代耕并管理土地,修身堂给了他80 亩地、一座院子和若干牲畜。土改时,那位李姓长工竟因此而被划为富农,后来才改为中农。,一家16 口人寄人篱下。
家庭规模的变化是从分家开始的。据《T县志》记载,明、清间,T县境内三代人构成的家庭居多,四世、五世同堂者受社会赞誉。民国以后,多代人组成的家庭日趋减少。“七七事变”以后,三代以上的家庭进一步减少。1949 年时,T 县全县人口总户数为25081 户,总人口109443 人,由此算得户均人口为4.36 人,与民国三十年(1941 年)的户均人口6.84 人相比大大减少。至1951 年时,全县户均人口进一步下降为4.28,两代人组成的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结构。而土改的进行加剧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根据1951 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土地证”)和1966 年《阶级成分登记表》③土地证包括每个户主的姓名、户人口数、户房产土地数量及其具体位置等信息。登记表所涵盖信息则更加丰富,有户主姓名、家庭出身、家庭人口、年龄、民族、本人成分、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土改时期、高级社时期、1966 年、现在)、家庭主要社会关系及其政治面貌、家史简述、家庭成员简况等内容。土改时期的经济状况包括土改前后土地、房屋、人口、劳动人口、实际参加劳动人口、牲畜、农具、枣树、收入等情况。每户填写项目各不相同。高级社时期内容与土改时期大体相同,有的家户还有牲畜和农具折价入社的信息。土地证中无土改前信息,而登记表可弥补这一缺憾。故可将土地证和登记表相互对照,从中可知社会阶层变化、家庭经济变化、人口变化以及土改后分家析产的情况。更为珍贵的是,登记表还提供了各家族三代简史,是家族史研究的重要依据。,B 村土改时分家的有4 例,土改后分家的有19 例,入社后分家的有30 例,另有分爨(分户但在一起伙住)者5例。如6 队的中农WDG 一家三口与其父母及妹妹分灶而同居一处,户口分开。有的属于阶段性分家。如3 队ZLX,土改前一家8 口人,土地23 亩,房屋11 间,土改时分得土地8 亩,大车棚一个;土改后,分给长子5 间房、10 亩地;高级社后,分与次子3 间房,自己留3 间。表1 显示,土改时期B 村全村264 户,其中1 口人的家庭竟高达64 户,2 至3 口人的家庭也高达106 户④王跃生对冀南农村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 个村庄的土改前单人家庭均占较高比例, 而且各村比例非常接近, 即基本上都在7%—10%的比例范围内。。因此,土改后B 村的户均人数仅为3.14 人,大大低于T 县户均人数⑤笔者根据土地证的全村人口和户数算得。。

表1 1949—1951 年土改时期B 村家庭规模
B 村家庭规模急剧缩小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土地改革运动对家庭结构带来的冲击不可忽视。这一点从《阶级成分登记表》中的家史简述以及笔者的口述史可窥见一斑,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土改政策。据T 县土改档案记载,T 县在土改时“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按当时人口计算并照顾(贫雇农)一口人分给两口人以上的东西,两口人均分三口以上的东西”①《土改实验村(程家庄)平分与建党总结报告》,1949 年2 月9 日,太谷县档案馆;《太谷新区四八区土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报告》,1949 年3 月,T 县档案馆。。贫雇农为了分到更多的土地和房产而分户,地主富农因财产被没收而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分户,如此一来,分户的自然就多了。
1964 年全国实行第二次人口普查,B 村在这一年重新进行了户口登记。该户口登记簿显示,当时B 村有337 户,总人口1163 人,户均人口为3.45 人,比之前略有提升(见表2)。1964 年至1975 年之间,B 村的家庭结构比较稳定,分家、分户的较少。
在随后的一段时期中,村民中即使有的人分了户,也不会积极地反映在户口簿上。2012 年,B 村户口簿上显示的总户数是417 户,而2013 年笔者从会计那里了解到的实际户数却是599 户,相差182 户。2011年以后,山西省的相关惠民政策促使村民积极分户,使得原本就已经很小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分户分得更为彻底。2011 年,产煤大省山西出台一项惠民政策,全省农村户口每年每户发一吨煤,并折成现金发放。全村总户数由2010 年的525 户(1670 人)增加至2013 年的641 户(1451 人),增加了116 户。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户数与实际生活中的家庭户情况也不完全相符,大多数家庭都是为了每年发放的一吨煤而分的户。
三、家庭经济
家庭经济是以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进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形式,它是一种在家庭范围内合理组织生产力各要素,体现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关系的形式③谭宗宪:《论新型农村家庭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持》,《安徽农业科学》2005 年第4 期。。明末清初,T 县商业发达,T县商人横跨欧亚,雄踞晋商之首。①1937 年以前,B 村商业繁华,有永隆泰(日杂用品、柴米油盐)、永隆泰栈房(制作酱醋面粉)、永隆和(一说布匹,一说粮油酱醋)、文治堂(太谷县饼、豆面面条、月饼等点心、文具)、义合兴(粮油酱醋、典当)、锦泰恒(布匹)、义逢源(一说“裕丰园”,租赁红白事用具,附设售肉店)、集全永(布匹)、崇德堂(中药)、静山堂(中药)、 “同心久”(瓜果鲜菜)、万有亨(粮油酱醋)、剃头铺、普利公(木匠铺),晋三堂(药铺)、驴肉宝(驴肉饼、干面饼、发面饼)、永兴义(不详)、恒义成、广慎诚、义聚兴、□慎堂、恒泰永、义盛长、宝天德、益泉□、□盛永、万顺湧、四海公、万庆德、四海中等三十余家商铺。据《阶级成分登记表》统计,1949 年以前B 村三代之内从事过商业活动的人多达127 人(见表3)。他们有的自己经商,有的在本村人开的商铺中做伙计或账房先生。除了从商之外,村民们主要从事的其他职业还包括厨师(26 人)、木匠(9 人)、佣人(6 人)、屠夫(2 人)、裁缝(2 人)、教员(1 人)、医生(1 人)和银匠(1 人)。

表3 1949 年以前B 村人经商情况
土改后,B 村的经商者逐步消失。在集体化经济时代,B 村与其他地区一样,家庭经济经历了否定、限制和恢复的过程②方宁生:《试论现阶段农民的家庭经济》,《南方经济》,1984 年第2 期。,但大部分农民的生计仍以集体经济收入分配为主,虽然也有少部分的家庭副业。这一时期,B 村家庭可自行支配的财产主要有房屋、自留地、若干枣树、家禽、家畜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等家用物品,家庭副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养猪以及自留地生产的少量农副产品。
《阶级成分登记表》可以帮助我们详细了解当时村民的收入情况(见表4)。从该表来看,各生产队之间的集体收入差距很大,四队的集体收入甚至为零。据当过会计的ZSK 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各生产队长的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四队是当年出了名的穷队,社员所挣工分不够支付一年的口粮钱,常常是年初预支,年底透支。③同样的现象在张思等人研究的侯家营也曾出现过。张思等:《侯家营:一个华北农村的现代历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并且,各队在副业收入所占比率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各家庭之间的集体收入和副业收入亦如此。辛逸根据山东省农村政策调查组对泰安县一个大队的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85%农户的家庭副业收入超过了集体分配的一半,亦即绝大多数农户总收入的1/3 来自家庭副业。④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家庭副业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5 期。B 村的情况则有些不同,除去未填写副业收入的五队,其他四个生产队平均副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4%。若再去除集体收入为零的4 队,一、二、三、六队的副业收入所占比重更少,仅为20%。不过,四队的例子也说明,在没有集体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副业收入是家庭现金收入的唯一来源,在家庭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

表4 1966 年B 村各队户平均收入及部分财产情况①由于各队统计规范程度不同,五队收入部分未区分集体收入和个人收入,这两栏为空白。此外,只有三队和五队记载了自行车或缝纫机的拥有情况。
农户一年的辛苦钱除了用于日常开销外,有条件的可以积上几年,用于操办婚丧嫁娶或修房建房等大事。集体化之前,农户的积蓄还可以用来购买土地。集体化以后,土地买卖不再存在,但房屋买卖依然在进行。根据村庄档案统计②1951 年土地证上有后来附贴的有关房屋交易的大队证明,下文统计数字来源于此。,1971 年至1984 年之间,农户之间的房屋买卖有11 件(包括调换房屋一件),农户与大队之间的房屋买卖有10 件。1971 年到1981 年一间瓦房的交易价格是100—200 元,浮动不大,但到了1984 年,房屋交易价格骤然上涨,两间瓦房的价格为1450 元,相当于725 元/间。这显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一新的生产制度使B 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B 村实行分产到户是在1983 年,人均分2 亩土地,每户另有若干自留地。1980 年代后期,B 村部分村民开始育种树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绿化工程随之而来,为苗木种植户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进入21 世纪之后,B 村的树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耕种面积随之减少。目前该村约有4000 亩耕地,其中90%的耕地用来育种树苗。除了自家耕地之外,大多数苗木种植户以平均每亩500 元/年的价格租种别人土地。出租土地的大都是村中年事已高无法劳动的,或是在外工作的村民,而种植户不仅向本村村民租种土地,也向外村、外乡甚至外镇租种,有的甚至扩大到几十华里外的Y 市。种植规模小到十几亩,大至上百亩。如今,B 村人经营的苗木种植土地已达到1 万多亩,其中有一半是租种村外土地。
目前,B 村村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种树③种树包括在村内外流转土地进行苗木种植以及在外承揽绿化工程。一般来说,30亩左右的苗木种植,需雇用10 个左右的劳动力,百亩以上则需要更多。苗木种植劳动有轻有重,通常轻活由女性和年老体弱的老年人承担,重活由年轻力壮的男性承担,工钱也因此而不同并逐年递增。如,2012 年,1 日8 小时,女60 元,男70—90 元。2013 年,女70 元,男80—100 元,到了2018 年,女80—100 元,男150—200 元。苗木种植为B 部分村民提供了另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他们利用苗木种植的优势,在外承揽绿化工程,承担经纪人的角色。,二是打工④包括在村里为苗木种植户打工和在村头的玛钢厂打工。。与大多数中国农村相比,B村不存在劳动力闲置或过剩的问题。相反,到了农忙季节,常常因人手不足而从村外甚至县外雇用劳动力。有的家庭夫妻搭伙,树苗远销全国各地。B 村村民很少到县外打工,打工者基本上不用离开本村。
B 村有少量土地用来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因投入多,产出少,许多村民都表示不愿意种植农作物。村头的玛钢厂极大地改变了B 村人的收入结构,为B 村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①2018 年,县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治理污染,关闭了该厂污染最严重的铸造车间,部分村民开始转向苗木种植劳动力市场。例如,LWY 的次子夫妻俩原来在玛钢厂铸造车间打工时每月两人收入约7 千元,车间关闭后,他们开始在本村为苗木种植户打工,两人每月收入约6 千元。。除了打工和种树外,B 村还有少部分村民从事大棚种植和养殖,另有少量的商业活动。但与以往商业发达的B 村相比,2013 年时B 村只有4 家日用商店、一家饼店、一家磨坊、三家卫生所和一家饭旅店。看好该村较高的购买力而经常驻足此处的各类游商,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
四、家庭消费
村民家庭财产的配置及消费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在农村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消费是与婚姻相关的房屋支出、彩礼支出、礼仪性开支,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需和生产用开支。
(一)住房
从土地改革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农村家庭的消费除了偶尔发生的房屋交易外,住房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没有太大的改观,而且房价也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实行分产到户后,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逐步增加,建房和彩礼成本也明显增高。B 村1984 年房价骤增的例子正是缘于此。
无论经济条件如何,儿子到了婚龄,父母必须要为儿子考虑婚后的居住问题,或者修缮房屋,或者扩建或新建房屋,选择哪一种要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而分家时间的提前所导致的从父居时间的缩短,无疑又加快了房屋修建的周期,增加了父母们的负担②传统的分家一般要等家庭中所有儿子都结婚后才举行,父母会把家产平均分给几个已婚儿子,之后或选择与某个儿子共同生活, 或者在几个儿子家中轮流居住。。对B 村的调查表明,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开始,大部分的家庭都在儿子结婚不久或结婚时就分家,儿子离开父母另立门户③阎云翔通过对下岬村的事例,区分了“单过”与传统的“分家”的区别。“单过”指结婚可另立门户,但家产不能分,直到幼子结婚方可分家。B 村的情况显然与下岬村有所不同,闫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二)彩礼
婚姻意味着一个新的家庭的产生,而彩礼和嫁妆是这个新家庭的重要财产,是新的家庭经济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相对而言,女方家庭只需要支付女儿的嫁妆,嫁妆又可以由彩礼来补贴,所以女方家庭的婚姻支出通常是很少的。而对于男方家庭而言,除了住房外,彩礼也是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其内容和金额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20 世纪70 年代,B 村彩礼很少以现金方式支付,主要是给新娘置办一些随身穿戴的衣服鞋帽等。结婚时的财产配置除了床、桌椅和衣柜外,男方还要购买“三转一听”,即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和半导体。例如老李家,据回忆他1971 年结婚时,国家提倡反对铺张浪费,当时礼金也不多,最多2 元,最少5 角。有的是三四个人合送一个价值3 元的镜框,还有的送脸盆,送搪瓷杯。等到1998 年老李长子结婚时,家里给盖了5 间房,新娘聘金给了13000 元。又如老孟,他是1951 年生人,1967 年初中毕业后到L 县红旗石料厂工作,非农业户口,月工资43 元。1973 年与X 村民乔氏结婚时,还没有给现金彩礼的习惯。结婚时准备的家具包括:一个箱子,两个柜子,两个凳子,两床新被,一块纯毛毯(26 元),一辆自行车175 元。结婚前几天,他带着120 元到县城给女方买彩礼,包括一双翻毛皮鞋17 元,一条涤卡裤子17 元,一件哔叽衣服30 元,一条腈纶围巾14 元,这些都是当时最贵的,余下40 元又带了回来。婚礼当天,他推着自行车到X 村迎接新娘,婚礼上他收到了170 元的礼金。
1980 年代中后期,除了3 间或5 间房外,现金彩礼平均在700 元左右。而2005 年元月L、Q 新婚礼账的彩礼单显示:除了现金2000 元,现金支票20000 元外,各类首饰、衣物、床上用品均为一式两份,此外还有自行车2 辆、摩托车2 辆、饮水机2 台、洗衣机2 台。
2013 年,B 村的彩礼上升到包括5 间房、一辆coco 汽车和128000 元现金。从2016 年前后开始,除了188000 元的现金和村里的房子外,女方还要求男方在县城买100 多平米的楼房和一辆小轿车。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楼房至少三十多万,装修十多万。一辆汽车十多万,娶一个媳妇前后要花70—80 万元。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得跟亲戚朋友借钱或在信用社贷款,有的父母在儿子尚未成年时就盖好新房准备迎接未来的新娘,而婚姻市场行情年年在变。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千方百计想满足孩子的要求,心甘情愿地将一生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全部用在儿子身上。当地有句俗话道:“生个儿子挨砖头,生个女儿吃罐头”,意思是生儿子负担重,生女儿负担小。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生个儿子,为家族延续香火。在生男生女的问题上,人们常常是生女儿不甘心,生了儿子又发愁。
为儿子操办婚姻耗尽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和心血,除了对儿女情感上的依赖外,B 村父母们自然还期待着孩子们将来能为他们养老送终。传统文化中延续香火的观念依然存在,人们期待儿子扮演关键的作用。不过父母对女儿和儿子的角色期待与现实情况往往是矛盾的,在养老问题上,女儿的作用常常超出父母的期待。国家实施二胎政策以后,B 村并没有出现新一轮的生育高峰。年轻夫妇对生育二胎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年轻人都向往都市化的生活,育儿成本的提高,他们宁愿少生,也不愿看到因增加生育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下降。这说明农村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已经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很难预测未来他们的孩子成家时,是否也会像老一辈那样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孩子们身上。
(三)随礼
不同时代的红白喜事礼单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变迁的情况。一位村民回忆说,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参加葬礼或婚礼通常不送钱,而是送东西,后来才慢慢改成送现金。白事送的食物叫孝饭,也称荤饭。从1962 年LYZ 妻子范氏出殡礼单来看,送东西的大体上有馒首、面、荤饭以及帐子(布)等,也有送钱的,称为“祭礼”,多则2 元,少则1 元。在59 份礼中,送钱的有30 人,约占50%。1965 年LYZ 妻子范氏三周年祭的规模则比出殡时规模小得多,送东西的多,送现金者寥寥无几。1965 年的三周年祭典帐显示,送礼者仅25 人,其中送现金的只有3 份,其余均为馒首、荤饭和面,关系较近者,在送面的同时加上一份帛(布)或送一桌荤饭,再加一份帛。到了1974 年,送东西的少,送现金的多了起来。从1974 年M 的结婚礼单来看,在103 个送礼者当中,送现金的有85 人。其余18人送的是衣料、被料、绒毯和镜框。其中,有8 人合送镜框一面,绒毯一块,现金金额与1962 年相差不大,少则1 元,多则4 元,近亲另加拜礼若干。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参加红白喜事时,送现金的开始增多。1988 年BMQ 出嫁的结婚礼单显示,43 份贺礼中,送现金的30 人,其中最少3 元,最多20 元。其余13 份礼分别送的确良布料、背心、床单、毛衣、尼龙衫、的确良衬衣、上衣等。1994 年BMS 的结婚礼单中只有一人送两台石英钟,其余都是现金,少则10 元,多则200 元。1997 年BMX 出嫁礼单中有一人送了一块毛毯,其余都是现金最少20 元,最多300 元。1998 年LXJ 结婚礼单和2000 年LXF出嫁礼单中,送的都是现金,最少的20 元,最多的400 元。最多金额多为近亲所予,额度大小与其经济条件相关。
从礼单来看,丧葬送礼比结婚送礼内容更加多样。例如2009 年赵氏母亲的出殡礼单、五天烧纸礼单以及三周年祭礼单显示,出殡礼单中既有现金,又有食品或物品。现金最低20 元,最多1000 元。其他有T 饼、纸、被面、荤饭、帐子(帛)、花圈、金银斗、馒首等。5 天烧纸则极少有人送现金,在57 份礼中,只有4 份是现金,其余都是T 饼和菓饭、荤饭、馒首、被面、花圈一类的祭品。三周年祭礼则比出殡多出很多,全部是现金,少则100 元,多则1000 元。2013 年LWY 父亲出殡礼单中,少则30 元,多则2000 元,近亲除了现金外,再加荤饭或花圈等。可见,在1962 年至2013 年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送礼的内容和金额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收礼物品金额的多少,反映了事主的社会交往范围以及亲疏关系的远近,有村外社会关系的,收礼相对多一些,礼金额度也比村里人送得多,如果事主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还会掺杂政治和权力的因素。
40 多年来,无论是白事祭礼,还是红事喜礼,都经历了一个从以物为主到以现金为主的阶段。礼金数量从1962 年的0.5—2 元增加到2013 年的30—3000 元,礼金的最小额与最大额之差。在1962 年至1974 年的12 年间一直保持着4 倍的稳定状态,而1979 年开始则逐年增加,到了2013 年,最小额与最大额之差竟高达100 倍。红事(结婚)礼单从1974 年到1988 年间,物品和现金并存,1994 年以后,物品没有了,只剩下现金。但是在白事中,物品自始至终都没有消失,尤其是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送荤饭、菓饭、帐子等的习俗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些物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在于其文化功能,因为它是当地社会确认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①比如,拿荤饭的都是近亲,兄弟姐妹、儿子、女儿和“主儿”家。主儿在当地的亲属关系中地位最为尊优,通常来说,女人的主儿是哥哥和弟弟,男人的主儿是舅舅,如果没有舅舅,主儿就是兄弟姐妹。丧主舅舅、叔叔和姨妈家必须拿荤饭,亲家也可以拿荤饭。礼节上荤饭比菓饭要重一些,尤其是两位老人合葬的时候,“主儿”家必须要拿荤饭。拿菓饭的也都是亲戚,但是关系比拿荤饭的要远一些。在2013 年的一份出殡祭礼中,拿荤饭的是丧主舅舅的儿子。另外,按照当地葬俗,出殡时孝男孝女要走出大门跪着磕头迎接主儿(舅舅或舅舅的儿子)家的到来,主儿家边哭边走进大门。主儿是最亲密的关系,家里有重要事情通常都由主儿做主。类似的习俗在华北其他地区也可见到。参见李霞:《娘家与婆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五、通婚与互助
(一)通婚
B 村一带居住的都是汉族,因此不存在不同民族间通婚的现象,婚姻规则与其他地区的汉族社会一样,同姓(同宗)不婚。1980 年代以前,B 村村民的通婚范围主要围绕着B 村附近方圆15 华里以内的几个村庄。清代及民国年间张氏家族在外经商者较多,但通婚范围仍很少超过晋中地区,只有极个别的娶了外省人。现在的通婚范围与过去大体相同,但也开始出现更大范围的通婚,主要是因为升学或在外工作而有机会结识县外人的缘故。笔者调查中只发现两例是同姓结婚,但已经超出五服,其中一例女方是领养的,无血缘关系。而且两个例子都是自由恋爱,若是介绍结婚,断不会发生在同姓之间,这说明人们在观念上还是认为应该避免同姓结婚的。
由此可见,B 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主要发生在近一二十年内,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相应改变了传统的通婚范围。
(二)互助
在传统村落社会,除了田间劳动、盖房修房以外,红白喜事是亲属之间和相邻之间互相帮扶的主要场合。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闻讯赶来的亲朋好友帮助事主忙前忙后,无人计较是否给钱,事主或以物相赠,或先欠着人家的情,下次人家有事,自己再去帮忙。这种村民之间劳动交换的换工(当地称“变工”),除了劳动力的交换外,还包含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人情以及道德层面的因素,它意味着非一次性清算的社会关系的延续。因此,婚礼和丧葬仪式是观察亲属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动员状况的最佳的时机。并且,红事和白事的社会网络动员情况有所不同。白事时,亲戚必须通知到,如果不通知,对方会怪罪下来;朋友则可告可不告,知道了自己会来。红事时,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有礼的(即有来往的)必须告知,亲戚之间、孩子结婚、父母的姑姑姨妈的孩子们(即,姨表和姑表)必须告知。若不告知,对方也会怪罪下来。在送礼人当中,有的是以前的旧关系,有的是新产生的关系,一旦有了礼,将来必须要还礼,即使两人反目为仇了,该还的礼还是要还,若不想继续来往,还礼以后方可断绝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助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以劳动互助为主,转变为用现金支付。一位村民曾调侃说,现在的人“没有情义,有钱义”。因为帮工与换工预期的是较为长久的社会关系,而现金结算是关系的一次性清算,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大大弱于前者。但“情义”和“钱义”之间至少有一个共项,那就是“义”。所以,我们不能肯定金钱结算的形式中不包含道德因素,因为即便是花钱找帮工,近亲仍然被放在首选的位置,而且有些时候,乡里之间面子或责任与义务也会掺杂其中。
根据1962年LYZ妻范氏出殡礼单的记载,葬礼中现金支出部分只包括香烟、厨礼、鼓乐、花草、棺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工费用,这说明当时礼房、刷碗等灯座都是村里人义务帮忙的。而在1987 年MQY母亲李氏的葬礼中,人工费用除了鼓乐、厨礼和棺罩外,多出一项阴阳先生的费用。大约从2000 年左右开始,红白喜事的人工劳务支出开始增加,帮工均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费用根据劳动强度的大小而不同。
六、结语
许多学者指出,当今中国的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日益增多。实际上,大家庭从来就不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家庭形式。许烺光在20 世纪40 年代的研究中指出,大家庭是中国人的理想,实际生活中还是以小家庭为主。①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2001 年。费孝通认为,过去有人把大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形式,这种观点至少在农村里是不符合实际的。②费孝通:《家庭结构变迁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482 页。李景汉的调查也如是:不满6 口之家庭数目为55%,超过10口之家庭仅占9%。①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第148-149 页。王跃生对18 世纪及1944 年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许烺光和费孝通的观点,核心家庭无论在私有制时期、土改后过渡时期, 还是在集体经济时期、家庭责任制时期, 均为占多数的家庭形态。②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4 期。针对中国家庭结构的特征,王跃生认为,在对中国家庭结构做出总体判断时,单纯将其说成是核心家庭为主题的社会或大家庭为主题的时代都与实际不相符合,若将其说成是核心和直系家庭为表现形式的小家庭和以一定数量户和家庭为代表的大家庭并存的时期是比较恰当的。③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立足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农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小家庭的规模会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
B 村调查显示,土地改革及国家的相关政策是农村家庭分户的催化剂。按照人类学家以往的研究,家庭结构的变化是逐步完成的,是需要一定时间酝酿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至少在形式上的分家分户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时甚至是一夜之间)完成的。20 世纪40 年代以后,B 村的分家分户频繁发生在1948 年至1953 年期间,土改中的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照顾一人户和二人户的举措导致了新中国后的第一轮分户高潮,此后余波未尽,直至集体化以后稍趋稳定。20 世纪50 年代末至70 年代中期是生育高峰,每户人口七八人以上的家庭并非少数。此时,还有一定数量的主干家庭和复合家庭。1990 年代以后,这些孩子们逐渐长大,随着他们成家立业,陆续分家者越来越多。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B 村的家庭规模逐渐缩小。2011 年,B 村迎来了第二轮分户高潮,地方政府惠民政策所导致的这一轮高潮导致了全村几乎彻底地核心家庭化。
促进中国家庭规模产生变化的政策,既包括计划生育政策,也包括资源分配政策。中国的社会变迁除了改变家庭规模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户籍上分户的家庭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保持原有的家庭生活,但这一形式上的分户成为实际分家的导火索,譬如因考虑到社会、道德等原因而不敢与老人分家的孩子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分家的愿望。在讨论家庭结构时须考虑两种情况,一是户口上的家庭结构,另一个是实际家庭结构。家庭内部的结构关系,户口登记册仅仅是一个版本,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另一个版本,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具有实践色彩的文化脉络。如果仅仅停留在户数的分析,而不具体考虑实际生活状况,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也是本研究所要强调的一点。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农村家庭规模急剧变小、核心家庭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容易忽略的。王跃生也曾指出土地改革对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并认为此影响主要体现在土改前拥有较多土地的富裕家庭,因土地绝对数量大幅度减少使其难以养活原本较多的人口, 而不能组成结构比较复杂的家庭。④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4 期。而本研究的个案说明,除了上述原因外,以户为单位的土地分配,不仅使富裕家庭因失去土地而发生结构性变化,而且贫雇农家庭也为了分到更多的土地和房产而分户。
农村家庭经济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随着生产形式的多元化,农村家庭收入逐年增高,但家庭各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高,农民的生活负担并没有因为收入增加而有所减轻。父母用尽一生的积蓄为儿子娶媳妇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在养老问题上,女儿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在中年以上的人群中依然根深蒂固。通过对跨度半个世纪的礼单的研究发现,送礼内容、礼金大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送礼行为本身一直就没有改变。在中国,送礼行为是维持社会关系、人情礼尚往来的重要基础。婚礼或葬礼的形式由繁到简,也在发生变化,但婚礼或葬礼本身并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
随着社会关系的扩大,B 村民的婚姻范围由近及远,人们的交往范围也越来越广,但B 村民的生活基础依然在本村,在这里笔者看到的是一个个完整的家庭,而不是像其他大多数农村那样只留下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在各类仪式中乡邻之间传统形式的帮工或换工逐渐被现金支付所取代,但以亲属关系和乡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依然在B 村家庭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红白喜事等各种人生礼仪一直都是乡村社会演绎个人或家庭社会网络以及实现文化功能的重要载体。
自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家庭生活和命运跌宕起伏,社会变迁过程曲折而复杂,本文展示的B 村家庭生活正是这一变迁过程的一个缩影,相信这一微观叙事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