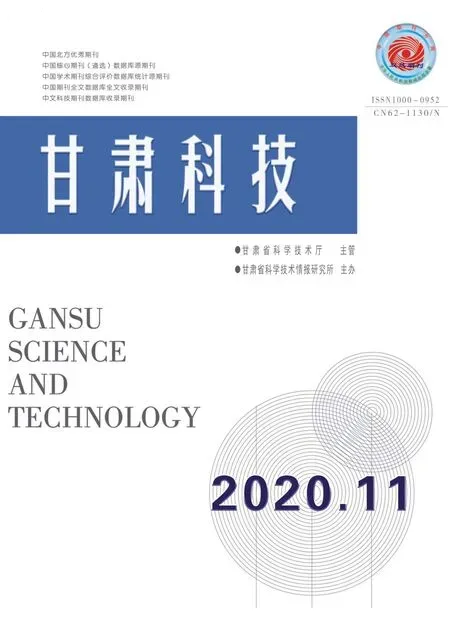公共图书馆法律责任探究
张 波
(安阳师范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公共图书馆法》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公共图书馆行为的法律,使得公共图书馆的设立、运行和服务做到了有规可循。该法的核心内容是公共图书馆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研究十分必要。
1 公共图书馆的义务及其凸显的该法的特征
涉及公共图书馆义务的法条共有26条,占全部法条总数的47%,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行政法意义的义务,主要有第3条的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的义务;第10条的依法保护和使用文献信息义务; 第 15、16、17、19、21 条规定的公共图书馆设立中的义务,涉及设立条件、章程、登记、馆长和工作人员的配备,剩余财产的处理等; 第 24、25、27、28、29、30、32 条规定的公共图书馆运行中的义务,包括馆藏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保存、目录公开、设施设备的检查维护、交流与合作等。另一类是对社会公众承担的义务,这类义务既有一定的行政性,又有一定的民事性、公益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图书馆属于民法上的公益法人,其提供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处于平等地位,从事的相关行为当然具有民事性质。此类义务主要规定在第四章的第33-43条,包括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原则和内容,依法提供文献信息并不得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对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特殊要求,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本馆相关信息要及时向社会公告,通过流动服务设施、自助服务设施、数字服务网络等提供便捷、优质服务,加强古籍保护和宣传,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服务水平,保护读者信息,提供相关文献信息和咨询服务于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和政策制定等。
考察上述条文可知,对公共图书馆的义务虽采用“应当”“不得”等强制性用语,但综观整部法律,一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履行义务的具体方式,义务性的规定多具有概括性、抽象性、模糊性,并不具备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行为模式的明确性、具体性要求;二是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仅有第49、50条规定了公共图书馆的法律责任,公共图书馆更多的义务没有相对应的违法后果,也即并未形成“义务--责任”的立法模式,缺乏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法律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公共图书馆法是一部软法,也即它主要不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正如有学者所言:“软法指的是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1]当然,我们称其为软法,并不能断然否定其“硬”的效力。首先,该法第五十条在采用列举方式规定公共图书馆的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同时,还以“其他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要求的行为”这样一个兜底性条款,使得我们对公共图书馆所有违反义务性规定的行为都有了追究的可能。其次,从规范的内容看,共有29条与国家、政府相关的条文,这一方面说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是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而言,这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如不能积极主动履行,将可能承担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因此,政府应当有所“作为”,比如政府应通过利益驱动机制,采用政府购买、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措施,鼓励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再如加快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细化《公共图书馆法》的相关规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以此确保法律实效。第三,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行业组织的作用,凭借强有力的自律机制,逐步推出行业规范标准,规范公共图书馆的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的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需求。
2 关于公共图书馆法律责任规定的实证分析
该法第五章“法律责任”共有六个法条,其中第49、50条主要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第51、52、53条分别规定了出版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和读者的法律责任,第54条是一个衔接性法律规定,涉及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本文仅就第49、50条加以分析。
1)对于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认定,可以参照《国家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的有关规定,此处不再赘述。
2)关于第五十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1)违规处置文献信息的行为。2017年12月14日,原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杨志今在2017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快研究出台与法律相衔接的配套政策,确保公共图书馆文献处置制度一年内如期出台。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这一制度尚未面世,这也给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此类行为的认定带来了困扰。理论上对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处置的研究成果可供行政执法参考。一般而言,在处置文献信息时,应首先考虑不予处置的文献信息,对于是否应予处置不确定的,要坚持不处置原则。有学者通过对国内副省级以上图书馆进行调研后总结了一般不予处置的文献信息[2]。对于需要处置的文献信息,在具体处置过程中,要坚持分类处置原则和标准,即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缩微制品、数字资源等采用不同的处置原则和标准。处置时主要应考虑下列因素:内容上是否已陈旧过时、已被更新或有关部门决定或通知的内容不健康、应停止流通的文献;外观上是否已残破不全且无法再修复;出版时间过久已超过有效使用年限;是否长期无人问津、流通借阅率过低;依据“剔复不剔种”原则,是否属于复本量过多、价值低及长期滞架的文献;是否存在违反著作权法的文献,对无合法版权者一律处置。当然,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急需相关法规、规章的出台,明确处置的原则、标准和程序,真正使行政执法有法可依。
(2)非法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这里的个人信息不仅包括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还包括诸如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过程中知悉的读者的借阅信息等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在具体认定哪些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时,要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刑法修正案(七)》、民法总则等,全面综合加以考量。对读者的个人信息,公共图书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他人非法提供,更不得出售以牟利。
(3)向社会公众非法提供文献信息的行为。关于该项规定,首先要注意,公共图书馆向社会公众违法提供文献信息仅限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包括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当然,如果公共图书馆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信息违反了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一般情况下必然会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时我们可考虑按第四十九条处理。其次,关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情形的文献信息,总体上而言,凡是可能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均属内容不适宜的。2017年1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2019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做出了详细的列举性规定,有待进一步讨论、修改和完善。
(4)将设施设备用于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活动的行为。
(5)其他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要求的行为。这是一个兜底性、概括性条款,需结合该法前述关于公共图书馆义务的规定加以认定。基于该条规定,也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法》的“硬法”效力也十分明显,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义务”都有了“法律责任”的坚强后盾。
(6)违规收费或者变相收费的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上述违法行为,不仅要追究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还要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3 结语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们在肯定《公共图书馆法》对于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传承人类文明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其不足或有待完善之处,如何进一步发挥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亟需各位同仁对公共图书馆的义务和责任做出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