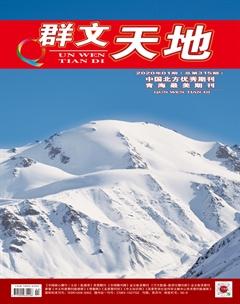河湟“花儿”的语言特色及修辞艺术
杨生顺
河湟“花儿”,是河湟地区的人们用当地习惯用语和方言俗语创作的,因此具有通俗性、口语化特征。譬如:
房子哈修着墙泥着,
墙头上土块俩垒着;
一搭儿不到心有着,
万人的口舌哈压着。
这首作品整体上采用了“着”尾结构,“房子哈修着”“墙泥着”“心有着”“万人的口舌哈压着”采用了倒装结构,这种语言结构是河湟地区常用的习惯用语。
杨柳树儿钻天高,
寒雀儿,
它落在树梢上了;
朽木头搭桥桥不牢,
好花儿,
你把我当桥里闪了。
这首作品中的“雀儿”“闪”是河湟地区的方言,“朽木头搭桥桥不牢”是河湟地区的俗语。河湟“花儿”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与民族性特征,譬如:
苦罢了一年又一年,
总不够官家的粮款;
又叫胡大的又喊天,
苦日子冇有眉眼。”
其中的“胡大”是伊斯兰教民口语,意思类同于“上帝”“天”,西北多回族,因此这个词语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河湟“花儿”的语言特色,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是通俗。“花儿”为口头创作,具有口语化特征与通俗性特征。“高山上落下了白雪了,平川里下了雨了;挣不上银钱哈不说了,天每日思谋掉你了。”不懂西北方言的人看这首作品,可能会觉得颇为费劲,很多人不知道“思谋”“天每日”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些都是河湟地区常见的方言,在河湟人民看来,这首作品浅显易懂,明白如话。
二是生动。河湟“花儿”语言虽然是老百姓的口语创作,但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很讲究的,很多作品生动传神。“山里的枇杷奶子白,香菜的叶叶儿紫葵;隔山的石头穿山的水,隔山者抛下个姊妹。”该作品的上片用“奶子白”和“紫葵”,简洁地描写了山中枇杷与香菜叶的色彩;下片用“隔”“穿”“抛”三个动词,准确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悲伤情绪,显示了人们优秀的创作才能。许多优秀传统“花儿”作品,语言上可谓千锤百炼,是人们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细扎绳把阿哥大绑下,大梁上悬悬地吊下;刀子拿来了头取下,不死了还这个做法。”“花儿王”朱仲禄将此类作品改为“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刀刀儿拿来头割下,不死哈就这个唱法。”改编后的这首“花儿”作品,后来风靡西北,成为了“花儿”中的经典。
三是形象。河湟“花儿”整体上是朴素的,朴素也不乏描述性语言,许多“花儿”作品也因此形象备至。“清清河里的长流水,当啷么啷儿地淌了;热突突儿地丢下你,泪涟么涟儿地想了。”这首作品的第一句描写了水的清澈,第二句模拟了水流的声音,第三句描写了别离,第四句表达了思念,整首作品运用了描述性语言,形象传神地展现了一幅别离悲戚图。
四是幽默。河湟“花儿”有说有唱,很多作品语言风趣幽默。“十八叉梅鹿血染了,口抬了灵芝草了;三魂七窍你拦了,起来着风吹倒了。”这首作品可谓“花儿”之极品,上片形象富有诗意,下片精彩绝伦,尤其“三魂七巧你拦了”“起来着风吹倒了”犹如神来之笔,比大词人柳永的“为伊消得人憔悴”要高明得多,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因为得了相思病,所以刚爬起来就被风吹倒了,这种语言何其幽默!
河湟“花儿”语言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多种修辞手段的广泛运用。现代修辞学公认的修辞手法(修辞格)有63大类,78小类。“花儿”修辞学研究早在上世纪就开始了,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1982年10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印了《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少年”(花儿)论集》,收录了30年的研究成果。其中与修辞学有关的论文有:巴水的《试谈“花儿”的比喻》明确提出“和一切民间文学一样,比喻是‘花儿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点,在‘花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孙殊青的《试谈‘花儿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点到了“花儿”作品的比喻(暗语)、疑问修辞。刘凯的《“花儿”散论》提到了“花儿”的夸张、比喻、反衬修辞。邓靖声的《“花儿”三题》认为“‘花儿也应用着各种修辞手段”,兼对“花儿”的隐喻、夸张修辞作了一定论述,同时提到比拟修辞。许英国的《“花儿”三题》对“花儿”的比喻作了论述。刘凯的《“花儿”对形象思维的运用———浅谈“花儿”的比和兴》,对“花儿”的明喻和暗喻、借喻和隐喻,作了深入论述。谢承华的《“花儿”艺术手法浅识》认为:“花儿”的艺术表现手法除赋比兴外,有叠字、数字、夸张、含蓄、颠倒、重复法。辛存文的《对青海“花儿”创作手法的分析和认知》,对“花儿”的明喻和暗喻,联想、陈述、借代、比拟、夸饰(夸张)、引用、摹状、对比、复叠(反复、复沓)、设问、示现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1989年,赵宗福在其《花儿通论》一书中论述了“花儿”的13种修辞,分别是比喻(明喻、暗语、借喻)、比拟、夸张、复叠摹状、对比、反复、排比、设问、示现、借代、对偶、引用和镶嵌。1993年,刘凯在其《西部花儿散论》中认为,“花儿”的艺术表现手法有15种,分别是赋、比、兴、夸张、双关、倒反、倒装、疊字、摹状、反复、对照、衬托、对偶、设问和序列。2001年,罗耀南在其《花儿词话》中,对“花儿”的叠字叠词、顶真(单字顶真、复字顶真、正反顶真)、嵌数修辞作了深入论述与说明。2004年,滕晓天在其《青海花儿唱青海》一书中认为,“花儿”有16种修辞,分别是排比、比喻(明喻、暗语、借喻)、比拟(拟人、拟物)、夸张、设问、反问、重复、象声、顶针(又叫顶真)、借代、数词、重叠、双关、照应、对偶、对比。上述研究文献对“花儿”修辞学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赋比兴并非都是修辞手法。二是修辞之间有交叉,譬如摹状与象声,相比之下,摹状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准确一些。三是修辞研究还不是很深入,仍然存在欠缺之处。
笔者认为河湟“花儿”的修辞格不少于20种,有比喻(明喻、暗语、借喻),比拟(拟人、拟物),夸张(夸大、缩小),设问与反问,对比,对偶,排比,引用,借代,镶嵌(嵌数),复叠,摹状(摹形状、摹声音、摹色彩、摹动作),双关,示现,顶真(单字顶真、双字顶真、正反顶真、特殊顶真),倒装,讳饰,反语,象征,含蓄。
1.比喻
用跟甲事物有相似之点的乙事物来描写或说明甲事物,谓之“比喻”。“花儿”中的比喻大致有三种:
一是明喻。通常用“好比”“活像”等词语直接比喻的句子为明喻,如:
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
天河的口,
七星儿摆八卦哩;
把尕妹好比个冷石头,
怀揣上走,
捂热时咋丢下哩。
(《花儿集·西宁演唱特刊》P124青海省西宁市文化馆1979)
这首作品,上片写景,下片言情。上片描写了星天月夜之景,“七星儿摆八卦哩”富有动态感。下片描写爱情。为了把爱情描写得逼真形象,作者把情妹比作了“揣”在情哥怀中的“冷石头”,受阿哥体温影响,“石头”由冷变热,两人走在了一起,然而又如何能丢下这被“捂热”了的“石头”呢?恋恋难舍之情顿显。这里,歌者用“石头”来比喻情妹是妥当的,用石头的冷与热写男女双方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来的热恋也是精彩的。这首“花儿”,从夜晚写到冷石头,过渡巧妙;石头的冷热,到最后的“咋丢下”,表达了作者复杂悲伤的情绪。
二是暗喻(又叫隐喻)。相对明喻而言,基本格式是“甲(本体)是(比喻词语)乙(喻体)”,如:
一根柱子三根梁,
凤凰么展翅地盖上;
尕妹的身套是一炷儿香,
尕脸脑活像是太阳。
(《花儿集·西宁演唱特刊》P73青海省西宁市文化馆1979)
这首作品,上片写盖房。第一句采用数字,具体可感;第二句用“凤凰展翅”描述盖房场景,展现了盖房的动态感和形象美。下片写情妹。把情妹的身材比作“一炷香”,把脸比作“太阳”,出人意料,极为奇特,这种大胆超凡的暗喻修辞,写出了情妹身材之苗条、为人之阳光。
三是借喻。用“喻体”代替“本体”,如:
新打的庄窠合龙口,
墙根里卧着个乳牛;
我煨的花儿担名声,
毛线上连了个斧头。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花儿专辑:湟中资料本》P50湟中县文化体育局民间文艺集成办公室1986)
这首作品的上片是说新打成的庄窠旁边卧着一头母牛;下片挑明了爱情生活的不幸,即空有其名,“花儿”并未得手,很可能面临着断绝的危险,对此作者作了形象的比喻———“毛线上吊给的斧头”,毛线上吊斧头暗示着爱情的不长久。
2.比拟
就是把一个事物当作另外一个事物来描述说明。将人比作物,将物比作人,或将甲物化为乙物。“花儿”中的比拟大致有两种:
一是拟人。把物比作人来写,如:
松布香的袜子麝香的鞋,
穿上着大门上浪来;
月亮哥打上灯笼来,
送我的情哥哥进来。
(《中国歌谣集成·青海卷》P805中国ISBN中心2000)
这是一首女子演唱的赋体“花儿”作品。整体上看,这首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在同类“花儿”作品中并不多见。女子希望情郎穿着香袜香鞋上一趟自家的大门,天上皎洁如玉的月亮哥打着灯笼护送情郎走进家门。从局部看,下片将月亮拟人化,勾画了一幅男女幽会图。
二是拟物。把人比作物来写,如:
尕妹是牡丹园中长,
阿哥是隔墙的凤凰;
左戏右戏的戏不上,
碰死在牡丹的树上。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2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花儿”作品的精彩之处,主要归功于拟物修辞的成功运用,即把人当作物来写,上片将尕妹比作长在园中的牡丹,把阿哥比作隔墙的凤凰;下片紧接上片之牡丹与凤凰,将笔墨落在“戏”上,生动地呈现了一幅“凤凰戏牡丹”图,可以说是对“身在花下死,做鬼亦风流”的别样表述,令人耳目一新。
3.夸张
运用丰富的想象,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扩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增强表达效果,谓之“夸张”。“花儿”的夸张修辞有两种:
一是夸大。如:
白牡丹白者耀人哩,
红牡丹红者破哩;
尕妹的跟前有人哩,
冇人时我陪你坐哩。
(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P220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这首“花儿”经典作品的上片采用了夸张修辞。通常来说,人的眼睛遇到强烈的白光就很难睁开,故为“耀”,“白牡丹白者耀人哩”显然是一种夸大,写出了白牡丹花朵之白;“破”字的意思是碎裂,这里也极尽夸张之能,写出了红牡丹开花之绚烂。“耀”与“破”都是动词,用字精炼准确,把白牡丹与红牡丹开花的场景,不仅写活了,而且写绝了。
二是縮小。
鸡蛋的罐子里照灯盏,
头发丝儿的捻子;
黑天白夜的巷道里转,
你冇有菜籽儿胆子。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33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中的“鸡蛋的罐子里照灯盏,头发丝儿的捻子”与“菜籽儿胆子”就采用了夸张修辞。蛋壳中照灯盏,捻子自然是很细的,人的胆子小若菜籽就已经够小了,没有菜籽儿胆子,就是说胆子小到了极点,这里作者有目的地缩小了“灯盏”“捻子”“胆子”的形象特征,起到了讽刺作用。
4.设问与反问
自问自答,谓之“设问”;自问不答,谓之“反问”。
一是设问,如:
家鸡儿好嘛野鸡儿好?
好不过山上的嘎啦;
家里的好嘛外头的好?
好不过娃娃的阿大。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32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在“花儿”会场上,优秀的歌手会一下子抓住听众的心,除了表情、声音、动作等,歌词方面的设问修辞,也往往会生发良好的艺术效果。设问的目的就是提出问题,启发人的心智,引发人的联想,调动听众的注意力。当歌者唱出第一个问题时,作为听众,一边在自己的脑海中思考这个问题并给出一个答案,一边会认真倾听歌者的答案。所以,设问修辞要有情趣性和艺术性,不能问得一般,答得平常,否则就索然寡味了。这首设问式“花儿”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作品,问得非同寻常,答得离奇幽默。“家鸡儿好嘛野鸡儿好”是提问,当歌者问到“家鸡儿”和“野鸡儿”时,人们一般会联想到女人,想到妻子、情人或妓女,而且很容易在二者中作出一个选择;“好不过山上的嘎啦”是回答,“嘎啦”是一种山雀,这个回答归于平常。“家里的好嘛外旁人好”是提问,“好不过娃娃的阿大”是回答,“阿大”是孩子的父亲,出人意料,却又顺理成章。
二是反问,如:
东边的云彩西边来,
阿一朵云彩里雨来?
阿哥是牡丹园中开,
阿一个晴天里折来?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29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歌者若有疑问,或希望得到对方的答复时,常采用反问修辞。这首作品的第一句和第三句是陈述,第二句和第四句是反问,反问是在陈述的基础上生发的。上片套用了“东边++西边+”的中国传统诗词语言程式,展现了“花儿”创作者即兴编词、即兴提问的能力与意识,按理说这是一般歌手都能够做到的。关键是下片,如何在语言结构上与上片保持基本一致,借景言情,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思想情感,就显得颇为重要了。这首作品的作者把自己比作了花园中开放的牡丹,然后反问对方“阿一个晴天里折来?”比喻形象,用字准确,疑问自然无扭捏造作之感。反问修辞促成了男女歌手之间情感的交流和互动。
5.对比
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谓之“对比”。如:
有心了看一趟尕妹来,
冇心了探一回路来;
活着时捎一封书信来,
死了后托者个梦来。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60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是一首“来”字尾结构的“花儿”作品,民间形象地称其为“独木桥体”。作品主要运用了对比修辞。上片两句构成对比,“有心了”与“冇心了”相对应,意思是:你若有心,就来看望一下我;你若无心,就来探听一下我住在什么地方。下片两句也是对比的,“活着时”与“死了后”相对应,意思是:你若活着,就捎一封书信给我;你若死了,就托一个梦给我。这首作品表面上看上去只有短短四句,却包含了情妹对情哥无限的思念之情。哪怕情哥对自己有心还是无意,都希望对自己有所关心;哪怕情哥活着还是死去,都希望能听到他的音讯,甚至在梦中相见。———这是多么动人的思念之情!而这种思念之情的表达,却是通过两个对比句来完成的。
尕妹好比是红樱桃,
我吃时好,
你长着树尖上了;
阿哥好比是路边草,
活的人小,
越活时越孽障了。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22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六句式“花儿”成功地运用了比较修辞。上片把情妹比作红樱桃,自己想“吃”,只是它长到了树尖上;下片把自己比作路边草,因为生活在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人越活越落怜。高高在上的情妹与低低在下的自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强烈的对比中,有力地揭示了主人公忧伤的爱情与悲情的人生。
6.对偶
用相同的字数,相同或相类似的句法结构,组成的表达两个对称意思的复句,谓之“对偶”。
四句式“花儿”中,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称、第二句与第四句对称。如:
骑马不管啥色的马,
单看个走手儿好哩;
煨人不说穷富的话,
单看个心肠儿好哩。
(《青海花儿选》P43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
这首作品中,第一句的“骑马”“不管”“啥色的马”分别与第三句的“煨人”“不说”“穷富的话”对称;第二句的“单看个”“走手儿”“好哩”,分别与第四句的“单看个”“心肠儿”“好哩”对称。再如:
你拉的马儿我拉上,
你拉的胳膊困了;
你担的名声我担上,
你担的脸脑害了。
(刘凯《西部花儿散论》P87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第一句“你拉的马儿我拉上”与第三句“你担的名声我担上”对称,第二句“你拉的胳膊困了”与第四句“你担的臉脑害了”对称。
六句式“花儿”中,第一句与第四句对称、第二句与第五句对称、第三句与第六句对称。如:
两朵桃花一条根,
好桃花,
我移到花园的土里;
两个身子一颗心,
好缘法,
我配到阴间的土里。
(刘凯《西部花儿散论》P86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这首作品中,第一句的“两朵”“桃花”“一条根”分别与第四句的“两个”“身子”“一颗心”相对称;第二句的“好桃花”与第五句的“好缘法”相对称;第三句的“我移到”“花园的土里”分别与第六句的“我配到”“阴间的土里”相对称。
对偶修辞的运用,使得“花儿”作品形式更齐整,音节更匀称,音律更和谐。
7.排比
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思密切相关,语气一致的词语或句子,成串排列在一起谓之“排比”。如:
一行一行的栽树哩,
一层一层的长哩;
一口一口的吃饭哩,
一阵一阵的想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5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花儿”主要采用了排比修辞,四个句子尽管字数稍有差异,但结构基本相同,“一行一行”“一层一层”“一口一口”“一阵一阵”把作品统领了起来,将人怎么栽树、树如何成长,人怎么吃饭、如何思人的动作场景、心理活动,整齐划一地刻画了出来,给人一览无余、一气呵成之感。此类作品很多,再如:
尕雨儿下在个江沿上,
尕雪儿飘在个脸上;
尕手儿做在个忙活上,
尕心儿牵在个你上。
(《青海花儿选》P31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
这首“花儿”与上一首一样,主要采用了排比修辞。句前用“尕雨儿”“尕雪儿”“尕手儿”“尕心儿”统领,“尕”是西北方言,小的意思,表示亲昵,整首作品显得非常柔婉,十分亲切。句中用“下在个”“飘在个”“做在个”“牵在个”过渡,句末用“上”字煞尾,保持了语言结构的一致性。上片言景,下片言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生动传神、诗情画意地表达了作者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
“花儿”的排比修辞,一方面强化了语言的表达气势,另外一方面打破了时空限制,将共同的一些场景或情景,用同样的语言结构罗列在一起,呈现出整体的美感。
8.引用
有意引用成语、诗句、格言、典故、俗语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谓之“引用”。如:
桃之夭夭灼灼华,
桃杏花折的者瓶儿里献下;
子之于归宜其家,
想亲人搂的者怀儿里睡下。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49- 5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作品的第一句和第三句采用了引用修辞,这两句均出自《诗经》的《国风·周南·桃夭》,原诗如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受河湟“花儿”顿挫限制,“花儿”的第一句省略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其”字,变成了“桃之夭夭灼灼华”;第三句省略了“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室”字,变成了“子之于归宜其家”。这首“花儿”大概出自文人之手。“花儿”的创造者是农民,对民间传说、民间俗语颇为熟悉,所以“花儿”中多有对民间俗语的引用。如下:
水冇爪子抓烂坑,
滴滴水,
石阶儿穿下的洞洞;
话冇箭头射烂了心,
从前是好,
只如今变成了仇人。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28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画龙画虎难虎骨,
请画匠,
要画个云里的雾哩;
知人知面难知心,
心扒开,
要问句心上的话哩。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9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上述“花儿”作品中,有些俗语直接被引用,如“画龙画虎难虎骨”“知人知面难知心”;有些俗语在引用时稍有改变,如“水冇爪子抓烂坑”“话冇箭头射烂了心”。通过引用修辞,丰富了“花儿”的趣味,增强了“花儿”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9.借代
不直说事物的名称,而是用与本事物有密切关系的事物来代替本事物,谓之“借代”。如:
大门前头的水晶晶,
绿绿儿剌剌地折上;
要煨了煨下个大眼睛,
人前头出去了领上。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花儿专辑:湟中资料本》P56湟中县文化体育局民间文艺集成办公室1986)
这首“花儿”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应该是第三句。“要煨了煨下个大眼睛”的意思是:要找对象就找一个“大眼睛”。“大眼睛”是什么?从第四句“人前头出去了领上”推断,一定是一位眉目清秀的大眼睛姑娘。这里“大眼睛”直接代替了“姑娘”。中国有句成语叫“画龙点睛”,说的就是眼睛的重要性。在河湟地区,人们也深谙此道,不自觉地运用了借代修辞,创作了诸如“一对儿大眼睛水合合笑”“笑眼里说实话哩”的优秀“花儿”作品。
白杨尖上的一架鹰,
杨树尖上的凤凰;
箭杆身材儿站起来,
凤凰展翅地走开。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53- 54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花儿”中的“箭杆身材儿”,同样运用了借代修辞,用“箭杆”比喻身材,用身材代指意中人。前面的“花儿”作品中的女性,其审美特点在眼睛上;这首“花儿”作品中的女性,其审美特点在身材上。眼睛和身材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审美意义。巧用借代,通过局部代替整体,既凸显了人物的特点,又增加了“花儿”艺术的形象性和幽默感。
10.镶嵌(嵌数)
将一个物体嵌入另一个物体中,使二者固定,谓之“镶嵌”。人们有意识地在“花儿”创作中嵌入数字,涌现出许多与“嵌数”有关的优秀作品。如:
两根皮绳接一根,
再短了续上半根;
我把你心里牵十分,
你把我冇牵个半分。
(罗耀南《花儿词话》P118- 119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在河湟地区,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青海又是中国四大牧场之一,牛羊肥壮。牛皮用途颇为广泛,把牛皮泡软,打磨锞成条状,编制成绳,叫作“皮绳”;用麻类植物纤维编制成绳,叫作“麻绳”。皮绳比麻绳要结实,捆绑东西更牢固。这首“花儿”作品,就是用皮绳起兴的。上片是说两根皮绳结成一根,如果短了再续上半根,作者重点表达的不是皮绳,而是数字。上片数字的妙用旨在引出下片中男女双方对彼此的牵挂程度,在作者看来,我对你的牵挂满满当当,足足有十分,而你對我的牵挂连半分都没有。通过数字的妙用与比较,传递出了作者对对方的不满情绪。
一更里打点二更里鼓,
三更里锣儿响过;
一更里想你二更里哭,
三更里满炕上摸过。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25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花儿”中的一个重要修辞便是嵌数,上下片嵌入了相同的时间,上片写的是打更,侧重于声音描写;下片写的是相思,有心理描写,还有动作描写。从一更的打点开始,作者就开始想念情人;在二更时分,耳畔传来巡逻人的鼓声,作者仍然没有睡意,想情人独自哭泣;夜至三更,耳畔传来巡逻人的敲锣的声音,作者全没有睡意,对情人的思念也达到了制高点———“满炕上摸过”。“摸过”二字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后来的倾诉之作。这首作品巧用数字,将时间的更替与想念的程度紧密挂钩,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相思之苦。
六棱的栽花的花盆儿,
院子里种的是海纳;
小阿哥煨你者十七八,
七十的挂零,
八十的头儿上抛下。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49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花儿”也运用了嵌数修辞。上片用“六棱”描述花盆的形状。下片则完全是数字的运用,意思是作者从十七八岁便与心上人谈情说爱,从70岁再到80岁后,其中一个人去世,谓之“抛下”。通过数字的运用,表达了“小阿哥”白头偕老的美好爱情夙愿。
在南北朝时期,嵌数修辞就已出现,不论文人,还是民间,都喜用嵌数诗。河湟“花儿”也是如此,嵌数修辞凸显了“花儿”艺术的趣味性,语言表达更连贯,且富有节奏感。
11.复叠
为了强调某种意思,突出某种感情,有意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或句子,谓之“复叠”。复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词语自身的复叠、词语的复叠。
一是词语自身的复叠。是指这个词语中的字自身的重复。如:
燕麦杆杆溜溜儿光,
穗穗儿打秋千哩;
尕妹的身子是一炷香,
模样儿赛貂蝉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花儿专辑:湟中资料本》P24湟中县文化体育局民间文艺集成办公室1986)
灶爷板儿三寸三,
瓶儿里冇献尕牡丹;
名声背了个忽闪闪,
实心啦冇走上两天。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11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层层摞摞一卷经,
白纸上画葡萄哩;
偷偷摸摸一片儿心,
想你的谁知道哩。
(罗耀南《花儿词话》P91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大门前头的红青稞,
绿绿儿剌剌地折上;
要煨了煨下个学生哥,
稀奇儿剌剌地领上。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花儿专辑:湟中资料本》P5湟中县文化体育局民间文艺集成办公室1986)
上述作品中多处用到了复叠式词语。这些词语可归纳为七种:一是“AA”式,如杆杆。二是“AA儿”式,如穗穗儿。三是“ABB”式,如忽闪闪。四是“ABB儿”式,如嫩闪闪儿。五是“AABB”式,如层层摞摞、偷偷摸摸。六是“AA(儿)BB式”,如绿绿儿剌剌。七是“AB(儿)CC”式,如稀奇儿剌剌。河湟方言中,复叠式词汇形式多样,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就“AA”式词汇而言,不胜枚举,譬如:大大、妈妈、爸爸、爹爹、婶婶、娃娃等;房房、桌桌、凳凳、门门、椽椽等,刀刀、碗碗、碟碟、筷筷等,馍馍、饼饼、汤汤、水水等,背背、尖尖、弯弯、端端等,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类重叠词汇增加了山歌的音乐色彩,重叠词后面加“儿尾”,舒缓了语气,使得山歌更加亲切柔婉。
二是词语的复叠。指一个词语在一首作品中重复出现,如:
一道道云彩一道道雾,
雾罩了姊妹的巷道;
层层石头儿修成路,
哪一个月儿里忘掉。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9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豆儿圆来圆豆儿,
冇知道豆儿滚的;
肉儿尕来尕肉儿,
冇知道你把我哄的。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7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青丢丢的菜来蓝丢丢的水,
悬丢丢崖上的刺梅;
尖丢丢的鼻子圆丢丢的嘴,
欢丢丢儿的笑给。
(罗耀南《花儿词话》P82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一首“花儿”中“一道道”出现了两次,第二首“花儿”中“豆儿”和“肉儿”各出现了两次,第三首“花儿”作品中,“丢丢”出现了六次。这种一个词语的反复出现就是词语的复叠。复叠,似乎减少了表达的内容,其实包含着以少胜多的艺术辩证思想。从表达效果和受众程度看,越是简单的词语,歌手越能积蓄能量,成功地传递出深沉的情感;听众也往往能牢记这些关键词语,起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12.摹状
对事物的声音、形状、色彩作摹写,谓之“摹状”。
青石头磨儿嘎啦啦转,
红青稞搭不到斗里;
见我的花儿啪啦啦颤,
人多着托不到手里。
(罗耀南《花儿词话》P83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葡萄树叶上一汪汪水,
风吹时水动弹哩;
毛敦敦眼睛酒窝窝嘴,
说话时心动弹哩。
(罗耀南《花儿词话》P82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第一首作品的“嘎啦啦”“啪啦啦”是对事物声音动作的摹写。第二首作品的“一汪汪”是对水的摹写,“毛敦敦”是对睫毛的摹写,“酒窝窝”是對嘴的摹写,是对事物形状的摹写。摹状修辞使“花儿”作品更形象,更有趣,更有情致。
13.双关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语义和语音的条件,有意使语意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谓之“双关”。如:
大河涨水小河浑,
半边清来半边浑,
中间流成鸳鸯水,
浪水冲沙永不分。
(刘凯著《西部花儿散论》P56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这是一首保留在河湟“花儿”中的吴歌,吴歌多双关修辞。吴地七夕节,把一半清水与一半河水倒在一起谓之“鸳鸯水”。这首作品表面上说清水与浊水流在一起,形成“鸳鸯水”,即便“浪水冲沙”,也永不分离,实际上说的是男女之间的不离不弃,因此“永不分”具有双色彩。
黄河沿上的孤落雁,
石头上蹲给了两天;
双双对对的真好看,
单膀子活的是可怜。
(刘凯著《西部花儿散论》P56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河湟“花儿”中有的作品也延续了江南民歌特有的双关修辞,上面的这首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上片的“孤落雁”,表面上说的是落伍的孤雁,实际上在说孤孤单单一个人。下片是对民间俗语“单膀子鱼儿难浮水”的“花儿”语言的形象表述,“双双对对”表面上说的是一对对结伴游走的鱼儿,实际上说的是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单膀子”表面上说的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鱼儿,实际上说的是孤单无依的一个人。
14.示现
就是把不能实现,属于想象中的事物,描写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谓之“示现”。
提起个石头打月亮,
早打着娑罗罗树上;
唱一个“少年”了再嫑唱,
再等者明早的后晌。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41~242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的上片采用了示现修辞,“提起个石头打月亮”本身就很荒诞,“早打着娑罗罗树上”更具荒诞色彩。这样一种荒诞行为的发生,荒诞行为结果的产生,完全与想象有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夸张修辞,这种修辞手法在“花儿”中经常出现,非常有特色。
西瓜的瓤瓤解不下渴,
山高者遮不住太阳;
尕妹是樱桃者口噙上,
打一个呵欠了咽上。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97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的上片重点在“渴”字上,下片通过想象,把尕妹比作樱桃,打了一個呵欠,便把尕妹吞咽在腹中,达到解渴的功效,这首作品通过示现修辞,从一重虚拟走向另一重虚拟,实现了新颖奇特的艺术效果。
15.顶真
前一句结尾的词语作为后一句起头的词语,谓之“顶真”。“花儿”顶真主要有四种:
一是单字顶真。如:
风吹三场顶不下雨,
雨下哈庄稼儿长哩;
煨下十个顶不上你,
你给我精神儿长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189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的第三句的最后一个字“你”是第四句的第一个字,这就是单字顶真。
二是双字顶真。如
圆头儿铁锨改水哩,
改水者浇花儿哩;
我拿个实心煨你哩,
你有个啥法儿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11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去掉语气词“哩”,这首作品的第一句的最后两个字“改水”是第二句打头的词,这就是双字顶真。
三是三字顶真。如:
石头哈打在缸底里,
缸底里有嗡声哩;
“少年”哈唱在庄子里,
庄子里有连手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155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的第一句的最后三个字“缸底里”是第二句的前三个字,第三句的最后三个字“庄子里”是第四句的前三个字,这就是三字顶真。
四是正反顶真。如:
鸽子飞了鹰冇飞,
鹰飞呵铃铛儿响哩;
身子回了者心冇回,
心回呵咋这么想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189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第一句的最后三个字“鹰冇飞”是否定,第二句仍用这几个字打头,但变成了肯定“鹰飞”;第三句的最后三个字“心冇回”是否定,第四句仍用这几个字打头,但变成了肯定“心回”。这样一种一否定变肯定的顶真修辞为正反顶真。
五是特殊顶真。如:
眉毛弯弯一张弓,
弓一张,
箭射了天上的凤凰;
小妹妹生下的贤良人,
人贤良,
说一句话儿者稳当。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69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两担水”作品采用了一种新的顶真修辞,第二句“弓一张”是第一句句末“一张弓”的倒装,第四句“贤良人”是第五句句末“人贤良”的倒装,我们不妨把这样的一种修辞称作特殊顶真。
顶真修辞使得“花儿”的语言结构更富有逻辑性,语言起承转合,朗朗上口。
16.倒装
根据语法习惯、表达内容或音韵需要,颠倒词语次序,为之“倒装”。如:
天上的云彩地下的雾,
地湿者雾不散了;
尕妹是神仙者阿哥哈渡,
阴阳的路不断了。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4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作品中的“雾不散了”“阴阳的路不断了”采用了倒装,正常的语序应该是“不散雾了”“不断阴阳的路了”。
青铜烟瓶银哨子,
鲨鱼做下的套子;
阿姐们煨下的人梢子,
翻墙去好像个鹞子。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5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作品中的“翻墙去好像个鹞子”采用了倒装,正常的语序应该是“好像个鹞子翻墙去”。
“花儿”中的倒装修辞,有时是与当地人们的语法习惯有关,有时也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或音韵需要颠倒词语次序。第一首作品通过倒装,使第二句“地湿者雾不散了”与第三句“阴阳的路不断了”更加顺口;第二首作品通过倒装,使第四句与前三句一并呈现出“子”尾结构的“独木桥体”,形式更加整齐,音韵更加和谐。
17.讳饰
遇到忌讳的事物不便直说,而用旁的话来代替它、装饰它,谓之“讳饰”。如:
核桃的碗碗里照灯盏,
你有了油,
我有个缸壮的捻子;
庄窠的园圈转三转,
你有了心,
我有个天大的胆子。
(《花儿集·西宁演唱特刊》P125青海省西宁市文化馆1979)
上山的老虎下山来,
涧沟里吃一趟水来;
我好比蜜蜂探花来,
你好比牡丹花刚开。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59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花儿”是情歌,有些话不便直说,便采用“讳饰”修辞。第一首作品中的“核桃的碗碗里照灯盏,你有了油,我有个缸壮的捻子”与第二首作品中的“涧沟里吃一趟水来”都与性爱有关,不能直说,只能用旁的话来代替它、描述它。
18.反语
又叫“倒反”,说出来的话与表达的内容意思相反,多为讽刺语言,谓之“反语”。如:
西宁城修下的太高了,
它压了碾伯县了;
光面子话儿嫑说了,
隔肚皮人心见了。
(《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P28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1979)
这首作品的第三句“光面子话儿”指表面上好听的話语,这是反语,实指虚浮不实的语言。
蓝不过天来清不过水,
黑不过墨盒和砚台;
阿哥的身子比不上你,
你是个娘娘么太太。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9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的最后两句便采用了反语,“你是个娘娘么太太”是说“你不是娘娘也不是太太”,意思是女方的身份地位没有那么高贵,起到了讽刺的效果。
19.象征
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这种以物征事的修辞格谓之“象征”。象征可分为隐寓性象征和暗示性象征。
城墙倒了城在着,
城门哈麻杆俩顶着;
心里有了存在着,
十年八年的等着。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87- 88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这首作品中的“城墙”“城”与“城门”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城墙”高大坚实,是古代防御体系之一。墙倒了,城和城门尚在,即便用脆弱的麻杆,也要顶住城门,守卫颓废的城池,举措虽荒诞,信仰却忠贞。在这样一种信仰下,便顺理成章地有了下片“心里有了存在着,十年八年的等着”,爱情与婚姻就是“马拉松”,就是一座屹立不倒的“城”!
“花儿”中不乏象征之作,譬如“上山的老虎下山来,涧沟里吃一趟水来;我好比蜜蜂探花来,你好比牡丹花刚开。”“老虎”是男性的象征,“水”与“牡丹花”是女性的象征。
20.含蓄
意未尽露,耐人寻味为之“含蓄”。如:
瞌睡醒时自醒哩,
叫着醒来者咋哩;
你心里明白想开哩,
我把你说破者咋哩。
(《中国民间歌谣集成青海省大通县卷:大通花儿集》P215青海大通县文化馆1986)
“花儿”是情歌,大部分相对直白,但有些作品也很含蓄。这首作品的上片,以明白如话的说理,点出了“自醒”不必“叫醒”;下片说自己要想开要明白,没必要别人来“说破”,这就点出了做人做事必要的含蓄。
长江的水里摇桨哩,
桨杆儿顺水流哩;
别人不想想你哩,
我搭你有恩情哩。
(纪叶《青海民歌选》P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这首“花儿”的上片,表面上写长江中扳桨,实质上“水”与“桨杆儿”是性的象征,而这种象征本身就具有含蓄性特征。下片的“有恩情”含蓄地说明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十分密切。“花儿”中含蓄修辞的运用,使得“花儿”更有味道。
河湟“花儿”修辞手段多样,其中“示现”“顶真”等修辞,较之其他民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河湟“花儿”中,并非每首作品都运用了修辞。一首“花儿”作品中,有时出现一种修辞,有时出现多种修辞,各种修辞的成功运用,让河湟“花儿”绚丽多姿。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口头诗学河湟‘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15XZW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