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珊》:沉思往事立残阳
乔世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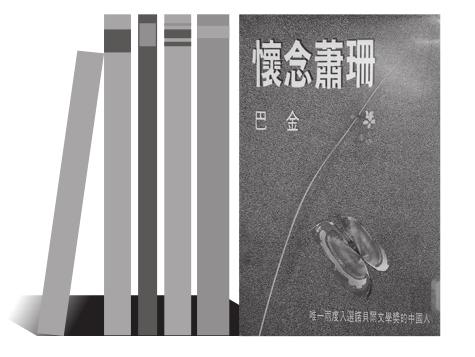
《怀念萧珊》是巴金缅怀爱妻萧珊之作。萧珊原名陈蕴珍,早年是巴金的一个读者,在巴金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和编辑活动,其翻译的屠格涅夫《阿西亚》《初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等作品得到巴金的欣赏:
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
萧珊与巴金1936年在上海第一次见面,此前他们已经保持了大半年通信联系,两人相恋8年后在贵阳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和谐,相濡以沫28载,1972年8月13日萧珊因患癌症去世。
“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这是巴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写作习惯。早在萧珊去世后两三天时间里,巴金就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但是每天坐上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来,“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是因为巴金感情匮乏吗?当然不是。“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语),感情正浓烈的时候,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岂是一纸素书就能够道尽说清的?萧珊从生病到去世的经历于巴金来说历历在目而又无比惨痛,再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回忆一番,这无异于往自己受伤的心灵上撒一把盐。
但是,积压在心里的话是迟早要爆发出来的,只是需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8月13日萧珊六周年纪念日便是触动巴金情感的关键时间节点,他从这一天起开始写作《怀念萧珊》,这篇总计九千余字的文章,巴金写得异常艰难,历时五个多月,直到1979年1月16日才写完,文章随后连续发表在1979年2月2日到5日的香港《大公报》“随想录”专栏上。

《怀念萧珊》中,巴金先后提到了四部作品,这些作品都和巴金、和萧珊的命运与感情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一部分,巴金提到了自己的《家》:
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
小说《家》中,觉新为封建陋习所限而未能见上瑞珏最后一面,因此生发很多自责和内疚;更令觉新代瑞珏感到不平的是,一向贤惠宽厚的瑞珏死后都已经“三七”了,高家长辈除了觉新的母亲和姑妈外就再没有一个人去吊唁过她,都生怕因此沾染上晦气,觉新因而有“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的愤慨之言。万万令巴金没想到的是,《家》中觉新和瑞珏所遭遇的命运,半个世纪后竟一语成谶似的在自己和亲人身上得到了活生生的现实搬演:就因为萧珊是巴金的妻子,她在患了重病后得不到必要的治疗,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才靠开后门住进了医院。我们自然能理解巴金此时的心情:“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怀念萧珊》的第三部分,巴金提到的又一部作品是自己刚刚阅读的梅林《马克思传》,书中马克思写给女儿的信件里提到马克思夫人临终的情形,有关描写令巴金印象异常深刻:“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巴金之能对这段话特别敏感,在于萧珊也有着一双“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并同马克思夫人一样也是死于癌症;要知道,当萧珊离世时,巴金等亲人不巧都不在她身边,作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人,巴金有许多话都没能向萧珊倾诉、没能同萧珊诀别送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成为巴金的终天之恨。尤其是当巴金意识到萧珊最后所说的“找医生”很可能是说的“找李先生”(萧珊平日这样称呼巴金)时,巴金对萧珊的愧疚更是无以复加,萧珊之死带给他的心灵创痛愈发难以平复。略略会让巴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在于萧珊弥留之际可能像马克思夫人那样并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
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巴金提到自己1939年三四月间出版的两册《旅途通讯》。在别人眼中这本书不足道:“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認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甚至巴金都不再打算出版旧作了,“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旅途通讯》之所以在巴金心目中保持着至高的位置,全在于这部书事实上记载了他和萧珊在抗战的紧张时期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的分散又重聚、相见又别离的生活经历。那段逃亡经历在巴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书中所收录的虽说“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旅途通讯·前记》)。而能支持巴金在彼时渡过重重难关的是“友情”:“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旅途通讯·前记》)毋庸置疑,“友情”中的很大一部分即来自于当时还是巴金恋人的萧珊。因此,这么多年间,巴金屡次翻看《旅途通讯》,实是在重温那段美好的感情经历,是在重新感受萧珊给予自己的精神鼓励,并因此而增添战胜困难、顽强生存的勇气:“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怀念萧珊》)当病情加重的时候,萧珊唯独没有想到自己,有的只是拖累亲人而生发的深深歉疚,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巴金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和在另一个病房里治疗的儿子,只是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才说过一句“我们要分别了”。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女人为巴金无怨无悔付出一切,该付出多么大的辛苦和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压力!正如巴金所看到的那样,萧珊始终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当萧珊的生命之火在一天天熄灭下去,作为丈夫的巴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而回天乏力,真是“世道沧桑不由人,生离死别惨难言”!
巴金如是评价在自己生命中打下深深印记的萧珊:“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对于能与自己分担寒潮风雷、共享雾霭流岚之人,巴金没有任何溢美之词,却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宣告:“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可谓对萧珊“我不会离开你”的爱之誓言的回应。生前,萧珊自始至终支持巴金,给予他莫大的勇气和温暖;逝后,其对巴金的精神慰勉依然鞭策着巴金:“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1984年1月21日,巴金还写作了《再忆萧珊》,那是病榻上的巴金记录前一晚上与萧珊梦中相见的泣血之作。正所谓“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作为一个情感型作家,巴金宣称:“只想把我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病中集·后记》)以《怀念萧珊》来说,这树生命之花就交集了巴金的百般情绪,有他对亲人的深切缅怀,有他对朋辈过早离世的惋惜,有他和妻子情深意笃相互搀扶的回首,有他对家人不安与愧疚的情感流露,有他对乱离之世人间真情在的珍惜,有他对伤痛与孤独的舔舐与品味,也有他对“四害”横行恶人当道的悲愤控诉。
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开设“随想录”专栏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谈〈望乡〉》,一如巴金所说:“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该文写于1978年12月1日,而《怀念萧珊》自1978年8月13日就开始写作,只是完成时间略晚(1979年1月16日)而成为“随想录”的第五篇;换言之,《怀念萧珊》实是《随想录》150篇文章中最先开始写作的一篇。我们可以说,要是没有爱人、亲人兼战友的萧珊的精神召唤、要是没有巴金对妻子深厚诚挚的情感,巴金是不可能拿出《随想录》这部拷问灵魂展示良知的世纪巨作,开启其晚年写作新高峰的。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