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场域与知识生产
——基于CiteSpace计量分析的对比研究
段永杰 徐开彬
一、引言
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迭代不可避免地带来交往方式与文化生产的急遽变革。国外学者最先提出将田野场域搬进互联网,并逐步完善网络民族志方法论建构。1994年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虚拟社区》的出版,标志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将网络空间作为研究领域[1]。在该研究成果启发下,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研究了网游玩家如何建构、使用在线身份,又怎样重塑他们的现实生活[2]。库兹奈特(Kozinets)于1997年提出“网络志”,认为它是传统民族志在网络空间交往与互联网文化生产中的阐释路径[3]。
由于互联网普及程度的差异,国内在网络民族志方面的研究相较国外稍晚。2002年,陈晓强提出“虚拟社群”概念,分析基于“人—机—人”的间接超时空互动方式,认为虚拟社群有利于弱纽带、高扩张群体环境的形成[4]。2004年,朱凌飞、孙信茹在论证虚拟田野时认为网络多媒体不仅便于展开调查,而且多文本、多链接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意义表达和阐释空间[5]。国内第一本网络民族志专著可追溯至2005年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作者从社区聊天室闲聊行为解析网络社区结构,提出网络社区公共管理规范的问题[6]。此后,国内运用网络民族志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多。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平台普及以来,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如何在大量中外文献中梳理出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脉络、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场域与知识生产存在怎样的异同?这些问题很难通过传统的文献梳理方法达成。而CiteSpace能将某一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与演进历程通过知识图谱进行直观呈现。本研究依托CiteSpace(5.3.R4),对截至2019年3月6日,与网络民族志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该领域的知识生产现状,总结、反思研究局限,并尝试提出其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
根据中外文献数据库收录文献的代表性、完整性,并结合CiteSpace软件数据库设置、参数特性等相关情况,本研究选取Web of Science作为国外文献检索数据库,在该数据库设置如下检索式“TS(主题)=(netnography)OR(cyber ethnography)OR(virtual ethnography)OR(online ethnography)OR(internet ethnography)”经过高级检索,剔除新闻报道、书评、会议通知等无效条目,得到有效文献752篇。选取CNKI作为国内文献检索数据库,设置如下检索式“全文=‘网络民族志’或含‘虚拟民族志’或含‘在线民族志’或含‘线上民族志’或含‘网络志’”,词频=2(全文至少出现2次以上检索词),剔除新闻报道、书评等无效条目,共获取有效文献216篇。国内外文献检索截止日期均为2019年3月6日。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软件的技术功能,对于各项参数进行如下设置:①时区分割“Time Slicing”设置为1996—2019,也即分析的时间是从1996—2019年。②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2,也即2年一分割,存在12个分段。③网络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作者、标引词、关键词。④阈值设置为TopN=20,也就是每年出现频率最高的20个术语。
通过以上设置,可将网络民族志自1996年第一篇文献出现至今,所有相关文献中出现频率在前20位的主题词、关键词等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呈现该领域关键知识节点、演变趋势、相互影响等可视图谱,多元动态地梳理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的学术场域与知识生产样貌。
三、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场域
(一)关键词与主题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分别按照CiteSpace识别的数据格式进行导入,选取“term”(术语)及“keyword”(关键词)进行分析,国内文献结果如下:N=33(节点数)、E=40(连线数)、Density=0.0758(密度);国外文献结果如下:N=247、E=1 114、Density=0.0367。如图2所示,三角形大小代表该主题词析出频次,各主题词之间线条粗细代表二者之间共现的强弱关系,节点间颜色变化代表文献发表时间的远近,密度数值代表主题词之间的关联紧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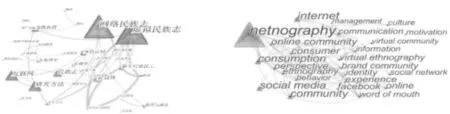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网络民族志关键词与主题词共现图谱
将图1知识图谱数据结果导出,得到表1。表中频次代表主题词在相关文献中呈现的次数,中介中心性超过0.1代表连接两个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表示节点的重要性较大[7]。
从图1和表1来看,国外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着重分布在netnography(314,0.07)、community(83,0.08)、consumption(78,0.10)等主题;国内该领域相关研究着重分布在虚拟民族志(19,0.37)、网络民族志(18,0.37)、研究方法(8,0.13)等主题。国内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网络民族志方法论相关引介与述评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异地迁徙群体的网络交往得到国内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另外,“微信朋友圈”“微信民族志”“微博”等新媒体社交网络空间成为较高关注节点。总体观之,国内网络民族志研究围绕方法论核心集聚圈的分支领域还未形成规模和热点,并且相关议题之间较少呼应与联结。这表明国内网络民族志研究还处于消化吸收阶段,相对分散、孤立地在网络空间进行有益思考与探索。
从国外网络民族志关键词知识图谱来看,研究主题较为多元,形成了以“卫生保健”“艾滋病”“药物使用”等节点组成的疾病医疗虚拟社群类议题集聚圈;以“市场营销”“品牌社区”“口碑”等节点组成的网络营销类议题集聚圈;以“青少年亚文化”“新部落”“反消费”等节点组成的网络亚文化类议题集聚圈;以“Meta分析”“产品研发”“网络信息计量学”等节点组成的网络开源技术交流类议题集聚圈;以“混合方法”“定性研究”“话语分析”等节点组成的方法论相关议题集聚圈;以“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节点组成的分享类虚拟社群相关议题集聚圈;以“网络成瘾”“第二人生”“后现代主义”等节点组成的网络伦理相关议题集聚圈;以“社会认同”“共同创造”“感知”等节点组成的虚拟社群协同创新类议题集聚圈;以“旅游业”“旅游体验”“迁移”等节点组成的网络文旅类议题集聚圈。整体上国外网络民族志研究较为活跃,各主题集聚圈相互联结颇为密切,初步形成了以方法论为基础,以多元主题互相勾连,以学术共同体协同创新为格局的网络民族志知识生产体系。
表1 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高频次、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排序

排序关键词(国外)频次中介中心性关键词(国内)频次中介中心性1netnography3140.07虚拟民族志190.372internet1000.04网络民族志180.373social media860.01研究方法80.134community830.08互联网80.145consumption780.10民族志60.056online community560.04新媒体50.017consumer560.06虚拟社区40.158online440.06新生代农民工40.009facebook430.02身份认同40.0110perspective420.03使用与满足30.08
(二)关键词聚类对比
聚类视图侧重体现不同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关键节点及重要关系网络。通过聚类,可以深度挖掘并直观展现该领域的交叉方向和热点。CiteSpace提供了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以评判聚类效果。一般而言,Q值在区间(0,1)内,Q>0.3就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当S≥0.7时,表明聚类结果令人信服,若S≥0.5时,一般被认为是合理的[7]。本研究通过LLR算法进行聚类,分别得到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主题聚类(见图2)。

图2 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关键词与主题词聚类对比
其中,国外网络民族志聚类图谱Q值为0.43(>0.3),S值为0.47(接近0.5);国内网络民族志聚类图谱Q值为0.64(>0.3),S值为0.45(接近0.5)。根据聚类原理,国内外网络民族志聚类图谱轮廓清晰,结构区划较为合理,同一聚类间信度较为可靠,总体聚类效果较好。通过分类整理,得到国内外网络民族志主题词主要聚类序列表(见表2)。
表2 国内外网络民族志主题词聚类分布序列表

聚类序号国外聚类主题词聚类节点平均轮廓值平均年份国内聚类主题词聚类节点平均轮廓值平均年份0互联网490.4892014青年亚文化140.81320161反消费主义400.4682012身份认同100.68320162价值共创390.6152013研究方法100.74920173自反性310.5942014互联网100.80120154旅游体验280.6972016扎根理论70.94520165质性研究220.7502013虚拟社区50.90820176决策过程180.7832014流行文化40.97120177感召力170.7542015后现代文化抒写30.87620168品牌社群150.7512014新闻生产20.93220179网络营销130.6892013受众展演20.8972015
根据CiteSpace功能原理,Cluster ID为聚类后的编号,聚类的规模越大,则编号越小。Size代表聚类中所含有的成员数量。Silhouette为衡量该聚类成员同质性的指标,数值越大,代表该聚类成员相似性越高。Mean Year代表该聚类中文献的平均年份,用来判断聚类中引用文献的远近。彼此相邻的关键词意味着它们经常出现在相同的文章中[7]。
表3 国内网络民族志主题类属分布

主题类属主题词类目节点青年文化网络泄愤、网络亚文化、乡村基督教、文化反身性、情感化游戏、自我暴露、爆吧军团、偶像工业、网络游戏、自我呈现、共意动员、亚文化仪式、网络表述、表情包、文化表达、文化腾挪、流行文化、全民直播、文化价值、粉丝经济、文化力等。身份认同自我认同、身份隐匿、身份建构、身份意义、中国志愿旅行者、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留学生、业余马拉松跑者、少数民族、跨性别者、身体社会学、劳工NGO、企业家、青少年群体、网络水军等。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方法数据采集、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实证研究、未知情同意、知识生产、内容分析、定性研究、一般经验方法、指标体系、定量研究、网络分析、系统论、社会研究方法、方法论、文献计量学、大数据、田野作业、田野调查、社会调查、质性研究研究趋势、前瞻分析等。互联网虚拟社区空间特性QQ群组、虚拟空间、相亲网站、微信群、朋友圈、少数民族社区、社交网络、新媒体、社交网站、新浪微博、跨媒体、自媒体、移动互联网等。互联网虚拟行为虚拟组织、媒介使用、民粹主义、内源动力、邻避运动、角色扮演、网络民族主义、外源动力、公民赋权、用户参与创新、商业爱国主义、人际交往、旅游者行为、教学交互、“帝吧出征”、抗争动员、赴日自由行、参与式同意、网游、课外学习、用户参与、口碑效应、社区参与、动员运动等。
表4 国外网络民族志主题类属分布

主题类属主题词类目节点互联网赋能规模流动、中日政治冲突、非正式学习、休闲、减少伤害、动机、自我管理、家庭度假、约束、精神疾病、在线抑郁社区、调解、赋权、分散机构创业、在线监管、异化、在线用户创新、职业培训、游戏教学等。网络消费意愿反消费、消费者抵抗、消费者行为、动机、消费者、主观性、社会阶层、场景、虚拟身份、后现代主义、情感支持、风险、分享经验、消费者权力、体验营销、在线营销、品牌社区、品牌管理、品牌忠诚度等。互联网意义生产与价值共创价值共创、决策过程、创新、实践社区、价值创造、实践、客户参与、众包、创意合作、开放式创新、用户创新、客户参与、客户参与行为、定制、客户间互动、开源软件、价值创造实践、产品开发、共同创造、变革性服务、服务主导逻辑、组织信任、消费者合作生产、协作实践、客户参与度、组织信任等。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定性方法、话语分析、混合法、共词分析、方法论、田野调查、研究设计、民族方法学、虚拟民族志、在线接收分析、社交网络分析、结构路线、媒体分析、消费者叙事、调查方法、多元方法、民俗方法学、访谈等。网络适应自反性反身性、内省、象征性互动、自我反思、真实存在、集体认知理论、极化、动机、共存、道德观念、可接受性、社会规范、自反性、新兴现象等。
通过对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主题词聚类结果进行整理、对比,可洞悉该领域国内外研究热点。通过表2发现,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在主题词聚类序列中,共同出现的有互联网和质性研究方法两类,除此之外,国外主题词聚类规模由大到小为:反消费主义、价值共创、自反性、旅游体验等。国内主题词聚类由大到小为: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扎根理论、虚拟社区等。将以上聚类序列主题词进一步并属归类,总结出国内外网络民族志重点主题类属分布(分别见表3、表4),整体直观地呈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主题内容。
四、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的知识生产
为了便于研究者从微观层面把握网络民族志知识图谱的肌理,本研究在参考主题类属的基础上,分别对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相关文献进行主题分析,梳理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各自特征和创新扩散情况,在联系与比较中呈现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知识生产图景。
(一)国内网络民族志研究内容
1.青年文化相关网络民族志研究
通过图2可以看出,青年亚文化这一主题处于核心位置。本研究将聚类分布列表中与“青年亚文化”较为类似的主题聚类“流行文化”进行合并,形成“青年文化”主题类属,通过对相关类属来源文献进行爬梳,获取这一主题类属主要包括网络亚文化、文化表达、文化工业等核心主题。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梳理出这一主题类属包括的主要内容:
(1)粉丝群中的青年网络文化表达。虚拟社交网络将志趣相投的粉丝联结在一起,粉丝成员由零散孤立的个体集聚成为成员庞杂却又组织井然的网络群体。粉丝群体的身份构建、虚拟迷群形成、网络粉丝实践互动等无不表达群体的情感和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时获得群体认同感、归属感[8]。在迷群个体看来,成人感需求的满足以及通过彼此价值观认同建立的仪式和表征是他们心灵的美好寄托。从迷群文化的文本生产行为与动机来看,迷群内部成员所构建的话语体系更独立,宣泄情感成为迷群文本生产的意义和目的[9]。
(2)网络直播中的青年文化呈现。网络直播作为虚拟视觉传播文化呈现方式,其视觉表达使得身体“在场”打破传统传播形态时空的局限,用户通过实时网络界面进行互动,以特定直播场景和观赏互动建构网络新部落的在线场景,形成强交互性虚拟在场体验。网络主播以身体传播获得在场意义和彼此认同,这种通过即时传播、在线表演和打赏互动的网络新部落空间,是青年亚文化人群借以表达自身价值,获得圈内认同,结成文化群体的网络场所,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网络视觉技术制造“景观”以吸引社会注意,表达“疏离”以求对主流文化叙事框架进行改造或颠覆,从而在日常“无意义”中寻求其特定“意义”,并试图从“弱抵抗”的行动取向中,将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的亚文化通过低成本制作、非常规叙事等方式进行合理化,以此成为互联网话语权的掌握者[10]。
(3)弹幕中的青年文化工业。“弹幕”本质上是青年群体借数字媒介,对文化工业产品进行解构和重组,通过符码生产等方式实现意义建构的。研究者主要通过网络民族志对弹幕中的文化生产过程和意义建构进行考察,认为由弹幕产生的青年亚文化带有商业性。在这场数字狂欢中,文化消费的欲望激发文化符号的设计者不断有意识地创造时髦的青年亚文化新符号[11]。弹幕符号转译中,用户沉浸在文本互动带来的娱乐狂欢之中,与此同时,通过主体间数字消费经验和符码审美体验,在使用与满足、共情与涵化的基础上逐步建构用户群体的区隔。
2.网络社会中的身份认同
网络社会具有类似现实社会交往的功能,线上身份认同的形塑与凝聚便是这种社会功能的体现。在这一主题类属上,国内网络民族志集中于虚拟空间中跨性别者、新生代农民工、少数民族等群体在网络交往中的身份认同、身份建构等话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同性恋群体网络交往中的身份认同。随着移动社交APP的发展,以往经常处于隐匿状态的同性恋群体开始通过虚拟空间呈现身份认同,互联网的连接改变了LGBT群体的身份认同方式,从被建构的少数群体到利用互联网空间开展社群活动。LGBT网络社群将其活动空间再生产为新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实践,使“身份认同”延伸为政治参与和权益平等等现实议题[12]。分性别来看,身份认同对于女同性恋群体而言,网络空间的虚拟化使得她们更容易释放自我,寻求公开身份,在认同中表达情感,获取理解支持。对男同性恋群体来说,匿名的虚拟表达促使身份认同转换为自我脱敏、压力缓解等性状。
(2)新生代农民工在网络交往中的身份建构。手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叙事系统。依托手机的社交网络服务,原本沉默的新生代农民工得以自我表达,恢复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中受到抑制的个体性和自主性。新生代农民工在虚拟空间能够获得自我社会身份建构,在现实身份与虚拟身份交织中形成全新的“自我”形象[13]。在这一群体自我社会身份建构过程中,人口结构性因素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人口结构性因素以教育程度、行业和单位属性的影响较为突出,互联网使用因素以网络操作技能的影响较为突出[14]。在地域差别方面,同地熟悉群与异地熟悉群之间没有本质差异;而同地不熟悉群的日常交往,则凸显城市的功利性交往。相对而言,前者容易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抱团意识,后者更容易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入[15]。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网络中形成的文化身份无法为其现实政治经济处境赋权,相反商业媒体对其网络亚文化现象具有收编和利用的作用[16]。
(3)趣缘群体在网络交往中的身份意义。移动趣缘类社交APP的兴起,为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分散个体提供网络联结的平台,各类网络趣缘社群的线上身份意义也成为网络民族志关注的热点话题。霍兴彦等通过对线上跑者社群的研究发现,跑者互动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体在其群体中的“地位”有关,个体对跑者身份的确认是通过互助与冲突等不同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17]。孙萍通过对网络“御宅族”的研究,认为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进行建构。同时,身份认同会产生跨国界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主要表现为对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观等不同文化因素的认同[18]。廖杨等通过对微信朋友圈的研究,认为“朋友”在微信场域中具有多重身份认同。通过多样化的象征符号及其表达,微信朋友圈的即时互动和超地域性使其具备了现实朋友圈难以企及的社会资本动员能力[19]。
3.网络虚拟空间行为呈现与公民赋权
网络空间行为作为一种虚拟互动场景,颠覆了现实社会交往过程中前台后台的区隔,使得用户欲望的表达和真情的流露更为直接开放,这种状况也为网络行为呈现与公民赋权提供了交流空间。国内研究者运用网络民族志对线上互动和赋权行为的研究较为深入。
(1)虚拟空间自我呈现。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技术条件正逐步重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青年群体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多表现为“理想化”的表演,主要表现为凸显自我意识,加强社会交往,拓展社会资本[20]。黄燕华认为互联网上的自我呈现可分为自我满足型、社会资本型和策略型。自我满足型更趋向于感性,策略型更倾向于理性,社会资本型则介于二者之间[21]。
(2)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与动员。网络虚拟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线下社会空间的影射和分化。张宁发现表情包作为一种传播符号,在网络互动中通过拼贴、恶搞等复合制作手法消解文本的原有意义;“表情包大战”所呈现的“抵抗的弱化”和“政治的消解”,换取特定意识形态在网络青年群体中的持续存在[22]。董阳通过研究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发现极化背后往往牵连社会情境线索,在议题演化机制的作用下,网络舆论的演变促进了公共空间的衍生[23]。在网络动员方面,陈先红通过探讨微博对草根社会运动组织的影响,发现草根社会运动组织间合作对抗争网络的构建和持续性社会行动的维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4]。
(3)网络虚拟空间公民赋权。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日常生活场景成为社会互动的不竭资源,这一过程也强化了公民赋权的渠道。新媒体的赋权行动可以借助“网络围观”的外部间接力量,以及通过@传统媒体及网络大V等功能借用资源,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形成社会合力,达成组织赋权和社区赋权的目的[25]。微博等社交媒体也为环保公益组织线上动员实现了网络赋权,在社会动员的话语框架和活动框架中塑造共意的情感空间,形成常规的日常行为,从而发挥将全民组织化并引领持续性社会行动的作用[26]。郑雯发现,微博空间更多地呈现出“公共空间”而非娱乐化空间的属性[27]。微信群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赋权时,一方面,线上交往形成的群体感促进了工友之间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低廉的信息传播进一步固化“内卷化”趋势,进而加深外来工群体独立又孤立的生存状态[28]。
(二)国外网络民族志研究内容
1.网络意义生产与价值共创
网络意义生产与价值共创体现在通过超越组织边界的共同创造,来获取外部知识、技能和创意。开放式创新、虚拟众包、虚拟共享正在成为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前沿。国外学者多方位研究网络用户在各类虚拟社区场景下的意义生产与价值共创实践。
(1)虚拟实践社区的开放式创新。虚拟社区的结构属性和共享机制提供了知识与技术交流的动态场景,并使得“混合型”开源软件等开放式创新成为可能,这类跨时空即时互动平台有利于知识的整合集成和技术交流创新[29]。塞西莉亚·卢雷罗·科克林(Cecilia Loureiro-Koechlin)通过研究开放式软件创新运作,发现开放式创新生产主要受虚拟开发环境、虚拟开发协作和复杂商业组织管理等因素影响[30]。杰维克(Jawecki)通过Enlightened-Swarovski Elements手表设计大赛“创新社区”的案例,发现开放式创新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虚拟创意人员与目标用户的产品观念对接,还取决于虚拟创新社区高效协作的组织管理[31]。在创新过程管理方面,蒂齐安娜·鲁索·斯佩纳(Tiziana Russo-Spena)通过研究10家公司的虚拟环境创新实践,提出了“5 Co-s”模型,包括共同构思、共同评估、共同设计、共同测试和共同发布,每个创新阶段都离不开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动态交互[32]。
(2)虚拟众包与共享。虚拟众包与共享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使得公司或组织利用虚拟群体的力量,化整为零地分摊运营成本和市场风险[33]。安妮·索伦森(Anne Sorensen)通过研究众包组织如何通过社区帖子创建共同小组,发现使用帖子专用网络语言能有效地吸引成员参与价值共同创造,成员之间的分享和转推有助于加强社区凝聚力[34]。尼古拉斯(NicholasInd)研究虚拟组织如何使用众包来创造价值,认为用户参与虚拟众包是因为它能提供表达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机会[35]。亚历山大·布雷姆(Brem Alexander)通过对24个众包项目的分析,认为众包可以提供以网络潜在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来证明投资合理性[36]。
2.虚拟品牌营销与网络消费行为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世界各地消费者可自由地分享生活经验,从而影响彼此的消费观念和购买行为。这种情况给品牌运营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为研究者运用网络民族志进行虚拟品牌营销与网络消费行为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场景与个案。

(2)网络购物与消费者在线行为。随着互联网走向日常生活,网购消费者的在线互动也成为价值创造的新场景。哈米德·贾法里(Hamid Jafari)研究了自行车零售中零售商和消费者如何互动来探索定制的过程,认为新技术、分销创新以及社交媒体互动等在为消费者提供购物体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零售商依靠消费者的反馈来改进他们的规划和实施流程,忠诚和积极的网络口碑源自共同创造的互动体验[40]。田小丽(Xiaoli Tian)通过对网络购物网站淘宝的研究,认为消费者不仅因为价格和便利而更喜欢网购,而且因为喜欢其中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赋予客户更多的自主权;与实体店相比,网购消费者感觉压力更小,并减少了情感劳动[41]。杨泰德(Ted Yeo)通过分析消费者在社交媒体的对话,认为消费者在虚拟交际过程中构建绿色产品的健康形象,成为价值和意义的共同生产者[42]。
(3)虚拟营销与客户管理。随着线上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商家也逐步重视互联网虚拟营销与客户管理。罗伯特V.科兹涅茨(Robert V.Kozinets)发现在线营销环境具备尊重消费者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使消费者与商家可以更好地直接沟通[43]。裴俊熙(Joonheui Bae)通过研究网络消费的信息共享不平衡问题,认为消费者倾向于使用低评级和负面评论作为获取更多信息锚点的策略,当评级很高时,消费者更倾向于使用客户协作消费平台来确认信息真假;当评级较低时,消费者倾向于相信这一结果[44]。博迪尔(Bodil)分析虚拟营销信息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究竟改变了什么,认为营销人员越来越多地尝试使信息到达并“感染”社交媒体用户。病毒传播过程的“不可控性”造成不可预见的话语意义,这种话语意义的再生产可能已经改变和超越原始信息[45]。
3.互联网知识生产与数字赋能
移动互联网的推进,使用户在满足社交、娱乐的同时,逐步向知识生产和数字赋能方向转变,无论是保健认知素养的提升,还是终身在线学习理念的深入,都能激发用户在社交媒体中创造有意义的使用体验。国外研究者运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对此做了积极回应。
(1)强化保健认知与健康医患关系管理。线上论坛对于医患双方理性认知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对于强化病人的保健认知和促进医患关系上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德鲁·福斯特(Drew Foster)探讨了患者之间的在线建议和知识交流,认为隐性医疗保健知识构成了患者赋权的有力来源,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所需的医疗,并与医疗专业人员和机构进行议价协商[46]。莎拉·肯德尔(Sarah Kendal)研究了心理健康失调的年轻人如何使用公益慈善机构管理的社交媒体以获取信息、建议或支持,发现在线论坛上的同伴支持和帮助有利于预防心理疾病的复发[47]。彼得·梅拉赫斯(Peter Meylakhs)通过研究俄罗斯最大的艾滋病线上社区,认为医疗保健工作者应该采用更复杂和更有针对性的方法,从而实现多样化的艾滋病预防[48]。
(2)虚拟同步学习与职业发展。虚拟同步技术使得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习者联系在一起,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实现了赋能。加西亚·德尔乔(Angel Garcia del Dujo)认为虚拟技术将不同时空的学生作为一个团队凝聚在一起,此时学生会重新调整他们的学习习惯和行为策略,同步交互成为自主学习的一部分[49]。玛丽亚·卡门·里科伊(María-Carmen Ricoy)研究了推特在高校学生中开展的活动,发现因为交互性与分享性,学生通过推特参与受教育过程逐渐增加,通过分享展示,他们感觉更有动力[50]。林忠轩(Zhongxuan Lin)通过研究数字资本主义中的非物质劳动,认为基于非物质劳动建立的情感社区赋予人们“家庭和归属”的集体情感,并为他们提供了积极人生态度[51]。
(3)旅游休闲过程中的在线分享互动。旅行者在旅游休闲的准备、体验、回味过程中,通过社交媒体与在线用户进行互动、分享旅行体验,已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法特梅赫·萨贾迪安(Fatemeh Sajjadian)研究了旅游分享网站tripadvisor.com上的互动,认为社交媒体为旅行者提供了赋权,他们可以相互分享知识、观点和经验;影响游客对景点评价结果的因素主要有风景、文化、安全、好客度等[52]。拉利斯·钱德拉勒(Lalith Chandralal)通过对旅行者使用旅行博客叙述难忘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认为旅行者积极的旅游体验通常与6个主题相关: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个人的难忘经历、共享经验、新奇感知、感知的偶然性、专业指导及旅游运营商服务、与难忘体验相关的情感[53]。王旺飞(Wangfei Wang)通过对158个在线博客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成年子女与父母假期旅行的动机主要包括健康出行、庆祝梦想实现、家庭团聚和融洽关系、表达孝道等;这些动机可分为以父母为导向、以家庭为导向和以自我为导向,并反映出中国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家庭角色的连续性[54]。
五、网络民族志研究的反思
整体而言,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已基本成熟,研究面向日趋丰富与多样,研究领域逐步细化和深入。特别是紧随互联网流动空间带来的知识共享与扩散,在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开展研究方面较为活跃。另一方面,反思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现状发现,优缺点同时存在。网络民族志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增强理论关照、拓展研究场域。
(一)亟须拓展本土经验创新
横向比较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现状,总体看来,国外较早具备成熟的方法理论体系,能够将这一方法运用在网络空间交往的多种场景。国内网络民族志研究虽然发展较快,但基本上囿于国外已建立的方法理论体系,缺乏独特的基于本土经验特征的方法论创新。在方法论层面的“网络民族志”引进以后,基于少数民族群体多样化、网络空间环境差异化、社会治理体系特色化等独特研究场景,国内网络民族志理论体系本应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但无论在理论演化、研究伦理等学理层面,抑或研究方法、操作步骤等应用层面,本土研究均未能突破国外所设框架。正如郭建斌所言:“对于网络民族志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方法层面,必须超越这个层面,针对新对象,提出新问题,进而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回答。”[55]
(二)尚待融合多学科交叉图景
通过对发文期刊进行比较,发现国外网络民族志研究成果均匀地分布在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期刊,国内该领域成果多集中在传播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少数几个学科刊物。这一现象与发文作者的学科出身相照应:国内该领域发文作者较多地来自传播学、人类学等少数学科,国外作者在学科背景方面较为多元。通过对研究方法的运用来看,国外除去单一地使用“网络民族志”这一定性方法之外,较多地结合话语分析、叙事分析、扎根理论、定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交叉使用。国内较为集中使用一种研究方法,较少使用混合法开展研究。国外该领域近年来在虚拟品牌营销、价值共创、开源共享等社会热点领域均有涉猎。国内较多地集中在研究方法、网络身份认同等基础理论探讨方面。总体来看,国内网络民族志学术场域较为单调,尚待融合多学科的应用。
(三)需要跟上急遽变化的虚拟空间场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人机交互等技术逐步进入现实生活,必然产生新的网络交互场景。它们日益影响社交行为和传播样态。过去的“虚拟社会”等概念也将越来越“实体化”,从而被“网络社会”等话语方式所替代[56]。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均未从学理层面论证该领域方法理论体系的变革及可能走向。面对网络社会变革,这种以传统互联网社交思维去应对新型空间场景、以传统网络社交体验去研究虚拟现实用户、以不变应万变的固化思维将会导致网络民族志方法丧失理论旅行的活力,也必然导致研究思路的陈旧、研究问题的弱化。因此,怎样适应虚拟空间场景的移位,何以在创新发展中完成方法理论体系的完善,有待学界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