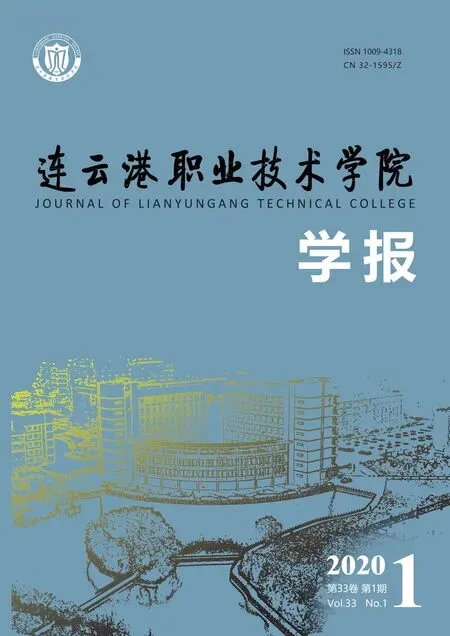《系年》申公屈巫适秦求师考
尚 洁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记载楚庄王杀夏征舒一事:“庄王立十又五年,陈公子征舒杀其君灵公,庄王率师围陈。王命申公屈巫适秦求师,得师以来。王入陈,杀征舒,取其室以予申公。”[1]170其中申公屈巫向秦国求师一事,为传世文献所未见。同时,多部传世文献中提到此次伐陈有诸侯国协助:
夏征舒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2]724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2]809
征舒弒灵公,楚庄王以诸侯讨之,而灭陈。[3]492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征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4]1910
对此,程薇认为这是对传世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让我们知道楚庄王伐陈是与秦军共同行动的[5],也就是说,传世文献记载的“诸侯”包含秦国在内。而《正义》认为“诸侯”为楚国属国,“经无诸侯,而云以诸侯讨之,诸侯皆庆者,时有楚之属国从行也。……明此时亦有诸侯,但为楚私属,不以告耳”[2]724。如果秦国在当时为楚之属国,那么出土文献《系年》的记载自然是对传世文献的补充,否则,二者之间的分歧则无法弥合。笔者认为“王命申公屈巫适秦求师”一事有待商榷,结合《系年》的史料来源及生成路径对此事的真实指向进行探析。
一、对“申公屈巫适秦求师”一事的合理性商榷
在当时,秦国与楚国存在何种关系,它是否有必要随楚入陈?依照当时楚国的国力又是否需要向秦国求助?这是我们探究“申公屈巫适秦求师”这一事件的合理性需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秦国无出师助楚之缘由
楚庄王与申叔时的对话中提到“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这揭示了楚国控制或管理所辖疆域的两种方式,一是存其国,纳为附庸,二是灭其国,设置县邑。附庸关系通过盟会的形式缔结,附庸国就是其所依附国家的属国。他们保留自己国家的社稷、君统,但是需要依附于大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受限。观《左传》用语,申叔时说“君召诸侯”,《说文解字句读》释“召”字,“泘也,《书·甘誓》‘乃召六卿’”[6]47。“召”字具有明显的上下属含义。所以,“诸侯”与楚庄王之间不是平等对立的关系而是臣属关系。
然而从政治地位上来看,秦国是楚国的与国而非属国,二者之间是平等友好关系而非依附臣属关系。同盟国有属国和与国之分,和楚国有附庸关系,国力微弱,需要依附楚国生存的是其属国,实力强劲又和楚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是其与国。自秦穆公时期,秦楚两国便以姻亲为系建立了联盟,即所谓“绊以婚姻,袗以斋盟”[7]649。秦国当时积蓄已久,企图东进中原,楚国也已称霸江汉,谋划北上,而两国又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晋国,因此结为盟国共同抵御晋国。一直到秦孝公施行商鞅变法前,两国都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友好的盟邦关系。
作为与国,秦国在楚国处于危难之际时确实会出兵相助,但是要基于利益判断。《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庄王三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2]649,而“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2]651。秦国联合巴国出兵助楚,灭了庸国。就此事分析,秦国出兵有两大前提条件,一是楚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抵御外敌,渡过难关。二是对秦而言助楚拿下庸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战略安排。饥荒是为内忧,群蛮叛楚、庸麇伐楚是为外患。秦国作为与国,出兵助楚一方面出于盟友道义,另一方面是因为庸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王夫之在《春秋世论》中论述此事:“庸者,秦楚之争地也。……得庸不有而授之楚,秦之亲楚何其至也。秦楚之相亲,晋故焉耳。秦戒晋,而楚挠其南,则晋掣。楚争晋,而秦捷其西,则晋疾视楚而不敢争,故秦之谋此甚深也。……抑秦唯委庸于楚,而后楚无忌于秦。……戎蛮尽,山木刊,道路通,发踪相及。秦之烧夷陵以灭楚者由是也,楚之余民扣武关以亡秦者由是也。故庸之灭,秦楚之大司也,而秦人之谋深矣。”[8]443可知秦国助楚夺庸有两个目的,一是借此压制晋国,二是消减楚国的警惕心,战国时秦国可以火烧夷陵而灭楚,亦源于此。
再看此次楚庄王讨夏征舒之时,楚国兵力强劲且占据主动位置,师出有名,局势一片大好,并不需要秦国相助。而且楚国拿下陈国对秦国而言并非一件好事。清人高士奇曰:“夫先世带砺之国,棋布星罗,南杆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者,最大陈、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黄,其次唐、邓,而唐、邓尤僻处方城之外,为楚门户。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9]659-660可知陈国是楚国北上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楚国突破这道防线后,入主中原,指日可待。那么秦楚两国之间的平衡便会被打破,楚国会成为秦国的一大隐患。
传世文献中所提到的“诸侯”与楚庄王之间有明显的臣属关系,而秦国又非楚国的附庸,加之对当时局势的考虑,秦国可以助楚灭庸,但没有必要随楚师讨夏征舒。
(二)楚国无向秦求师之必要
首先,从楚、陈两国的综合国力来看,陈国不足以与楚国抗衡。春秋初期,陈、楚并无过多联系,至鲁僖公十九年,陈、郑、楚、蔡盟于齐,陈楚两国开始建立政治同盟关系。僖公二十一年,陈国参加了宋国在盂地组织的盟会而得罪楚国。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2]467。僖公二十五年,“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2]488。陈楚两国原本相对平衡的联盟关系发生倾斜,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的逐渐拉大,陈国渐渐臣属于楚国。楚庄王即位后,灭庸、糜,稳定西疆;灭若敖氏,巩固王权;伐舒蓼,划定疆界;盟吴越,安抚东方。而陈国因其位于南方楚国与北方中原诸国的临界地带,卷入晋楚争霸之中。宣公元年,楚国联国伐陈,晋赵盾救陈,“陈共公之卒,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秋,楚子侵陈,遂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宋”[2]678。宣公五年,“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2]705。陈国两面受敌,处境艰难。至宣公十一年楚庄王杀陈夏征舒之时,楚国实力已臻及鼎盛,陈楚实力悬殊极大。
其次,楚庄王此次出兵以讨伐乱臣贼子为号,乃是正义之师,不会有别国诸侯前来阻拦,加之有公孙宁、仪行父在陈国的势力相助,诛杀夏征舒并非难事。《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楚庄王“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2]724。这表明楚庄王最初只欲讨贼,无意灭陈,最起码能消减陈人的警戒心,其入陈并未受到强烈抵抗。又杜预曰,公孙宁、仪行父“能外托楚以求报君之雠,内结强援于国,故楚庄王得平步而讨陈,除弒君之贼”[2]722。公孙宁和仪行父作为陈国的大夫,且与国君交好,在国内必然有其利益团体,与楚庄王里应外合,使楚师入陈如履平地。
最后,在军事上楚国的属国有随军出战之义务。自西周晚期以来,楚人便扩疆启土,随着实力的强劲,北上争霸中原,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南部以及江淮流域的一些小诸侯国成了楚国的附庸,附庸国在其所依附的大国有需求时要应召出征。《左传》里有所记载:宣公十二年邲之战中,唐侯为左拒,“使潘党率游圈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2]747;昭公四年,蔡侯、陈侯等随楚伐吴,“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2]1369;昭公十七年长岸之战,使随人守舟,楚“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隋人与后至者守之”[2]1578;昭公二十三年,吴楚鸡父之战,顿、胡、沈、蔡、陈、许助楚参战,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己,是以来”[2]1652。在这些战事中,都有楚国附庸国的身影,他们便是传世文献中楚庄王口中的“诸侯”。因而在两国实力悬殊极大、入陈难度系数极低且又有附庸国相助的情况下,楚庄王讨夏征舒并不需要特意使申公巫臣向秦国求师。
二、对“申公屈巫适秦求师”一事的实际指向探析
从秦、楚两国的实际情况着手考量,楚庄王在讨夏征舒时并不需派申公屈巫适秦求师,而随楚入陈的诸侯指的是楚国的附属国,自然也不包括秦国,所以,“申公屈巫适秦求师”一事可谓子虚乌有,那么《系年》中此句的真正指向是什么呢?《系年》的编者又是因何将此句错置于此?
(一)楚人适秦求师
从史料来源来看,《系年》中文献吸收了民间口传资料。杨博认为,“《系年》采撰史料涵盖西周王朝记录、春秋战国史官实录以及流行的春秋战国故事等三大部分”[10],即《系年》中既包含官方的史书记载又含有民间的口传资料。而这种口传资料往往在保留事件主干的基础上再附加历史背景和人名[11]324,在此过程中便容易出现历史误植。“申公屈巫适秦求师”是进入《系年》之后的面貌,语法结构上呈现为“S+V1+V2”(主语+动宾+动宾),在流传的初始阶段,故事背景及“S+V”三个核心要素可能都十分清晰,但是在流传过程中,“S”(主语)和故事背景逐渐模糊混乱,只有核心事件完整保存,那么它在被采录进史书《系年》中时,就再构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非常容易出现背景和人名误植的情况,从而导致历史失真。由上文可知,“适秦求师”一事不可能发生在楚庄王入陈讨伐夏征舒之时,那么将“申公屈巫适秦求师”抽象为“楚人适秦求师”,或可寻找出真相。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国大举进攻楚国,攻破其都城郢。危难之际,楚人“申包胥如秦乞师”,他“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2]1793-1794。从二者的句式和文义上来看,《系年》“适秦求师”与《左传》“如秦乞师”如出一辙。二者均为连动式结构,且在《左传》的文献记载中,“求师”与“乞师”同义。《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2]865“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在文中的另一种表达是“郤子……受命以求师”,“乞师”可用“求师”替代。据笔者统计,《春秋》经传表达向他国求助借兵之义时多用“乞师”而非“求师”,书中共计21次提到“乞师”(成公十六年出现三次,僖公二十六年、成公二年、成公十三年、成公十八年均出现两次,隐公四年、桓公六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十三年、昭公二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二十四年各出现一次),仅成公十三年一次言及“求师”,且出现于孟献子的口头话语中。可知“乞师”为正式书面术语,而“求师”多具有口头性。
《系年》用“求”而非“乞”,也暗示了其文献来源的民间属性。那么“申包胥如秦乞师”一事在民间几经流传后发生史实错乱衍变为申公屈巫适秦求师,并由编者错置于《系年》中也就形成其发生的路径依据。因而,“楚人适秦求师”确有其事,只是其事件发生于楚昭王时期而非楚庄王时期,楚人指申包胥而非申公屈巫。而究其错误原因,时空的错乱应是由于民间口传导致人名的混淆产生的。
(二)申包胥之“申”与申公屈巫之“申”
“申公屈巫”与“申包胥”之间的混淆错误是由姓氏衍生出的。申公屈巫本为屈氏,但成公二年,屈巫借出使齐国之机,携夏姬奔晋,后不复以屈为氏。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七真》云:“申公,春秋时楚僭王号,其县尹皆称公。……巫臣,字子灵,谓之申公巫臣。其后或以申公为氏。《风俗通》止言‘巫臣之后’,又曰:‘汉太子傅申公。’误矣。巫臣尽室奔晋,申公止姓申氏。”[12]89申公屈巫(即巫臣)由屈氏变为申氏一支,可谓明了。唐林宝《元和姓纂》释申氏:“姜姓,炎帝四岳之后,封于申,号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时,有申公巫臣、申包胥、申亥。”[13]367明确说明申公屈巫与申包胥同属申氏。岑仲勉先生在校记中说:“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13]367又将申公巫臣与申舟同列于申氏之下。所以,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误将同属申氏一族的申包胥如秦乞师一事安置在了申公屈巫身上。况且,在《系年》中围绕“申”这个姓氏发生的错误不只此处,第十一章便误将申无畏记为申公叔侯。
《系年》记载:“宋公为左盂,郑伯为右盂,申公叔侯知之,宋公之车暮驾,用抶宋公之御。”[1]160而《左传》文公十年记此事为:“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2]611其中,《左传》之“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与《系年》之“宋公之车暮驾,用抶宋公之御”为一一对应关系,均记载了宋昭公违背命令致使其仆人被笞打且在全军面前示众一事,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左传》中所记实施惩罚的为申无畏,而《系年》中记为申公叔侯。杜预注此事曰“为宋人宣十四年杀子舟张本”[2]611-612,子舟即申舟,即申无畏。《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庄王派申无畏出使齐国,“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2]760,为宋人所杀。同样,《系年》第十一章在记载笞打宋昭公仆人之后紧接着便书“申伯无畏聘于齐,……宋人是故杀申伯无畏”[1]160。从事件的前后关系考虑,只有得罪宋昭公的人是申无畏,二者之间的衔接才合理。因而,综合《左传》与《系年》来看,与宋昭公有仇确有其事,宋人因仇杀申无畏亦确有其事,所以,当从《左传》之说,“抶宋公之御”者应为申无畏而非《系年》所记的申公叔侯。
综合来看,《系年》中的错误与申氏姓氏的复杂性密不可分。楚国与“申”相关的姓氏有申氏、申叔氏和申公氏。邓名世释“申氏”:“伯夷为尧太岳之官,封其后于申。楚文王灭申以为县,其后以国为氏,楚大夫申侯是也。”[12]84释“申叔氏”:“出自楚。大夫食邑于申而字叔,谓之申公叔侯,因为申叔氏。”[12]89《左传》中称申氏者有申无畏(文公十年)、申犀(宣公十四年)、申骊(成公八年)、申无宇(襄公三十年)、申亥(昭公十年)、申包胥(定公四年)。称申叔氏者有申叔时(宣公十一年)、申叔展(宣公十二年)、申叔跪(成公二年)、申叔豫(襄公十一年)等。杜预认为叔时、叔跪、叔豫皆连叔为名,也属于申氏[14]256。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之下《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从杜预之说,将申叔氏合于申氏[15]1375。加之申公屈巫之后申公氏,申氏共计三个分支,这无疑会对《系年》编者造成困扰,从而容易出现史实混淆。春秋战国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其历史背景及人名都易发生错乱,而申氏姓氏的复杂性是其故事人物名字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由于混淆了申包胥之“申”与申公屈巫之“申”,从而产生了史实误植,继而导致了时代穿梭,将申包胥“如秦乞师”之事与“申公屈巫”嫁接到一起,致使《系年》多了一句与史实相悖的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