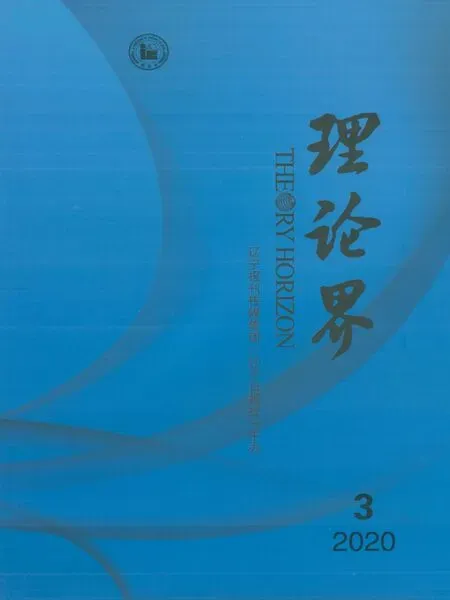朱子理气关系探析
刘泽宁
朱熹谈论理气关系时,把理与气放在了相对待的位置上。他曾明确说到理与气“绝为二物”,但又认为理与气是不可分的。处于对待位置上的理与气的关系,不是理气区别基础上的合一,更像是一体浑成,后分为理与气。那么理解朱熹的理气就需要从统一和区分两方面来看,说二者一体浑成,是因为朱熹强调“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1〕“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理气虽是一体,但就其不同特征、作用等来说二者又相区别。从理与气区分来说,理气关系就有了理气的先后等问题,但理气二分所产生的问题又是不能离开理气不分的前提来说的。
理气这一相对范畴作为朱子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就使得我们对于朱子哲学的理解,必然受到对朱子理气关系的解读的影响。对理气地位的不同解读,使朱子哲学分别呈现为宇宙生化论和一种本体论即理一元论。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两种角度分而论之,虽然可能对每一视角有更深刻的研究,但却不能很好地诠释朱子的理气关系,而更应该将不同视角结合起来理解朱子的理先气后。
一、朱熹理气观的形成
朱熹博采众家所长,将前人的各种思想创见组合改造,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他的理气观,并形成了系统的哲学体系。二程的理、张载的气和周敦颐的太极动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朱熹理气观的形成。
1.上承明道、伊川
理或天理在二程的哲学体系中就是作为核心范畴而存在的。在二程那里,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有其理,理是事物运行的必然法则。朱熹继承二程的这种看法,把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思想。
二程十分重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把理看作万物最一般的原理,认为理的存在是绝对的、普遍的。在二程那里,理与事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一般原则的、形而上的理是与具体的、形而下的事物区别开的。“感性地存在的东西是形而下的,只有用理性才能把握的东西是形而上的,天地、万物、阴阳都是形而下的器,事物的规律、本质、共相才是形而上的道。”〔2〕朱熹把二程这种形而上下的区分运用于他的理气关系之中。他的理承接了二程的理的形而上的地位,是绝对的、普遍的存在,而气则是作为形而下的器而存在的。但朱熹没有把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气截然分开。在二程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谈到理与气的关系,二程的理气观是通过道与阴阳的关系展现的,二程认为阴阳的变化是气的循环过程,道则是作为阴阳变化的内在依据而存在的。从二程对理与气关系的有限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出理与气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朱熹将二程的这种道与阴阳关系的看法与他的理气关系相结合,发展出他新的理气观。和道与阴阳的关系相对应,气的往来运动以理作为其运动变化的内在依据,而形而上的理又是不能离开气的,必须挂搭在气上才能发挥作用。气的往来运动体现着宇宙运行过程,而理则是这一运动过程的规律。
2.兼采横渠
不同于二程把理作为世界的本体,张载把气上升为世界本体和万物本源。张载以气为本体的气学对理学所产生的冲击,使朱熹把气提到了与理相对待的位置上,将理与气结合起来探讨万物本体问题,深入细致地讨论理气关系问题。
在张载的宇宙论中,最根本的是“太虚之气”。他的宇宙构成分三个层次:太虚、气和万物,他认为宇宙运行过程就是这三个层次的构成物交替变化的过程。“太虚之气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气,气散而为太虚。”〔3〕气之本体是“太虚”,即太虚是气本来的存在状态,它是作为本体存在的,它既是本体又是本源。具体形态的气由太虚之气聚成,是在太虚之外的、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的无形而有象的气。万物在根本上是由太虚之气演化来的,正是具体形态的气的运动变化,才使太虚之气能不断地生化万物。朱熹虽然不赞同张载把气作为世界本体和万物本源,但他的理气观容纳了张载的思维方式。“他把太虚解释为理,‘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便变成气安顿于理,太虚生成万物变成了理生成万物,太虚与万物的对立变成了理与气的对立。”理与太虚之气具有同等的地位,都是万物之上的本体。朱熹汲取了张载的太虚之气与气之间的转化模式和气运动变化产生万物的方式,他以理来承接张载太虚之气所起的本体作用,接过气运动变化产生万物的方式,结合于他的理气观。朱熹用理取代太虚,但不改变这一本体与运动变化的气之间的联系,就使得理对气的作用等同于太虚之气对气的作用。朱熹的理对太虚之气的替代更增强了理对气及化生万物过程的本体作用。气经过这样改造后,既巩固了理的本体地位,更增强了与理之间的联系。
3.融合濂溪
朱熹对《太极图说》的书解完成于《程氏遗书》和《西铭解义》之后,所以说朱熹“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纳入‘理’学体系里来”,〔4〕也即是说用理学的术语、思维逻辑来解读周敦颐的思想。朱熹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容纳着他对二程、张载及周敦颐思想吸收后的新见解。
朱熹以他自己所体悟的理及理的状态和所处的本体地位,诠释《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朱熹认为,无极而太极体现的是一种无极而有理的状态,这种无极而有理的状态才是对宇宙本体的完备表述。朱熹将无极而太极中的太极定位为宇宙演化的最初本原和最高本体,无极则表示的是太极的无形无象、无声无臭的状态,此句并不是说太极之上又有个无极,而是说作为太极之状态而存在的无极与太极这一实体互不相离。“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5〕朱熹用理来规定、解释太极,他把太极这一周敦颐哲学的最高范畴解释为无形的理。朱熹还将太极与阴阳的动静关系,与他的理气关系结合起来。太极对应理、阴阳对应气,太极动静即是阴阳之气的动静,太极动静通过气的运行实现,而气运行之理又在太极。在朱熹这里,太极或理是一般性的存在,无形象可循;而阴阳与气则是宇宙运行的无形而有象的存在。阴阳之气作为万物化生过程的构成者,是形而下者,太极则是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一般存在,是形而上者,但二者相依,共同推动宇宙运行,正如朱熹的理与气。
从朱熹对二程、张载和周敦颐思想的承接来看,朱熹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同时注意到张载的气学对理学所产生的冲击,将张载的气引入他的理学体系,从而将气提升到与理相对待的位置上,增强了理对万物的本体作用;在他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诠释中可以看出,朱熹将他的理气与周敦颐的太极和阴阳相融合,加强了理对气的支配作用。
二、理气不离不杂
朱熹既强调理气之不可分,又明确说“所谓理与气,此绝为二物”。在朱熹看来,万物的形成发展都有同一的理作为其规律,这一理若直接落于万物之中,就降低了其必然性和存在于万物的现实可能性,所以朱熹用气来接替理的流行发用。朱熹将理与气分为具有不同作用的二物,赋予它们不同的特性:理是天地万物存在所依据的普遍原理,是某物之为某物的内在规定,气则运动流行发育万物。理气的不可分则表现在,理必须挂搭在气上才能流行发用,而气的运动流行以理作为其化生万物的依据。
1.理气不杂
朱熹将理与气做了形而上下的区分,从而确立了理的本体地位。“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理气共同作用化生万物,但理是形而上的本体,是化生万物的依据。
理作为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普遍原则,是不同于实有之物的无形无象的存在。朱熹给予理一种至上性,把理设定为不受到任何影响的初始的纯净状态,赋予这个理以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特性,认为理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朱熹坚持理的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和洁净空阔的特性,是为了保证理的形而上的地位,保证理不会落入形而下,使理能够必然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天地万物又都是理与气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一切具体事物的生成,都需要理与气的结合。万物之间的不同是由于各物所秉受的气各不相同。气也是构成天地万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与形而上的理不同,气是构成万物的一般物质实在,对万物不具有统摄作用。气作为形而下者,是有情意、有计度的,是凝结造作、酝酿凝聚而产生万物的,其动静作用受到理的种种规范限制。理无形体,也就不具备具体万物所受的时空限制,也就成为比一般万物更高层次的存在,而气这一虽然无形但实际存在的物则不同,它同万物的变化一样,都是时空中的动静,是具有时空特性的物。理气的不同特性就决定了它们二者作为相对范畴时的不同地位。理作为万物形成、运行的规律法则,就成为此物之为此物的所以然、所当然,就具有了决定物质本质的形而上的意义,具有了本体的地位。
2.理气不离
理决定着某物之为某物的性质,是事物化生所依据的法则,而为了保证理存在于万物的现实可能性,理又必须挂搭在气上才能流行发用,所以在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中,理和气都是不可或缺的。朱熹将理与气对应到万物存在的普遍与特殊的地位上,来解决理与气共同作用化生万物的问题,即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
在现实层面来讲,世间所存在的万事万物的形态、性质等各不相同。朱熹认为,万事万物从形态上来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其理则未尝不同,即虽然事物之间各有差别,但是它们的理又是相同的,他认为这些各不相同的事物只是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同。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分类的,而每一类事物又有各自的道理所在,这些相同的道理在不同的事物中的不同表现,就是分殊。朱熹又说万理同出于一源,把太极作为包含万物之理的最终的、唯一的天理,而万物则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有了作为唯一天理的太极的存在,就使得天理作为本体,从根本上讲具有唯一性,那么万事万物产生运行的规律也就只能是同一个天理,从而保证了天理的绝对统一性,使其具有形上本体的地位。理与气分别作为万物存在的依据和事物的表现形式,就都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样既保证了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性的存在,又使得同一的理能合理地存在于各不相同的万物中。理一分殊理论就保证了形而上的理存在于万物的现实可能性。
在朱子哲学中,理与气的关系错综复杂。理是形而上的,气是形而下的。理与气截然不同的地位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性质,理是洁净空阔的,气是矫揉造作的;理与气的不同性质又确保着理作为万物本体的地位。另一方面,朱熹又通过其理一分殊理论解释了理与气共同作用化生万物的过程。从理与气都是构成万物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来说,理与气又是不可分的。通过对朱熹理与气地位、性质以及理与气区分和统一条件的论述,就初步整理出了朱熹的理与气的关系。“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与气在化生万物上地位的不同,就有了理与气的先后问题。
三、理先气后
关于理气先后的问题,朱熹说“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从前文对理气关系的梳理来看,理气的先后关系表现出两个方向:一是从理与气对万物的构成,也即从经验领域来说是理气无先后,二是就理与气二者的存在及二者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来说是理在先气在后的。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混沦,不可分离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6〕在物上看,也就是在理与气所共同构成的万物上来看理与气的关系。在理上看,是从理与气作用以化生万物的过程,也即是本原上来看理气关系。在物上看,理气混沦不分,但朱熹认为,理气在构成万物上起着不同的作用,理气在物上的混沦不分又不影响理与气各自为物,而在理气各自为物的理上看,物之理先于物而存在。“所谓‘在物上看’是就具体的存在说,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是由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共同构成的,理气‘浑论’,不可分先后;‘在理上看’,理在物先,但这不能理解为在时间序列上的在先,而是说逻辑上理为本,具体事物有成毁,而理是恒在的。”〔7〕这里的“理在物先”不是时间序列上的在先,而是逻辑上在先。这里的逻辑上在先即是从形而上的本体角度而言的,理是作为万物本体而存在的,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所以理就具有在存在上在先的特点。理又是剥离在天地万物之外的存在,是出于时空限定之外的存在,还是统率万物的唯一的“天理”,则作为本体的理又是可以脱离万物而单独存在的,所以理在存在上是先于气的。
“在本原上朱熹讲理在气先,但在构成上朱熹并不讲理在气先,而常常强调理气无先后。”朱熹论及理气先后问题,总是先强调“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后才说“但推上去时”“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毕竟未有物先有物之理。这个推上去,肯定不是从理与气构成万物的方面说的,而指的是由理与气混沦不可分的“在物上看”推到“在理上看”。且之后朱熹紧接着就说“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可见,朱熹的“在理上看”就是将理置于万物之上而言的。朱熹在关于理气先后的谈论中,都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理气二者本无先后,但若必推其所从来,须是说先有是理。“对朱熹而言,在经验领域,具体事物的生成既以理,也以气为其必要前提,……这里的本无先后是就经验之域而言,推上去或推其所从来则是从形上之域加以追问,与之相应的便是理气‘本无先后’与‘理在先,气在后’的二重认定’。”〔8〕
对于理与气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理气先后问题,一般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的思想是动态的、复合的,不能单纯从时间上界定理气先后。理先气后的逻辑上在先是说理先气后是在理气不离基础上的逻辑假设。从理与气共同参与化生万物的过程来说,理气确实没有先后之分。朱熹认为就算山河大地都陷了,理依旧存在。理这种相对于气的形而上的地位,以及理自身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性质,使本无先后之分的理气在保证了理的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在逻辑上确立了理的形而上在先的地位。
四、结语
从对朱熹理气观形成过程的探究可以看出,朱熹同二程一样,认为理是形而上的。他将理从化生万物的具体过程中抽离出来,又赋予理以纯粹的至上性;又用理接替了张载“太虚”所起的作用,既加强了理气和万物的联系,更巩固了理的本体地位。朱熹为了保证他理气体系的合理性,既讲理气不离又讲理气不杂,使得理与气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朱熹这一理气体系中,他又因理与气的不同地位,赋予二者不同的作用和性质。理与气都作为构成万物的必要条件,在物上言,理与气是不相分离的;但是理是万物生成的法则,所以是高于气的形而上的存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从整体上看,是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体系,他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中心的形而上的理世界,并且把气放在从属地位,理气共同构成现实的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