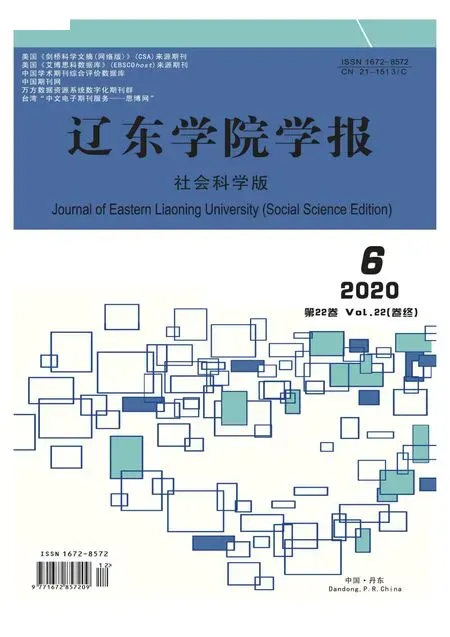埃德蒙·威尔逊的社会文化批评
戴东新
(沈阳师范大学 外语教学部,沈阳 110034)
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的社会文化批评,多以文学批评作为媒介,对社会文化领域公众关注的主题,以社会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批评与阐释。在《到芬兰车站》(1940年)这部历史传记中,他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的细致梳理,文本中不乏文学想象的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37年)一文中,他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运用;在《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年)中,他发掘了象征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史,对七位代表人物进行独特、细致的阐释。
威尔逊一方面作为社会批评家,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可能会受到传统观点的影响进行一般性的观察;另一方面,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对批评传统进行继承和革新,常常表现为“社会的良心”,真正价值理念的支持者。在始终贯穿了批评的“文学人生”中,他从意识形态、道德、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阐释和批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开阔视野、批评方法和实质性内容让其批评具有一定的权威和经典性,文学批评是其社会文化批评的载体。“埃德蒙·威尔逊是在欧洲最为知名和读者最多的美国批评家。在美国他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会批评家。他的许多著述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1]170雷纳·韦勒克的评价表明了他对威尔逊在欧美批评界权威地位的肯定,对其批评广度、深度以及社会文化批评的高度赞许。
一、文艺意识形态和人本质特征的追问
在《冷战和所得税》(1963年)中,威尔逊对冷战、税收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批判。在对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进行研究,发现大笔资金用于战争和探月工程后,他联合美国一些优秀作家对此进行批判。对美国政府花重金与前苏联展开武器竞赛他感到震惊,对在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方面的研究投入表示痛心。威尔逊指出:如果国家通过税收征得的大笔资金用于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压迫人的政权,就背离了美国一直秉持的理想主义——解放和自由。这种走向“死胡同”的举措,让人噤若寒蝉,感到朝着正常理想奋进的路径受阻。普通人和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士都饱受着数不尽的律令的禁锢,这些规定对人的能力和智慧的培养没有价值可言,人们只能被迫沉溺于徒劳无获的“训练”中。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少数人敢于用行动挑战这种“规定性”:二战期间将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的克劳德·埃瑟利少校(Cloude Eatherly)为自己夺去无辜生命的行为痛悔不已,良心发现后试图通过捐助资金来帮助当时遭受重创的日本人。
在批评中,威尔逊能够把社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的解决办法结合起来,足以证明其积极的批评观。他大声疾呼:出现的危机在召唤美国人要重新审视业已建立起来的价值观。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惯常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来不去思考其中有何问题,但是这个时代不允许如此行动;美国人必须重新检验一下,如果把思想和行动的责任付诸于一些社会机构,诸如政党、工会、教堂或是政府,就要思考一下自己有多大程度是自愿的;这些机构没有一个有足够的能力就道德问题提供绝对可靠的建议,他们想提建议的要求会受到质疑。威尔逊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的质疑和严厉的批评是其意在引领社会文化正向发展的行动。实质上,美国政府使用国家权力强迫人接受相关的规定,其实质是绑架了道德。本应该在推行道德方面发挥调节和促进作用的政府机关、社会机构等,遭到了质疑。
威尔逊表现出来的文艺意识形态理想是希望通过社会文化批评提出谏言,以弥补和修正历史错误,推动和牵引社会变革。也就是说,威尔逊试图通过文艺意识形态价值目标的阐释促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结构建设富有“人性”,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对文艺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实践性行动。
《爱国者之血》(1962年),这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断代史,收录了曾亲身经历了南北战争的30多位人物的讲演、时事评论、信件、日记和回忆录,在前言部分,威尔逊说明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任何国家自我标榜的那些战争无一可信。他以迪士尼制片厂拍摄的海底动物海参做比照,阐述它“如何用身体一端的洞孔吞噬另一种比它略小一点的生物体;哪怕它碰上的是另一只海参,只要身体比它略小一点,它也会把其大口大口地吞食下去。一般来说人类之间的战争通常也主要是由像海参所具有的那种贪婪本性所引起。除了人以外,在动物界里实在难以找到一种动物具有人类所发生的那种有组织的侵略行径。……通常,所有的动物都以其它的生物为食,无一例外,只要是能够捕捉到的,就一概吞食,而且又总是那么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人同动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人类成功地精心编造了一套所谓的“道德”和“理由”,用“美德”和“文明” 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人在准备攻击并‘吞噬’他人的时候,总要事先自我标榜一番,歌颂荣誉和上帝,奢谈民族的理想,引证逻辑上的大道理。一旦战争开始,这些自我标榜就失去了它们的本来意义,再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了。”[2]他犀利地指明了人类战争是由贪欲引起的,那些为之找寻的理性、高尚的理由都是空洞,虚伪的。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理性思维和道德,而这两种属性往往成为对“侵略”进行辩白的借口,它们已经在人本真自我方面出现了异化。当美国努力要建设一个为大洋所环绕的国度,让这里成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时,这种所谓“善意之举”“利他主义”融入到了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中,当美国对别国发动战争时,那是进行“拯救”和“解放”。对于这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虚伪、欺骗性的渗透和操作,威尔逊暗示了解决办法——人需要恢复真正的理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两位将军格兰特·李和谢尔曼将军从坚持南北联合、友好相处的态度突然变为对手,失去了人的真正理智;在一战和二战中,参战各国在一夜之间将年轻一代送上战场,失去了人的真正理智。威尔逊提出并讨论的这个问题是人类始终面对并难以解决的,只要人有其自然的贪欲本性,并且没有能力使之得到充分的控制——真正理性的控制,人始终会在此道德方面有着西西弗斯神话的表现。
威尔逊用海参吞食和人类战争作类比,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社会性与类属性,这种本质特征表现在对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上。一方面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暴露了人自然本性中的“夺食”,和海参相似,这是生物类属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决定了人的行动不但为其自然本性所驱动,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性使然。
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性及其发展。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有所差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3]但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只是人的类本质的表现,是人本质的一般性,还应该重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本质的差异。威尔逊的文艺批评表明:一方面,动物与其自身的生命活动关系是直接统一的,而人有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与阶级的不同影响了人的本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不是个体的独立活动,而是社会劳动,是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所以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对外攫取利益,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使然:资本主义社会交往是在私有制的环境下进行的,它注定会带来奴役人、压迫人的的手段,最终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与畸形发展。
二、从文艺批评的多元视角切入艺术美的本真属性
理查德·A·波斯纳评价艾略特、威尔逊在道德方面的批评是“骑墙派”,而马修·阿诺德、卢卡奇是道德主义者[4]285。波斯纳略有偏颇的“骑墙派”判断并未否定威尔逊在文艺作品中的道德批评,其批评中关注的这方面的问题便是驳斥的理由。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他并非意在否定艺术作品本身能以情动人的力量,而是与此同时对人类本性和社会互动表示关注。“这就意味着,批评不仅涉及社会、历史和道德视角,而且也涉及文学和美学的视角。”[5]91批评不能在缺乏美学鉴赏的情况下,机械地去分析艺术和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关系;只有不受到固定的批评范式的束缚去考量、评价艺术作品,才能从文艺作品的多元化视角去表现文化,因为“文化意味着社会活动的全部。”[5]89如果将威尔逊的批评理解为:总是在提醒读者在文学作品中寻找、领会和把握对生活有所启示的实用性功能,试图激发读者从历史、哲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作品,不免过于轻率。因为他相信文学中蕴含美的情感力量:“光彩闪烁的知觉,以一种道德话语无法达到的力量,径直地贯穿了他(指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存在。”[4]304威尔逊对罗森菲尔德(P Rosenfeld)的音乐评论方面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肯定便是这一点的证明:一个人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只有记住,他所做的工作是倾情的自我付出,必有收获,因为这是对生命的求索,为爱而去行动;在行动中,人的精神得以升华和解放,人必会心安理得。”[6]
在《文学的快乐》(1938年)中,威尔逊分析了艾略特的批评风格是“完全不带历史批评特点的。他好像领悟了从时间和空间中抽象化出来的各个时代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次盛大的展览,在其中他沉着冷静,进行比较评价。肯定取得了很大的智识成绩,其论文有很珍贵的价值;但是这种成绩的取得一定是把书从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事务中分离出来作为代价的……”[7]576威尔逊对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的纯美学特征及其潜在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是对作品中将艺术创作与生活实际截然分开的创作观进行了批评。另外,还对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纯工具性动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了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过分强调社会性,文艺批评完全沉溺于失去了美学意义的政治与社会批评中。“今天人们对一个人物进行分析时面对的是一种纯粹分析性的哲学社会批判,几乎总是得出否定的结论;政治社会批评是根据作者对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机械口号的服从、接受程度,对他进行等级高低的评定,从来不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中对作家定位。”[7]577威尔逊做了如此评论,并非表明他对政治、社会批评切入点的否定,(因为其本身的批评往往从此角度入手)而是对当时出现的怪象进行透析:文艺作品中社会批评和范式的机械化运用导致了文艺批评真正属性的丧失和作用的失衡。
威尔逊批评了年轻一代的实用性读书观和批评观。“年轻人,经常激情澎湃,而今对读书却非如此:他们只有在考虑作品是否适合自己的政治需求时,才表露自己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没有领略到读书的乐趣真是令人遗憾。他们应该与伟大的艺术作品和思想为伴,这才有可能在对抗这个时代的野蛮主义时获得一定的支撑力量。”[7]578读书真正的主旨在于领略艺术作品中的丰富文化和思想资源,达到艺术和实践活动的审美旨归。文艺欣赏的绝对的工具性动机背离了文艺审美的本质属性。“在现代的合理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吞没了价值理性,不详的命运像铁笼一样正不可挽回地落向人类的头顶。”[8]启蒙时代以来的批评在当时正在失去其批评的意义和力量蕴含,被政治化了,所以批评界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商品消费文化和商品逻辑向文化工业渗透的批判,也出现了威尔逊对意识形态表现出机械的工具理性的批判。
他引证了一些伟大人物通过读书而有所收获:“这里我要说,回到文艺复兴中,一览这个时代的作品吧!去找马修·阿诺德吧,他认为‘文化是人类所思所想的最美好的东西!’(1)“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felt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的意义就是去了解世界上最深邃的思考和最精炼的话语。去读约翰·济慈的诗歌《初赏查普曼的译作荷马》(2)这是一首十四行诗,英文韵式为ABBAABBA CDCDCD,是济慈在读了乔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之后,被诗触动,提笔写下的。此诗严密的结构、有深意的典故、丰富多彩的想象,让人深思和咏怀。去吧!去读卡尔·马克思每年读一遍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吧!”[7]577这些典故的使用揭示了读书的真正获得感:济慈对伊丽莎白时代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译自如的《荷马史诗》感到由衷地惊异,因此写了诗作《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有感》,此诗表达了伟大作品的情感力量;阿诺德对文化能培养完美的自我,促进和谐的参悟,肯定了读书让人浸润于文化之中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对埃斯库罗斯作品的反复阅读和体会,见证了马克思从普罗米修斯那里领悟了要为人类的发展肩负一定的责任。
威尔逊将马克思与普罗米修斯做类比是其一直延续的观点。在《到芬兰车站》(1940年)中的“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一章,他使用典故,诗性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反叛精神和责任担当。“普罗米修斯是马克思最喜欢的希腊人物,他特别在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引用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对赫尔墨斯讲的一句话:‘你要了解,我绝不会拿我的不幸和你身上的枷锁交换,我宁可被绑在这块石头上,也不愿意浪费我的生命去当天父宙斯的忠实信差。’”[9]108威尔逊借用此典故,肯定了马克思的“英雄”特质:他自愿将人类需要的智慧“火种”撒向世界,不惜牺牲自己,对当时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提出质疑、挑战和行动,坚决帮助普通民众摆脱将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献祭”给资产阶级的磨难,这说明马克思和普罗米修斯都敢于对既定的权力和意志发出质疑和挑战。另外,威尔逊还使用马克思的别称“老尼克”(Old Nick),意在突出马克思敢于反叛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是“浪漫主义者最常见的面具,然而我们这种角色要比浪漫主义的乖僻世界丰富多了。”[9]109威尔逊使用这两个文学指称,说明了其史学叙事中常常插入文学想象,让历史人物形象更为生动,具有反叛精神;再有,马克思绝对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试图通过爱、游历等去寻找经历,积累经验,尝试生命的可能性,他是在实践和理论中寻找人类摆脱困境的方式,因而他的努力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具有公共情怀。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怀揣着个人主义精神,经常会反抗、拒绝和信任社会,不时有着“被边缘化”的情感体验。
可以见得:威尔逊一方面坚持文艺批评的公共属性,从政治和道德等方面进行切入;另一方面从美学角度去发掘其中的美学和道德涵义。这和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和谐的完美”的文化理念有同一性:“文化就是或应该是对完美的探究和追寻,而美与智,或曰美好与光明,就是文化所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10]。
三、文艺创作需要历史行动与社会行动
威尔逊的批评反映了其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观和社会行动观。在《失业的缪斯》(1927年)中,他批评了很多当代美国诗歌“形式优于本质内容,也许是诗人本身生活缺乏趣味性,但是诗人不能拿‘写作诗歌’作为唯一的行动”[7]170。三位英国诗人敢于参与历史行动,在游历世界风云的经验中,其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活动的成绩斐然:沃勒处理并解决了保皇党的阴谋(3)William Waller.威廉·沃勒,英国17世纪议会将军。,弥尔顿一直是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外交官普赖尔签署了一系列条约(4)Mathew Prior.马修·普赖尔,英国外交官,诗人。早年受教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697年担任驻海牙大使馆秘书,签订了结束大同盟战争的《里斯威克条约》。安妮女王时,加入托利党,促成了英法之间于1713年4月签订《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此条约让英国从西班牙取得直布罗陀战略要地,并获得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专卖黑奴的权利,从法国取得纽芬兰、阿卡迪亚和哈德逊湾等北美属地。乔治一世即位后,仕途受阻,1715—1716年为辉格党人所监禁。以写作讽刺诗闻名,有《感时感事诗》。;罗马伟大诗人维吉尔、贺拉斯,以及英国17世纪的诗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的历史行动,但是因为他们与宫廷关系密切,对当时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十分了解,所以这些诗人的创作有一定的本质内容。而现今的美国青年诗人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为自己定位,那些全身心投入诗歌写作的诗人对政治毫无兴趣,来自职业专业化的压力让品味文学之美变得愈加困难,很明显与社会关系的疏离是他们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何让这些年轻诗人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后再融入创作?威尔逊给予了忠告:不要从一开始就完全倾身心于诗文创作,或者隐居于世,或在格林威治村糊口度日,或是到法国的度假胜地里维埃拉去逃避,也不要做杂志编辑到出版社工作,银行家、官员和演员等职业值得考虑。作家自然会在遭遇挫折时经历情感的冲突和对社会的批判,否则,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作品中表达的内容就会贫乏。爱尔兰诗人叶芝之所以受到举世瞩目,是因为他创作源泉的洪流汇聚:自身的奋斗目标与民族、党派的目标一致。美国诗人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创作便是融入了社会生活的体验。
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威尔逊同样表露了此种批评观:真正参与、推动社会发展的作家值得肯定,因为他们相信人生价值观的存在。“一些富有浪漫气质的作家如威尔斯与萧伯纳则尝试尽力在布尔乔亚世界里推动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让人像某些最个人化的浪漫主义者如雪莱或卢梭一样,相信世上有一种值得我们去守护的普世的快乐。但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没有兴趣,亦无意于针砭时弊,他就不会奋力抵抗,也不会发表牢骚以渴望引起别人注意:他会尽力避开社会议题,让自己的想象得到解脱。”[11]191如果说这些19世纪末期的诗人不根据历史,采取合理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不能接受如威廉·莫里斯的社会理想主义或自然主义,则注定会是心理失调的人。”[11]192他们对世界和社会无归属感,这只会让其在幻想中耗尽精力和热情,由于长时间滞留于其中,其创作产出只是“慢慢地把文学五彩的外壳一点一点地分泌出来”[11]201,只是个人主义的、没有与历史发展相关的真正纯文学主题的表达。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离开欧洲去非洲,不是割舍原来的象征主义创作去积极行动,相反,他抛弃了社会和社会观念,抛弃了和这个社会对抗积攒经验的机会,试图从现代文明回到原始文明中,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逃避。威尔逊对此种象征主义作家表现出来的消极性进行的分析,再次证明:批评提供“一种人类的观念和想象如何被环境模塑的历史”[11]30。结合了历史行动和社会行动进行创作的作家,一定会受到历史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从而思想得以提升,对未来有所预见。否则,只强调内在的生活倾向,其作品必定会死气沉沉,招致“化脓溃烂”的后果。
威尔逊对那些旨在纯美学创作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批判,因为它们表现出的是“一种消沉,一种慵懒,一种向内生长而且有时发生恶化的活力意识。”[1]185但这并不是说他否定了文学艺术的自主性。威尔逊对象征主义的代表T·S.艾略特及其作品《荒原》加以进一步释析,表明其“完美平衡”的美学观——艺术的美学韵味,包括纯艺术美和实践生活中的美。他以文本为基础,从社会角度去探求文本潜在的蕴含,以便让人能够理性地参与社会生活。
威尔逊指出,艾略特通过《荒原》中一些意象的浮现和描绘,刹那间再现了一战后商业和工业文明给欧洲和美国城市带来的荒凉、美学和精神上的干枯。“现代大城市中可怕的阴郁气氛,就是《荒原》之所在——在这种阴郁中,浮现出简洁与活跃的意象,蒸馏出简洁的、纯粹的情感时刻;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身边,数以百万计的无名者正在进行着索然寡味的办公室例行公事,在不间断的操劳中把灵魂磨蚀净尽却无从享受任何对他们有益的报酬——人的享乐是那样的龌龊和脆弱,以至于几乎比他们的痛苦更加哀伤。这个荒原还有另一面向:这不只是一个荒芜的地方,也是混乱与怀疑之地。在我们这个战后世界,机制四分五裂,神经紧绷,理想破碎,生命不再显得严肃或完整——我们不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结果我们就失去了意志。”[11]81其对《荒原》的批评解析正是艾略特批评功能观念的进一步垒实。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对批评的目的和作用做了如下阐释:“我敢说从来没有一个解说批评的人曾经做过这样荒谬的结论,认为批评本身就是目的。我并不否认艺术可以有本身以外的目的;但是艺术并不一定注意到这种目的,而且根据评价艺术价值的各种理论,艺术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不论它们是什么样的作用,越不注意这种目的就越好。但是,另一方面,批评就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这种目的,笼统说来,是解说艺术作品,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12]艾略特的“批评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恰当地总结了威尔逊的文艺批评观,这也说明为何威尔逊在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发行初期遭遇难解之围时,极为细致地阐释了《荒原》和《尤利西斯》:一方面,他对各个民族文化中的文学典故现代版的解读帮助读者理解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另外,从社会、历史等多方面进行切入,让读者体味“文不离史”的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唯物史观时,认识到历史观是其文艺创作的标识。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威尔逊的社会文化批评进行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文化生产的文艺创作应当与社会、文化和政治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应认识到文化的政治性;文艺批评中的社会性是对某特定社会的否定和挑战。威尔逊在文艺批评领域采用“反学术化”批评的方式,其批评中的“自我大众化”[4]8表达在政治、道德及美学领域得以施展,让读者感到多元的文艺之美就在身边。其作为文艺批评家的社会行动,对“公共责任”的认知,对知识分子在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如何发挥作用应该会有所启发。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从阅读其丰富的大部头作品开始,但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除了三部作品《爱国者之血》《到芬兰车站》和《阿克瑟尔的城堡》以及文章《文学的历史阐释》有汉语译作外,其余大部分作品都有待翻译。因此,期待国内文艺界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威尔逊,以飨其文艺批评之更多实质性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