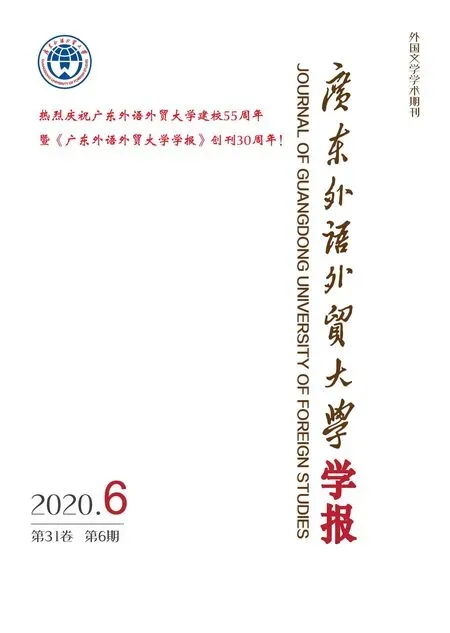乡关何处?
——克里斯托夫·海因小说《征服土地》中的“家乡”
潘艳
一九四四年生于西里西亚的前民主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凭借小说《陌生的朋友》(DerfremdeFreund,1982)与《霍恩的结局》(HornsEnde,1985)声名鹊起。两德统一后,海因不断突破创新,陆续推出新作,获得多项文学大奖。
海因曾经不止一次提及,真实的历史题材及个人经历是他作品内容的重要来源,是其文学创作的“采石场”。由于德国在二战中战败,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协定,中东欧各国重新划定边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大量德裔居民被驱逐和强制迁出。原本生活在西里西亚的海因被迫与家人一道离乡别井,最终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小城巴特·迪本(Bad Düben)安顿下来。在一次谈及当年经历的访谈中,海因提到他对逃亡的经过已没有太多印象,但作为难民之子的痛楚记忆在几十年后仍然存在:“人在孩童时会对归属某个团体感兴趣。如果在很早的时候就必须经历无可归依的感觉,会留下烙印。时至今日,这段经历对我也许仍然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没有家乡”(Albrecht,2009:53)。这段艰难的迁徙之旅与融入的历史在海因的多部作品中均有所涉及,在其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征服土地》(Landnahme)中得到尤为细致地呈现。
《征服土地》与被驱逐的历史
《征服土地》在出版之初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德国较大的日报与周报都刊登了该书的评论,海因本人也接受了大量采访。评论称该作品是“作者迄今为止写过的最好的小说”(Hage,2004),是在转折时期盼望已久的“优秀德国小说”(Magenau,2004)。全书以“报告和记录式的叙述口吻”“让半个世纪的德国历史再度复活”(Hartwig,2004),是一部“构思严密的编年史”(Scheller,2004),“展现了社会的一个横截面”(Blochmann,etc,131),是“民主德国的社会风情画”(Karasek,2004)。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原东部居民被驱逐和逃难的历史,有评论称赞海因“写了一本绝妙的、扣人心弦的书,敏锐地观察到了德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即当时的德国人对移民极不情愿的接纳”(齐快鸽,2004:25),展现了“德国迄今为止在对待难民的敌意问题上尚未痊愈的伤疤”(Richter,2004)。
“驱逐”(Vertreibung)这一概念是德国记忆历史的一部分,作为“记忆之场”的一个词条出现在多部历史书籍中。这个概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东德地区的组织传播到西德,带有一种强烈的对暴力和程序不公的道德批判的内涵。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被驱逐者”(Vertriebene)的概念,指的是那些逃亡和被驱逐的德国人,这一词汇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日常用语中,而此前西德官方的文档中使用得较多的表述是“难民(Flüchtlinge)”(Struve,2005:282)。据相关统计,自一九四四年秋季起,超过一千二百万的德裔居民被迫从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及苏台德等地区迁出并踏上逃亡之路,超过二百五十万人在西行途中或死于饥饿、寒冷,或被枪杀、打死(Hahn,2001:335)。
在海因二〇一九年新出版的文集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过去一切都不一样》(Hein,2019:16-19)的文章,海因在文中叙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对待丧失的东部领土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海因提到自己的许多亲属对西里西亚的向往,多年来一直希望能获准重返故土。在二战结束后的头几年,以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为首的前东德政府曾希望收复丧失的东部领土,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民主德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就能大致与当时的联邦德国比肩。乌布利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拒绝遵照斯大林关于德国东部领土的指示并坚持要求归还这部分的领土。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对民主德国政府的抵制行动感到厌烦并下达最后通牒,乌布利希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强权。德国五年来一直拒绝接纳的东部新边界被最终确立,史称“奥得河-尼斯河-和平边界”,奥德河畔以东的省份划归波兰所有。民主德国内部不再允许谈论丧失的东部领土,从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强制迁出的德裔居民不得再被称作“被驱逐者”(Vertriebene),而必须使用更为中性的名称“移居者”(Umsiedler),因为“驱逐”一词带有复仇主义色彩被视为禁忌。历史书籍与中小学教科书也不允许再提及从前的相关政策,这一段德国历史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清除”了。
《征服土地》中的“家乡”主题
小说《征服土地》运用多声部叙事的方式,通过五位与主人公贝恩哈特·哈伯尔相关的叙述者对往事的追忆,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主人公成长发展的个人经历,另一方面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变迁。《征服土地》的故事发生在以海因本人成长的城市为蓝本虚构的东德小城古尔登贝克(Guldenberg)。不同于以往作品基本都以知识分子作为关注的对象,海因在《征服土地》中首次将目光聚焦于外来移民的群体,关注外来者的生存境遇与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与海因相仿,《征服土地》中的主人公贝恩哈特生于布雷斯劳(Breslau),二战后全家被驱逐出西里西亚,年幼的他随父母一道历经逃难的艰辛,最后在古尔登贝克定居。在小学同学托马斯与玛丽安的叙述中呈现的是贝恩哈特在到达小城后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而校友兼搭档彼得、小姨子卡塔琳娜和生意伙伴希古尔特讲述更多的则是青年时期以后的贝恩哈特白手起家的升迁发迹之路。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物资匮乏。从东部涌入的大量难民挤占了当地居民的住房和本已相当有限的资源,激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与敌视。哈伯尔一家作为难民大潮中的一员被安置在一个农户家中狭小、如冰窖般寒冷的阁楼房间里。贝恩哈特的父亲由于残疾无法找到工作,只能靠母亲为农户帮工换取全家的口粮。本地人避免与外来者打交道,哈伯尔一家在小城备受冷遇、排挤与歧视,但为了生计只能忍辱求存。
作为城里唯一的残疾人,贝恩哈特父亲缺失的手臂就像是一块“古尔登贝克不曾为输掉的战争和牺牲的七名战士所竖立的方尖碑”(Hein,2004a:24),不断唤起人们有关德国战败以及屈从于战胜国的耻辱记忆。在到达小城一年半后,他终于获得营业许可开设了一家木工作坊,却由于其移民身份没有本地人光顾。他苦心经营的作坊后来被人恶意纵火焚毁,闻讯前来的消防队员袖手旁观不去灭火,警察态度冷漠拒绝调查事件真相。在经历了被迫离乡丧失一切后,哈伯尔一家再次面临一无所有的命运。然而厄运并没有到此终结,几年后贝恩哈特的父亲由于受到当地人的仇视而被谋杀,两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贝恩哈特从小饱尝人情冷暖,个性内向孤僻,外来移民的身份加上落后的成绩使他在学校遭受冷眼和歧视,但他意志坚定,顽强刚毅,在对待自己的出身问题上坚持立场。数学老师因为贝恩哈特的出身在课堂上对其讽刺挖苦,在听到他回答出生地为“布雷斯劳”时大为不满,要求他回答“弗罗茨瓦夫”(Wrocaw)①。当老师再次提问家乡并要求“正确”答案时,贝恩哈特在回答完“弗罗茨瓦夫”后倔强地补充道:“但我出生在布雷斯劳”(Hein,2004a:20),这是十岁的贝恩哈特对与已丧失的故土相关联的个人身份认同的最后捍卫。关于贝恩哈特对家乡的记忆与情感,书中没有过多着墨,仅有一次在玛丽安妹妹的墓前,贝恩哈特提起自己深爱的祖父,但祖父的墓地对全家人而言已无法企及。在备受冷遇与排挤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哈伯尔一家想必也与大多数外来移民一样怀念过熟悉的风土和曾经拥有的物质财富,只是旧日的故土已不可复得,只能开辟新的天地。
丧失故土与新建家园是海因小说的两个基本主题,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贯穿全书始终。对“外来者”“陌生”和“陌生感”的描述以及有关“惧怕过多受到外来影响”的刻画在书中一再出现(Saalbach,2017)。在当地人眼中,外来者一无所有,完全依靠城市的馈赠与本地居民的救济过活,是“蠢人和懒汉”,与“寄生虫”无异。当地人视这些德裔的外来移民为异类,认为大部分的被驱逐者都很古怪,他们说的语言、生活方式都与当地人不同。他们不被看作“真正的德国人”,本地人贬称他们为“波兰佬”或“其他的俄国人”,以示与真正的俄国人或占领区的俄国士兵相区分(Hein,2004a:37)。当地人无法认同这些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同胞,也没有耐心和兴趣了解他们的过往和处境:“他们来自另一个德国,不是我们的德国。他们从自己的德国被驱逐,但我们的德国却不是他们的家园”(Hein,2004a:35)。
与“外来者”和“陌生之物”作为无法揣度与潜在威胁的表达相对,家乡是一个熟悉的场域。小说中详细叙述了木匠波希勒对于“家乡”的看法,他的观点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普遍心态。
……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地球上都有一个位置。我们都被分配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它。要是放弃这个位置,人就没有归属之所了,世界就是如此。这个位置和出生有关。你的出生之地是你的家乡,只有那里才是家。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就等于放弃了家乡。离开故土也许能让你在人生中达成很多事情,也许比你不离开要多,但你失去了家乡……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父母要反对外来移民。现在我明白了,我知道他们是对的。(Hein,2004a:339-340)
在波希勒眼中,“家乡”是一个与出生地相关联的命定的概念,是传统和遗产,带有“血统和土地的思想”(Ehlers,2008:100),具有唯一性与排他性,是个人无从选择与变更的,就像私有财产一样,不容外来者觊觎。波希勒敌视外来移民,对从故土被驱逐的德裔同胞不抱丝毫同情,把小城中发生的一切负面变化均归咎于外来者。
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侵占别人家乡的权利,只因为有人侵占了他们的家乡。从战争时开始,古尔登贝克就不再是我出生时的样子,不再是我们的城市。在难民到来前,这里从未经历过这么多的火灾,在战时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团结一致。但一切都过去了,都变了。外来人口太多,太多不在这里出生和不属于这里的人。(Hein,2004a:340)
在波希勒看来,外来者和吉普赛人一样,是偶然来到古尔登贝克并且随时可能离开的,所以他们对新的环境缺乏归属感,不会在意城市是否遭到破坏,本地人着力维护的东西在他们眼中无足轻重。波希勒认为外来移民不值得信任,因为无从了解他们过往的生活方式和经历,也不清楚他们从前的生活规范与准则,“外来者永远都是外来者”。除了由于情感与信任基础的缺失所造成的弥合困难,本地人更担心既有权利受到威胁。他们视外来移民为入侵者和敌对者,不希望城市的操控权被分享,将排挤外来者视为家园保卫战的一部分。这种由于对外来移民出身背景不认同所导致的反感和排外情绪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上升为极端的纳粹式仇恨。
在这些难民到来之初就该把他们溺死在慕尔德河,全部统统。
全是没用的东西。
应该把他做成一磅肥皂,至少还能有点用处。(Hein,2004a:312)
他们说起城市和给市政预算造成重负的许多被驱逐者。……他愿意为每弄死一个外来移民支付一百马克,在他看来,为了城市卫生值得花费这笔钱。(Hein,2004a:364)
在一个自诩隶属于战胜国阵营因而与纳粹罪行划清界限的新政权中,带有种族灭绝色彩的用语和思维依然延续下来并被运用到对待自己的同胞上,人性中的自私、偏执与狭隘从不因政权更迭而改变。外来移民的融入之路道阻且长。
《征服土地》中主人公的融入之路
古尔登贝克是海因设定的一个在地域上相对确定的虚构之城,该城也是其长篇小说《霍恩的结局》中人物的经历与回忆之地。在该书中,斯波迭克医生将之与《圣经》中的罪恶之城“蛾摩拉”相提并论(Hein,1985:9),该城名字中的“古尔登”(Gulden)在历史上曾是支付的货币(Ehlers,2008:94),“贝克”(Berg)在德语中是“山体”或“大量、成堆”之意,暗喻了小城居民拜金市侩的思想倾向。玛戈瑙(Jörg Magenau)将古尔登贝克看作是民主德国的首都,不是政治地域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气质上的首都(Magenau,2004)。
海因曾在一篇有关德国人排外现象的散文中用讽刺的口吻尖锐地指出,仇外心理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
不,我们不仇视外国人。我们不害怕你们的肤色或宗教,也尊重在我们看来陌生的文化,甚至还对此很感兴趣。但是我们憎恶贫穷。可惜实情是你们当中的很多人特别的贫穷。我们害怕你们的贫穷,因为它使我们感到恐惧。我们害怕你们贫穷的病菌,害怕会被感染。对于变穷我们感到恐慌。至于带有这个世界最可怕疾病病菌的是外国人还是德国人,对我们而言都不重要。(Hein, 2004b:141-142)
哈伯尔一家在西里西亚时曾拥有自己的木工作坊,由于逃难被迫放弃所有,在初到古尔登贝克时极度贫穷。与广大丧失家园、流离失所的逃亡者一样,“贫穷”是哈伯尔一家的“原罪”。正如托马斯所言:“战后的那几年我们这里没有富人,但即便贫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有一种仅能激起蔑视的贫穷”(Hein,2004a:67)。纵观全书,古尔登贝克人对外来者的恐惧总是与对贫穷的恐惧相连。外来移民的贫穷以及对自己可能由此致贫的忧虑使小城居民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这是被驱逐者在小城不受欢迎的根源。在他人冷漠与鄙夷目光中成长的贝恩哈特日渐明白,只有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才有可能在新的环境扎根立足。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资本看作是参与社会权力和优化社会地位的主要基础,并把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外来者既没有经济资本(即物质财富),也没有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而唯一拥有的文化资本却不被人看重(Saalbach, 2017)。《征服土地》中贝恩哈特的发迹与融入之路可以看作是对布尔迪厄理论的一个佐证。
首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集体化的政治运动中,素来内向低调、不问政事的贝恩哈特积极投身执政党的政治运动,在为自己争取社会资本以改善社会地位的同时打击报复自己的仇人。他和宣传队的其他成员前往拒不加入集体化的农户家中施压,其中包括曾在哈伯尔一家初到小城时为他们提供住处的农户。当地居民对贝恩哈特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他的行径“厚颜无耻”,恩将仇报。在与彼得的对话中,贝恩哈特吐露了当年行事的缘由与动机。贝恩哈特永远无法忘记他们一家初到古尔登贝克时所遭遇的蔑视、怀疑与不公:“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污物”(Hein,2004a:256),贝恩哈特希望那些残酷对待他们一家的人也能经历失去所有的滋味。自从贝恩哈特加入强制集体化的队伍,本地居民对他突然变得畏惧和忌惮起来,贝恩哈特享受这种报复的快感,认为“复仇是美好的”(Hein,2004a:256)。
除了借助政治运动实现个人意图外,贝恩哈特不断努力积累经济资本以扩大自己在小城的影响力。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贝恩哈特不惜铤而走险,用汽车帮助东德人偷渡到西柏林。通过这种非法的方式,贝恩哈特得以迅速积累财富,并把更多的资本用于木工作坊购置新的机器设备。贝恩哈特行事稳健,经营有道,他的作坊发展成为当地最现代化和最大型的家具工场,物美价廉的产品为他赢得了大量客源。伴随经济资本累积提升的还有社会资本。作为实力雄厚的企业主,贝恩哈特为当地的企业家协会所接纳并被选为议员,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并跻身上层社会,物质财富让贝恩哈特拥有更多行政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权。为了保障包括自己在内的精英团体的既得利益,贝恩哈特建议协会每年收取高昂的会费,以金钱巩固和扩张势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一直反对贝恩哈特加入协会的波希勒由于工场被毁失去了企业主身份,被排除在协会之外。经此一役,贝恩哈特在古尔登贝克的地位更加稳固。这是商业资本取得的胜利,外来移民的出身背景已不再成为贝恩哈特发展的阻碍。正如希古尔特所言,“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即便他只是个被驱逐者。要是不了解的话,根本觉察不到”(Hein,2004a:334)。通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和钻营,贝恩哈特终于在古尔登贝克站稳脚跟并实现了阶层的跃迁。家乡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紧密相连的。外来移民想在新的环境立足并融入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这是关乎生存的战斗,贝恩哈特为争取归属权所进行的抗争最终成为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
对于曾经遭遇的打击和伤痛,贝恩哈特一直牢记在心,他曾对彼得说:“我什么都不会忘记,永远”(Hein,2004a:257)。在父亲被谋杀后,贝恩哈特曾发誓要找出真凶替父报仇。在发现木工作坊被人恶意纵火后,贝恩哈特扬言要让作恶者付出代价:“我绝不会落得像父亲那样的结局”(Hein,2004a:336, 337)。然而事隔多年,在父亲遇害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时,此刻功成名就的贝恩哈特却对是否要获悉谋害父亲的凶手感到十分犹豫。他深知自己一旦走上复仇之路把凶手送上法庭,必将再次与整座城市为敌,破坏自己多年不懈努力得以融入的成果和艰难打下的基业,失去已经获得的渴望已久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无法接受放弃一切,离开古尔登贝克重新开始。在经过痛苦纠结和内心挣扎后,贝恩哈特最终决定放下个人恩怨。
在中世纪,我听说,教堂和宏大的建筑物总是由鲜血修筑的。要是想让建筑物屹立不倒的话,就得把一个无辜者的血,最好是孩子的血,混入灰浆里。也许这是迷信,也许一直就是这样的。也许只有依靠父亲的血,我那无辜的父亲的血,我才得以在这里立足,才能被人接纳。(Hein,2004a:367)
哈特维希(Ina Hartwig,2004)认为《征服土地》讲述的是一个“放弃复仇的故事”,也是一个“苦痛但成功融入的故事”。上述这段引文道出了作为外来移民的贝恩哈特心底的酸楚与无奈,他已不再是那个一无所有,徒有一腔孤勇的莽撞少年。纵然内心无比苦痛与不甘,贝恩哈特最终还是屈从于现实的考量。
在小说末尾的狂欢节活动中,贝恩哈特的儿子保罗把节日游行队伍中的两个外国人赶出了队列,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而狂欢节是德国的节日。贝恩哈特告诉儿子祖父也曾被驱逐,让保罗不要打扰那些外来者:“他们是可怜的难民,过得足够糟糕了。他们影响不了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东西夺走”(Hein,2004a:379),保罗却认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祖父是德国人,有资格要求在德国的土地生活。哈特维希在评论中指出《征服土地》在人物设计上有一个欠缺:主人公最终放弃了复仇,但他的儿子却表现出对外国难民的仇视情绪,她认为贝恩哈特不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尽管保罗与当年对待祖父和父亲的小城本地居民一样自私与狭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贝恩哈特却对自己的儿子深感骄傲与自豪。移民后代对外来者的排挤和敌视正是全文最具讽刺意味和发人深省之处,全书末尾的这个细节恰恰是海因的着意设计与安排。如果哈特维希能对海因的历史观有所了解,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在海因看来,在世界和各国的历史中,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出现过“转折点”,一切都是前后相继的,是“结果的结果的结果”(Hein,1991:3)。
结 语
海因小说的标题“Landnahme”在德语中一般指“占领、征服一块区域并向此地移民”(Ehlers,2008:90),联系文中具体内容可以作多重解读:“征服土地”首先可以指涉以政治或军事手段对土地的强行掠夺与侵占。以哈伯尔一家为代表的德裔居民在二战后被强制从生活的土地驱逐,流离失所,丧失故土和家园;其次,小说标题让人联想到书中政府通过宣传或胁迫等手段将私人土地收归公有的举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东德推广的农业合作社集体化政治运动中,原本属于农户私有的土地被充公,收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征服土地”的第三层含义可喻指外来移民逐渐适应并融入新的环境,建立家园,成为土地新的主人。
在小说中,除了五个人物的叙述各为独立章节外,开篇与结尾的两部分构成了一个叙述框架,讲述贝恩哈特的小学同学托马斯在离开古尔登贝克多年后重返故乡的见闻和感受。在海因早年的长篇小说《霍恩的结局》中,托马斯作为其中一个叙事者讲述了小城在一九五七年的历史风云和人事变迁,少年托马斯立誓要离开这个让他感觉窒息的巢穴。在《征服土地》中,托马斯离开小城外出求学并定居柏林,离乡多年后重临故地感觉熟悉而又陌生。他在狂欢节的活动上偶遇晚年发福的贝恩哈特,此时的贝恩哈特早已从一无所有的移民之子逆袭为当地位高权重的企业名流。托马斯在与小城居民交谈中刻意不提及自己与小城的渊源,并称古尔登贝克为“你们的城市”(Hein,2004a:381)。出生和成长的城市让托马斯感觉陌生而疏离,父亲当年的药店已物是人非,他知道自己早已不属于古尔登贝克,已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外地人”。在驾车行驶到小城出口时他有意加速驶离,“仿佛想要赢回一段逝去的时光”(Hein,2004a:383),又似乎要与从前的一切作一个交割。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本地人选择放弃原籍离开故土,在新的环境开疆辟壤;而以贝恩哈特为代表的外来者则在异乡落地生根,反客为主。
“家乡”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与祖籍、出生和居住地紧密相连。但人在一生中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因而家乡并不必然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唯一与排他的。“家乡”同时又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概念,与人的情感依归相关。倘若一个地方让人感觉不适,缺乏认同感,哪怕在其中生活的时间很长,恐怕也未必会被看作“家乡”;反之,如果一个地方能给人安适和归属的感觉,就有可能会被视为“家乡”。再者,“家乡”是一种与权力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保护区,用以对抗潜在的外来影响。总而言之,“家乡”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受到内部和外在因素影响制约,伴随人的活动范围、心理感知和生存境遇等因素持续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乡并非所源之地,而是人为的创造。
乡关何处?此心安处是吾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