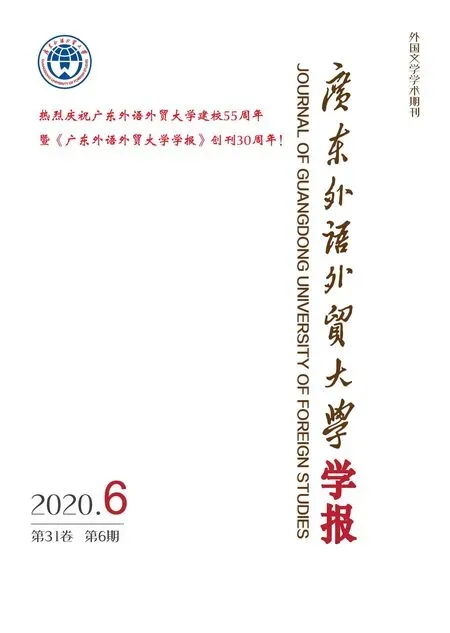伯纳德·马拉默德小说的伦理解读
李莉莉
引 言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坛杰出的犹太作家。国内外文学批评界普遍认为,马拉默德的作品关照犹太个体的命运,其中的犹太主人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现实世界里艰难跋涉。实际上,马拉默德最为显著的创作成就,就是以其选用的题材和表达的主题展现人类伦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天生的运动员》(TheNatural)到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的《基辅怨》(TheFixer)、再到后期创作的《房客》(TheTenants)以及最后出版的《上帝的恩赐》(God’sGrace),马拉默德先后刻画了多种迥然不同的伦理境遇,充分显示了他对伦理问题的关注。
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公正地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上的文学和文学现象,研究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聂珍钊,2005),其意图“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或是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更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聂珍钊,2004)。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可以展现作家的伦理思想及其特点,阐明作品中的道德劝诫对社会和读者产生的影响,“既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快感,又带来了自我认识和伦理思考”(周静,2015)。马拉默德的小说蕴含深厚复杂的伦理思想,在揭示人类面临的伦理境遇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人们如何才能摆脱伦理困境,不仅为犹太人,更为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指明方向。
《天生的运动员》中的人际伦理救赎
马拉默德在美国出生长大,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强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在现代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创业、进取、勤奋、竞争,另一方面又强调机会均等原则”(李其荣,2005:60)。个人主义价值观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产生负面影响。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就会逐步演变为对财富和成功的渴望。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并且常常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人们失去对彼此的信任,相互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就受到阻碍。个人主义在马拉默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生的运动员》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种价值观致使小说的主人公棒球运动员罗伊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产生连续不断的心理焦虑,陷入人际伦理困境。
罗伊遭遇人际伦理困境首先表现在他与球队老板班纳无法建立良好的关系。班纳拥有球队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控制着球队里甚至比赛场上的一切。班纳信奉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以自我为中心,目的就是尽可能追求个人财富,而不是帮助所经营的球队取得比赛胜利。班纳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致使罗伊在与他交往时陷入痛苦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班纳只把罗伊视为获得利益的工具。虽然罗伊在比赛场上发挥出色,即将带领球队冲击联赛冠军,但是当他遇到困难向班纳寻求帮助时,班纳却冷酷无情地拒绝了请求。更具嘲讽意味的是,罗伊因为暴饮暴食导致腹部疾病,这时班纳考虑的不是如何让他尽快恢复健康,而是为了节省费用把他送到一家妇产医院进行治疗。其二,班纳引诱罗伊参与赌球。这样他可以赢取赌金,能够从比赛中获得暴利。赌球经纪人伽斯的话很好地说明了班纳这些人的行为:“我们可以在一切人或者事物身上下赌注。我们会赌投手投掷出的好球、投手的失误、安打、跑垒、每局比赛以及整场比赛的结果” (Malamud,1991:108)。为了获取钱财,班纳他们心肠凶狠、手段毒辣,甚至毁灭异己。罗伊与班纳在一起,无法实现事业上的追求,看不到未来前景。
罗伊与女友迈莫也无法建立亲密的恋人关系。迈莫年轻漂亮、才智超群,但同时也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信奉者,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她把爱情和婚姻当作商品,盼望未来的丈夫能够让自己过上梦寐以求的安逸奢侈的生活。她对罗伊说:“我想要通过别人的资助,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不想如同奴隶一样地生活。我要有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有帮我做家务的女仆,有很好的汽车让我外出购物使用,天气冷时有毛皮大衣御寒。……我一定要得到这些东西” (Malamud,1991:199-200)。迈莫不可能在婚姻家庭中承担责任,也不会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她对罗伊仅仅是随意应酬,从来没有真心地爱过罗伊。她之所以引诱罗伊,就是为了让他分散精力,在比赛场上无法打出好成绩。正是由于“错误的爱欲,罗伊被毁掉了。他在欲望的诱惑之下,被迫放弃前程事业”(Baumbach,1963:443)。罗伊在与迈莫交往的过程中忍受着身体上的病痛和精神上的折磨,无法继续上场参加比赛,前途渺茫。
但是,马拉默德并没有让罗伊在困境和危机中沉沦下去,而是让他在另一位女友艾丽斯的帮助下,找到救赎的途径。杰弗里·海尔特曼(Helterman,1985:8)认为,“马拉默德小说的主题强调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以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理论为基础”。这里所说的“我——你”关系指的是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信任,承担对彼此的责任。罗伊在与艾丽斯交往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我——你”关系的转变。艾丽斯曾经对罗伊讲述自己独自抚养女儿时遭受的苦难,她用亲身经历证实,人应该肩负职责,做出某种牺牲,为别人做些事情。罗伊在艾丽斯的影响下逐渐恢复信心,认识到班纳和迈莫只是利用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他决心承担起对球队的职责,而且还接受艾丽斯以及他们的孩子,认可作为父亲的责任。“爱与责任是马拉默德小说的救赎力量,是最崇高的美德”(Baumbach,1963:439)。爱与责任可以促使人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能够做到既关心自己,又关爱他人,从而代替冷漠的人际关系,彼此之间的联系就会更加密切,生活也会更加幸福。罗伊经历种种不幸和阻碍之后,最终理解爱与责任的重要意义,走出与他人交往的伦理困境,实现伦理救赎。
马拉默德在《天生的运动员》中通过罗伊的经历指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导致人们缺乏沟通和理解,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造成巨大障碍,而爱与责任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相互关爱与责任的承担就仿佛生活中的指路明灯,引导个体摆脱人生困境,继续前行。
《基辅怨》中的犹太伦理回归
罗伯特·斯科尔斯(Scholes,1987:47-51)曾经指出,“马拉默德是犹太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在传扬犹太性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成功”。他认为,马拉默德作品的犹太特征非常突出,反映犹太伦理对犹太人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犹太伦理可以被视为犹太教伦理,指的是犹太教所信奉的伦理价值观。犹太伦理在犹太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动力和支持。犹太民族在历史上不断遭受屈辱和灾难,但是集体迫害和大屠杀并没有使犹太人畏惧退缩,犹太伦理就是他们强大生存能力的精神来源。犹太人大都有着深厚的犹太情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犹太伦理。马拉默德在《基辅怨》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对于犹太人来说,与自身的生存问题相比,坚守犹太伦理更为重要。犹太人必须首先承认本民族的地位,之后才能思考个体的生存问题。否则的话,背离犹太伦理传统将会使其生活在苦闷与困惑之中。小说的主人公犹太人雅柯夫在反犹主义势力的压迫下,隐瞒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因此陷入犹太伦理困境。
雅柯夫遭遇犹太伦理困境首先表现在他不愿意认可犹太人身份。生活在犹太小镇时,他就不再蓄留象征犹太人身份的短胡须,遭到其他犹太人的奚落和嘲笑;离开犹太小镇前往基辅时,要不是岳父斯莫尔提醒,他也不会带上装有经匣、犹太教徒头巾和《希伯来圣经》的布包;雅柯夫乘船渡过第聂伯河,听到了船夫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船夫说完之后,还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他吓得发抖,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也不得不按照船夫的方式画了一个十字;雅柯夫在基辅改用了听起来更有俄国特色的名字,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俄语,努力使自己在穿着打扮、举止行为方面看上去与俄国人一样。雅柯夫绞尽脑汁放弃犹太身份,积极主动适应俄国社会的生活,但最终不但没能融入其中,反而陷入困苦而恐惧的精神境地。
雅柯夫遭遇犹太伦理困境还表现在他没有接受犹太教信仰。犹太教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家庭和婚姻生活至高无上。“犹太人的家庭不仅建立在经济和生理等的考虑上,而且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离开了女人,男人就无法生存;离开了男人,女人也无法生存’”(科亨,2009:35)。犹太教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神圣化,犹太人竭力保持完整的家庭和幸福的婚姻。但是,雅柯夫却没能处理好与妻子拉伊莎的关系。他们结婚五年多,一直没有生育后代。他对此非常不悦,开始冷淡妻子,甚至与妻子分居。雅柯夫与岳父斯莫尔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分歧。斯莫尔对犹太小镇有深厚的情感,认为犹太文化只有在这里才能保留、传承下去,所以他反复劝说雅柯夫留在小镇。但在雅柯夫眼中,犹太小镇却是一个如同坟墓的地方,只有离开这里,才能寻求自由。雅柯夫还承认,关于犹太法典他知道得很少,对于犹太教教义了解得也不多。雅柯夫把犹太伦理视为束缚,想方设法融入俄国社会,但结果却被人陷害,被指控为杀人犯,在监狱里经历了寒冷、饥饿、酷刑等等折磨,承受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磨难。
雅柯夫遭受种种苦难之后,认识到整个事件不仅涉及自己个人的冤屈,还关乎犹太民族的生存。他最终意识到回归犹太伦理是解决面临问题的唯一途径。雅柯夫在监狱生活中对犹太教教义有了更多的理解。他开始注重亲情,改变以前对待家人冷漠粗暴的态度。当他反思与拉伊莎的关系时,更多的是自责。他觉得她还是一个不错的女人,是自己没有珍惜她。他给予拉伊莎足够的关心,甚至原谅她的出轨行为,接受她与别人生下来的孩子。雅柯夫开始在狱中实践犹太伦理中的乐观精神。“犹太教的特征,犹太教传授给其他民族的东西,是它对世界的伦理肯定(affirmation):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乐观主义宗教”(拜克,2002:77)。犹太民族正是凭借乐观精神,用坚强的意志面对生存境遇中的苦难。监狱的生活单调、枯燥,但雅柯夫却以乐观的心态来安排每天的事情。他用扫帚打扫监牢,这样既有助于保持室内清洁,又可以锻炼身体。雅柯夫还珍视生命的价值。犹太伦理思想强调生命的意义高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把生存看作是不能逃避的责任,即使遭遇痛苦磨难,也必须生活下去。雅柯夫放弃结束生命来逃脱屈辱生活的想法。他与卫兵接触时,不再采取对抗的方法,而是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努力保全性命。雅柯夫和那些让他遭遇苦难的人抗争,拒绝承认政府当局强加的罪名,因为他知道一旦认可罪行,“犹太民族就会被牵连”(Malamud,1966:280)。作为犹太人,他承担对整个犹太民族的责任,与反犹主义势力进行斗争。
犹太民族在遭受苦难和迫害的生存境遇中,最为重视的就是犹太伦理传统。犹太人在犹太伦理中找到使其内心安宁的避风港,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以及维持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基辅怨》中雅柯夫意识到只有犹太伦理才能使自己走出困境,而且每个犹太人都与犹太民族的生存紧密相连。雅柯夫的这种转变与“他对本民族同胞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Ochshorn,1990:167)。犹太伦理深深地扎根在每个犹太人的心中,使犹太民族团结起来,即使遭遇难以言说的欺侮和迫害,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介于个体与民族之间的伦理模式也表明马拉默德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从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提升为个体与整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房客》中的民族伦理构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犹太人在经济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成为中产阶级成员。与此同时,美国黑人的生存环境虽然有所好转,但他们的境遇总体说来还很恶劣,职业和身份也没有显著的改变。在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中,黑人所占数量最多,他们不断抱怨生存处境的艰难。美国犹太人在与黑人接触时,往往会产生优越感,而黑人则妒忌犹太人的经商能力和经济上的优势。马拉默德在《房客》中关注的就是美国犹太人与黑人的关系。不同民族文化成员交往时“往往想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是最与众不同的,因为每一种文化在所有成员中维持着这种‘差别’的感觉”(吉拉尔,2002:25)。《房客》的主人公犹太作家莱瑟和黑人作家威利就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对对方持有“差别”的倾向,因此遭遇民族伦理困境。
莱瑟对威利抱有偏见和歧视。莱瑟视自己为文明和教养的代表,而把威利看作野蛮人。他厌恶威利的生活方式,认为他粗俗卑微。威利居住的房间以前生活着一位德国绅士,里面干净舒适,现在却凌乱不堪,到处是污迹。莱瑟觉得威利的身上散发出难闻的异味。他去威利的房间时,总能闻到那脏兮兮的手稿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气味。在莱瑟的潜意识中,威利是一种威胁。威利刚搬来公寓楼时,莱瑟听到他打字的声音,就有一种“竞争和妒忌掺杂在一起的感觉”(Malamud,1988:26)。莱瑟认为威利不可能成为与自己地位平等的朋友,在与其相处的过程中也往往采用冷酷甚至恶毒的手段。威利在创作中遭遇困难,莱瑟持有隔岸观火的态度冷眼旁观,没有对其施以有效的帮助。莱瑟第一次参加威利的聚会,就试图接近他的女友艾琳。莱瑟的动机显而易见,那就是趁着威利忙于写作,疏远艾琳之际,夺人所爱,以此来挫败他的信心和自尊。
威利对莱瑟也表现出冷漠和敌意。初次见面时,莱瑟出于礼貌,伸出手表示友善和欢迎,但是威利根本就没打算与莱瑟握手,让莱瑟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威利不信任莱瑟,他们一起探究写作时遇到的问题,莱瑟谈论自己小说的创意,威利却不肯透露自己作品的内容与细节;他对莱瑟心怀戒备,外出时把打字机暂时放置在莱瑟家里,却不让莱瑟保管自己写作的手稿。威利认为莱瑟这些犹太人看重金钱,待人冷酷无情。他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很难得到认可,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犹太房东总是烦扰他,使他无法静下心来全身心地进行创作;犹太出版商质疑他的创作能力,让他的作品无法出版,创作信心遭受极大的打击;而且莱瑟还抢走他的女友,使他作为男性的自尊丧失殆尽。威利认为,他在社会生活中处处遭受犹太人的压迫和剥削。虽然犹太人曾经给予黑人群体和事业长期有力的支持与帮助,但是《房客》还是探讨了“六十年代黑人持有的反犹主义情绪”(Abramson,1993:90),莱瑟与威利彼此存有戒心,甚至达到敌对和仇视的程度。
马拉默德创作《房客》的意图不是为了展示莱瑟与威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是为了阐明他们怎样做才能防止“差别化”倾向,避免分歧与争斗。马拉默德显然把他们的经历当作前车之鉴,这样人们就能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使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构建美好和谐的伦理关系。
《房客》中莱瑟与威利也曾经互相关照、互相欣赏,马拉默德指出这是构建和谐民族伦理关系的重要途径。在相识初期,莱瑟体谅并且理解威利,他觉得他们是作家同行,所以应该帮助和保护威利。他替威利存放打字机时,提醒他要谨慎,以免被房东发现;威利的行踪暴露后,莱瑟帮助他把打字机藏在浴缸中,还让他躲在书房里;威利的住处被房东毁掉,莱瑟建议他住在自己家里,还出钱买来新家具。莱瑟的行为主要源自两个原因:其一,莱瑟对威利的生存境遇深表同情。他是一个成名作家,凭借之前出版作品的稿酬,过着惬意舒适的生活,但是威利却仍然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因此,他认为威利想要有个安身之处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其二,莱瑟对威利的同情是出于愧疚感。莱瑟已经融入主流社会,但他在威利的身上看到犹太人曾经的苦难遭遇。“犹太人对黑人的境况感同身受,对黑人的苦难感到难过。相对安逸的生活让他们深感不安,有一种罪过感,所以与黑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Berson,1971:183)。莱瑟对威利的包容和慷慨正是出于这种情感。莱瑟还渴望能够过上威利他们那种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生活。在他眼里,黑人代表的是力量和神秘,威利在创作时就比他更加精力充沛。莱瑟被黑人的生活深深吸引,认为他们更看重世俗的享受,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莱瑟通过威利了解创作之外多姿多彩的世界,他的生活不再单调沉闷,有了新的希望,仿佛也看到人生的意义。
莱瑟与威利之间的体谅和理解还表现在他们拥有共同的事业——写作。他们曾经并肩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像亲密的朋友一样轮流吸一支香烟,深入探讨在写作中遇到的难题。莱瑟将一些文学创作技巧传授给威利,还送给他一本语法手册和一本字典。威利则由衷地佩服莱瑟对创作形式的把握,认为他的作品用词精练,形式尽善尽美。他们互相鼓励,计划创作出最好的作品,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两个人构建了和平宽容的生存环境。也就是说,犹太人和黑人可以在共同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很好地合作,平等相处。
马拉默德在《房客》中反思了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那就是如何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化”倾向。如果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展开激烈的斗争,被各自的偏执所蒙蔽,就会在交往的过程中陷入民族伦理困境。只有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相互宽容和理解,才能摆脱困境,实现互补共存。马拉默德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也转变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伦理关系。
《上帝的恩赐》中的生态伦理理想
二十世纪末,生态灾难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爆发,生态伦理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文学素材来源于生活实践,人类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便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马拉默德在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上帝的恩赐》中思考的就是迫在眉睫的生态伦理危机,其关注的重点转变为人类与生态自然的关系。马拉默德在小说中以虚构的科幻故事形式,讲述热核战争爆发后,唯一幸存的人类科恩与一些动物在一个小岛上实践生态伦理理想的历程。科恩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企图控制其他生物体,扰乱了正常的生态伦理秩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只有人类才是价值主体,才具有内在价值,才拥有自己的善或利益;而一切非人类存在物都不过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手段,因而只能是价值客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自己的善或利益: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人类的目的,因而人类便是宇宙万事万物的中心”(王海明,2008:437)。科恩认为,自己处于生态自然的中心,是主宰者和控制者,而其他生物体只是物质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可言。黑猩猩布兹具有天赋,尤其在语言学习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能够开口讲话,但是科恩却始终把它视为低等生物,缺少对它的理解和关爱。他无法忍受布兹原来的名字戈特罗伯,不顾它的一再反对,强行更改名字。科恩把自己信奉的犹太教看得比布兹它们信奉的基督教更重要。他执意将犹太教传授给黑猩猩,相信犹太教能够帮助它们最终进化成人类。实际上,布兹这些生物体具有感受能力,应该拥有利益和需求。科恩把自己当作小岛的绝对主人,不关心其他生物体的感受。他将自己凌驾于这些生物体之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训练和改造。很快,黑猩猩就起来反抗他。
科恩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对其他生物体的本性和需要却视而不见。科恩生活在寂寞孤独之中,只有黑猩猩能够给他些许安慰,雌猩猩玛丽更唤起了他的欲望。玛丽在科恩教导下,逐渐摆脱动物本能,对性与爱的涵义有了初步理解,拒绝和雄猩猩交配,反而与科恩坠入爱河。科恩甚至打算与玛丽生育后代,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具有人类和黑猩猩优点的物种。在他的理念中,自己最具智慧,其基因与玛丽的基因结合起来,可以推动黑猩猩的进化过程。雄猩猩对玛丽的行为感到不解和愤怒,而且更加仇恨科恩。它们的本能和欲望被无限制地压抑,无处得到释放和满足,最终采取暴力反抗的方式把科恩送上了祭坛。“科恩把自己所属的物种、信仰、文明以及智慧看得过于重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制定出行为规则,忽视其他生物体的想法和主张”(Helterman,1985:108)。科恩的所作所为荒谬愚妄,违背生态伦理原则,不仅破坏幸福和谐的生活,而且还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之中。
马拉默德通过科恩遭遇的伦理困境,展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目的不是为了描述生态危机,而是为了警戒人类,提醒人们爱护生态自然中的其他生物体,珍视生态自然。科恩的经历显然是一种警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深刻理解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马拉默德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人与生态自然融洽相处的场景:科恩生活在生机盎然的植被草木之中,与动物在共同的生活中彼此帮助,相互关爱。此时的科恩关心其他生物体,与它们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达成与生态自然的和谐共存。
小岛的生态美景表明存在摆脱生态伦理困境、实现生态伦理理想的可能。热核战争之后,人类文明已经毁灭,但是小岛上的花草树木依然顽强生存,实现着各自的生命价值。“热带丛林广阔无边,笼罩着交叉的枝叶,点缀着遍布苔藓的圆形蔓藤,阳光几乎照不进来……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花丛映入科恩的眼帘。人类与兽类都已经灭亡,鲜艳的花朵却依然香气扑鼻。上帝喜欢这样的色彩和芬芳”(Malamud,1982:42)。虽然没有昆虫授粉,但是植被却仍然繁荣兴盛。它们灿烂美丽的色彩、沁人肺腑的芳香既增添了美丽的生态景象,也展现了恒久的生命活力。小岛丰富的生态景观深深打动了科恩,它们在科恩眼里不但富有诗意,而且还具有灵性,甚至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科恩在这如同天堂一般的生态自然中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马拉默德通过描写生态自然,展示其生态伦理理想:即只有保持平衡的生态环境,人类才能够生存下去,才能为后代子孙的生存发展留下空间。
科恩也曾经把小岛上的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之内,与它们和谐相处。小说开始时,科恩眼中的布兹非常机灵,可以使用手势语进行交流,就如同一个聪明的小男孩。科恩认为,布兹与人类拥有共同的生命本源,存在众多相似之处,应该被看作独立的、与人类平等的生物体。他为陷入饥渴之中的布兹提供食物和饮水,并且帮助它消除热核灾难带来的害怕和恐惧。他还向布兹传授语言技巧与文化知识,把它看作渴望学习的孩童。大猩猩乔治自始至终都体现生物体存在的意义。科恩曾经病重陷入昏迷,幸亏得到乔治的救助才幸存下来。乔治甚至具有同人类一样的情感,可以感受到痛苦和快乐,它听到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被深深地打动,好像都要哭出来……这些描述表明布兹和乔治都是小岛生态共同体中的成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去谋求生存与发展。马拉默德通过科恩与其他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爱护,说明“人和动物之间并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完全可以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李培超,2001:89)。也就是说,动物拥有同人类一样的伦理地位,具有情感和意志,应该给予它们同样的伦理关怀。
马拉默德在《上帝的恩赐》中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融到一起,为人类实现生态伦理理想指明了途径。当科恩违背生态伦理原则,在动物身上强行实践自己的意愿时,就陷入生态伦理困境之中。当他把自身看作生态自然的成员,承担生态伦理责任时,就达成与生态自然的默契。小说的结尾,乔治为祭坛上的科恩祈祷,唱起赞美诗,让自己的道德仁爱充盈世间,润泽万物。马拉默德凭借这一情节表明,只有道德仁爱能够消除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误解,加强彼此的沟通和理解,从而实现和谐的生态伦理理想,维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马拉默德的小说不仅展现人类遭遇的伦理困境,而且更加强调走出困境、实现救赎的途径。他的小说考察这一过程中各种伦理关系的变化,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从创作早期的个体在事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人际交往困境,到成熟时期的反犹主义势力下犹太民族遭受的犹太伦理困境,到后期的人类文明进程中遇到的民族矛盾冲突,再到最后的生态伦理危机,马拉默德小说的伦理思想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关注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之后演变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最后则是人类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变表明马拉默德的思想与创作日益走向成熟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