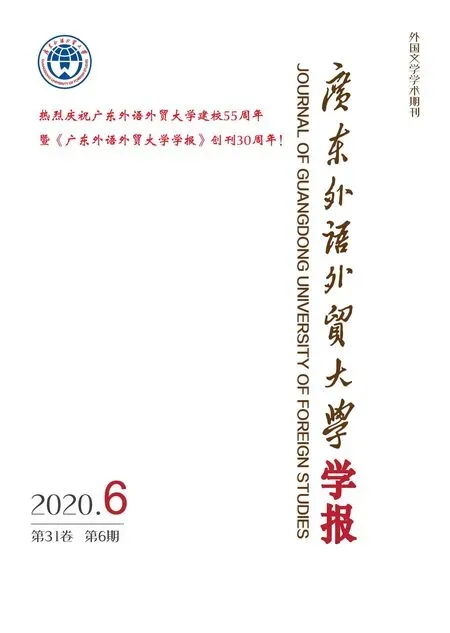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帝国的男性气概
——以《所罗门王的宝藏》为例
王荣
引 言
博埃默(1998:13)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两大文类是三卷本小说和历险小说”。在一八八○年以后,历险小说被大量印刷,在文学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十九世纪末历险小说的复兴与繁荣背后的原因很多,既有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有文学市场化的刺激。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刺激了人们对远方异域的想象。格林(Green,1979:3)将历险小说定义为“政治帝国在文学类型上对应物,英格兰认识、探索、征服与统治世界的能量神话”,而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出版行业的改革为小说市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那就是大英帝国的男性气概危机,这一点经常为批评家们所忽略。历险小说毕竟是一种男性文本,是一种“阳刚之气”的文学想象。不过,这时期历险小说中“阳刚之气”的想象与建构总是绕不开“帝国”这一中心主题。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历险小说还有另一个称谓——“帝国罗曼司”(imperial romance)。确切地说,这一术语指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文学市场上以殖民地为背景的历险故事。帝国罗曼司诞生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与大英帝国的经济衰落、全球影响力下降存在密切联系。斯蒂文森、哈格德、吉卜林和康拉德不像十九世纪早期历险小说家罗伯特·莱顿、R.M.巴兰坦、马里亚特那样乐观,对于帝国扩展的态度也更加模棱两可,充斥着对英雄冒险机会减少的担忧,对帝国前途未卜的焦虑以及对古老骑士风范的怀旧。由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建构都无法回避“帝国”这一中心主题,尤其是从瓜分非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帝国事业是所有英雄行为展开的时代背景,因此帝国罗曼司文本中的男性气概经常被冠名为“帝国的男性气概”(imperial masculinities)。国内学者指出,“这种富于侵略性男子汉气概具有明显的帝国意识……蕴含着明显的殖民主义潜台词”(陈兵,2012)。这种说法似乎简化了男性气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十九世纪男性气概的历史发展与帝国扩张存在密切联系,但是这里的“帝国”与“男性气概”两个元素值得深入探讨。帝国如何影响男性气概的认知?如何满足男性气概的需求?男性气概与殖民主义是一种简单的共谋关系吗?
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所著的《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Solomon’sMines)被西方批评家帕特森(Patterson)誉为最典型、最成功的帝国罗曼司文本,讲述了三位英国人前往非洲内陆寻亲,却意外发现一个失落种族并获得宝藏的历险故事。哈格德将这本书献给“大大小小的男孩们”,男性气概或者男性身份无疑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主题之一。西方学者将哈格德笔下强悍的男子汉形象视作十九世纪晚期英国男性气质的典型,而国内学界基本停留在作品中帝国话语的讨论上。本文以《所罗门王的宝藏》为例,探讨帝国扩张与“退化”焦虑影响下,理想的男性气概标准的变迁及其在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体现,试图揭示男性气概与殖民主义之间既支持又对抗的复杂关系。
十九世纪末理想男性气概的变迁
简单地说,男性气概是特定历史时期对男性特征或者专属于男性的行为表现的社会期待。曼斯菲尔德(2009:57)指出,“男性气概不是某种所有男人都具有的性质,而是少数男性以一种高级的方式具有的品质”。男性研究领军人物R.W.康奈尔从社会学研究入手,强调男性气质的历史属性和多元存在。具体地说,男性气质是一个复数概念,不存在一种本质主义、单一的男性气概。一个社会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男性气质,往往只有被主流社会认可“支配性男性气质”为人们所熟悉,并随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断发展与变化。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气质在十九世纪就发生了多次变迁,各种男性气概观念之间充满冲突,这种不稳定感与危机感在世纪末达到顶峰。
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Showalter,1990:9)指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男性的权力、地位和角色都在悄然改变,男性在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层面都感受到一种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触发了男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彼时,女权运动颠覆传统的性别秩序,“新女性”要求分享更多的公共空间,主张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另一方面,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量男性失业。物质财富一直被视为构成男性阳刚之气关键的要素,失去工作之后男性甚至有一种被阉割的感觉。《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亨利爵士就是这样一名“多余的绅士”,他在农业大萧条后,失去了原来体面的社会地位;另一位主人公古德上校从皇家海军退役后,身材臃肿,意志消沉。显然,在十九世纪晚期,维持传统的男性价值观和行为变得困难。
在政治、经济、性别变化的压力下,人们所期望的男性气概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十八世纪以来,理想的男性气概被冠以绅士的称号,一直与良好出身、拥有财产、彬彬有礼、控制欲望、重视道德联系在一起。绅士阶层也局限在贵族阶层,至少是中产阶级,工人阶层不大可能被称为绅士。维多利亚时代初期非常看重“家庭”对男性气概的界定,体面绅士的核心道具是“妻子、家庭与孩子”,男人不仅要有体面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应该对妻子忠实尽责,对孩子关爱有加,热爱家庭生活。然而,“一八七○年之后,英国中产阶级的男性气概开始偏离家庭价值观,不再强调理性、逻辑思辨能力是理想的男性品质”(Tosh,2005:32)。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非常在意男性的内在品质,如道德修养、自律勤勉、温柔体贴、多愁善感等,这些行为与品质在十九世纪末却被认为女性化的表现。谨慎克制、彬彬有礼的绅士不再是理想的男性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强壮、有勇气、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男性,这明显与帝国扩张的需求有关。海恩(Hyam,1991:72)指出,“十九世纪末,传统基督徒的男性理想被身强力壮的男性标准所取代,上帝信仰、强烈的道德感与良好的学识让位于行动敏捷、充满活力、身体强壮”。身体力量与体育精神是十九世纪末男性气概的重要构成因素。在一八六○到一八八○年之间,竞技体育是英国公立学校的必修课,对竞技运动的狂热席卷了所有学校,甚至连哈罗公学、拉格比公学都将重心从学术转向体育。政策制定者认为竞技场与战场具有一定的关联,鼓励竞技精神可以帮助未来的中产阶级男性成为更好的殖民管理者。
人们不仅质疑传统男性气概的构成因素,还对男性气概的意义展开公开辩护,将男性气概与帝国的存亡联系起来。十九世纪末,尽管英国统治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但是衰落的迹象若隐若现。一八八一年二月,第一次布尔战争英军伤亡惨重,被迫同意议和。一八八五年总督乔治·戈登在苏丹被击毙,国内舆论哗然,指责英国军队战斗力低下,英雄气概堪忧。童子军的创始人巴登·鲍威尔直言帝国衰落背后是男性气概的衰落。在《童子军》(1908)中,他写道“请记住,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与今天的大英帝国一样伟大,可是它最终覆灭了,因为年轻的罗马人放弃了男子气概……”(Baden-Powell,1932:277)。巴登·鲍威尔创立了童子军运动,目的是为了拯救英国青少年的道德堕落、体格衰弱,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与骑士精神。著名思想家约翰·蜜尔在《论文明》(1836)中指出,“一股精神上的娇弱女子气正悄然逼近有教养的阶层,逼近英国所有的绅士,它不适于任何形式的斗争”(布劳迪,2007:335)。对男性阳刚之气衰弱的担心被英国士兵在海外战争中的表现所证实。布尔战争期间的新闻报道称,英国志愿者中仅三分之一勉强合格,而毫无问题的人只有十分之一。在工业城市曼切斯特,应征入伍的士兵有四分之三未能通过体检。一九○○年英国入伍士兵中身高低于一米六八的人与一八四五年多了四倍。为此,一九○四年英国政府专门设立体格退化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帝国是由男性来管理的,如果国内的男性气概出了问题,他们怎么能够在海外有效地管理殖民地呢?帝国衰退与种族退化的双重焦虑在男性气概这个话题上达成了一致。
十九世纪晚期,当旧的男性气概受到挑战,新的男性气概尚未形成,男性更希望通过同性社会关系来重构自己的男性气概。托什(Tosh,2004)发现维多利亚时代“支配性男性气质”尤其重视以下四个方面:“健壮的身体、个人权威、独立性以及男性同社会交往”。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同社会交往使男性作为一个性别阶层共同压迫女性,越在性别体制或者性别结构不稳固的时候,越是需要被强化,以重建被女权运动冲击的社会秩序与性别体制。去哪里寻找更适宜建立同性社会关系的环境呢?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帝国是绅士活动的一个极好的舞台,是责任、进步观念,是与邪恶战斗,是履行职责,是取得荣誉的终极实验场所”(Cain & Hopkins,1993:43)。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几乎完全由单身汉来统治,当时不少著名的帝国英雄都是同性恋者,如塞西尔·罗德斯、赫克托·麦克唐纳、贝登堡与基奇纳。虽然女权运动要求进入公共空间,但海外殖民活动尚未被白人女性染指。前往殖民地工作的年轻人,一方面被殖民地财富所鼓舞,同时也庆幸可以从家庭生活的程式中逃离出来,去拥抱一个男性团体的边疆生活。帝国的边疆不仅为国内失业男性安排出路,还可以让其远离“新女性”的干扰,在一种同性社会关系中建构、证明自己的男性身份。
《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原始的男性气概
十九世纪晚期,当男性气概衰落成为共识之后,许多人渴望用一种原始的、野蛮的,但充满生机的力量拯救处于危机中的男性气概。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历险小说中的男性几乎都感受到城市文明对男性的束缚,城市狭隘的环境限制了男性的活动范围,让男人局限在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上,从而丧失了在社会事务之外冒险的冲动与机会。只有离开文明的英格兰,到帝国的边疆去,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在“高贵野蛮人”的影响下,才能重塑男性气概。正如《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夸特曼说的,“只有辽阔大海和怒吼狂风的洗刷,才能吹净他们的是非之念,把他们改造成真正的绅士”(Haggard,2002:16)。
《所罗门王的宝藏》将非洲荒原描述为与现代文明对立的伊甸园,一个浸润在深山中的农业社会。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雨水充沛,气候宜人,洋溢着大自然的和谐气息,有着“极度荒凉迷人的景色”以及“英俊的大羚羊”等着白人去享用和开拓。在这个伊甸园中,男人得以挣脱文明的束缚,重新活得像一名男子汉。他们通过身体行动,挑战冒险、狩猎、战争等危险性的性别实践,来习得、建构、展开并体现自己的男性气概。在紧张刺激的冒险活动中,男性气概本身就是目的,男性气概对抗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成为一种虚无的形而上存在。
狩猎活动是十九世纪历险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许多历险小说甚至可以视为一连串狩猎活动的串联。狩猎制造了紧张氛围,让历险活动变得更加值得期待。狩猎需要冷静、耐心与敏捷的行动,让男人们在与严峻大自然对立中,展示自己的百科知识、忍耐力、勇气,并提供对野生动物习性、充满敌意的自然环境的描述机会。这些狩猎活动是典型的身体力量与霸权的完美结合,带来了征服的权威感和兴奋感。哈格德的小说倾向于把非洲看作英国贵族的后花园,那里有各种可以猎杀的大型动物,如大象、麋鹿、河马、羚羊等。阿兰·夸特曼是维多利亚文学史上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猎象人,是南非草原上最好的神枪手。即使是最凶暴的非洲象、狮子、犀牛,只要被他瞄上,一枪就了结它们的性命。《所罗么王的宝藏》中单辟一章来讲述猎杀大象的情景,赞扬夸特曼的谨慎与机敏,展示了欧洲白人在狩猎活动中的团结协作。在海外历险,他们需要开枪涉猎以保证自己的食物供应,这种简单质朴的饮食与国内贵族骄奢淫逸与空虚无聊形成对比,而以鲜肉为主的饮食对贫困的下层阶级形成了一种诱惑。
除了狩猎,帝国边疆为男性气概提供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战争。当男性气概受到威胁与挑战时,男性尤其需要战争来激发杀戮的本能。“战争既不属于利欲熏心的中产阶级,也不适合任性放纵的女人,它就像一个座熔炉,净化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腐化堕落,在渣滓中提炼出阳刚的奋斗精神”(布劳迪,2007:41)。自古以来,很多文化中男性参加战争不仅是一项不间断的义务,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激发、培养男性气概,仿效英雄榜样的舞台。哈格德(1826:103-104)在自传中说,“男人本来就是杀戮的动物,从荷马时代甚至几千年之前就是如此。战争可以磨练一个男人最好的品质,如爱国主义、勇气、对权威的服从,对苦难的忍耐以及对朋友的忠诚”。《所罗门王的宝藏》中三位英国人打着正义与友情的旗号加入土著人的内战。然而,这一切都是托辞,他们似乎就是为了体验杀戮的快感而来。夸特曼形容自己“从内心深处,产生出战斗的激情……一种野蛮的厮杀的欲望被激动起来。我回顾身后一排排勇武的士兵,忽然觉得自己的面孔似乎和他们并不两样”(177)。古德认为“打仗是很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亨利爵士更表示“我们就是为打仗而来的,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182)。这里的战斗是复古式的,荷马史诗般的语言暗示着农业社会才是理想男性气概的温床,男性气概需要诉诸对抗、战斗与杀戮的本能。穿着土著服装的亨利“手持战斧,全身为鲜血染红,面目与他那丹麦武士祖先一样”(183)。在非洲,在英勇的厮杀中,亨利与远古的自我相逢,绽放了野蛮的本性。在最后关头,亨利弃用手枪,拎着斧头,与国王决斗,用动物天性的狂暴,砍下了国王的头颅,维护了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
可以说,《所罗门王的宝藏》为原始男性气概的回归提供了一个梦幻世界。尽管每次长途跋涉、狩猎与战争都惊心动魄,但主人公总是有惊无险地逃离了一个又一个陷阱,这点与游戏非常相似。弗莱(2007:190)曾经如此评价哈格德的历险小说:“这种故事旨在给我们生活的连续体提供某种理想化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一个无尽的梦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保持迷失自我的状态”。哈格德的历险故事让“大大小小的男孩们”摆脱了十九世纪早期男性气概所要求的道德规范,让男人重新发现体内的那个儿童,并在帝国边疆将其复活,在洞穴、丛林、深山中,释放了那个内心深处、渴望无政府混乱状态的原始自我。维多利亚文化史专家布兰特林格(Brantlinger,1988:190)指出,“非洲可以让英国男孩成长为男人,但是哈格德的小说中英雄们却从成年人退化为男孩了,这其中的区别似乎很难分辨”。的确如此,成长为男人与退化为男孩,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哈格德笔下的白人渴望非洲荒原,因为这里提供了一个可供游戏与冒险的场所,让他们回归神话世界中男性理想,拥有中世纪罗曼司中高贵的骑士精神。在这里,他们变成了行动的动物,品尝杀戮带来的快感,却不用担心被惩罚。
加拿大作家兼文学批评家阿特伍德指出,哈格德与康拉德二人笔下的非洲都是欧洲文明“黑暗心脏”的隐喻,是对未知自我与潜意识的探索。“财富不是主人公前往非洲的真正目的,他们要去遭遇、重新发现文明人已经丢失另一个自我”(Atwood,1972:113)。埃瑟林顿(Etherington, 1978)也认为哈格德的小说不是庸俗帝国话语的宣传,“非洲腹地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景观,在那里欧洲白人经历了身体与道德的双重考验,直面并屈服于内心深处的恐惧”。的确如此,哈格德注意到一个原始的、令人道德败坏的“他者”蛰伏在白人内心深处,而非洲荒原是将文明深处的“黑暗”暴露、释放出来的绝佳场所。不同的是,在康拉德那里,“返祖”转变成为文明的悲剧,臣服于野蛮诱惑的库尔兹淹没于可怕的荒原中,再也回不来了,而哈格德则赞同文明与野蛮的合二为一。野蛮是男性气概的本质属性,它代表了一种本能的自然力量。非洲不仅是一个让自我与超我相遇的地方,一个现在与过去交融的场所,还是一个“自我”与“他者”混淆的场所。作者不止一次将亨利与库库安纳国的王子参照对比,他们身高、衣着、神情和语气都极为相似,暗示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高贵的野蛮人:男性气概的标本
性别身份的建构无法在真空中进行,男性气概总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与互动来建构自我。这里的“他者”可能是大自然、女性、或来自不同种族和阶级的男性。与大自然的对峙体现在狩猎与战争考验中,女性他者则以天使、妖妇或者地理空间的方式来考验男性气概。前文提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男性气概尤其重视同性社会交往,并强调男性同盟在男性身份建构中的作用。在这个男权中心社会,男性总是把身份认同与获得建立在其他男性的认可之上,而不是与女性之间的联系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男性同社会交往不局限于三位白人男性之间,同样包括与“高贵野蛮人”的同性社会交往。辛哈(Sinha,1995:5-6)关于殖民地男性气概的研究表明“男性身份的建构与其他社群中男性之间的关联程度,并不亚于男性身份建构与女人的关联”。与野蛮人的同性社会交往,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白人之间的男性同盟更加重要。迪恩(Deane,2014:268)指出,“维多利时代晚期与爱德华时代的男性气概标准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与种族的真实与想象的交往之上的”。这一时期的历险小说融入很多外来者的男性气概,并颂扬他们身上的阳刚之气。
在《所罗门王的宝藏》的开篇处,夸特曼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叫绅士?我也说不清楚。我曾和黑鬼们一起干活。不,我要彻底抛掉‘黑鬼’二字,我熟悉当地人,他们都算得上绅士,我的孩子哈里也会这样说,我也熟悉那些有钱的白人,他们就算不上绅士”(43)。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绅士”形象的国度。“绅士”理想就是一个时代“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代表了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对理想男性品质的定义。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绅士概念崇尚理性克制、彬彬有礼的男性类型,非洲土著的嗜血好战曾被视为放纵本能欲望的表现而遭到唾弃。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种族退化的焦虑与战争的威胁使得代表自然力量的“野蛮人”形象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十九世纪末的报刊杂志甚至公开赞扬非洲男性的男性气概。《所罗门王的宝藏》中野蛮人超越了笛福历险小说中的“星期五”的模式,成为欧洲白人反思、建构男性气概的参照对象。哈格德不仅把库库安纳国的男人列入绅士的行列,还暗示他们才是男子汉的标本,欧洲人若想重塑男性气概,必须以其为榜样,才能对抗现代文明对男性气概的侵蚀。
哈格德笔下的祖鲁人算得上英国文学史中最聪明、美好的野蛮人。他们身体强壮,勇敢忠诚,还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库库安纳国的王子伊格诺希就是“绅士”形象的典范。在白人面前,他始终不卑不亢,“我们都是男人,我和你是一样的”(70)。在面对危险时,他感叹道“生命不过是一根鸿毛,生命是一颗飘来的草籽”(80),表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绝望,暗示了真正具有男性气概的人不会算计、推论和控制风险,而是奋勇向前,奉献并创造了生命。《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野蛮人是天生的战士,他们不虚伪、庸俗,也没有现代人的歇斯底里症,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与学习榜样。即使作为反面角色的国王,在最后的决斗中被砍头,也表现得光明磊落。这里没有赛义德“东方主义”里所强调的“他和我不一样”的差异性,更多地体现了霍米·巴巴提出的杂糅性。在非洲这个“第三空间”中,英国人原来的文化身份被颠覆,他们要重新协商自己的男性气概,通过效仿黑人同伴重建男性身份认同。在男性气概的对抗与交往中,混杂性占据主导,殖民话语权威被颠覆。
在西方人那里,关于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曾经是最普遍地解决文化问题的工具。文明人通过他与更原始状态或自然状态的人的差异来解释他的认同,在建构他者中塑造自我,表现出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文明”曾经成功地建构了男性支配,建构、维护了中产阶级白人在阶级、性别和种族上的权威。文明是一个完美种族的最高成就,就像男性气概是一个完美男人的最高成就一样。一直以来,种族都是定义白人男性身份的重要维度。殖民者利用白人优越的观念,创造了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男性优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殖民地的男人经常被情欲化与女性化,殖民话语中对于东方男性“女人气”的刻板印象的建构无处不在。欧洲人在殖民过程中存在一个潜台词,那就是殖民地的男人粗鲁野蛮或者女子气。总之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这就赋予了殖民统治与控制一种合法性。“文明教化”的任务就是要用基督教将被殖民者驯化为克制自律、彬彬有礼的绅士。
然而,如果男性气概不再与“文明”的内涵、种族身份绑架在一起,无关乎绅士的彬彬有礼、自律控制,而与野蛮的身体力量、坚强的意志力密切相关,那么欧洲人“文明教化”的使命在逻辑上就被否决了,殖民主义的合法性随之轰然倒塌,殖民话语的权威也将土崩瓦解。《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土著男性丝毫没有殖民地男性气概的刻板印象,他们勇敢善战、高贵忠诚,充满民族自豪感。具有悖论性质和讽刺意义的是,三位英国人不但没有完成“文明教化”的使命,反而被野蛮“他者”身上唤醒了“自我”内心深处的欲望。他们不是来消灭落后与野蛮,也没有履行道德教诲与基督教传播的责任,却在野蛮人的感染下,拿起了斧子、刀剑,与其并肩战斗。他们识破了文明虚伪堕落的本质,从复杂的社会规范与生活矛盾中解脱,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欲望。在这里,野蛮与冲动并不意味着无序、混乱,令人烦恼的担忧,不再是一种犯罪或者缺乏自律的表现,而是一种力量的符号,是男性气概真实血性的表达。很明显,《所罗门王的宝藏》表达了一种反文明、反理性,渴望回归自然和本真状态的“原始主义”,这种原始主义与殖民扩张不是简单的相互复制、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是一个充满抵抗、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三位英国人对非洲土著的模拟揭开了殖民话语的含混,破坏了其权威,最终超越了殖民主义扩张的初衷。
结 语
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男性气概遭遇挑战,新的男性气概标准呼之欲出,并在历险小说中找到最好的表达。《所罗门王的宝藏》提倡一种野蛮粗狂的男性气概,拥护一种刚性、质朴、好战的男性品质,试图复活被文明压抑的活力,以应对帝国衰落与种族退化的双重焦虑。在这里,男性气概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品格,寻求冒险,欢迎意外,对于金钱和物质财富不感兴趣,不依赖于装腔作势的文明教养。这种简约版的男性气概迎合了帝国扩张的欲望,广袤的殖民地成为检验、重塑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同时它又跨越了种族与文化的界限,沟通了过去与现在、自我与超我、自我与他者之间男性气概的本质认同,颠覆了殖民话语的权威,进而质疑帝国扩张的合法性。
自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将历险小说当作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范本之后,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历险文本中充斥着浓厚的帝国主义情绪。历险小说似乎是为了宣扬帝国意识而存在的,并随着帝国的衰退而衰落。不可否认,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发展与帝国扩张活动密切相关,但是诞生于帝国统治能力危机的焦虑,帝国宣传并不是历险小说的文学初衷,历险小说本质上是一种“阳刚之气”的文学想象。男性要到帝国边疆去,因为那里可以逃离“过度文明”的压迫与国内“新女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解决男性气概危机、逃离现代文明与殖民扩张是同步进行的,这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输出,也不是“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输出,而是为了满足迷失男性的深层心理需求,完成男性气概的自我拯救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