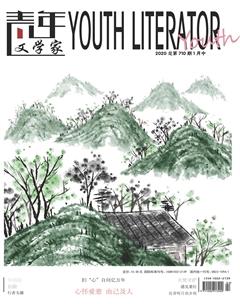泰戈尔早期历史小说与印度传统文化
摘 要:泰戈尔的早期历史小说《王后市场》与《贤哲王》均以16、17世纪的莫卧儿王朝为历史背景,从孟加拉地区的视角出发,反映了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地方王国中王室的生活状况与权力斗争。泰戈尔的历史小说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不仅折射出莫卧儿时期印度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权力运行机制,更折射出孟加拉地区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传统中蕴含的种种危机,表达出了生长于孟加拉大地的泰戈尔对印度本土文化的敬重和反思以及寻求变革的呼声。
关键词:泰戈尔;历史小说;印度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孙剑奇(1996-),女,山东淄博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2
泰戈尔的历史小说取材于莫卧儿王朝的历史事实,是印度的政治机制、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问题的集中体现。这些作品既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又超脱传统,表达出破除陈规束缚、抗击权贵势力等新派思想。这体现了泰戈尔本人对待印度传统的理性辩证的态度。
一、基于孟加拉文化的改革与创新
泰戈尔的作品多用其母语孟加拉语创作,其历史小说也以孟加拉地区为中心,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相比于印度其他地区,孟加拉地区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在历史上曾有过多彩灿烂的文化;同时,该地区又是印度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先驱,它地处东部沿海,是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最先占领的地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想影响,产生出受过英语教育的新集团。[1]近代印度的新派文化最先产生于孟加拉地区,19世纪的印度教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也发端于以泰戈尔故乡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孟加拉一带。19世纪初,罗易成立了具有宗教改革和启蒙色彩的组织“梵社”,后泰戈尔之父德本德拉纳特成为“梵社真正奠基人”。梵社由社会精英阶层和高种姓的贵族阶层领导,[2]出生于婆罗门知识分子家庭的泰戈尔自然便耳濡目染地受到孟加拉地区新思想的熏陶,在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新思想的烙印。
《王后市场》与《贤哲王》两部小说都反映了在莫卧儿王朝统治下孟加拉地区本土王室的生活。16世纪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帖木儿帝国后裔征服了南亚次大陆,建立了莫卧儿王朝。而之前各地的本土邦国在归顺莫卧儿帝国后,原邦国首领仍被允许管理之前的土地。莫卧儿王朝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为避免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教徒的冲突,他宣布各教派平等,并任用印度教官员。因此,各地本土邦国的印度教信仰和仪式被保存下来。印度教教派林立,体系繁杂,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信仰。孟加拉地区多崇拜性力派的杜尔迦女神与迦梨女神,带有一定的女性崇拜意识。《贤哲王》中的戈宾多马尼克国王在初见女孩哈湿时,对她说“小母亲,我是你的孩子”,当他目睹哈湿用纱丽擦拭杀生祭祀留下的血迹的行为之后,认为“伟大的女神化作一个小女孩来见我。她对我说,作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圣母,她不忍心看到生灵流血”。[3]崇拜迦梨女神的情节也多次出现在泰戈尔的历史小说中。在反映孟加拉传统信仰的同时,泰戈尔也反映了宗教冷酷的一面,如《贤哲王》中的祭司罗库波迪因不满国王戈宾多马尼克的废止杀生祭祀的政策,便令人杀害国王,要将他的血献于迦梨女神的脚下。这一情节影射了孟加拉地区宗教祭祀、偶像崇拜仪式的复杂繁琐以及婆罗门祭司权力的至高无上,而这些恰恰是印度教阻碍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弊病。以“梵社”为代表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正提倡简化宗教仪式,由外在礼仪转为内心崇拜,把矛头指向印度教神学体系中的偶像崇拜和繁琐祭礼,并在得救道路上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虚无的来世转到现实生活上来。[4]《贤哲王》明显体现了这种思想,它赞扬了戈宾多马尼克废止杀生祭祀这一决策的英明,对他的仁爱、慈悲等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元素表示歌颂。同时,在婆罗门阶层的权力问题上,作者塑造了两个形成对比的人物——婆罗门罗库波迪和比尔邦。罗库波迪坚持以杀生祭祀为代表的传统祭仪,对国王废止杀生祭祀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并认为自己通过种种手段推翻戈宾多马尼克这一“亵渎神明”的国王是合乎正义的。比尔邦是一个思想前卫的婆罗门,他拥护戈宾多马尼克的统治,支持新政,并打破种姓偏见与教派偏见,在瘟疫中照料遭难的帕坦人。在比尔邦身上体现了泰戈尔所颂扬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作者心目中新式宗教人物的典范。作者并未把罗库波迪塑造为一个反派典型,而是细致刻画了他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使其自己醒悟,意识到残暴的杀生祭祀不是维持信仰和统治的良方。罗库波迪思想的转变,更表明了在基于同情之上的人性普遍法则与受到刻板僵硬的传统制约的仪式主义礼法之间的较量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胜利,使这个故事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所以,泰戈尔的历史小说深深植根于孟加拉地區的文化传统,展示了孟加拉地区独特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同时,他的历史小说又体现了近代孟加拉地区思想的开放性与多元性,针对陈腐的陋习表示出批判,传达出改革与创新的时代呼声。这使他的历史小说具有了借古讽今的意义,对于印度近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对印度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对印度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进行反思批判的同时,泰戈尔的历史小说中也蕴含着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表达了他对民族传统的热爱与重视。泰戈尔自身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艺术渗透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泰戈尔的泛神与博爱的思想与印度教传统的泛神论有密切的联系,他继承了印度传统的优秀成分,并加以时代性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富有前瞻性与人道主义色彩的新的创作思想。所以在他的历史小说中,充满了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烙印,这些传统成分与所传达的新思想相结合,更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具有思想启迪意义。
《王后市场》与《贤哲王》两部历史小说都反映了王室的生活,而在印度传统文学中,反映王室生活的作品不在少数,如两大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等。在印度的传统文学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贤明君王形象的固定模式——如国王必须骁勇善战、体察民情、遵守正法、铲除非法、宗教信仰虔诚、有牺牲和苦行精神等。“正法”是印度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不仅代表着维系社会运转的法度,也代表着个人修养需要达到的重要准则。符合“正法”的行为往往与“非法”相对,印度传统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善恶取向,正邪双方泾渭分明。《王后市场》与《贤哲王》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中,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学里贤明君主的影子,这些人物的品德同样也是传统文化层面的典范。而传统文学中的贤明君主作为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一定程度上是泰戈尔历史小说中正面人物的文学原型。
《王后市场》中的王子乌多亚迪多不满父亲的暴虐统治,但在与之抗争的过程中并未实质上改变现状,而是最终远离宫廷和政治,过上了归隐的生活。这是一个看上去并没有通过斗争推翻恶势力的“消极”结局。但在这个结局背后,隐含着一个普遍的文学原型——传统文学中的遁世归隐模式。《罗摩衍那》中的罗摩有遭流放14年的经历,《摩诃婆罗多》中的般度五子因在赌局中失掉了国家,输给了难敌及其兄弟而流亡12年。这些都是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遁世并不代表着最终的失败,而代表着一种磨练、修行,是使精神境界获得提升的一种途径。并且在印度教传统文化中,遁世、林栖与隐居也被赋予重要的含义,印度教徒的一生被划分为四个时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与遁世期。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遁世归隐现象与宗教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即使身为征战四方、保卫权势的国王,但仍应服从并遵守宗教规范,其行动与思想与宗教关系紧密。在遁世流亡期间,他们大多化身为婆罗门,遵守瑜伽与苦行。同样,《贤哲王》中的国王戈宾多马尼克,也是在经历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遁世隐居后才获得了思想和精神上的升华,进而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国土。泰戈尔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延续了传统文学中“经过放逐获得重生”的模式,可见其文学创作对于传统的发挥与继承。
另外,泰戈尔的历史小说中有意运用传统文化的各种典故,使读者很容易将小说中的具体人物与传统文化中的某个原型联系起来,且小说人物与传统原型之间具有遭遇上或者气质上的相似性。如《王后市场》中的碧帕与《罗摩衍那》中的悉多相对应:像悉多因为贞洁受到怀疑而被丈夫抛弃类似,碧帕也被昏庸懦弱的丈夫罗摩琼德罗抛弃。小说中也有意将这两个人物相联系,如碧帕得知自己被丈夫抛弃后,心中祈求“啊,大地母亲,请你为我裂开一条缝吧!”[5]而悉多最终为了证明自己的贞洁,恳请地母將大地裂开一条缝收容自己:“于是女神那地母,两臂合拢抱悉多;向她致敬并欢迎,把她放上了宝座。悉多坐在宝座上,一下子没入地中;撒到那悉多身上,不断花雨落碧空。”[6]碧帕与悉多一样,集合了印度古典女子的美好品质:谦逊、贞洁、温顺、美丽、注重家庭利益。面对陷入困境的兄长乌多亚迪多,她默默地在其背后给予支撑;对丈夫罗摩琼德罗,她始终保持女子的贤淑与谦逊,并在心中对其寄托希望与爱意;对丈夫手下的贤臣拉姆莫洪,她用敬重和信赖赢得了对方的支持。碧帕这一具有古典美的形象与其父、夫的昏庸丑恶形成鲜明对比,是泰戈尔笔下爱与美好的象征,“王后市场”一名也代表着人民对她的一种纪念。《贤哲王》中的两兄弟戈宾多马尼克与诺科特罗正与《摩诃婆罗多》中的般度族与俱卢族相对应:戈宾多马尼克推行仁政,遵从正法;诺科特罗意志薄弱,被人当做棋子来利用,获得权力后荒淫无度;戈宾多马尼克在得知弟弟反叛自己的消息后,也像般度族那样被亲情和伦理关系所困惑,不能坚定地做出大义灭亲、与对方抗争的决定。由此可见,泰戈尔的历史小说中多处采用了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框架,表现了他对印度古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同时,对于优秀的传统美德,如奉献与仁爱,泰戈尔对此表达了热烈的赞扬,对于作品中主人公的正义行为,他直接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对其表示肯定,同时对他们不幸的遭遇表示同情。这体现了他基于印度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
三、结语
泰戈尔的历史小说与印度传统文化关系密切,表达了他对印度传统文化的态度:他热爱博大精深的印度文化,歌颂符合传统文化的古典美,并身体力行去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他又站在时代的潮流中,理性地看到传统文化中阻碍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元素,如宗教问题、种姓问题和妇女问题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种种构想。泰戈尔历史小说中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并不是通过尖锐激进的改革,而把希望寄托于改革人们的思想,提升民智。正如《贤哲王》中的罗库波迪一样,在经受种种实践的洗礼之后最终获得思想上的超越和醒悟。这种从内向外的改革也与印度传统文化注重精神世界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因此,泰戈尔的思想与印度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即植根于传统,又超越于传统。
注释:
[1]王雪.19世纪印度教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5卷第2期..2008年6月.
[2]吴高帅.19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15年5月.
[3]泰戈尔全集.第十一卷.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主编.黄志坤 董友忱译[T].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王雪.19世纪印度教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5卷第2期.2008年6月.
[5]泰戈尔全集.第十一卷.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主编.黄志坤 董友忱译[T].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6]季羡林文集.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T].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