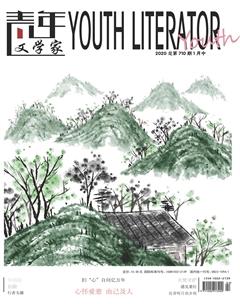空谷回荡的救赎
摘 要:《伤逝》作为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大有不同,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是用小说的形式,将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通过这个悲剧揭露旧社会的腐败和罪恶,同时深刻指出孤立地追求个人的幸福是没有出路的,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投身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
关键词:《伤逝》;救赎;爱情
作者简介:王慧妮(1996-),女,汉族,辽宁省铁岭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1
《伤逝》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主题的作品,它的唯一性和文本的多阐释性引起了无数学者的极大兴趣。爱情只是肤浅的表层形式,透过表面我们能从中看到隐于背后的纠结的鲁迅,看到一如既往地对社会担忧、致力于启蒙救亡的文学战士。文本中所呈现出的救赎呼之欲出,这种救赎不止属于涓生,它更存在于鲁迅的心中,与时代洪流中的每个人相联系,是笼罩于整个社会且无法逃脱难以避开的。因此本文力图以“救赎”为切入点,对鲁迅的《伤逝》做一种解读。
飘于子君死后空荡天空的忏悔、自责与内疚,子君听不到看不到,更无谈感悟与原谅,这种悔过毫无意义而涓生又何故惺惺作态,说到底不过是为自己,为自我开脱,自我救赎罢了。开篇第一句便已引发深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一个假设式复句造成了歧义,“如果”“能够”,悔恨和悲哀是否能够,有没有写下。“为子君”“为自己”是为子君,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子君进而就是为自己,显而易见是后者。如果是为子君的死的祭奠,则通篇未感受得出伤情缅怀,对子君的形象也没有正面地描写,子君的出场,始终都是在涓生“眼”中,从一个爱人、男子的视角来刻画子君,对子君的怀念与回忆带着批判,子君不是子君自己,而是涓生眼里的子君,子君一生的浮沉都存于“别人”眼里没有自我,尽管她有对婚姻自由的自我骄傲与反抗但最后仍逃不过沦为爱情的附庸与牺牲品。涓生为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勇气,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子君,选择坦诚于自己的内心而告知子君“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罪孽自私的行为致子君于死地而悔恨,并将对子君的爱情与生活上的高要求视作理所当然,因而这样的看似深重的悔恨与悲哀也不过是为自我开脱,为子君的死忏悔而求得一种自我心安,子君的遗憾与他相关,而他的歉疚也与子君相关,虽因背叛而愧疚却也不觉得不对,那一副对不起的样子,无非是为自己,为自我赎罪,所有的困惑好像用一句“不该”便可抵消。
反观涓生与子君的爱情生活,鲁迅赋予其最多的意味便是“空虚”。“空虚”一词贯穿全文,源于爱情,终于爱情,最后不过是空妄一场。涓生始终周游于虚空与真实之间无法抉择,这是他、也是鲁迅性格的双重性与思辨性,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标签性格。他一直信奉所有事情应该不断向前,但又总是踌躇新的生活是前进还是退守,对爱情是抛弃还是虚伪。在他心里,他与子君始终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他们谈论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家庭专制,表面看似冲破封建走入了开明,可事实是涓生从未将子君放在与他平等的位置,不过是一味向她索取,要求她需尽妇道照顾好家庭,又需时刻审视自己反省不足保持上进,还要求他们之间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因一时而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便可以随随便便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看似云淡风轻却杀伤力极大的语句。这属于子君的悲剧,也是时代妇女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尽管做出了选择也会不断自我否定与纠结,即使涓生没有选择真实,如果子君也没有死,涓生也仍然会活在自己设立的思想樊篱中纠结盘旋,虚空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无法逃离的心理怪圈。
“浪漫”容不下计较,经不起世故。他们是一对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不顾社会遗老遗少的冷嘲热讽,热烈追求婚姻自由,如同两只桀骜不驯的飞鸟,却不料飞行途中碰壁于现世并亲手葬送了幸福,他们所预设的完美的爱情經不起柴米油盐下的琐碎,涓生开始心生厌倦并且浮躁,曾经欣喜并自愿而为的事,如今竟成了叨扰,烦复。脱离了社会的革命潮流,孤立追求个人幸福的反抗实则是无力的,当黑暗的社会以更大的压力袭来时,他们便凄然、怯弱、茫然不知所措,幸福也迅即化为泡影。
《伤逝》虽然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但其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大有不同,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是用小说的形式,以爱情为主题,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通过这个悲剧揭露旧社会的罪恶和腐败,同时深刻指出孤立地追求个人的幸福是没有出路的,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投身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探索新的道路,这是存在于鲁迅脑中也是时代的困境,那条新的生路,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是一个人的发轫,还是一群人的奔涌,这是一直被思量的困惑。
《伤逝》中的救赎说是为了涓生自己则不然,不知而为何人,或是为时代,或是为现世真实……它是飘荡的,无处落脚无处安放且无人认领,这种空而虚飘在每个人的头顶,飘在每人仰面便可望见的苍穹,这救赎属于各人,是时代荡浩下的回响。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9.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