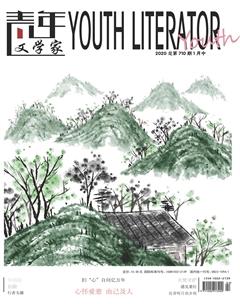浅析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叙事策略
摘 要: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常青树,莫言用生动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高密东北乡的生活图景。2011年12月,他的最新长篇力作《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以其创新性的叙事结构、独异的叙事视角和极具个性的叙事手法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
关键词:莫言;《蛙》;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手法
作者简介:丁晶,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2
前言:
《蛙》这部小说主要以乡村卫生工作者姑姑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回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件带来的影响,作品中隐含着对人性的剖析以人及来自灵魂深处的忏悔。在《蛙》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进行了许多大胆尝试与创新。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与岁月的沉淀之后,莫言在长篇小说叙事方面非但没有沦为讲述大众故事的奴隶,反而能够保持创作热情,坚持不断创新。
一、叙事结构的创新性
“形式即内容,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批评观念。”[1]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即作品的叙事结构。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讲,它的叙事结构是作者艺术构思的体现,良好的叙事结构可以重新解构故事,从而达到超越故事本身、彰显更深层次的意蕴的效果。而在《蛙》这部作品中,莫言却打破平铺直叙式的传统叙事结构,将书信和话剧融入小说之中,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表现形式。
《蛙》全书由五大部分构成,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有一封蝌蚪写给他日本的师长杉谷义人先生的信。在第一封信中,交代了“我”(蝌蚪,下同)创作话剧的初衷:想以姑姑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一部感人的作品,但又不愿与他人的小说撞车,因此决定写一部话剧。在第二封信中,揭示了杉谷先生的隐藏身份——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平度城驻守的日军指挥官杉谷的儿子,这位指挥官曾“囚禁”姑姑、大奶奶和老奶奶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作者这样的刻意安排,是为了将杉谷先生与整个事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第三封信中,蝌蚪总结了计划生育的成败,也借他之口道出了姑姑的忏悔之意,同时还介绍了家乡高密的新变化。在第四封信中,“我”告知杉谷先生:“年近花甲的我,最近成为一个新生婴儿的父亲!”[2]在第五封信中,“我”告知杉谷先生自己仅用五天时间完成剧本。在信的结尾处指出自己的迷惘困惑之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恶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3]在前四封信的后面,分别附有小说体式的叙述作为交代具体故事情节的载体,对书信内容进行延展与补充,而第五封信的后面,则是一部九幕话剧《蛙》,将前面所讲的故事进行了概括与总结,没有违背“我”的创作初衷。
莫言在《蛙》这部长篇小说中灵活运用书信、小说、话剧这三种文体形式,为体现主旨搭建了強有力的结构框架,这是一种文体互渗。“文体互渗,指的是不同文本体式相互渗透、相互激励,以形成新的结构性力量,更好地表现创作主体丰富而别样的人生经验与情感。”[4]茅盾文学奖在颁给《蛙》这部作品的授奖词中这样评价此种叙事结构:“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由此可见这种创新性的叙事结构的意义与价值。
二、叙事视角的独异性
巴赫金在研究“长篇小说的话语”时,一直强调:“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5]在莫言的长篇小说中往往不止有一种声调,如若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即使是一个叙述者, 他的身上也存在着多种叙事视角,从而构成多层次的叙事空间。
单从故事内容来看,小说《蛙》讲述的无非就是妇产科医生万心从辉煌走向落寞的故事,但莫言在向读者展示这个故事时没有落入俗套,他避开了让主人公自己发声这种表现形式,而是选择姑姑万心的侄子万足(笔名“蝌蚪”)作为叙述主体,这样的设置使得一切都有了不同的意义。
首先,作为全知视角,蝌蚪熟知姑姑身上的曾经过往,包括她个人的工作、生活经历等。身为故事的叙述者,蝌蚪的职责是向杉谷先生和读者们讲述自己知道的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公正客观,至于期间涉及到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则需要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例如小说中想要表现姑姑的愤怒情绪时,只是这样写道:“姑姑一抡胳膊,将碗拨到地上,跌得粉碎”“滚!滚!滚!姑姑抬起头,大声吼叫着: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
其次,蝌蚪这一全知视角也是一种观察并叙述历史的视角。虽然在第一封信中就交代了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要以姑姑为原型创作一部作品,但其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想通过姑姑的故事来展现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进而剖析当下中国混乱且急需整治的生育问题。在对计划生育这一历史事件的回顾中,时不时地穿插着蝌蚪的个人话语,作者用这种打通现实与历史的时空隧道的方式,削弱了历史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减少作品与读者的距离障碍感,从而建构起多层次的叙事空间。
这种同一叙述主体却包含多种叙事视角的情况形成了一种复调的表现效果。作为全知视角的叙述,使故事情节呈现出清晰严谨的逻辑性,这一部分致力于还原事件的历史的真实;而通过观察和叙述历史的视角的叙述,又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带有个人情感倾向的理解与体会,从而削弱了这种历史的真实性。这两种叙事视角由此形成对话,使小说的复调效果得以凸显。
三、叙事手法的延续性
所谓戏谑反讽,就是“通过戏拟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忤逆制造反讽意义”[6]。这是对传统叙述模式的颠覆,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对立与错位,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使得作品的意义空间得到极大的丰富,作品的审美意蕴得以彰显。《蛙》这部长篇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采用的叙事手法,将戏谑反讽运用在情节安排和形象塑造等方面,使得作品妙趣横生,增强了小说的喜剧效果。
在情节安排方面,《蛙》中出现了一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剧情,比如小说后半部分写道,“我”的患有不育症的妻子小狮子竟然“怀孕”了,姑姑在得知小狮子“怀有身孕”的“喜讯”后,她的反应是这样的:
“那天,姑姑拿出听诊器,煞有介事地为小狮子听诊。小狮子袒腹仰躺,满面幸福;姑姑凝神细听,神情严肃。听诊完毕,姑姑用她那只被我母亲多次赞誉过的手,抚摸着小狮子的腹部。姑姑说:有五个月了吧?挺好,胎音清晰,胎位正确。”[7]
事实上小狮子并没有怀孕,只是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产生了幻觉。而经验丰富的姑姑竟也陪着小狮子演出了这样一场闹剧,或许是为了忏悔、赎罪、亦或是寻求心灵的慰藉,才使得姑姑做出如此荒谬之举。这一情节的设计看似荒唐,实际上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古训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饱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小狮子想要为“我”家传宗接代,她正是千千万万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写照,她们的身上承载着延续家族血脉的希望,若是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重任,她们就要遭受别人的白眼与冷嘲热讽,这种压力与痛苦极易把一个人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形象塑造方面,《蛙》中许多人物形象前后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典型代表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姑姑,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她是“送子娘娘”这样一个光辉的形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菩萨转世”式的人物,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却化身为不惜大义灭亲的“屠婴妖妇”。她既是造人使者女娲的化身,又是肩负政治使命的生命体,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和身份地位的矛盾表明:很多人事物既可以成为创造主体的“神”,同时也能成为扼杀或改变主体命运的“魔”,这是社会背景和时代旋律以及身份地位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这些前后对比强烈的形象反差,将戏谑之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以莫言的长篇力作《蛙》为研究对象,从小说的敘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手法三个方面简要分析该作品的叙事策略,其中不乏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学习与参考,并加之以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不足之处还望批评与指教。
参考文献:
[1]林建法主编.说莫言·上[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331.
[2]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80.
[3]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81.
[4]黄道玉.论莫言《蛙》文体互渗中的多视角叙事[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34(12):103-104.
[5]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9-40.
[6]郭小东等.为什么是莫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43.
[7]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