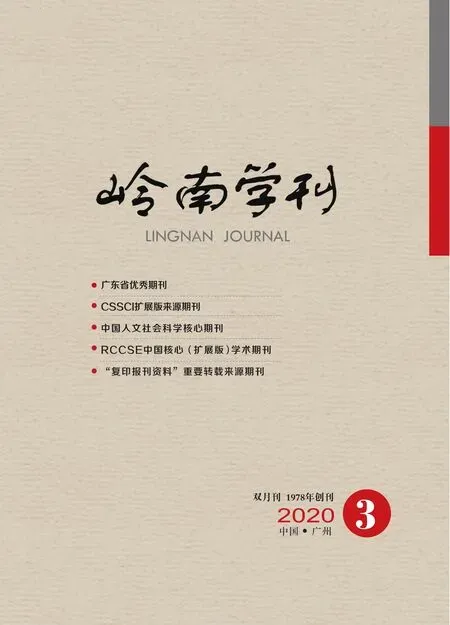从“发现”与“证立”两个维度 论法律解释的功能
沈明敏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言
从宏观上看,我国大规模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以2011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标志。但相当完善的立法只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个先决条件。法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系统性的条件支撑。我国早先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四项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就是对此的充分体现。新近提出的法治建设“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也大体是这种建设法治国家思路的进一步细化反映。抛开其他需要予以考虑的社会条件支撑,单单从这些建设法治国家的宣传口号来看,仅仅科学的立法显然不够,其只是实现依法治国长征路的第一步。如何把先在的立法之法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无疑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与“实践中的法”(law in action)[3]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将具体的法律条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相勾连,这中间当然缺少不了法官个人能动性的存在。据此,很多学者认为接下来我国将进入一个“释法时代”,即经由法官对法律规则/条文予以解释使其“舞动”起来并进而实现法律的适用。应当讲,这种思路大体是符合法治发展的进程的——这从一些被普遍认为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的法治建设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无疑凸显了法律解释对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但问题是,仅仅从经验层面上认识到法律解释的重要作用还不够。我们必须在学理层面上分析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以及其如何发挥,亦即法律解释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此外,也只有在理论上厘清了法律解释的功能作用,才能让法律解释的使用更为明晰与自觉,避免“日用而不知”的尴尬局面。
二、研究思路
目前学界有关法律解释的研究正可谓方兴未艾。虽然我国司法系统还未完全进入法律解释的时代,但学术界却早已进入了法律解释研究的时代。当然研究法律解释功能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但通过系统梳理,笔者发现既有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倾向:对法律解释功能研究呈现出“短平快”甚至“大杂烩”现象,也即赋予法律解释以多种功能,有的学者甚至赋予了法律解释以社会功能。毋庸置疑,这类研究并不是没有意义,它至少拓展了我们对法律解释功能的了解。但这种研究倾向很难做到标准统一的穷尽列举,难免挂一漏万,甚至会给人一种“头脑风暴”的感觉。譬如有观点就认为法律解释的功能(即“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为:使抽象的法律变得具体、经由法律解释使得稳定的法律适应变化的社会需求、通过法律解释完善法律。[4]293-294这三个方面当然是法律解释的功能,但问题是这三个方面的功能划分以及列举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并且在笔者看来,第二个与第三个功能明显存在交叉。为了避免陷入上述研究倾向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必须在逻辑上找到一种功能划分的工具,也即在既有的逻辑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对法律功能予以研究。这种研究思路至少能保证它在逻辑上是自洽完整的,并且能大大提升研究的学理化深度。退一步说,它至少也是对当前既有的研究思路的一种补充——如果不是替代的话。
从哲学上看,任何一项知识之所以成其为知识都需经历两个阶段——即知识的“发现”(discovery)与“证立”(justification)。所谓知识的发现阶段是指认识主体运用自身的“前见”(诸如个人直觉、想象、偏好、兴趣、经验等)对其予以揭示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并非是纯然理性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相当个人化的能力,譬如法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就深刻地体现着这一点。我们知道法官适用法律往往并不是先找到相关法条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而往往是法官一看到案子就先有结论,再往回寻找法条等证据予以证立。一个优秀的法官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得出结论的“感觉”总是很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一种个人化的能力。事实上,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早已表明直觉本身就是一种“潜思考”,尽管由于其是内化的并且速度非常之快而往往不被人们所意识到。至于知识的证立则是指认识主体对已经发现的“知识”予以证立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在自然科学中具体表现为观察与测量、科学实验、数学推理等,而在社会科学中则往往是利用理论、概念、逻辑等工具证成其一致性、圆洽性、融贯性等。仍以上面提到的法官适用法律为例,法官在有了结论之后再去寻找相关法条等证据证明其所得结论符合现有法律规定的过程就是一个证立过程。
法律解释作为法律知识(也就是司法裁判)获取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也需经历这两个阶段。至此,我们在逻辑上便可以将法律解释的功能划分为发现与证立。需要预先作出回应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发现和辩护之间没有一道鸿沟,它们正在逐渐接近。……发现和辩护可以看做同一件事,它们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别”[5]367。应当说,这种认识符合大多数人的经验感觉。毕竟,“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宣示,至少你认为“发现”的东西本身是有价值的,否则也不会称之为“发现”。由此可以推出“发现”的过程本身至少也包含着初步的“证立”——关联着本文的论域则是法律解释的“发现”与“证立”功能是一体的。那么笔者对法律解释功能的分类还有必要吗?这会不会给人一种“为了分类而分类”之感甚或仅仅是一种“智识的炫耀”,而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却是“屠龙之术”?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第一,经验上的“发现”与“证立”到底呈现何种样态,并不能直接证否逻辑上分类研究之必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因为“发现”与“证立”二者之间的模糊状态,才更有必要对其予以分类廓清。任何的分类都仅仅具有“分类学”层面上的意义,但这显然并不构成无需予以“分类”的理由。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在现实中,严格的区分往往是不可能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明确的概念就更加必要。”[6]240第二,即使经验实际中的“发现”与“证立”是难以区分的,逻辑上的分类研究也仍是必要的。因为理论研究并不要求其完全符合经验实际,逻辑上的自洽是理论研究的直接追求,不能为了迎合经验事实而放弃对理论的追求。理论研究首先应当仅仅并且紧紧关注自身的逻辑周延与自洽,其次才是考虑与经验实际的结合,因为经验实际往往讲求的是妥协,故而它首先追求的是办事并且是办成事。倘若我们一开始就企图用经验实际来左右理论研究,结果往往就是理论研究得不到深入。事实上,“理论联系实际”并没有要求理论完全屈服于实际,而是说二者不能割裂,否则理论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澄清了如上的疑问,下面本文就将从这两个维度展开来分析法律解释的功能——即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和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
三、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
一般来讲,“法律发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立法论意义上的法律发现和司法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发现。立法论意义上的法律发现主要是基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认知、理论——即认为作为秩序的法律已先验地存在,人类立法意义上的法律不过是对已然先验存在的法律的发现(而不是创造)。换言之,法律不是经由所谓的立法人员/机构予以现实创造,立法人员/机构的任务仅仅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科学工作者以找寻先存的法律(规律)。这种法律思想理论被很多古代的大思想家所接受并推崇,在当今仍有一定的市场,譬如哈耶克(Hayek)的“自发秩序”与“扩展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归属这一理论阵营。至于司法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发现则大体是指法官发现与当前案件事实存在内在逻辑关联的规范。[7]68申言之,法律发现是指法官提炼出特定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并找寻恰切的法律规范予以适用。考虑到本文的论域,论述的重心将主要是作为司法方法论意义的法律发现。值得说明的是,与“法律发现”相关的则是“法律适用”这一概念。当前存在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具有根本不同。“所谓‘法律适用’,是当拟判断的案件已经被规定在可适用于绝大多数案件的法律时;这时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包摄’。相对于此,法律发现就是少数的例外,当对拟判断的案件找不到法律规定,而这个法律规定是依照‘法律秩序的计划’必须被期待时,亦即当法律出现‘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时’”。[8]77这种把“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割裂开来的处理原则符合人们对于司法决策的一般想象,也符合人们对这两个语词的直观印象。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法律适用”一词本身就暗含着其是机械性以及模式化的,它不需要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法官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的自动售货机”,它仅仅是一种标准的程序化运作;而“法律发现”一词则暗示了法官的能动作用。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即便是最为标准的司法三段论演绎(也就是最典型的法律适用)也需要法官予以居间调适、整合、推动。因为案件事实必须予以法律意义上的构造,法律规范必须予以识别、解释,这些显然都不是仅仅由简单的“三段论”就可以完满解决的。故而,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的区别并不是在于人们一般直觉意义上的有没有合适的法律予以适用,而仅在于发现的“难易程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适用只是法律发现的一种情形,后者是上位概念。[8]77
基于上述的法律发现的基本内涵,那么法官在实际的司法裁决中是如何实践法律发现的呢?首先,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法律发现的过程不仅仅是“法律”的发现过程,也同时是“事实”的发现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律发现”这一术语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如下的一种典型误解——即法律发现的过程仅仅关涉着法律规范的选取而与案件事实的构造认定没有关系,这显然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必须使自己的目光往返流连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因为法律意义上的案件事实并不会自动生成,法律规范也不会自动显现并适用。这就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选择适当的法律规范以及根据法律规范来构造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循环往复,因而其并不是线性的。之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而不是线性的,还需从有关法律发现的一个“迷思”(myth)说起。经典的司法三段论演绎推理认为司法裁判的结论是可以经由法律(大前提)与事实(小前提)在逻辑上推导而得出。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逻辑上的一致推导必须建立在大前提与小前提都非常精确与清晰的基础之上。如若不能满足这个前置性条件,那么三段论演绎推理就是一种理想状态。考虑到法律规范的构成以及案件事实的生成,我们认为三段论演绎推理只有在经过模式化的处理之后才能开始运作,也即让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与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都显现。而这个模式化的处理过程,也就是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发挥作用的过程。
具体而言,法律为了追求普遍适用性,作为法律规范构成的概念都不是明确单义的,它需要在概括性与精确性之间达致一个平衡。精确性当然是法律规范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但并不是其唯一的价值。因为正如考夫曼所说:“语言上的极端精确,其只能以内容及意义上的极端空洞为代价”[9]17。换言之,法律规范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针对不特定案件的反复适用,必须策略性地选择一些类型化、模糊化的表述。虽然这种立法特质使得法律的延展性以及包容性变得更强,但立法的此种特质也带来了适用上的困难——即很难直接找到“字面意义”上一致的法律规范,法官必须对法律规范予以解释才能将其适用于当下的案件,而这个过程也恰恰就是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仍然只是初步的,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构造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于成文法国家,法律规范以法典的形式颁布在先,而法官适用在后。当法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就必须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来丰富特定法律规范的内涵,证明拟使用的法律规范适合于待判案件。至于法律意义上的案件事实也并不是天然地摆在法官的面前,相反,摆在法官面前的仅仅是一堆不成体系并且初步看起来没有关联的证据。法官必须根据相关法律规范赋予这些经由证据勾连起来的事实以法律意义。事实上,由于案件事实发生于过去并且永远地停留在过去,法官必须借助证据等“回构”(reconstruction)案件事实。而这个“回构”的过程以及赋予“回构”的事实以法律意义就是法官对相关证据等进行法律层面意义上的解释。
总而言之,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并不是一一严格对应的关系,毋宁是一种互相找寻、识别、解释、构造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发现仍是一个具有初步理性的过程,它并不是什么电脑等判案机器所能完全胜任的。但毋庸讳言,这种初步性也关联着法律发现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法律发现往往是一个经验直觉式的过程(但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随意的、非理性的)。这种经验直觉来自于法官长期浸淫于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所养成的法感以及是非感。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些老法官会比新入职的年轻法官办案效率更高,原因并不在于青年法官法学知识素养不够,恰恰相反,当今中国青年法官的法学知识素养在整体上要高于老法官——如果学历大体可以测度知识水平的话。真正可能的一个原因在于老法官丰富的办案经验培养了其一种相当“准确”的法律感觉。一俟拿到具体案件,他们的法律感觉会直觉性、应激性地告诉他们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以及应该适用什么法律。
至此,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大体已经呈现出来,但可能的诘问也随之而来,既然已承认作为法律发现的解释只是初步的,又如何保证这种法律发现是恰切的并进而是可接受的呢?如果不能有效地回答这个诘问,试问我们又怎么能相信法官司法裁判的过程是理性的呢?实际上,这已经关联着法律解释的另一个功能,即证立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法官为证立其司法裁判过程的正确性,会用到多种工具。除了法律解释,诸如法律论证、法律推理等也是常用的工具。但考虑到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法律解释的功能,故而只论述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
四、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
关联着法律证立工具的多样性,证立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但给予其一个虽未必全面但至少揭示其特征的定义仍是必要的。法律证立一般是指法官为证明其所适用之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具有内在一致关联的过程。法官适用法律为什么需要证立呢?因为法律适用是一项由公权力背书的说理性过程。虽然法律适用的过程当中少不了作为公权人员的法官的权力决断与使用,但其本身却又要求法官不能仅仅依凭于权力,而必须通过说理来证立其判决。申言之,法律证立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是一个说理过程。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曾提出“普遍证立规则”:“任何一个言谈者必须应他人的请求就其所主张的内容进行证立,除非他能举出理由证明自己有权拒绝进行证立。”[10]239考虑到法官的制度角色,其天然地符合普遍证立规则。换言之,法官必须将其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理由、论证公开,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职业上的义务。
问题的关键与难度也许不在于论说法律证立的必要性与该当性,而在于法律证立本身的有效实现。揆诸目前的实际状况,法院的判决书(法官进行法律证立最主要的一个场域)之所以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判决书本身缺少了其最为重要的结构性要件——法律证立。如果法官不能有效地在判决书中展现法律证立的过程,在当今司法公信力严重不足的宏观背景之下,出现如上的情况就是逻辑上的必然。更为严重的是,如若长此以往,只会给人留下法官以及法院“不讲理”并由此生发出诸多未必符合实际的“联想”,譬如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因为在普通百姓的直觉朴素认知中,有理你为什么不说?不说,恰恰是因为你无理!虽然这种认知具有情绪性且并非完全正确,但法官通过判决书说理确为不易之理。如若我们再考虑到提升当前的司法公信力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虽远非法院系统独自可以完成的重任,但对法院系统而言,在判决书中充分展现法律证立的过程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努力之路。
毋庸置疑,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在其中必然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第一,在法学中所有的论证在本质上都关联着证立者对其命题的解释。如上的论断也许会让一部分人产生疑问,既然论证与解释在本质上具有逻辑上的关联,那么为何会造出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其予以指称?这岂不是有违“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并增加人们的“交流成本”,甚或引起不必要的“交流混乱”?这种诘问乍看似乎有理,却是建立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前提假设之上——即本质上的关联就应该在形式上表现为一致。但即便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它远远超过“关联”)的事物,在实际当中却可能产生极为不相同的形式指称。例如,男人和女人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人甚或动物,如果按照如上的逻辑,这种区分显然就是多余的。这虽有“抬杠”之嫌,但恰恰说明了问题。再者,概念术语本身也未必需要有清晰的事实对应,因为概念术语的存在是作为分析之工具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对象之本身。实际上,任何概念术语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通约”掉一些事实中存在的差异以求得一种适用上的普遍性。既如此,我们就完全可以接着说:不同的概念术语本身的不一致未必就表明两者具有完全不具关联的指向。当然,这倒不是说法律证立与法律解释是没有依凭的存在,而是强调概念术语本身具有一定的超然性。事实上,解释与证立不是相互割裂的独立存在。证立本身就蕴含着解释或者说证立往往通过解释而达致,这在法学中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譬如,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往往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来证立自己的裁判,即经由法律解释将法律规则与待决案件进行逻辑上的意义勾连,使法律规则得以运行,而法律规则天然地就是证立的工具。也正是认识到了法律解释与法律规则的密切关联,有的学者甚至声称:“规则甚至都不可能包含自身的适用标准。在任何案件中,肯定都需要解释”[11]62。解释与证立在逻辑与现实上的关联性使得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基础。
第二,法律解释本身具有证立的功能属性。虽然传统的法律解释学理论认为解释本身不构成对解释对象的超越,即解释对象预先划定了解释的范围(不能超越特定法律文本)。而一般意义上的证立则涉及引入外部系统条件予以支撑,毕竟“明希豪森困境”从体系内部根本无法予以化解。但这种完全“理想化”地把法律解释与法律证立分属不同的功能领域是不切实际的。传统的法律解释学最为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它把认识主体的主观性予以忽视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法律解释仅仅视为对法律文本的被动反映。在其看来,法律解释不具有证立的功能,法律解释无非是“立法者自己已经作出合理判决这一前提的兑现”[12]179。换言之,法律解释就是“发现”已经存在的合理理由,它无关乎解释者本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也就更谈不上证立了。可当代的哲学解释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任何解释都不是一种消极的、价值无涉的客观程序,它必然包含着解释者本人的能动参与,事实上这也是解释得以进行与展开的基础。申言之,(法律)解释不是主体与解释对象的单项作用过程——不论是主体认识对象抑或是对象反映于主体——而是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解释主体与解释对象的“视域融合”。如若再考虑到法律解释不具有自我指涉性,那么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就更应当成为一种必须。也正是由于法律解释所具有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往往从解释论证的观点,而非解释方法来处理制定法解释的问题”[13]182。法律解释的本质决定了法律解释具有法律证立的功能属性。法律解释不仅是“寻章摘句”,而且是“寻找论据”。
五、结语
“毋庸置疑,我们的时代是解释的时代。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再到艺术,有大量的数据显示,解释成为20 世纪后期重要的研究主题。在法律中,‘解释性转向’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14]104法律解释对于司法裁判的重要性早已成为时代的共识,但仅仅是在宣传口号或者朴素直觉上认识到其重要性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以解释。从法律解释所具有的功能出发也许是认识其重要性的一个较为恰当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法律解释在逻辑上所具有的“发现”与“证立”功能出发,分别论证了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与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此种研究进路最大的优势在于功能划分的标准统一并进而在逻辑上具有周延性。但也毋庸讳言的是,它同时也面临着司法实践的诘难。试想,当我们问一个法官他如何在一个具体的司法裁判中区分二者,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模糊的。但法律解释所具有的两种功能与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区分二者并无逻辑上的关联。申言之,即便在实践中不能对二者予以精确地区分也并不能在逻辑上否认二者的存在。司法裁判是一个实践理性的过程,只要法官在理论上认识到法律解释所具有的这两种功能,即便在实践中不能区分也并不妨碍其理性运用这两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