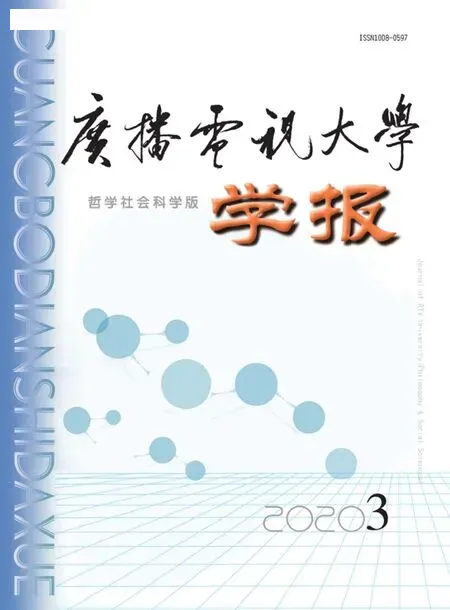中美经贸协议下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通知中的善意问题
汪文涵
(宁波大学, 浙江 宁波315000)
2020年3月15日,中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经贸协议》),其中第1.13条规定:“中国应:……(二)免除善意提交错误下架通知的责任……”,该协议中“善意提交错误通知免责”由中美两方共同确认并实施;同年6月10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批复》)中第三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下架的通知内容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但其举证证明无主观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构成错误通知,其不承担因通知产生的民事责任。”《批复》规定的“无主观过错提交错误通知免责”弥补了我国通知错误但无主观过错的责任空白问题,《中美经贸协议》的达成与《批复》(征求意见稿)的颁布完善了我国的知识产权通知制度,但协议背景下《批复》适用的法律问题值得关注。
从性质看,《中美经贸协议》属于双边协议,双方应当共同遵守;我国随后颁布的《批复》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予以回应。若这一推断成立,《中美经贸协议》中的“善意”与《批复》中的“无主观过错”是否为同一语源?可以肯定,协议中的“善意”应当是正确通知者怀有的主观状态。但仅以我国应当遵守协议证明《批复》中“无主观过错”为“善意”是不充分的,还应当探寻我国通知制度中善意的本源。这是《批复》适用“通知错误但无主观过错免责”需要解决的第一个法律问题。其次,若两者不同源,导致善意在我国通知制度中产生适用偏差的成因何在?若同源,法官在实践中应当选择何种标准判断善意?这是协议背景下《批复》适用“通知错误但无主观过错免责”应当解决的第二个法律问题。
一、知识产权侵权通知中善意的适用
(一)通知制度中的善意要求
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保护法》(以下简称DMCA)512条规定了合格通知的要件,其中512(c)(3)(A)(v)是善意声明,即通知人善意的相信此种对作品的使用未得到权利人及其代理人的授权或法律的许可;违反善意者受512(f)的规制,即任何人在通知或反通知时存在知晓的实质虚假陈述(knowingly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使网络服务平台对相应内容采取措施;……都应对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在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以伪证罪论处。[1]我国合格通知的要件在不同立法文件中的表述有所差异,[2]①以《信息网络保护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为例,通知书应当满足:第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第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第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通知书以单独形式表达了真实性要求,这与美国DMCA512条(c)(3)(A)(vi)的真实性声明一致,但与美国不同,通知书并未包含善意声明。尽管如此,我国针对恶意设定了惩罚条款,《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第42条规定恶意通知加倍承担责任。
(二)善意的立法原意
“善意”是拉丁文“bonafides”的意译之一。徐国栋教授指出:罗马法中有两种诚信:其一是适用诉讼法的客观诚信,表现为裁判官运用自己的权威解决疑难案件被描述为“裁判诚信”的过程,也表现“遵循正义”的行为标准;其二为适用物权法的主观诚信,是一种当事人确信自己未侵害他人权利的心理状态。一个是外部行为,一个是内心状态;似乎是分属两个世界的东西,却都用“bonafides”表示。[2]同时,他认为我国法律文化受德语世界影响,使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两种诚信, 客观诚信以“诚信”的术语表达之;主观诚信以“善意”的术语表达之。[3]按照徐国栋教授的观点,主观诚信在我国以善意表述。因此对本文第一个法律问题思考的关键是,《批复》中的无主观过错是否为主观诚信?若无主观过错表达的是主观诚信,当然谓之善意;若为客观诚信,在我国民法语境下不能以善意表述,仅能说明权利人尽管通知错误但无须承担责任。
(三)《批复》中“无主观过错”与《中美经贸协议》中“善意”的同源性
对这一结论的论证是:将“善意、主观诚信及无主观过错”分别以甲、甲1、甲2指代。存在甲、甲1、甲2三方,直接说明甲与甲2同义困难,则需论证甲2与甲1一致,而甲与甲1一致,则甲与甲2当然一致。第一,协议中的善意与国内民法理论中的善意一致。协议的中文版既然采用善意的说法,表明我国是在确保此处的善意与国内民法理论中的善意同义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若怀疑协议中的善意与国内民法中所用善意不同,将会出现同一立法体系下同一词汇不同义的情形,显然会导致立法语意的混乱;此情况在我国立法中并非没有,但通常存在于不同的部门法学科中,如“动机”在刑法与民法中适用的差异。[4]由此可知,《中美经贸协议》中的“善意”与我国民法理论中通常所用的善意一致。第二,《批复》中“无主观过错”是一种主观诚信。根据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5]序编第10条确立的诚信原则:“自以为未侵害他人权利而实际上作了这种侵害的人,具备主观诚信,法律将基于他的这种主观状态赋予对他有利的法律效果”;[6]权利人将非侵权行为误认为侵权而发送通知产生错误结果,其与《批复》中“权利人自以为未侵害被通知人而实际上发出了错误通知,给被通知人带来损失”的内涵一致。另外,现代学者指出主观诚信的表现之一是:主体在形成这种确信时尽到了注意义务, 未发生故意和过失。[3]基于此,我们认为《批复》所称的“无主观过错”符合主观诚信,也可谓之善意;同时与协议中“善意”一致。这一结论符合我国遵守《中美经贸协议》的逻辑,也符合民法理论中善意同义的逻辑。
二、中美关于侵权通知中善意认定的差异性
中美双方对知识产权通知制度达成的共识,有利于保持两国立法在空间层面的统一;但两国司法实践对善意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具有不同特征。从发展历史看,美国法院对善意认定标准的争议经历了较长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美国相比,我国电子商务兴起较晚,对善意、恶意的探讨基于我国实践中产生的恶意通知问题,立法的规定则更晚,这一点可见2019年《电商法》第42条对恶意通知的规定。从善意认定的具体标准看,美国法院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争;我国则偏向完全的客观标准或客观标准。
(一)DMCA实施以来,美国司法实践对善意标准适用尝试的不同阶段
第一,Online Policy Group v. Diebold③案的客观标准。权利人Diebold公司向IndyMedia的网络服务商OPG(Online Policy Group)发送删除通知,涉案的两名学生及OPG随后起诉Diebold 构成知晓的实质虚假陈述。法院认为,512(f)中“知道”包括“确切知道、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及没有合理怀疑时的应当知道”。被告Diebold承认一些邮件是公开发表且属合理使用,法院认为其主观对事实确切知道,认定虚假陈述成立;除自认外,法院采纳“客观理性人”标准,指出任何一个理性的著作权人都不会相信讨论技术细节的邮件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分析法院对善意的释明,权利人对不侵权的事实不仅包含确切知道,还包含履行注意义务后的应当知道,符合客观理性的范畴,可以肯定法院采纳了客观标准认定善意。遗憾的是,本案并未运用客观标准判决权利人的虚假陈述,而以调解结案;同时,本案被告对邮件不享有著作权,是其特殊之处。
第二,善意认定的主观标准。尽管美国司法实践有“遵从先例”的习惯,然而Diebold案的客观标准并未得到延续。Diebold案后实践中采纳主观标准认定善意,一时期内主观标准得以建立。典型的案件:其一,Rossi v.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④该案中原告Rossi主张善意包含权利人的初步审查,而第九巡回法院认为512条的善意声明是一种主观标准,理由:DMCA512(c)(3)(A)(v)的法条用语采纳“主观”而非“客观理性人”;512(f)仅包含明知虚假陈述下的损害赔偿责任,若非明知,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而“明知”与Rossi 主张的初步审查不符。本案中“明知不侵权”便符合善意,除非权利人自认,否则明知几乎无法被证明,从该层面理解法院认定善意是一种主观标准。其二,Dudnikov v. MGA Entertainmen。⑤原告Dudnikov在eBay网上售卖从权利人处所购帽子,上面附有权利人商标,原告对此提出“合理使用”与“首次销售”抗辩,但法院采纳Rossi案的主观标准,认可被告MGA公司具备善意。其三,Recordings v. Augusto。⑥原告Augusto将所购权利人的唱片放在eBay上售卖,被认为侵权后原告主张“首次销售”;法院承认“首次销售”抗辩,但认为其为不确定的概念,忽视这一认定后仍然采纳Rossi案的主观标准认定权利人为善意。若法院对权利人明知被通知人的行为属于首次销售已经明确,具备认定权利人故意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仅因首次销售的概念不明确径直忽视,选择既有的主观标准认定善意,明显降低了对权利人善意的要求,也失去了再次探讨认定善意标准的机会。
第三,善意认定客观标准的首次胜利,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⑦案是典型案例。2007年Lenz 发布了一则孩子随音乐跳舞的视频到YouTube网站,视频中音乐的版权人Prince,Universal公司以版权代理人名义通知YouTube网站视频侵权并要求删除;后Lenz以Universal公司违反512(f)构成故意虚假陈述诉之。Lenz引用Diebold案的客观标准,主张被告明知或应当知道视频不侵权;但Diebold 案与之有别;Diebold案中的电子邮件并不涉及著作权,本案中的涉案作品明确受著作权保护;Lenz又主张权利人发送通知时应当考虑合理使用,Universal公司抗辩DMCA512(c)(3)(A)并未提到合理使用且其应当被放在通知后起诉前考虑。法院认为DMCA已然要求版权人在通知前对是否侵权进行初步审查,否则无法满足512(c),而合理使用审查仅为初步审查的一部分;最终认定被告在发送通知时未考虑合理使用的初步审查认定权利人缺乏善意。
(二)我国有关认定善意的探讨
我国对与此相关争议并非正面的探讨,即如何认定善意;而是从善意的反面探讨权利人是否为恶意,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立法模式。美国DMCA512条将善意声明规定在合格通知的要件中,当被通知人认为权利人构成DMCA512(f)虚假陈述时,需要举证权利人主观非善意,因此当事人主要围绕是否善意讨论;我国《电商法》第42条是恶意通知的立法依据,在诉讼中,被通知人只有证明权利人的主观为恶意才能援引立法依据,因此当事人主要围绕是否恶意讨论。另外,法院对权利人是否构成恶意的认定多采用完全的客观标准或客观标准。
在杭州曼波鱼贸易有限公司与台州市康贝婴童用品厂、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③中,两级法院的审判体现了认定善意的不同逻辑。一审法院裁判要旨:法院认定原告曼波鱼公司、被告康贝厂两者属于具有竞争关系的同行,被告明确其投诉前已购买过原告产品,并将其与涉案实用新型专利进行技术比对。经审查,法院得出原告产品尚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据此认定被告在“知道也应当知道”原告产品尚未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下,仍然投诉原告仿冒专利产品的行为为恶意。二审法院则认为:康贝厂在投诉中所主张的侵权事实最终是否属实,不排除投诉人基于认识水平所囿做出错误判断。被告的投诉仅向淘宝公司提出,且符合淘宝公司设定的形式要件,就现有证据而言,不能当然认定被告明知涉案被控侵权产品不构成侵权而进行投诉。
对该案两级法院认定恶意的分析。一审法院:被告通知前已经购买涉案侵权产品进行比对的行为,属于对涉案侵权的初步审查,审查后被告仍坚持原告侵权,最终从结果看系判断错误;法院却认为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的专利产品并未落入保护范围,这属于主观认为被告应当对不侵权做出正确判断。该判决告诉权利人,仅初步审查是不够的,还要保证初步审查的结果与法律判断一致。一审法院这一审判逻辑不仅可以称之为“客观理性人”标准,更可谓之完全正确标准,我们将其称为完全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可能将权利人的判断能力拉至与法官等同,将判断负担全部转移给了权利人。二审法院认为投诉人限于自身认识对是否侵权做出错误判断是维权中可能发生的正常现象,若要求只有侵权投诉得到司法的最终侵权判定方可认定为合适投诉的话,显然对权利人责之过苛。我们认为,与当事人的判断能力相比,法官的判断是专业的;但法官并不能因此要求当事人必须做出正确判断;二审法院基于此纠正指出权利人投诉可能存在的误判,但主观仍然是善意的。二审法院的审判依据是民法中证明程度的“客观理性人”标准,也可谓之客观标准。在该案中,二审法院选择的客观标准显然更能还原权利人的主观状态,但这并非意味着每一案件都更适合客观标准。
三、中美经贸协议下善意认定的路径选择
尽管美国司法实践对善意认定的标准拥有长期、丰富的经验,也不能说Lenz案解决了善意认定的问题,[7]因为Lenz案认定善意的客观标准仅是审判法院的观点。究其本质,中美司法实践将判断善意的方法转化为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这一视野未跳出认定善意的形式特征。不论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只有在适用特定案件时,才可能更具有说服力,但这种结果将导致善意认定标准之争无法停止。除形式特征外,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存在共同的基础,即形成善意的内容,如建筑物的地基。建筑物本身可能存在国别、高度、价值、位置等诸多不同,但地基却是建筑物差别外观下的本质共性。认定善意的标准如同建筑物虽然外形迥异,却离不开善意内容这一“地基”。无论哪一标准均需从事实层面与法律层面分析权利人的行为:从内容看,对事实与法律的重视程度、要素搭配的重新排列组合,便形成了判断善意的不同标准,即认定善意的形式标准。
(一)运用认定善意形式标准原理对中美实务案件的分析
其一,善意形成的事实基础。根据Rossi案界定善意的主观标准,版权人通知前无须实施全面调查,更不用考虑合理使用;但为了保证主观善意,版权人必须对涉嫌侵权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查。当讨论Rossi案时,评论员并未提到MPAA对其网站的调查,仅仅宽泛地认为Rossi案坚持主观标准。[8]然而,MPAA确实浏览了Rossi的网站,尽管未点开链接查看导致判断错误;实质上这种审查行为正是善意形成的事实基础。但Lens案的法官并未指出善意的事实基础,即未讨论Universal公司所采取的审查措施;实际上Universal公司的雇员只需播放视频就能做出判断。若Universal公司主张已查看视频,至少能为善意提供一些事实支撑,但他们只是看了视频标题,标题也没有出现类似Rossi案中引人误解的语言,因此Lens案并不具备善意形成的事实基础,其属于无任何证据情况下因胡乱猜疑而投诉。我国曼波鱼案件中,法院明确被告即权利人通过购买涉嫌侵权专利进行对比,可以视为对侵权事实做了初步审查,也即具备了善意形成的事实基础;但因权利人的审查结果与司法判断不一致而径直认定被告恶意,超越了权利人应负担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合理性。法官的司法判断与权利人审查判断要求是不一致的。法官应当依据法条做出司法判断,而权利人维权仅需站在普罗大众的视角即客观理性人程度的判断即可,至于判断结果是否正确,在所不问。我国曼波鱼案的一审法院便混淆了两者的判断程度差异。但仅审查事实基础可能不充分,还需审查法律基础。
其二,善意形成的法律基础。即便是Rossi案与Lenz案也未解决权利人通知前是否应当考虑合理使用及其他抗辩。[9]但立法可对其做出解释,可以肯定,知识产权侵权中,特定的抗辩只能对抗特定的专有权,如Rossi可能侵犯版权中的“传播权”,Lenz可能侵犯“复制权”,将Lenz合理使用的抗辩对抗Rossi传播权侵权则不成立。法院通过审查美国法典第17章第106条(1)-(6)⑧列举了衡量合理使用的四个依据,根据第四个“使用行为对作品潜在市场的影响”,以及Lenz视频的目的是分享给家庭成员且背景音乐混沌,对版权人粉丝购买的CD无法形成替代这一判断,支持 Lenz的合理使用抗辩。由此,权利人并非均需审查侵权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而是根据侵权行为的抗辩要素审查对抗侵权的内容,也即善意的法律基础。
由此,我们认为形成善意的基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事实基础,指权利人通知维权时对涉嫌侵权行为做了初步审查;其二是法律基础,指初步审查行为应当审查与侵权事实相关的特定内容,而非完全不相关的随意内容,包含构成抗辩的常见事由,如合理使用、合法来源;但权利人对法律审查的程度并非无限,符合民法理论对民事主体“客观理性人”的要求即可。简言之,善意判断以审查行为为事实基础,以一般理性人视角审查特定内容为法律基础。因此在中美经贸协议共识的背景下,通过分析善意形成基础认定善意的裁判具有稳定性,可减少因中美法系及实践经验差异导致的审判逻辑差异,保持中美实践中的一致。
(二)对《中美经贸协议》通知共识的延伸思考
协议中“善意发送错误通知免责”这一共识涉及中美两国社会利益多方面的统一;从法律层面看,并非仅限立法制度的一致,还应当包含中美司法实践善意认定逻辑的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从中美双方经济贸易开展看,由于立法的一致,企业无论在任一国家进行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交易,对其行为可形成合理的预估,鼓励跨国贸易的开展,减少中美经济贸易中的制度隔阂。
综上,同样是对错误通知免责的规定,《中美经贸协议》与《批复》(征求意见稿)采用了不同表述,基于中美双方应当遵守双边协议的逻辑,厘清《中美经贸协议》中“善意”与《批复》(征求意见稿)中“无主观过错”的关系十分必要。首先,协议中的善意与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善意同义。其次,按照徐国栋教授的观点,我国民法受德语世界的影响,主观诚信以善意表述;主观诚信指权利人自以为未侵害他人权利而实际上做了这种侵害,与错误通知但无主观过错的内涵一致,《批复》中无主观过错表述符合主观诚信,可谓之善意。最终得出“善意”与“无主观过错”具有同源性。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对善意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差异,司法实践不统一。美国DMCA512条规定了善意声明,当事人多从正面角度证明是否为善意,且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的争议;我国规定了恶意通知的处罚,当事人往往以此为据论证当事人是否为恶意,且实践认定善意选择完全的客观标准或客观标准。类似建筑物均有地基,认定善意的标准离不开对善意形成内容的分析,这便是善意形成基础的“地基”。具体而言,善意的形成基础包含以审查行为为中心的事实基础与以客观理性人视角审查相关内容的法律基础。以此认定善意能够减少中美两国不同法系、不同经验的审判差异,使得裁判结果即便跨国界也具有稳定性;也使跨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交易的企业对通知制度有合理的预期,实现促进中美贸易的目的。
[注 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为:“(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
②杭州曼波鱼贸易有限公司与台州市康贝婴童用品厂、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浙知终字第196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③Online Policy Group v. Diebold, Inc., 337 F. Supp. 2d 1195 (N.D. Cal. 2004)。
④Rossi v. Motion Picture Ass'n of Am., Inc., 391 F.3d 1000 (9th Cir. 2004)。
⑤Dudnikov v. MGA Entm't, Inc., 410 F. Supp. 2d 1010, 1018 (D. Colo. 2005)。
⑥UMG Recordings, Inc. v. Augusto, 558 F. Supp. 2d 1055 (C.D. Cal. 2008)。
⑦Lenz v. Universal Music Corp., 572 F. Supp. 2d 1150 (N.D. Cal. 2008)。
⑧U.S.C. § 106(l)-(6)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