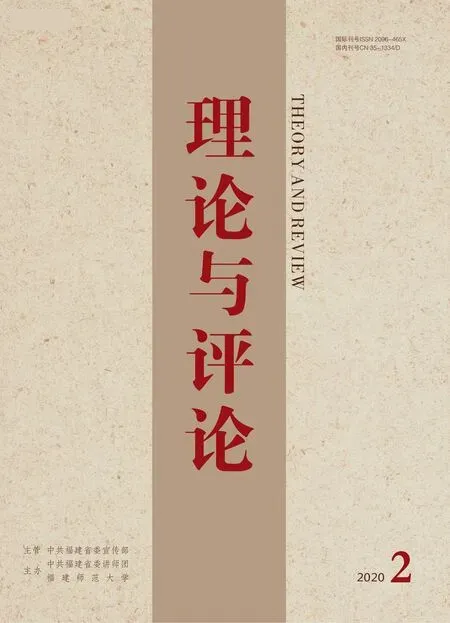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柯尔施的解答及其当代启示
李逢铃
一直以来,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存在各种差异甚至对立的观点。这种差异、对立观点背后实际上反映的不仅是不同作者对马克思文本思想把握程度上的差异,还体现了不同作者作为文本之外解释者立场的差异。毋庸置疑,马克思本身就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鲜明立场上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论述的,所以《资本论》不仅是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之作,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因此,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难处既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科学的形式,也不在于它是否体现某种价值的立场,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关涉“柯尔施问题”中更为深层或本质的问题,即马克思中后期带有明显实证色彩的经济学研究与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柯尔施(1)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生于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针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机械性解读,柯尔施在该著作中重新强调了马克思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所针对和力图解决的问题亦以“柯尔施问题”被理论界学者所称谓和普遍认识。1933年,柯尔施受到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迫害而流亡英国,并于1936年移居美国直到去世。其代表作还有《卡尔·马克思》(1938年),试图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理论上重新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始终没有彻底或详细展开对此问题的解答。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构成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在理论上要么回到康德哲学以补充马克思主义,要么撇开哲学以科学、实证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直到今天,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的哲学论证或解读本质上也是对此问题的解答。但被我们所忽视的是,柯尔施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中恰恰试图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回答此问题。这种解读和回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一种方法: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在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问题上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问题,即通过何种方法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时柯尔施的视野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大的误读就是从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解读。在这种方法的解读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要么被资产阶级批判者视为一种非经济科学的道德说教,要么被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一种与价值无涉的逻辑演绎。为此,柯尔施试图回归马克思自身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这也是柯尔施从早期写作就开始并一以贯之的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已提出马克思哲学与其后期经济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并指明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论方向。“看起来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于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以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上,他们远非忽视了这一问题,他们实际上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他们的哲学批判。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与某些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很流行的错误观念相对立,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充分的革命意义就够了。”(2)[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页。可见,柯尔施在当时认为马克思后期的经济学研究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发展了其前期的哲学批判,要认识这种关系需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意义。那应当如何恢复这种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义呢?柯尔施在1923年的文本中并没有详细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但实际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时,他已指出当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问题是忽视或无法理解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柯尔施认为许多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之所以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后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方法”(3)[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4-25页。。这种方法在柯尔施看来,就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所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其本质性特征就是强调理论和现实的不可分割性。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柯尔施认为他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一种纯粹理论或观念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了其应有的实践或社会革命性。以对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的批判为例。柯尔施直接抓住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即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同样运用其以描述因果联系为目的科学的政治学。这意味着在希法亭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是没有价值判断的。这是柯尔施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因为这样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仅被视为一种经济学科学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向社会主义的结论中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而在实践上就会出现改良主义的企图。当然,当时柯尔施的理论重心在于说明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实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因此搁置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现实革命意义的阐述。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忘强调“把任何哲学的考虑放在一边,就会明白,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是必然得出相反的结论”(4)[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7-48页。。
在《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延续了这种观点,并将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的方法进一步明确为“历史论述原则”。但有所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更倾向于通过论证“现实”是什么,并以此说明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现实的一部分,而在历史论述的原则中更多地是说明理论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作用是如何在现实历史的特定情景中发生的。柯尔施以马克思对“地产”和“资本”两个经济学概念的解释为例(5)这两个例子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方法,即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阐述时所使用的例子。,说明了这种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其看来,马克思无论对地产还是对资本的各种历史形式的论述,最终都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形式下的地产、资本,即把这些范畴置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联系中去理解。这不同于诸如李嘉图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地产或资本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观念置于一切时代。因此,李嘉图致力于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在柯尔施看来,这也是马克思最终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而将“资本论”作为书名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在“历史论述原则”的方法论视域下,“马克思并不把经济学的概念理解为不受时代限制而普遍有效的范畴”(6)[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在这种强调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的历史论述原则指引下,一方面,柯尔施认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代表了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最初时期的社会新科学,是“在它争取实现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斗争中创立的”(7)[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6页。。它在理论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在现实中通过革命的方式摆脱封建社会桎梏,“表达了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变化了的现实以及与此实际变化相适应的新的资产阶级意识”(8)[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6页。。李嘉图在其经济体系中总括了这一时期的创造性成果,在形式上表达了资产阶级事实上已完成的发展。而在李嘉图之后的“庸俗经济学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退化为“纯粹的”理论研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积极的社会职能业已破灭。另一方面,柯尔施认为正是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实际的社会变革,“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成为无对象”(9)[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4页。。这种由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意识。它所表达的并不是以往资产阶级在现实和理论上的继续发展,而是对其全面彻底的变革。与此同时,柯尔施又强调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表达同样也不能跳过那个时代的历史存在及其政治经济学的一定思想形式。
可见,柯尔施试图通过强调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的“历史论述原则”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在革命意义上,柯尔施才让人明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毫无生气、一无用处的纸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不是纯粹观念或学科式的理论研究,而是前期哲学批判深入市民社会中更为全面的完成。换言之,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否定哲学,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继承了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的哲学方法,同时在内容上和前期的哲学批判一同构成了作为一种“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10)[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页。的马克思哲学。
二、两条线索: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经济学理论
大多数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都会从两个重要的视野切入,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和马克思自身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但是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继承发展还是超越独立?这种继承或超越是完全经济学意义上的吗?柯尔施亦在这两个重要视野中理出了两条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线索,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经济学理论。前者是主线,体现了马克思批判革命立场的不断发展,而后者解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某些方面显得与前者背道而驰。正是在这两条线索的梳理和论述过程中,柯尔施阐述了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与早期哲学批判的关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批判”过程。在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的“历史论述原则”下,柯尔施认为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体现了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是在理论上的批判,而且本身是后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前一阶段的现实“批判”。正如柯尔施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当于这种理论批判的各个阶段”(11)[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1页。。从一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特别在反对封建社会过时的生产方式时,它将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与普遍社会利益的进步等量齐观。在此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是以无党派科学的形式,参与解决着无产阶级对经济学提出的问题。但是从1825年的经济危机开始,这种科学性就丧失了。在理论上,李嘉图体系是转折点,是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科学的自我批判。在此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一是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试图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得出反资产阶级的结论;其二是“庸俗经济学”的模仿者,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肤浅化。这两个理论派别直接反映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现实。
与此同时,出现了第三个流派,即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柯尔施强调马克思的这种批判“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12)[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6页。,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始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认识。所以,马克思在早期是以超越经济学的哲学形式研究经济学,并以此指责蒲鲁东。但随着对唯心主义的完全克服,马克思是站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上批判蒲鲁东。直到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首次表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13)[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0页。,将资本视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加以揭示和批判。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理论的充分发展,正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研究市民社会所得出的结论。从此时开始,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同时是经济学理论。
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冷静“第二”阶段的理论反映。在柯尔施看来,如果19世纪5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是热情、幻想的第一阶段,那么50年代之后则是革命的冷静阶段,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研究以马克思唯物主义新的形式总括了现代欧洲以往的一切革命经验。这种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以后相关国家的革命找到了入门的途径。在这种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柯尔施认为,马克思肯定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结论之间的联系,运用了相同的经济学范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著作;它作为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批判的结合物;同时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14)[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发展古典政治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理论是在两个重要方面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其一是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特别是对使用价值予以经济学定义,从而区分了社会劳动的具体与抽象;其二是将现实的具体劳动,即生产“别人的商品”的奴役、受剥削的雇佣劳动引入政治经济学。前者使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获得合适的出发点,即在批判基础上被完善的“劳动价值理论”。后者使得经济学理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关于“劳动”的科学。“它成为关于社会劳动,这种劳动的生产力,关于这种劳动通过当前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束缚以及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这种关系以革命方式进行破坏的直接的科学。”(15)[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可见,柯尔施通过以上两条线索的梳理,不仅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阐述了马克思在其自身思想发展过程中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范围,实现了主题的转化。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实现了从法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对唯心主义的克服,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唯物史观。这就是说,马克思不再是局限于哲学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是在哲学高度之下、经济学之中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柯尔施所认为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革命的社会理论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形式,但在内容上实现了根本性的创新,即在本质上是关于“劳动”的科学,而不是商品、资本的科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同时也使原来的哲学批判,特别是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通过经济学研究获得科学的表达。
三、三种特质:科学性、哲学性和革命性
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性质的理解上,我们往往将其置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分离或比较的视野之中,导致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似乎与哲学、社会革命无涉。这也是大多数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及后来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的模式。对此,柯尔施不仅重申了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同时也试图恢复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不仅表现为其晚年通过《卡尔·马克思》试图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也体现在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之中。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科学的,同时也是哲学,更是革命的。
在柯尔施的视野中,所谓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是指理论上逻辑推演的自洽性或实证性,而更多是指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柯尔施也承认它们最初也同样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体现为满足当时社会新经济形态,即反对封建社会的需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变化现实与资产阶级意识相适应的表现。但在李嘉图之后的“庸俗经济学家”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科学性,因为资产主义社会现实危机已使得它丧失了科学的对象,所以他们只能拘泥于从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中寻求必然性或从实证科学的方法以辩护它的纯粹“科学性”。这也是马克思极力批判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理解,柯尔施认为首先在于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形式,认为“马克思毕生都反对这样的误解:他在关于价值的经济学研究中,是要研究不同于资产阶级关系的别的东西”(16)[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2页。。这种科学形式赋予了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表达,例如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表述转化为对商品拜物教的表述。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更在于其内容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在经济学上的现实要求,体现的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彻底全面的变革。对此,柯尔施认为马克思《资本论》虽然在名义上是关于资本的科学,但实际上是关于“劳动”的科学,即如何从没有自由、被剥削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的科学。简言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是否符合实证科学,而是在于是否符合现实“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深入,从完全成熟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使其经济学批判更具深刻和普遍性意义。柯尔施并不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不兼容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意识形态”(17)[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3页。的讨论中,他强调“包括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和其他从它们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现象”的社会意识形式要比法律、政治国家这种政治上层建筑更为真实。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也属于意识形态,也是“现实”的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压迫与剥削关系的“托辞与掩饰物”(18)[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94页。。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批判,也包括对其社会特殊意识形态的批判。只是马克思对这种意识形式给予了特殊地位,即“新的哲学概念”(19)[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4页。。以柯尔施对《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认识为例,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并且它实际上还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对于这种特别的、使哲学‘观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遭受的困境来说的基础”(20)[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5-86页。。换言之,马克思是以经济批判的形式继续了早期“异化”的哲学话语,通过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赋予这种批判“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21)[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7页。。当然,这背后体现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影响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获得完全或成熟的表达,它“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22)[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在柯尔施的阐述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为显著的特质无疑是革命性。“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23)[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7页。这种批判首先意味着一种变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指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超越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全面彻底的变革”。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性指认伊始,革命性就一直贯穿于其思想中,特别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达到从最为根本性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即使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冷静的“第二”阶段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为之后的诸如俄国的革命提供了入门途径。柯尔施之所以认为《资本论》是关于“劳动”的科学,这是因为,在其看来马克思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当下劳动的过程及其被束缚、压迫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揭示,反映出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在于以革命方式破坏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资本”与“雇佣劳动”两个对立范畴所隐藏的阶级对立过渡到现实历史与社会的论述。与此同时,柯尔施认为“商品拜物教”的研究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对于形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类似于卢梭的“契约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的形成所具有的革命意义是一样的。简言之,“《资本论》整个的、贯穿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24)[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在这三种特质中,柯尔施始终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放置在首位,其他两种特质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们印证了这种革命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对现实的变化及对这种现实变化的把握。这种现实变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及其引起的政治变化,“从这时起,对社会发展严肃的科学研究只有从这样一个阶级的立场才是可能的,即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于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最终地消灭阶级”(25)[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62页。。换言之,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符合了无产阶级现实革命的必然要求。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哲学性,则使那些包括商品拜物教、资本原始积累在内的现实不再当作纯粹经济学问题加以研究,而是直接回到历史中得以阐述,并通过革命实践的方式获得解决。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使得辩证唯物主义获得完全的成熟,从而让无产阶级能在市民社会中探索自身受压迫的根源和求得解放的道路。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批判在内容上的深度和方法上的成熟是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得以体现和实现的。这也是为何柯尔施强调只要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意义就可以明了其前后哲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内在的连续性。当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革命性的认识有赖于从理论与现实辩证统一的科学性和完全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性得到理解。
四、批判性反思与启发
如上所述,柯尔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有其独特和合理性方面。他试图突破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纯粹理论“科学”的研究,强调它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反映着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本身构成现实具有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意义。可以说,柯尔施是以非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现实革命立场和意义的基础上,柯尔施阐述了马克思前期哲学批判与后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所具有的哲学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柯尔施是以总体性的方式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当然,柯尔施的这种理解本身也存在局限。例如,他将现实或实践过分理解为“革命”,在突出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时,却忽视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揭示。虽然他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源于它的辩证法,但他始终没有解释科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又如,柯尔施通过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原则将马克思前期哲学批判与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批判、革命的辩证法在理论上是否只是简单地对以往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克服才达到。虽然柯尔施提及了经济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但是对此并没有做足够的解释。当然,我们对柯尔施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的阐述,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把握它对我们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其一,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柯尔施十分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唯物辩证法,强调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当前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也需要继承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要研究当前我国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供给与需求、短期与长期、生产与分配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要重视研究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有效处理好传统与新兴、实体与虚拟、规模与质量、效益与生态等之间寻求平衡的关系问题。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要研究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观察、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在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特别是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最大实际,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困难。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要重视研究如何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二,反对教条、机械地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思想源泉。柯尔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态度是非教条的,他总是从社会现实,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实际变化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当有非僵化的态度,在处理这种思想源泉时我们至少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能忽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根本性意义上的批判,因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渊源上还是延续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在根本意义上要抓住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即如何更好、充分地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效益问题。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批判资本作为一种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对人的剥削关系。那么,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需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如何把握、调控“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行规律。
其三,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柯尔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突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即强调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在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而在以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政治阶级立场。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根本价值目标规定的,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坚持以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强调这种需要和利益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对此,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要深入展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研究。其次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主体作用。对此,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要深入研究就业保障机制、劳动力结构机制、人才培训、奖励机制等,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后要以实现最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劳动、发展成果,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对此,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入研究更为合理、先进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机制、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等。